別想擺脫書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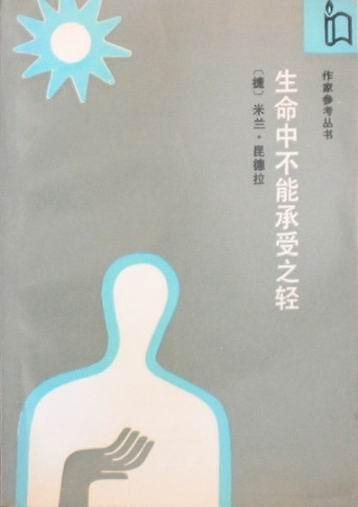
露西·埃爾曼在談?wù)撍牟伎霜?jiǎng)提名小說時(shí)說:“藝術(shù)不是空中樓閣,會(huì)不可避免地成為時(shí)代的同謀。”文學(xué)首當(dāng)其沖,僅從書名就可見一斑。書名與時(shí)代精神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緊密,甚至成為后者的標(biāo)記。《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小團(tuán)圓》等已像幾代翻唱的經(jīng)典曲目,不斷且廣泛地被引用和演繹。而雷蒙德·卡佛的《當(dāng)我們談?wù)搻矍闀r(shí)我們在談?wù)撌裁础犯情_創(chuàng)了引發(fā)共情兼具漂亮句式的“書名體”。

本文標(biāo)題援引自讓-克洛德·卡里埃爾(Jean-Claude Carrière)與安貝托·艾柯(Umberto Eco)的對話錄《別想擺脫書》。
失敗者敘事,開放性結(jié)局,一切終將失落的宿命感。這些喚起孤獨(dú)和疏離的文學(xué)作品,反而成為我們無力承擔(dān)現(xiàn)實(shí)時(shí)得以喘息的“精神泡沫”。就連它們的書名,也別想擺脫。拿到這一張隱藏菜單,至少彼此能在人生的歧途上說一句:原來你也在這里。
《當(dāng)我們談?wù)搻矍闀r(shí)我們在談?wù)撌裁础?/strong>
這一主要由對話組成的同名短篇,像一部小成本的室內(nèi)劇:從天亮到天黑,兩對情侶就著杜松子酒,就“愛情”這一話題展開的一場圓桌談。特芮堅(jiān)信艾德愿意為愛情而死是真正的愛情,梅爾對此嗤之以鼻,他認(rèn)為一對車禍后勉強(qiáng)維生的年邁夫妻,老頭兒不為車禍卻因?yàn)槟X袋綁著石膏看不見老太太而悲傷,才是真正的愛情。通過對話我們可知,四個(gè)人都曾經(jīng)歷過至少一次愛情,梅爾和特芮因?yàn)樘剀堑那叭伟露嗌儆行┎豢欤瑒诶湍峥藙t還沉浸在彼此溫柔的愛里。談?wù)摰慕Y(jié)果令人不快和沮喪。

極簡主義代表雷蒙德·卡佛盡量簡略地交代故事和人物背景,減少描述,拒絕闡述。他的這部短篇小說集,據(jù)說在編輯的建議和修改下刪減了大量不被認(rèn)為必要的內(nèi)容。像戈達(dá)爾的“跳切”,設(shè)計(jì)出許多情節(jié)的留白。這種風(fēng)格增加了閱讀的阻礙,但對樂于鍛煉想像力的讀者而言,也增強(qiáng)了閱讀的趣味。
“所有這些,所有這些我們談?wù)摰膼矍椋徊贿^是一種記憶罷了。甚至可能連記憶都不是。”梅爾說出這句話以后,又“率先承認(rèn)”自己“什么也不清楚”。“不確定性”充滿了卡佛的敘事和對話,它和“留白”簡直是一份半命題式句型援引的邀請,我們也的確做出了熱烈的回應(yīng)。
《我是個(gè)年輕人,我心情不太好》
網(wǎng)上一度盛傳這樣的說法:現(xiàn)代年輕人的神經(jīng)十分脆弱,每個(gè)微不足道的小問題,都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這部挪威小說的主人公即是例證。25歲生日那天,他和哥哥打槌球輸了,他的世界就此崩潰了。他任性地退了學(xué),獨(dú)自借住哥哥不在家的公寓。他在公寓里讀書、列各式清單、買打地鼠玩具,梳理和治愈自己。他知道許多知識(shí),只是不知道它們的用途。他對自己坦白渴望,也提出疑惑。他在摸索“童心”與“成人標(biāo)準(zhǔn)”之間的平衡和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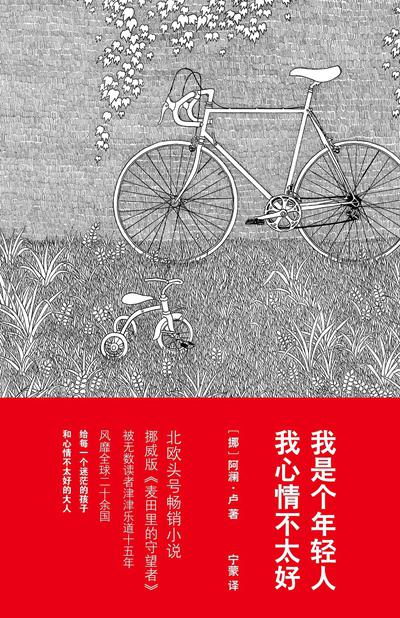
挪威作家阿瀾·盧的第二部小說,可謂“喪”文學(xué)風(fēng)潮的先鋒,從第一人稱視覺出發(fā)的話癆式敘述,直抒胸臆,大快人心。單句成段的結(jié)構(gòu)看似形散,但讀起來輕松過癮,更重要的是,阿瀾·盧將目標(biāo)對準(zhǔn)不愿告別孩童時(shí)代,對成人世界負(fù)隅頑抗的“年輕人”,他們因?yàn)槊糟偸遣豢鞓返纳瞵嵥楸痪珳?zhǔn)地捕捉。這個(gè)龐大的人群因此感到被理解,這份真誠的感同身受給了他們一個(gè)歸屬,消解了他們的孤獨(dú)。
只要身處成人世界,就會(huì)對這個(gè)書名一見鐘情。或者說,察覺到自己對號(hào)入座,我們也確信已被推入成人世界里。“不管準(zhǔn)備好沒有。”
《世間已無陳金芳》
故事始于久別重逢,“我”偶遇了同學(xué)陳金芳,開啟了對一個(gè)鄉(xiāng)村女孩力爭上游的青春時(shí)代的回憶,但她已不是從前的她了。陳金芳已熟諳城市生存的游戲規(guī)則,盡管如此,她“只想活出個(gè)人樣”的心愿還是落空了。
一部帶著北京大院味兒的中篇小說,石一楓講述陳金芳的人生起伏,也反觀了“我”——一個(gè)中年男子殘缺的觀念觀。雖然立意和情節(jié)落入窠臼,但流暢的閱讀體驗(yàn)、不吝自嘲的行文風(fēng)格,以及對社會(huì)環(huán)境的真實(shí)寫照,都使這部小說產(chǎn)生不容小覷的影響力。其中“世間已無”四個(gè)字道盡自我喪失的悲涼與惋惜,最是深入人心。
成功難以定義,失敗的代入則容易得多。即便過得體面,背后的妥協(xié)、被改變被同化、底線的一再淪落,都會(huì)引起掙扎和自責(zé)。如此語境下,小說書名歸結(jié)了大部分異鄉(xiāng)人的精神狀態(tài),今昔對照,也許人人都是陳金芳,或遲或早、或多或少都在追求中嘗過失去的味道。當(dāng)我們飽含溫情回憶,“世間已無”是句決絕的告別,也是遺憾的挽歌。
《孤獨(dú)及其所創(chuàng)造的》
或許可以將這部作品看作保羅·奧斯特的回憶錄,書由兩部分組成。《一個(gè)隱形人的畫像》通過相片、巧合、回憶,用拼貼式手法使父親這個(gè)隱形人顯影,《記憶之書》以離間的第三人稱,講述具有自傳性質(zhì)的作家的人生。這位作家也成為了父親,延續(xù)了第一部分“探討父親意象”的主題。
狄更斯形容牡蠣“神秘、自給自足,而且孤獨(dú)”。“神秘”符合我們對一般意義上孤獨(dú)的想象和迷戀,“自給自足”則更貼近奧斯特回憶其父親的“退隱意義上的孤獨(dú)”:“孤獨(dú)。但并不是說孤身一人。而是退隱意義上的孤獨(dú)。是不必看見自己,是不必看見自己為他人所見。”當(dāng)他寫作記憶之書時(shí),他通過故意的不在場制造了自己的孤獨(dú),“把自己視為另一個(gè)人,以便講述他自己的故事。”
奧斯特和父親的孤獨(dú)連成一座布滿伏筆暗號(hào)和小徑分岔的迷宮。寫作將奧斯特從孤獨(dú)中解放出來,從現(xiàn)實(shí)逃往虛構(gòu)的世界里。只要寫作不停,就不用回到現(xiàn)實(shí)中去。而我們在迷宮里感知和探索,走出迷宮的時(shí)候,我們也得到了與創(chuàng)作者相同的慰藉。孤獨(dú)所創(chuàng)造的,正是這份慰藉。
《生活在別處》
用米蘭·昆德拉的原話說,這“是一部青春的敘事詩”。 他描寫了一位抒情詩人的誕生和成長,當(dāng)詩人充滿激情的青春終結(jié),他短暫的一生也隨之結(jié)束。
在昆德拉看來,詩人在革命面前繳械妥協(xié)使詩的神圣感隨之崩塌,他將因此產(chǎn)生的對價(jià)值體系的懷疑和吊唁嫁接在雅羅米爾身上,雅羅米爾所代表的詩人有一意孤行的浪漫,是抒情的化身,他所經(jīng)歷的青春、愛情、母子關(guān)系,都是極端的“抒情形式”。他發(fā)現(xiàn)比起復(fù)雜的人間,詩歌是座純潔的天堂,并隱匿其中;他回避母親,因?yàn)椤八牟恍倚枰陋?dú)與黑暗”。那些急于獨(dú)立成長的人們,都在雅羅米爾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寄托。
雅羅米爾創(chuàng)造的人物克薩維爾更接近渴望離席的讀者的烏托邦:他只活在夢中。一個(gè)夢結(jié)束了,克薩維爾就必須到另一個(gè)夢中去。換言之,他也可以在危險(xiǎn)的時(shí)刻逃脫,舍棄因果,免于責(zé)任。現(xiàn)實(shí)中選擇的可能性和機(jī)會(huì)的喪失都在夢境中具象化了,套娃式的夢境也讓生活的多義性得以成立。夢境與現(xiàn)實(shí)相似,但結(jié)局和細(xì)節(jié)不同。它和詩一樣,是對失敗現(xiàn)實(shí)的補(bǔ)償。它確實(shí)在別處,只是并非生活本身。
米蘭·昆德拉的這部小說最初題為《抒情時(shí)代》,后代以蘭波的“生活在別處”——巴黎的大學(xué)生們曾將它作為口號(hào)涂鴉在墻上——使書名比內(nèi)容更為人熟知,并一度被我們誤解為理直氣壯的逃避。不幸(或者說慶幸)的是,遲早我們都會(huì)意識(shí)到,盡管存在所有未實(shí)現(xiàn)的可能性,可一旦做出選擇,命運(yùn)就被注定且不可逆。雅羅米爾活在鏡中,一旦走出了鏡子,也就走向了死亡。
《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
美國南方文學(xué)代表作家弗蘭納里·奧康納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說集,她的人物像一個(gè)起初不愿認(rèn)錯(cuò)的人最終受到了懲罰。同名短篇中的主人公朱利安的母親將對黑人的施舍視為自己的善良,卻遭到對方的抗拒,也加劇了朱利安對她的不滿。這雙重打擊竟然致命。本來只是一個(gè)朱利安陪母親去減肥班的尋常日子,因?yàn)楣嚿习l(fā)生的事件惡化為生死之間的分水嶺,也動(dòng)撼了朱利安對自我的認(rèn)知。
自認(rèn)為厚道的地主梅太太、將偏愛變成挾持的老頭、要把自己寫進(jìn)小說拯救男主角的作家……他們以相似的“救世”姿態(tài)出現(xiàn),小惡釀成大錯(cuò),令人慨嘆;而利用存在于日常生活縫隙間的問題制造出意外、悲痛的結(jié)局,也令人叫絕。奧康納聚焦的是美國南方的家庭生活和人際關(guān)系,書寫的人性善惡細(xì)節(jié)和兩者間的矛盾卻具有普適性。人們說她筆下的世界是個(gè)煉獄,一邊為她哥特風(fēng)格的陰暗筆觸著迷。
“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語出以科學(xué)語言解釋神學(xué)的法國天主教神父德日進(jìn),他稱匯合點(diǎn)為“omega point”:“保持真我,但同時(shí)要向更崇高的意識(shí)和更博大的愛攀登!在頂峰,有從不同方向而來卻抵達(dá)同一高度的人們,你會(huì)發(fā)現(xiàn)自己是其中的一員。因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質(zhì)疑宗教、直面人性丑陋的奧康納,將“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作為小說標(biāo)題。也許,勸人向善是她最后的樂觀,也是我們最后的祈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