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曼·黑塞和他的出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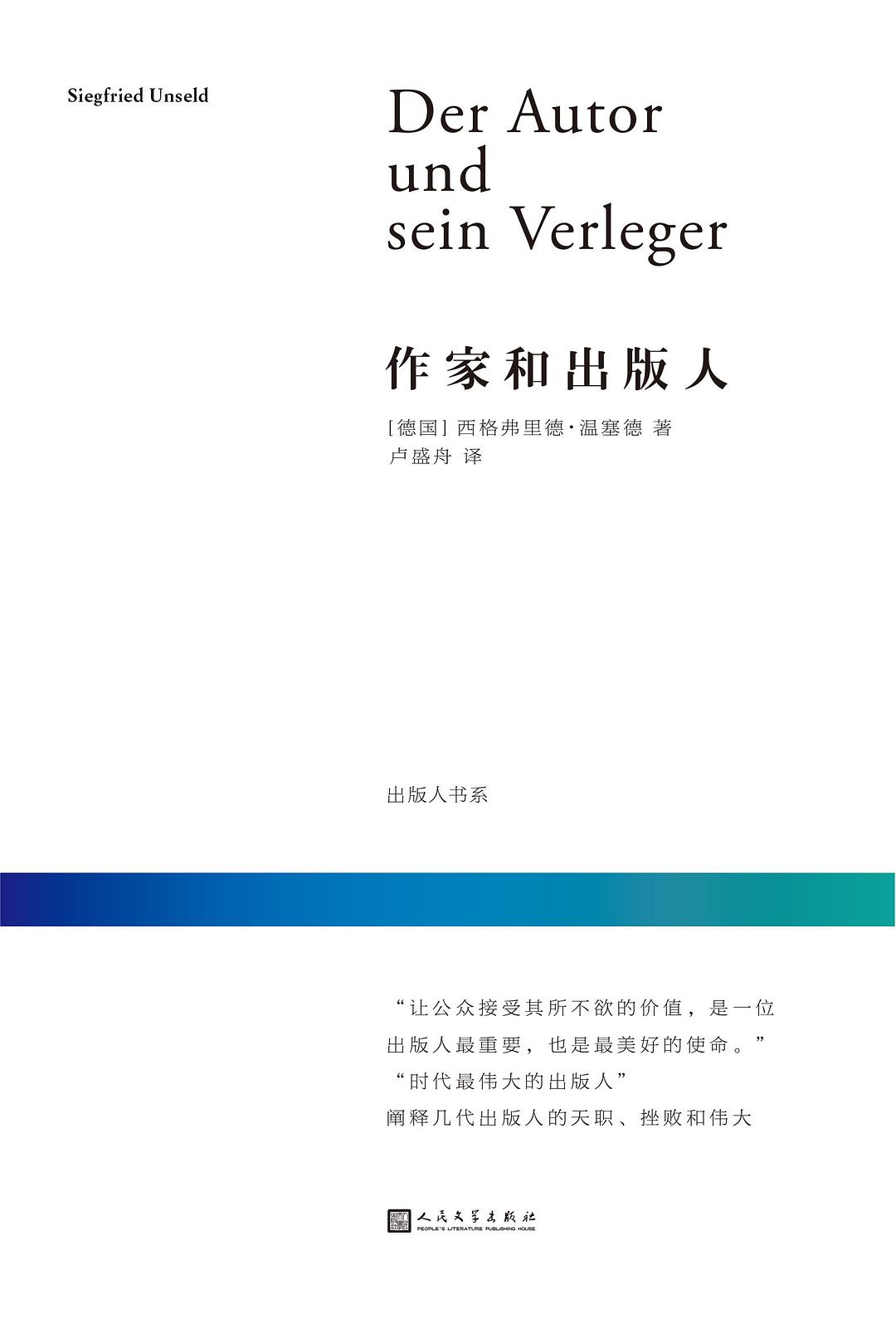
黑塞與他所有的出版人的關系多種多樣,不乏意外。與其他人不同,他顯然知道世上還有出版人這個職業(yè)。1903年,黑塞在他重要的論文《書的魔力》中寫道:“在所有非自然饋贈,而是人類從自我精神那里創(chuàng)造出的世界中,書的世界是最廣袤的。”通過他的父母,通過他的自我教育(仰賴博覽群書的自我教育),更重要的是通過他做書商的經(jīng)歷,黑塞很早就與書的世界結緣。1895年10月,黑塞進入圖平根的海肯豪爾書店當學徒,一天的工作漫長而艱苦,時長十到十二個小時。他的學徒期結束于1899年7月31日。從1899年9月15日到1901年1月31日,他在巴塞爾的萊希書店擔任書店營業(yè)員。對于這份職業(yè),他在1899年寫道:“這份職業(yè)很有趣,但我并無法熱愛它。這主要得怪我的同事,他們中間有三分之二的人都缺乏教養(yǎng)、舉止粗魯;其次因為我雖然是個內(nèi)行的讀書人,但卻是個蹩腳的生意人。”
我們待會兒會說到,黑塞后來在維護自身作品的經(jīng)濟利益方面其實非常在行。當年,他在出版人身上只看到了生意人的影子。1899年,在黑塞宣布自掏腰包承擔一部分出版費用后,他的第一部詩集——寫于圖賓根的《浪漫之歌》才得以在德累斯頓的E.皮爾森出版社出版。他拿出了175馬克,這在他的學徒保證金里占了很大的份額。一些日后在菲舍爾出版社成名的作家都是先以自費的方式在E.皮爾森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處女作。《浪漫之歌》共印600冊,第一年賣出43冊平裝版,11冊精裝版,共計54冊;他的版稅共計35.1馬克。
彼時的黑塞同海蓮娜·沃伊戈特有魚雁往來,這位年輕的女士(當時她年方二十二歲)在《詩人之家》雜志上讀到了黑塞的詩句,便在1897年11月22日寫信表露了對他的好感。從黑塞給這位“尊貴的小姐”略顯傲慢的回復中(他當時“由于工作而精疲力竭”)生出了一場真誠的通信,兩人互陳創(chuàng)作上的努力,并相互啟發(fā)。黑塞與這位“令人驚艷的”、未來的“北德年輕女詩人”從未謀面,當她在通信的第一年與出版商迪德里希結婚時,他也毫不驚訝。她向他表示,愿意把《浪漫之歌》推薦給自己的丈夫。黑塞對此做出的反應很能說明他的個性:“您想讓我把我的手稿交給您丈夫的出版社,這讓我感到既欣喜又榮幸。我也很樂意如此為之。但我感覺,我的第一本書——誠實地說——不應該受惠于您的幫忙,我想自力更生,不知您可否理解?”他的第二部作品——收錄了九篇散文的文集《午夜后一小時》,后來還是由迪德里希在萊比錫出版。奧爾根·迪德里希這樣做主要是想討他夫人歡心,其實他對黑塞一無所知,況且此書與他的出版計劃并不相符,因為當代文學并不在他的規(guī)劃之內(nèi)。“坦白說,我不太相信這本書能取得商業(yè)上的成功,但這反而讓我更加堅信它的文學價值……我也沒料到會印出600冊。但我希望,這本書能單單通過引人注目的裝幀來彌補作者并不響亮的名頭所帶來的不利。”
在與迪德里希的通信中,黑塞又一次展現(xiàn)出他特有的行文風格:“我對您的幫助心存感激。此外,我要感謝您如此誠實地描述了您對我的印象。”黑塞要求出版商提供字體和印紙的試樣。對于迪德里希提供的合同條款,他“斗膽提了一些問題”:“我完全同意您的建議,僅僅是出于興趣想要澄清一些東西。您寫道:‘1.10本贈書。2.所有版次的權利。3.根據(jù)出版人的原則,新版附送作者一定報酬。’我應該怎么理解第二點呢?這是說:您永遠擁有版權,還是我在書每次再版后都有權得到10本贈書?再者就是出版人的原則。這是視具體情況而定,還是有一個固定的計算規(guī)則?我問這些,僅僅是出于好奇,并且想一勞永逸地了解這些術語。您實際上已經(jīng)得到了我的應允。”現(xiàn)在我們就能料到,黑塞會畢生反抗所謂的“出版人原則”,如果這種原則限制了他的自主權的話。
由W.德魯古林悉心印制的《午夜后一小時》于1899年7月出版,第一年共收獲53名讀者(當年在皮爾森那兒出版的《浪漫之歌》還賣出了54冊)。但不同的是,《浪漫之歌》并沒有得到批評家的注意,而《午夜后一小時》卻無疑找到了一位舉足輕重的評論家——萊納·瑪利亞·里爾克。“這些詞語如同金屬一般被鍛造出來,讀起來緩慢而沉重。不過,這本書的文學性不強。最精彩的段落顯得急迫而富有個性。它令人肅然起敬,它心懷大愛,其間所有的感覺都是虔誠的。要之,它已處在了藝術的邊緣。”當《午夜后一小時》出版時,它恰好也處在作者記憶的邊緣。當時,黑塞開始為迪德里希出版社出版的圖書撰寫評論,“為了減少我那可憐的書使他蒙受的損失”。黑塞遭受了一個雙重打擊:一方面,公眾并不重視此書,另一方面,他在卡爾夫的父母對這本書“徒感憤怒”。1899年6月16日,在一封寫給他母親卻從未寄出的信中,面對母親“你寫了一本邪惡之書”的指責,黑塞義正言辭地為自己辯護道:“我無法繼續(xù)寫作。你說這本書從一開始就顯得很自負。比起你掂量你那封可愛的信,我對我的書的權衡恐怕要周全得多。遺憾的是,這一切都無法彌補了,道歉也于事無補。我不相信我的書帶給你的痛苦能及你的態(tài)度帶給我的痛苦的一半多。多說無益。你們肯定知道‘清者自清’這句話,而你們竟把我歸到了不潔者之列。”
若干年后,《午夜后一小時》售罄,黑塞收回了版權,不允許再版,這本書直到1941年才在蘇黎世作為研究資料得以再版。它在黑塞的文集里消失多年,對此,黑塞在新版的導言里解釋說這有其“私人原因”。他想在書中創(chuàng)造“一個藝術家的夢幻國度,一個美麗島,他的詩意味著逃離白晝的風暴與洼地,遁入夜中、夢里以及美妙的孤獨中去。這本書并不缺少美”。這本書的銷聲匿跡要歸咎于銷售上的失敗,以及他母親和親戚們的抗議。他的下一本書是一個經(jīng)由第三者手抄二十遍的手稿,名叫《諾圖爾尼》。黑塞標價20個弗朗克,于1900年秋在朋友圈子內(nèi)小范圍銷售(“未被邀請者的訂購不予接受”)。雖然他在同年8月16日從巴塞爾給迪德里希又寄了一篇文章(《莉莉亞公主》,即《勞舍爾》的“露露”一章)并且打算自費出版,題名《施瓦本短篇小說集》,可后來他不但改變了主意,改換了標題和出版社,還另署其名,把自己隱藏在編者的面具后面。1900年底(版本說明上寫的是1901年),《赫爾曼·勞舍爾的遺著和詩歌——赫爾曼·黑塞編》在巴塞爾的萊希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沒有廣為流傳,“完全僅僅為巴塞爾考慮”。小范圍的出版卻帶給了黑塞便利。“我的作品能逃過商業(yè)投機和胡言亂語,只供朋友和友善人士閱讀。”
人們不應該太過較真于此時他對出版界的個人態(tài)度,這不過是階段性的。但是,黑塞做什么事都會表現(xiàn)得很堅決、徹底。漸漸地,出版人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發(fā)生了轉變。不久,他和奧爾根親自會面,他“帶著驚異與享受傾聽一個人如何傾訴生意和規(guī)劃上的衷腸”。不久,他又會在薩穆埃爾·菲舍爾那兒獲得同樣的感受。每本書自有其命運。《勞舍爾》僅僅為巴塞爾而作,印數(shù)甚少,除了瑞士的文學愛好者之外,鮮有人耳聞。然而一個瑞士人——鄉(xiāng)土作家保羅·伊爾戈干了一件非比尋常的事,他同薩穆埃爾·菲舍爾既無私交,也無業(yè)務上的往來,卻把《勞舍爾》寄到了菲舍爾的出版社。菲舍爾對里面的詩文印象深刻,也許出版社的編輯,莫里茨·海曼也讀了這本書,并向菲舍爾推薦了此書的作者。大約是在1903年年初,菲舍爾寫信給黑塞:“最尊敬的先生!我們滿懷愉悅拜讀了《赫爾曼·勞舍爾的遺著和詩歌》,短短數(shù)頁,卻妙筆生花,所以我們油然生出一個奢望:如果您能讓我們拜讀您的新作,我們將喜不自勝。”
黑塞在1903年2月2日給菲舍爾的去信中說,他很高興菲舍爾給他寫信,不過暫時他沒有東西可寄,但他保證,他會寄給他一篇“雕琢數(shù)年”的散文詩。1903年5月9日,黑塞就把作品寄了過去,5月18日,菲舍爾對于新作《彼得·卡門青》這樣寫道:“正值復活節(jié)之際,我想及時向您表達我對這份絕妙之作的衷心感謝。您寫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些本身不值一提的小事透過一個詩人的心靈得到傳遞,使得這部作品變得豐沛而光彩照人。伊麗莎白、理查德、納笛妮夫人、木匠的孩子,還有瘸子,這些人物讓我身臨其境,歡心喜悅。我向您祝賀,如果能出版大作,將不勝喜悅。”1903年6月9日,菲舍爾向黑塞寄去一紙合約。合同規(guī)定給他平裝書銷售額的20%作為酬勞,首印1000冊,黑塞則向出版社提供接下來五年內(nèi)他所有作品的優(yōu)先購買權。其實,對《彼得·卡門青》一書,菲舍爾并非信心十足,這體現(xiàn)在他給黑塞的信中。
1903年6月9日和1904年2月5日他曾兩次寫信給黑塞,暗示《彼得·卡門青》不會取得銷售上的成功。在1903年6月9日附帶合同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出,菲舍爾更青睞和寄望于誰:“我非常希望,即便您的《彼得·卡門青》不會帶來銷量上的成功,他也能找到許多朋友和崇拜者,特別是他能給讀者預先留下一種印象。我感到您正走在成為一位優(yōu)秀散文家的路上。如今,您與埃米爾·斯特勞斯毗鄰,他是我們最大的希望。”今天,我很難理解在和作家打交道方面至少頗有經(jīng)驗的出版人菲舍爾會在和一位作家的首次通信中把另外一個人說成是“最大”的希望,而把通信對象僅僅看作“正走在成為一位優(yōu)秀散文家”的路上。菲舍爾想把這篇小說介紹給《新眺望報》的讀者。為了預先把小說刊登在報紙上,黑塞同意刪去小說五分之一的內(nèi)容,而這本書的印刷工作也必須提前到1904年年初完成。奧斯卡·比厄——《新眺望報》的出版人——在1903年9月至11月間分三期刊載了這部小說,稿酬共計487.5馬克。1904年2月15日,《彼得·卡門青》以埃米爾·斯特勞斯《朋友海因》使用的開本、紙張和字體為模板發(fā)行。與出版人的預期恰恰相反,《彼得·卡門青》一書大獲成功,出版兩年就賣出了36000冊,到了1908年,銷量甚至達到了50000冊。
1923年,黑塞在《生平札記》里寫到此事。“當時,我開始動筆寫《彼得·卡門青》,菲舍爾的邀請對我鼓勵極大。作品完成后即通過審讀,出版社寄來了友好甚至是衷心的信,這本書在《新瞭望報》上預先連載,獲得了埃米爾·斯特勞斯和其他我所敬仰的人的肯定。我成名了。”“可不光是成名了”,黑塞的傳記作者胡戈·巴爾對此寫道,《彼得·卡門青》一書讓黑塞一夜之間在德國變得家喻戶曉。胡戈·巴爾寫道:黑塞“現(xiàn)在站在屬于他的位置上,站在一個得以繼續(xù)被人傾聽的平臺上。這種關系對他來說在另外一層意義上也是很重要的:即便在最艱難的年代,菲舍爾也懂得如何把文化精英凝聚在一塊兒。這個圈子在作品還未寫就之時,就給了它以現(xiàn)實和團體的標識。出版人的這種堅定意志、對領導和尊嚴的強烈意識,也許正是黑塞大展身手的先決條件,也極有可能只有這樣的出版社才能讓詩人感受到他創(chuàng)作的意義和公眾對他創(chuàng)作的期望,沒有這些,我們今日所見的黑塞作品或?qū)⒉粡痛嬖凇薄N医?jīng)常引用胡戈·巴爾的這句話,因為一位文學出版人的職守在這句話中得到了確切的表達。
1904年4月初的一天,黑塞在慕尼黑與菲舍爾見面,當時菲舍爾還把托馬斯·曼介紹給他認識。從今以后,作家和他的出版人之間的關系是友好、務實的。和黑塞打交道并不容易。雖然《彼得·卡門青》的巨大成功賦予他新的獨立性——他辭去書商的職業(yè),四處云游,并在蓋恩霍芬安置家業(yè),但敏感、緊張、時刻處在內(nèi)心沖突下的黑塞對于出版人來說并不是一個輕松的伙伴。1904年11月,當S.菲舍爾向他詢問近作的進展時,他堅決反對這種“匆忙的生意經(jīng)”。1906年,《在輪下》問世,1907年《此岸》出版,1908年《鄰居》出版。然后,正如彼得·德門德爾松所述,發(fā)生了一些“怪事”。在1903年6月10日《彼得·卡門青》的出版合約中,黑塞向菲舍爾出版社許諾了未來“五年”內(nèi)作品的優(yōu)先購買權。合同到期后,優(yōu)先權若不被解除,將視為“自動續(xù)延五年”。但黑塞解除了這項優(yōu)先權。
《彼得·卡門青》的成功不僅讓讀者,也讓出版人知道了黑塞,早在1904年11月4日,菲舍爾在給黑塞的一封信中就表達了此種擔憂:“在《彼得·卡門青》大獲成功后,您肯定會從四面八方獲得各種建議,包括一些以用誘惑的條件騷擾成功作家為業(yè)的出版商,他們會親自登門求訪,以這種外在的方式使您陷入一種驚恐而危險的不安中。”果然不出所料,黑塞多次前往慕尼黑,在為雜志《三月》和《癡兒西木》工作的過程中結識了出版人阿爾伯特·朗恩和格奧格·穆勒,為了得到黑塞,他們展開了強大的攻勢。出版商的競相追求,或者說,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機制使黑塞內(nèi)心對獨立的渴望與日俱增。他在與薩穆埃爾·菲舍爾的合同里為自己爭取到了當時該出版社旗下其他作家無法染指的東西。1903年的第一份合約在1908年2月被延期。黑塞必須把接下來的四部作品中的三部交給菲舍爾,同時有權把四部中的一部提供給阿爾伯特·朗恩出版社,這是其一。另外一點同樣驚人:黑塞要求確定一個與菲舍爾出版社所有的優(yōu)先權等價的條款,據(jù)此,菲舍爾必須“在未來三年內(nèi)以每月150馬克的標準付給黑塞共5400馬克。稿酬需另付”。這一數(shù)額在當時來說非同一般。菲舍爾無法再按常理出牌,但最后黑塞所陳述的理由還是讓他想通了。黑塞要的是自由和獨立。如果黑塞在一段時間內(nèi)為寫作而放棄了他的獨立性,那出版社就必須給他相應的補償。
在這份合約到期后,1913年3月31日,黑塞和菲舍爾出版社“第二次續(xù)約”:黑塞必須把“未來六年內(nèi)的所有作品”交給菲舍爾,作為等價交換的金額在“接下來六年內(nèi)共計9000馬克,按每季度375馬克的方式結算;稿酬需另付”。這筆按月或按季支付的錢本身并不多,但根據(jù)門德爾松的說法,菲舍爾聲稱1913年10月由于雙方意見分歧,他被迫重新給黑塞算清這筆賬,數(shù)額最后至少達到了18000馬克。對于一位凡事必須精打細算的出版人來說,這可不是筆小數(shù)目。
黑塞一板一眼地履行著合同。1910年,在把三本書交給菲舍爾后,他把第四本小說——主角是音樂家的《蓋特露德》給了阿爾伯特·朗恩出版社。在這段合約上事先約定好的外遇開始之前,菲舍爾就頻頻致信黑塞,直到最后一刻,他依然反對把書交給朗恩。在1910年1月29日一封未發(fā)出的給菲舍爾的信中(后收入《書信選集》),黑塞對菲舍爾的態(tài)度表達了不滿:
“既然您極力把事情說成是您心懷慈悲幫我出主意,那我情愿放棄和您的合同,因為您現(xiàn)在想強行把我拴在信和合同上。我跟您的合同讓我完全有權利把任意一本書給朗恩。但您現(xiàn)在表現(xiàn)得就好像我把《蓋特露德》給他是多么不當,為此必須給您補償……對這種把您描繪成施恩者,把我描繪成那個必須感恩戴德的人的腔調(diào),我不想繼續(xù)加以探討。我在最近的一封信里表現(xiàn)得如此忠誠,我向您承諾,今年將停止一切和其他出版商的談判。可您對此還是不滿。您把我每個忠誠的表達當作繩套使,想把我拴牢在合同上。我不想再繼續(xù)這種無益的通信。我手握四位德國最重要的出版商的信,在信中,他們都承諾給我25%的版稅,我之后還不用承擔任何義務。如果您對我不滿,不想給我安寧的話,那我就站在一個商人的立場上再解釋一遍,我履行了跟您的合同上的所有條款,希望得到安寧。我可以把一本書給朗恩,這不是您的恩賜,只是合同中的一個條款。與朗恩小小的越軌是合同上早就寫好的,而通過新的合約來彌補它給您帶來的損失,只對您一人有利,對此我不想言聽計從。我非常尊敬您的出版社,知道它有多么重要,但在德國,并不是獨有您一家出版社,我沒有理由讓自己對您愈加百依百順。”
雖然這封信沒有寄出,但態(tài)度是明擺著的。在寄出的那封信里,黑塞在語氣上要友好一些,但對此事依然很堅持。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直至菲舍爾退休,黑塞都和他的出版人保持著務實友好的關系。他在為菲舍爾七十歲生日撰寫的簡短賀詞里說明了這點:“我并不認為,我和我的出版人在性格上有許多相似之處。這的確十分遺憾,蓋因我們的職責是如此不同。但在某些方面上,我們畢竟還是擁有相通之處:比如我們處事都堅定不移,思維縝密,不易滿足,不斤斤計較。我們恪守信用,在合同上也能做到令人放心,所以二十五年來,我不僅和我的出版人保持著良好的關系,還學會了愛他、尊敬他。”1934年菲舍爾去世后,黑塞寫道:“我認識出版人菲舍爾已有三十余載,我對他的尊敬隨著交往的深入而日益增長,從尊敬中油然而生經(jīng)得起考驗的由衷的好感……當時我不是總能和他觀點一致,也不是一直都對他滿意……但我也漸漸將自己的棱角磨平,懂得了如何拋開私心去理解他作為出版人的職守。我看到,菲舍爾內(nèi)心一直裝著他的出版社的現(xiàn)在和未來,他以高度的責任感和清醒的直覺追隨著他的設想。”
菲舍爾的工作并不輕松。他無時無刻不想著他的出版社,他挑選能夠追隨他的設想、常年跟他保持聯(lián)系的員工,比如他的編輯莫里茨·海曼和奧斯卡·洛爾克。出版社就是他的一段生命,他的一部作品,一部使別人(即作家)的作品成為現(xiàn)實、成為“神圣的商品——書籍”(布萊希特語)的作品。他的設想必須吻合作家的設想,而他的理念必須拓寬作家的理念。在他的晚年,他努力為旗下的作家出版全集。到1925年,已有22套全集出版,他把這套書冠名為“現(xiàn)代人藏書”。在介紹中,菲舍爾寫道:“現(xiàn)代人藏書由我們出版的當代頂尖的詩人和思想家的作品全集組成。德國和歐洲精神生活的偉大代表在此共同譜寫了當今人類精神最深刻的畫卷。”門德爾松說,當時還沒有哪個出版商能交出一份與之媲美的答卷。此言不虛。
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黑塞結交了一批與菲舍爾同時代的出版人,比如阿爾伯特·朗恩、格奧格·穆勒、庫爾特·沃爾夫、恩斯特·羅沃爾特、奧爾根·迪德里希和其他同仁。他和許多人都保持著真誠的關系,比如阿爾伯特·朗恩,在他那里,黑塞能干成在菲舍爾那兒(由于菲舍爾的較真勁兒)不可能實現(xiàn)的事情,比如“用一杯紅酒誘惑他鋌而走險”。阿爾伯特·朗恩出版了黑塞的《蓋特露德》,并定期把黑塞的文章發(fā)表在他旗下的雜志《三月》和《癡兒西木》上,對黑塞來說,他代表著出版人的另一種風貌。朗恩清新而靈活,黑塞寫道。“這個擁有瞬間讓人為之振奮的能力和利落、具有實干精神的人,完全是為活在一群富有天賦和創(chuàng)見的人周圍而生的,他時而是啟發(fā)者,時而是實干家,時而是推手,時而需要被他人刺激一下。他帶著運動員一般任性的熱情從事他的工作,時而堅持,時而慵懶,時而有趣,時而戲謔,像神經(jīng)質(zhì)一般行事,但卻是誠實的、全心全意的。”他“對待文學是真誠的”,不像一個出版商,倒像是一個“愛好者和有天賦的享樂者”。
朗恩和菲舍爾的形象顯然相去甚遠。菲舍爾周密、堅定、可信。朗恩戲謔、慵懶,是一位有體育運動員氣質(zhì)的享樂主義者。
黑塞還描寫過一位和菲舍爾有著微妙差別的出版人。他借編輯迪德里希出版社旗下的一本題為《通往德國文化之路》的出版目錄的機會,描述了奧爾根·迪德里希所做的工作。他提到了后者的“快樂的樂觀主義”,在強調(diào)菲舍爾的出版計劃呈線性(這種線性,菲舍爾師承于托馬斯·曼所說的“自然主義時代的科塔”)的同時,洞察到迪德里希的出版計劃在內(nèi)容和觀點上是多元的。“因為他全身透著一股實干勁,以及對他人的崇拜所帶來的虔誠的歡樂,不墨守成規(guī),不屈從于思想家和作家的一家之言。所以,他的出版社并沒鋪下一條自命不凡的窄路,而是打造了一所花園,這所花園雖只應有善和美,但它也不會放棄追求對立和多元。這位出版界的理想主義者好像忍不住要給他出版社的每一本書或者每一種走向,都找到它的對立面,從而達到一種平衡。”迪德里希是“獨一無二的,他對待古代文化的態(tài)度是由衷的、積極的,既沒有在舊事物中疲于奔命地翻箱倒柜,也沒有無力地嗅尋新刺激(這倒是在現(xiàn)在許多出版目錄冊里作祟)”。
黑塞一直反感于出版人“無力地嗅尋新刺激”,他經(jīng)常要把這樣的出版人從自己的道路上攆開。在《生平短記》1925年修訂版中他寫道:“過了一陣我當然發(fā)覺,在精神方面,一種只活在當下,活在新和最新之中的生活是難以承受的,也是毫無意義的,與過往的、歷史的、古老的事物建立關系才是精神生活的存在前提。”
黑塞作為世界文學的編纂者和評論家所取得的成就并沒有得到充分重視。他的論文《世界文學藏書》一直都可以作為藏書或閱讀指南使用。黑塞寫了大約3000份書評,福爾克爾·米歇爾斯在《文論》第二卷中整理出大約300篇“從中能應運而生一部文學史”的書評。這部選集的論述對象自《吉爾伽美什史詩》、佛陀語錄和中國哲學開始,經(jīng)卡夫卡、普魯斯特和羅伯特·瓦爾澤的作品——在二十年代,黑塞應該算得上是他們的發(fā)現(xiàn)者——再到瓦爾特·本雅明、安娜·西格爾、阿諾·施密特、馬克斯·弗里施,J.D.塞林格,最后以彼得·魏斯的《告別父母》收尾。
同樣堪比這份評論集的是《黑塞自編世界文學作品》的編目。福爾克爾·米歇爾斯編的《赫爾曼·黑塞出版或為其撰寫前言后記的圖書》中就列舉了66本書!第一本是1910年菲舍爾出版社的《德國民歌集》,接著是《宗教經(jīng)典》《少年魔法號角》《東方故事集》《羅馬人傳奇》《奇人怪談》(文集)《萬茲貝格的信使》《奇跡小書》《中世紀文學》《傳說軼事》《阿勒曼恩書》以及歌德、凱勒、荷爾德林、諾瓦利斯和其他浪漫主義作家的作品。門德爾松寫道,和菲舍爾討論并計劃出版的《浪漫主義精神》文集不翼而飛。
在黑塞的遺物里我們發(fā)現(xiàn)了此書詳盡的目錄,也許我們可以把這個重要的計劃付諸實踐。黑塞研究最深入的作家是讓·保爾。黑塞的許多短文、評論、編輯、導言、后記都與他有關;黑塞不知疲倦地提起當時還不為大眾所知的讓·保爾:“人們應該心懷一種更加歡快的心情來推薦讓·保爾。因為他能給詩意以歡樂,給思維以無盡的啟發(fā),給庸人以芥末藥膏。”讓·保爾,“我們偉大的業(yè)余藝術愛好者,我們最偉大的大師,是唯一不缺乏激情、天賦和浪漫主義的真情實感,而又活在德國經(jīng)典人道主義蒼穹下的德國詩人”。黑塞為出版人格奧格·穆勒寫的悼詞,有三分之二都是講“當代德國古老的恥辱”——數(shù)十年來都沒有“最具德意志精神的德意志詩人”讓·保爾的作品善本出現(xiàn),現(xiàn)在,格奧格·穆勒的去世讓黑塞心懷已久的心愛計劃——在這家出版社出一個讓·保爾的新版本——蒙上了一層陰影。我在我的博士論文《赫爾曼·黑塞論以寫詩為志業(yè)》中論述了黑塞和讓·保爾之間的關系,并指出,黑塞在研究讓·保爾的過程中經(jīng)常表述自己的詩學理論。
這種置身于文學中并與文學共生的活動(托馬斯·曼稱之為“一種服務、效忠、遴選、修改、重現(xiàn)并大膽地為此發(fā)聲——這些足以充實文學家的生活”),帶來了數(shù)不勝數(shù)、被幸運地保存下來的黑塞與出版人的通信,還有同樣數(shù)不勝數(shù)的有關出版人工作的文章。“我作為書商、古董商、作家和批評家以及許多出版人和藝術家的朋友對現(xiàn)代圖書業(yè)頗為了解。”從他的認知、他的事業(yè)和他的文學作品,以及他的作品的樣式和出版順序中,我們能看出黑塞明確的出版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