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比利亞枷鎖,桎梏了拉丁美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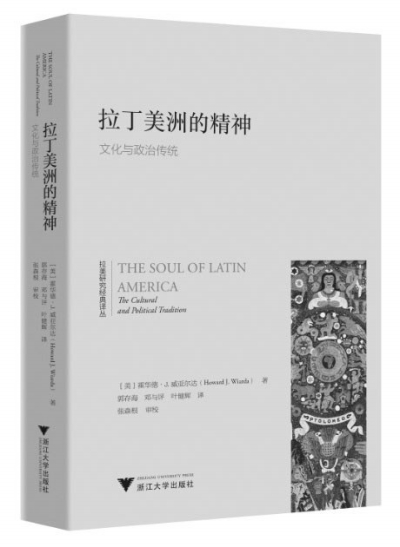
《拉丁美洲的精神:文化與政治傳統(tǒng)》,[美]霍華德·J.威亞爾達(dá)著,郭存海、鄧與評、葉健輝譯,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定價78.00元
在《拉丁美洲的精神》里,霍華德·威亞爾達(dá)斷言,獨立后的拉丁美洲罹患了“精神分裂癥”。的確,它是大病難愈之人,一只手握著獨立自由的新生,另一只手卻被舊日枷鎖牢牢銬住。
1815年,委內(nèi)瑞拉獨立運動受挫,日后被尊為“解放者”的玻利瓦爾逃亡加勒比海島。他反思美洲的歷史與現(xiàn)實,尋覓革命失敗的癥結(jié)。在那一年發(fā)表的《牙買加來信》里,玻利瓦爾犀利地將矛頭指向了宗主國。
霍華德·威亞爾達(dá)筆下,伊比利亞史和拉丁美洲史是不可分割的,前者無縫融入后者。正因如此,玻利瓦爾的聲音振聾發(fā)聵。《牙買加來信》不僅是一篇反抗殖民的檄文,也是一本剖析美洲的報告。伊比利亞困住拉丁美洲的第一道枷鎖,就是經(jīng)濟(jì)剝削。哥倫布遠(yuǎn)航之后,征服者與殖民者懷揣著一夜暴富的夢想,前往美洲尋找“黃金國”。他們沒能發(fā)現(xiàn)傳說中的寶藏,卻意外覓得不少銀礦。無數(shù)印第安人被皮鞭驅(qū)使著,加入繁重的采礦勞動。他們在黑暗巷道的血淚,化作了一船又一船駛往西班牙的白銀。三個世紀(jì)里,超過一億公斤白銀跨過大西洋,抵達(dá)了伊比利亞半島的港口。有人說,西班牙就像一張嘴,填進(jìn)食物加以咀嚼,僅為把它送到別的器官,除了經(jīng)過的氣味和偶爾粘在牙齒上的碎屑,什么都沒有留下。的確,坐擁財富的西班牙將白銀揮霍一空,養(yǎng)肥了歐洲,但西班牙人至少嘗到了金銀的味道,美洲人卻只能望之興嘆。不止如此,正像玻利瓦爾所說,西班牙人還壟斷了殖民地貿(mào)易,各地只能向宗主國高價購買制成品,而不能私下互通有無。食鹽、火藥、紙張、墨水都在專賣清單之列,足見控制之細(xì)密。
單一的出口模式與粗暴的垂直管理相伴而生,葡萄牙人在巴西的統(tǒng)治可謂典型案例,紅木、蔗糖、黃金、咖啡周期里,殖民地往往集中產(chǎn)出某一種物資,缺乏經(jīng)濟(jì)活力。在全球擴(kuò)張進(jìn)程中,由于沒有財力與精力大肆征伐,葡萄牙人傾向于在沿海建立商站,而非侵入內(nèi)地。在腹地廣闊的巴西,盡管殖民者一度向亞馬遜挺進(jìn),但絕大多數(shù)時間滿足于在海岸線上搭設(shè)居民點,轉(zhuǎn)運紅木和黃金。對于殖民地的建設(shè),統(tǒng)治者漠不關(guān)心。拉丁美洲豐富的資源,在伊比利亞的剝削模式之下,無法轉(zhuǎn)化為商業(yè)繁榮,借用前輩學(xué)者索颯的書名,這正是“豐饒的苦難”。直至20世紀(jì)中葉,單一產(chǎn)品出口導(dǎo)致的周期性經(jīng)濟(jì)危機(jī)仍困擾著拉丁美洲,勞爾·普雷維什稱之為“依附性”,而它的始作俑者正是伊比利亞模式。
制造苦難的,不惟嚴(yán)苛管理,還有移植自伊比利亞半島的社會階層。歷史上,西班牙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斗爭的前沿陣地。在收復(fù)失地運動里,立下功勛的將領(lǐng)和士兵獲得大片土地,成為國內(nèi)新貴。征服美洲之際,統(tǒng)治者沿用此法,吸引游民和窮人遠(yuǎn)渡重洋。在阿茲特克和印加故土,許多雙手沾滿鮮血的“先遣官”,憑借軍功一躍成為大地主。他們及后代經(jīng)營著大莊園和大種植園,終日以斗雞、比武和舉辦奢華宴會為樂。宗主國派往殖民地的總督和大小官員是莊園的座上賓。在遙遠(yuǎn)之地,總督對國王命令奉行“服從但不執(zhí)行”的原則,過著土皇帝的生活。耕種和采礦的重壓,通過勞役派遣制,施加在印第安人身上。當(dāng)大量印第安人死于繁重勞作和歐洲疫病,官員和莊園主引入了非洲奴隸。奴隸生產(chǎn)的財富,先由殖民地的掌權(quán)者層層盤剝,繼而運往舊大陸。與宗主國風(fēng)氣如出一轍,美洲的上流社會貪圖享樂,迅速將財富換成了奢侈品,民眾常年生活在貧困之中。時至今日,貧富懸殊仍是拉丁美洲的關(guān)鍵詞,良田千里的莊園與臟水橫流的貧民窟同在一城,形成鮮明對比。
無論在西屬美洲或巴西,天主教都是殖民者的一大遺產(chǎn)。對天主教的倚重,源于伊比利亞獨特的歷史進(jìn)程,在與穆斯林王朝長達(dá)幾個世紀(jì)的斗爭里,宗教被用作籠絡(luò)人心的精神武器。征服美洲,是用劍與十字架完成的。傳播福音是大航海的最初動力和說辭,印第安人的原始信仰被禁止,天主教會滲入社會的每個角落。在殖民地,從生老病死到賦稅教育,教會都扮演著重要角色。教親關(guān)系則是串聯(lián)社會的關(guān)鍵紐帶,大莊園主和官員互為對方子女的教父教母,構(gòu)成了更牢固的統(tǒng)治階層。對于普通民眾而言,教會是一副無形枷鎖,裙帶關(guān)系盛行,阻斷了窮人的上升通道,它宣揚的神學(xué)限制了知識傳播和思想交融,使得獨立以前的拉丁美洲文盲率奇高,在一些小市鎮(zhèn),甚至找不出十個能夠識文斷字的人。不容忽視的是,教會擁有令人咋舌的財富。在獨立運動之前,它占據(jù)了拉丁美洲三分之一的土地,一邊收取莊園和牧場的捐贈,一邊借助放貸生財。在墨西哥,教會在獨立后的半個世紀(jì)仍是凌駕于世俗之上的權(quán)威,共和國不得不打響一場戰(zhàn)爭來擺脫它的束縛。
墨西哥的教會頑疾,只是獨立后拉丁美洲困境的一個縮影。拋開經(jīng)濟(jì)、社會與宗教的桎梏,單是如何統(tǒng)治國家,就曾讓“解放者”玻利瓦爾憂心不已。手握大莊園和大種植園的克里奧爾人,對錦衣玉食并不陌生,對治國理政卻無甚經(jīng)驗。宗主國放任他們窮奢極欲,卻緊緊掌控著總督等高級職位的任免權(quán)。玻利瓦爾說道:“美洲人突然站了起來,事先一無所知。最成問題的是,他們沒有掌管公共事務(wù)的實踐,難以在世界舞臺上掌握立法者、律師、司庫、外交官、將軍等以及其他高級或次一級的官職,而這些官職是一個有組織的國家通常必設(shè)的……一個剛剛掙脫鎖鏈的人民在進(jìn)入自由的領(lǐng)域時,不會像伊卡洛斯那樣,翅膀燒壞、墮入深淵嗎?”果然,拉丁美洲沒有逃過伊卡洛斯的命運,在奔向自由的旅程里,伊比利亞枷鎖牽絆了它的腳步。新生國家不能填補宗主國遺留的政治真空,也無力對抗虎視眈眈的英美法諸強,更沒有辦法敉平國內(nèi)多如牛毛的派系。在許多國家,獨立與共和成了一出你爭我奪的鬧劇,人們只得求助于某個強權(quán)人物來穩(wěn)定局面,“考迪羅”應(yīng)運而生。
“考迪羅”原意是“領(lǐng)袖、頭目”,在拉丁美洲成為一個特殊的政治名詞,他們在獨立戰(zhàn)爭登上歷史舞臺,獨攬一方大權(quán),引領(lǐng)了過渡時代的社會走向。法國大革命已經(jīng)證明,太過激烈的社會變革會帶來不可預(yù)測的危險。故而,欠缺政治經(jīng)驗的拉丁美洲選擇妥協(xié),將國家藍(lán)圖交給保守的權(quán)威。大莊園主與天主教會是“考迪羅”的堅實后盾,他們不愿放棄既得利益。底層民眾也不乏“考迪羅”的擁護(hù)者,他們希望強權(quán)人物革除弊病、換來新生。在風(fēng)靡全球的文學(xué)作品里,“考迪羅”往往是墨西哥圣塔·安納那樣的亂世梟雄,或是阿根廷羅薩斯那樣的暴虐屠夫,事實并非如此。戴著現(xiàn)代化面具的“考迪羅”不在少數(shù),他們修建鐵路、興辦教育,引入外資、奠基工業(yè),確實掀起了新風(fēng)氣。進(jìn)入20世紀(jì),與“考迪羅”一脈相承的軍政府唱起了主角,成為新舊之間的調(diào)解者,一面推進(jìn)著自由貿(mào)易,一面鎮(zhèn)壓著進(jìn)步人士,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國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了烙下了深刻痕跡。
美墨邊境以南的廣袤土地上,獨立降臨已近二百年。然而,曾經(jīng)物產(chǎn)豐饒的拉丁美洲,依舊在窮困與動蕩里苦苦掙扎。西班牙與葡萄牙統(tǒng)治時代早已遠(yuǎn)去,但它們留下了有形和無形的枷鎖,仍在桎梏著昔日殖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