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詩人博納富瓦的晚期詩學(xué):乘“彎曲的船板”出發(fā)
用散文來談?wù)撛姼枋菢O其困難的。盡管可以從為數(shù)不多聰明的頭腦和精彩的論文中獲得某種真實(shí)感和教義,還是避免不了寫出一篇庸俗的文章。對(duì)于博納富瓦這樣的詩人尤其如此。同時(shí),詩歌為我們?cè)O(shè)置了一個(gè)逃逸的出口:從自身出發(fā)尋找事物的存在的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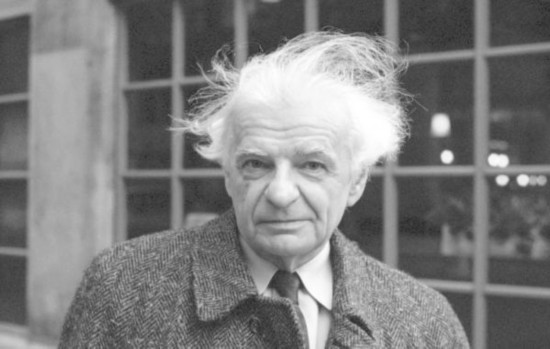
博納富瓦
博納富瓦生于1923年的法國圖爾。他在中學(xué)學(xué)習(xí)數(shù)學(xué),20歲時(shí)到巴黎,參與超現(xiàn)實(shí)運(yùn)動(dòng),三年后又與它決裂。在這個(gè)時(shí)期,他在巴黎索邦大學(xué)研讀哲學(xué),加斯東·巴什拉給予他很多啟示。二戰(zhàn)后,博納富瓦回避了當(dāng)時(shí)潮流“介入文學(xué)”,轉(zhuǎn)而以“在場”(présence)建構(gòu)自己的詩歌美學(xué),1953年《論杜弗的動(dòng)與靜》奠定了他的詩壇地位。隨后,他也發(fā)表一系列詩學(xué)論文,《論詩的行動(dòng)與場所》等,著力構(gòu)造自己的詩學(xué)地圖。1981年,他執(zhí)掌法蘭西公學(xué)院(le Collège de France)“詩歌功能的比較研究”(études comparées de la fonction poétique)教席。他也翻譯了莎士比亞、彼得拉克、萊奧帕爾迪、葉芝等人的詩歌和劇作,并撰寫關(guān)于詩歌和繪畫的散文。
《彎曲的船板》是詩人晚期作品(并非最后一本)。在近百年的研究中,對(duì)于“晚期”的指認(rèn)是一個(gè)值得一說的事件,先是愛德華·賽義德出版《論晚期風(fēng)格》,再是哈羅德·布魯姆編輯《直到我停止歌唱:最后的詩選集》(Till I End My Song: A Gathering of Last Poems)。何以晚期變得如此重要?概因?yàn)橥砥谑莿?chuàng)作生命中的某種奇觀,部分文人以凋零的姿態(tài)面對(duì),但強(qiáng)勁的詩人則在加劇的有限性和肉身消磨中學(xué)習(xí)生長。他們給予那些虛假的現(xiàn)代景觀以最強(qiáng)有力的反擊和輕蔑。
晚期博納富瓦探索了新的主題:回憶、希望、生命的再生,這些主題在詩人過往的作品中也是題中要義,但這一次,他把優(yōu)先權(quán)授予了這些和善的客體。他進(jìn)入到一種夢(mèng)幻般的語調(diào)里,在其中,語言成為一種補(bǔ)充,并且語言自身也攜帶著更多的原始、粗糙、破碎。“香氣,顏色,味道,/同樣的夢(mèng),/而鴿子另在別處/在咕咕聲里。”寫出這幾行的博納富瓦,像極了博爾赫斯,但于詩人而言,記憶不是博爾赫斯意義上的旋渦,而是博納富瓦意義上的指涉,一條道路,漸行漸光明的道路。
從《杜弗的動(dòng)與靜》到《在門檻的圈套中》再到《彎曲的船板》,代表著一條從聲音,到行動(dòng),再到記憶的進(jìn)路。博納富瓦一生的詩作都在生產(chǎn)一種介于獨(dú)白和對(duì)話之間、呼吁和神啟之間的語言,它有很強(qiáng)的戲劇面向,每每向讀者召喚和致意,但在這個(gè)“戲劇地質(zhì)層”之上,其詩歌又呈現(xiàn)不同的地貌。《杜弗的動(dòng)與靜》圍繞著聲音而發(fā)生,這個(gè)聲音可以看作是杜弗所分娩的,又可以視為與杜弗并存。“隨時(shí)生,杜弗,/隨時(shí)死”一句在“說”之中注入一種光與暗、死與生的角力,在杜弗之生中“說”,在杜弗之死中“說”。與“徒然的加冕禮”的話語不同,“說”是一種詩性之光,它“最終把自己變成風(fēng)和黑夜。”《在門檻的圈套中》表現(xiàn)了迭升高崛的行動(dòng),其中是一個(gè)催眠和喚醒后的杜弗。從聲音到行動(dòng),是從沼澤到山陵的變化,也是從母體到父體的變化。“撞擊,/永遠(yuǎn)撞擊。”在客體之中,杜弗的糾纏不再是以命名的方式呈現(xiàn),而是直接地和客體發(fā)生搏斗。所謂“門檻”并不純?nèi)皇钦Z言,它同時(shí)也是“詞語之風(fēng)”,是“水中露出一張臉”的露出動(dòng)作,是在一切之中的擺渡人。
《彎曲的船板》呈現(xiàn)出杜弗的視覺化形象,這樣的視覺化既是聲音的視覺化,也是行動(dòng)的視覺化,它讓早期的高亢和決絕變得曼妙、溫和,凍僵得像霧一樣。詩集中常有的一個(gè)形象是少兒時(shí)代杜弗,他對(duì)于客體的處理是跨越性的動(dòng)作,而不再是辨認(rèn)性的動(dòng)作,而詩句中所稱的“回憶”仿佛是少年杜弗對(duì)于未來的希望和期許。正是以未來之貌出現(xiàn)的回憶讓戲劇聲音過渡成為影像。晚年的博納富瓦也表現(xiàn)出對(duì)于人間的關(guān)懷和接納,房子建筑在他的詩句之上,取沼澤和山陵而代之,這種關(guān)懷和接納并非具有某種事態(tài)的反面,反而是他暮年衰老的肉身上的某種生長:在嶄新的慢調(diào)背后是更深的詩。
先繞開詩歌文本,看一看博納富瓦的詩歌觀念。1972年博納富瓦應(yīng)比利時(shí)皇家學(xué)士院之邀發(fā)表演講,在演講的結(jié)尾他說,“我們簡單地說吧:一要有夢(mèng)想,夢(mèng)想像我方才談過的那樣去寫作;二要有意愿,愿意從某種語言的羈絆中將詞語解放出來;三要有希望,希望從話語的深處找到那些原初時(shí)期即已誕生的、尚存的和已消亡的詞匯與句法。……事實(shí)上,詩早在鐵器時(shí)代即已具有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眼下的當(dāng)務(wù)之急,或許更應(yīng)當(dāng)去理解這些規(guī)律,而不是提出什么新的綱領(lǐng)。”
他遠(yuǎn)沒有同輩詩人保羅·策蘭那樣殘暴和幽暗,他是質(zhì)樸的、溫和的乃至中庸的。但兩者同時(shí)也分享了一些相似之處,在那篇《論策蘭》里,他毫無保留地贊賞了這位離散者,“對(duì)于那條河而言,只要某個(gè)像這一死亡一樣的行動(dòng)使它變得更加寬廣,使它能聚集起一切場所內(nèi)的生活嘗試、一切求索中的思維、一切希望和一切回憶,作為真實(shí)的虛空的這條河便能涌動(dòng)起來……”他相信策蘭的死亡對(duì)于他的詩歌是一次偉大的完成。在回答《巴黎書評(píng)》的采訪中,他再次聲明詩歌能夠?qū)⑺劳雠まD(zhuǎn)成積極事件。同時(shí),他說,“詩歌讓這個(gè)世界變得更致密了,它的一致性也變得更易察覺,我們會(huì)感到整體中的更多部分,在一瞬間里的永恒。”
《扔石頭》無疑是這句話的實(shí)踐。這篇散文詩幾次復(fù)寫了“扔石頭”這個(gè)動(dòng)作,先是寫在溪谷里投石頭,再寫夜里閃光的石頭,再寫我們將石頭播散在深淵里,最后寫手流血、但我們抓得更緊、并且發(fā)出笑聲來。“扔石頭”瞬間過渡到一種寓言,在寓言里,人們受盡剝奪、創(chuàng)痛,但人們對(duì)即將到來的一切、對(duì)建筑生命飽含希望。
面對(duì)先輩們、同時(shí)代作家群體的對(duì)于塵世生活的解構(gòu)(據(jù)他說,馬拉美也是如此),博納富瓦希望回避這一異化。他也批判現(xiàn)代詩學(xué)中的唯我論,據(jù)讓·斯塔羅賓斯基對(duì)他的詩學(xué)做出的解釋,“不是自我,而是世界應(yīng)該贖罪,或者更確切地說,如果世界和自我在一起,自我才能夠贖罪。”博納富瓦晚期詩學(xué)的種種傾向,在他早期和超現(xiàn)實(shí)主義分道揚(yáng)鑣之時(shí)就已經(jīng)清晰反映。正如秦三澍所論述的那樣,“他認(rèn)為靈知主義-超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缺陷和誤區(qū)在于將注意力放置在后-象征主義的理念化立場上,而忽略了現(xiàn)實(shí)的‘鳥’與‘石頭’;他們遺忘了人之有限性境況的界限,卻滿足于接納那些漂浮于‘自動(dòng)寫作’岸灘上的無意識(shí)的殘余物。”詩人呼吁我們從浪漫主義陰影里走出來,從自我表現(xiàn)中撤出來,去真正理解他人。
他的詩歌與其觀念一脈相承。在《在詞語的圈套中》一詩中,博納富瓦虛構(gòu)了一次漫游,這既是精神的漫游,又是歷史的漫游,更是生命的漫游。“我們是背負(fù)自身重量的船,/滿載著封閉的事物……/也許能忘掉海面所有的島嶼,/唯有一顆星愈發(fā)清晰。”我們皆是擺渡人。我們?cè)谶@里和別處的世界之間,在生與死的雙重性之間。他在《在門檻的圈套中》一書中寫道,“我是擺渡者,/我是穿越一切的一切之船,/我是太陽,/我在石叢中停步在世界的頂端。”這不再是浪漫主義的自我拔高,而是基于存在的對(duì)于自我的確認(rèn)和允諾。
他期待詩歌能重新迎回本體論的詩神,期待詩歌能夠保持著驚奇贏得其始源的真正面目,期待詩歌能夠把物和世界承擔(dān)起來,納入由土地明確擔(dān)保的統(tǒng)一體中。越到死亡的當(dāng)口,詩人對(duì)于希望的囑托就越鄭重、越飽和,在《當(dāng)下此刻》一詩的第三節(jié)最后,他寫道,“遺贈(zèng)給我們不在絕望中死亡的可能。”
“詩正在經(jīng)歷蛻變,從結(jié)果到可能,從回憶到等待,從荒陌的空間到緩慢的進(jìn)展,再到希望。……事實(shí)上,假如我們不能抵達(dá)那個(gè)真實(shí)的場所,我們又能指望什么呢?”博納富瓦如是說。
參考資料:
馮婧,《博納富瓦:不被納入到任何一個(gè)主義里的“不倒翁”》
陳力川,《博納富瓦:為萬事萬物重新命名》
哈羅德·布魯姆,陸毅棟,《直到我停止歌唱:最后的詩選集》(Till I End My Song: A Gathering of Last Poems)序言
秦三澍,《〈彎曲的船板〉:在詞語的童年測(cè)聽希望——晚期博納富瓦及其“在場”詩學(xué)》,自《彎曲的船板》
讓-呂克·南希,白輕,《在貧困的時(shí)代,詩人何為?——關(guān)于博納富瓦的詩歌》
讓·斯塔羅賓斯基,《詩,在兩個(gè)世界之間》,自《博納富瓦詩選》
伊夫·博納富瓦,劉楠祺,《論詩的作用》
伊夫·博納富瓦,劉楠祺,《論詩的行動(dòng)與場所》
伊夫·博納富瓦,秦三澍,《彎曲的船板》
伊夫·博納富瓦,樹才,郭宏安,《杜弗的動(dòng)與靜——伊夫·博納富瓦詩集》
伊夫·博納富瓦,樹才,郭宏安,《博納富瓦詩選》
伊夫·博納富瓦,葛雷,《語言不再是初始時(shí)代的語言》,自《面對(duì)面》
John T. Naughton,The Notion of Presence in the Poetics of Yves Bonnefoy
Michael Bishop,Presence and Image: The Poetics of Yves Bonnefoy
Shusha Guppy,Yves Bonnefoy,The Art of Poetry No.69, The Paris Re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