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經(jīng)與利劍》:1840年,英國(guó)的另一場(chǎng)對(duì)外戰(zhàn)爭(zhēng)
1840年4月,英國(guó)議會(huì)以微弱票數(shù)通過決議,通過了出兵中國(guó)的決議。6月,英軍抵達(dá)廣東海面,隨即北犯廈門、定海,鴉片戰(zhàn)爭(zhēng)正式爆發(fā)。但這場(chǎng)在中國(guó)婦孺皆知的鴉片戰(zhàn)爭(zhēng),并非是英國(guó)在1840年唯一一次對(duì)外軍事沖突。從近了講,英軍此時(shí)在阿富汗的山區(qū)苦戰(zhàn)。往遠(yuǎn)了說,英國(guó)的軍艦又炮轟貝魯特和阿克城,聯(lián)合奧地利海軍進(jìn)逼埃及的亞歷山大,逼迫埃及統(tǒng)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放棄了自己在地中海東岸打下的大片江山,把即將重建的“阿拉伯帝國(guó)”扼殺于搖籃之中。
為什么英國(guó)要在與中國(guó)和阿富汗鏖戰(zhàn)之時(shí),又要聯(lián)合歐洲列強(qiáng),甚至包括自己的宿敵沙俄,去幫助奧斯曼帝國(guó)遏制穆罕默德?阿里的擴(kuò)張?著名的歷史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圣經(jīng)與利劍:英國(guó)和巴勒斯坦——從青銅時(shí)代到貝爾福宣言》(Bible and Sword: England and Palestin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Balfour)一書中,從宗教虔誠(chéng)和帝國(guó)利益這兩條線索予以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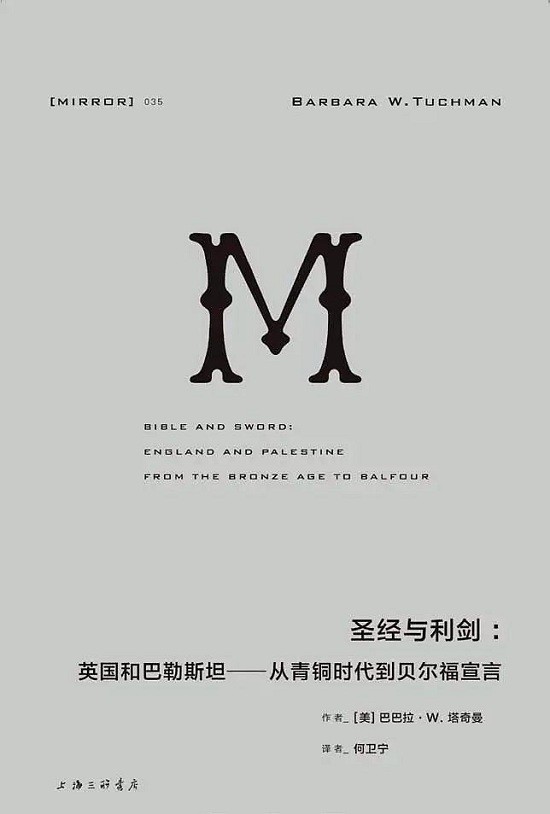
《圣經(jīng)與利劍:英國(guó)和巴勒斯坦——從青銅時(shí)代到貝爾福宣言》
“重返家園”:猶太人改宗基督教的前提
根據(jù)《圣經(jīng)與利劍》,英國(guó)人與巴勒斯坦的淵源可以追溯到羅馬帝國(guó)時(shí)代。興起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傳播到英國(guó)后,宗教紐帶又增加了兩地的聯(lián)系。不過,在中世紀(jì)很長(zhǎng)的一段時(shí)間內(nèi),與基督教有著共同淵源的猶太教,在英國(guó)卻備受敵視。這種強(qiáng)烈的反差充分體現(xiàn)在十字軍戰(zhàn)爭(zhēng)期間。夾雜著世俗利益的宗教情緒既讓十字軍把矛頭指向東方的穆斯林,也同樣使他們把屠刀揮向了巴勒斯坦的猶太教徒,甚至連英國(guó)境內(nèi)的猶太人也不能幸免。例如,塔奇曼指出:
公眾對(duì)猶太人的仇恨情緒本來其實(shí)并不高漲,但被“圣戰(zhàn)”激化了。部分原因是中世紀(jì)的人們對(duì)教會(huì)以外的異教徒有一種迷信般的恐懼。另一個(gè)原因是人們對(duì)債主的仇恨……在十字軍東征期間,人們認(rèn)識(shí)到在十字軍旗幟下動(dòng)用的暴力,是輕松抹掉債務(wù)、奪取猶太人財(cái)產(chǎn)而不受懲罰的捷徑……到了1190年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時(shí),十字軍與猶太人大屠殺已經(jīng)變得不可分割……殺戮風(fēng)潮就像洶涌的波濤一樣從倫敦蔓延到所有猶太人居住的城市,最后的恐怖高潮出現(xiàn)在約克——在那里,只有那些先殺死妻兒后引頸自殺的猶太人才能逃脫暴民的屠殺。
但宗教改革后的英國(guó)清教徒開始強(qiáng)調(diào)《舊約》。用塔奇曼的話說,對(duì)希伯來文化的推崇,在17世紀(jì)的英國(guó)蔚然成風(fēng),克倫威爾便是代表人物。當(dāng)然,這些清教徒畢竟也是基督徒的一部分,他們友善對(duì)待猶太人有著自己的宗教邏輯,并非是出于單純的包容。塔奇曼指出:
隨著清教的興起,讓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運(yùn)動(dòng)在英國(guó)開啟了。(但)這場(chǎng)運(yùn)動(dòng)并不是為猶太人本身,而是為完成《圣經(jīng)》中對(duì)猶太人的承諾。根據(jù)《圣經(jīng)》的說法,當(dāng)以色列人回到錫安后,全人類的以色列國(guó)將會(huì)到來。此時(shí)彌賽亞,或者按基督教的術(shù)語——基督將再次降臨。
當(dāng)然,在理想主義盛行的18世紀(jì),這種宗教熱情較為薄弱。但“在經(jīng)過18世紀(jì)希臘化的間歇后,鐘擺又?jǐn)[回到希伯來化的道德緊迫性。18世紀(jì)的懷疑主義讓位于維多利亞時(shí)代的虔誠(chéng);18世紀(jì)的理性主義再次服從于神啟。”在這樣的社會(huì)氛圍下,19世紀(jì)的英國(guó)又出現(xiàn)了福音主義,并推動(dòng)了早期的猶太復(fù)國(guó)主義。因?yàn)楦R糁髁x者與之前清教徒的邏輯相似,即“圣經(jīng)預(yù)言+以色列人改宗和返回家園=基督復(fù)臨。”可見,他們對(duì)猶太復(fù)國(guó)主義的支持不是出于對(duì)猶太教信仰的認(rèn)可,而是覺得返回巴勒斯坦是讓猶太教徒皈依基督教的前提。而此時(shí)1840年的大馬士革事件則為福音主義的宗教熱情提供了契機(jī)。
根據(jù)塔奇曼的敘述,大馬士革事件并非是猶太人與穆斯林的沖突,而是法國(guó)人及天主教徒對(duì)猶太人的迫害。這就引發(fā)了沙夫茨伯里伯爵的關(guān)注。作為福音主義的代表,沙夫茨伯里伯爵認(rèn)為“新教英國(guó)將幫助信奉英國(guó)國(guó)家的以色列人復(fù)國(guó),一舉挫敗天主教,使預(yù)演應(yīng)驗(yàn)并拯救全人類。”當(dāng)然,光有宗教熱情是不夠的,還需要國(guó)家力量的支持。如此,沙夫茨伯里伯爵便動(dòng)員輿論和政府介入中東局勢(shì)。

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1801-1885),塔奇曼稱之為“除達(dá)爾文之外,他是英國(guó)維多利亞時(shí)代最具影響力的非政治性人物”
那政府又會(huì)出于什么利益考慮而出兵中東呢?此時(shí)的中東局勢(shì)又與天主教法國(guó)有什么關(guān)系呢?這就要從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說起。
“阿拉伯帝國(guó)”: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
穆罕默德?阿里,這個(gè)出身阿爾巴尼亞的煙草商人早年加入奧斯曼軍隊(duì),在埃及抵御拿破侖的侵略。亂世出英雄,穆罕默德?阿里憑借高超的政治手腕,當(dāng)上了奧斯曼帝國(guó)的埃及總督。起初,他還頗為順從中央,例如在希臘戰(zhàn)爭(zhēng)中派出艦隊(duì)北上援助奧斯曼帝國(guó),特別是還東征阿拉伯半島,消滅了困擾奧斯曼蘇丹近半個(gè)世紀(jì)的沙特王朝。就國(guó)內(nèi)而言,他大興“洋務(wù)”,促進(jìn)了埃及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馬克思稱贊道他治下的埃及是“奧斯曼帝國(guó)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當(dāng)然,奧斯曼帝國(guó)此時(shí)在蘇丹馬哈茂德二世的領(lǐng)導(dǎo)下,也開展了深刻的近代化改革,其內(nèi)容也不拘泥在軍事領(lǐng)域,甚至蘇丹都帶頭換上了洋裝。但1830年代的兩場(chǎng)“敘利亞戰(zhàn)爭(zhēng)”則證明奧斯曼帝國(guó)的洋務(wù)運(yùn)動(dòng)遠(yuǎn)不如自己的“屬國(guó)”埃及。
為了在希臘戰(zhàn)爭(zhēng)中支援奧斯曼中央,穆罕默德?阿里曾派遣16000人的龐大艦隊(duì)。當(dāng)然,無利不起早的穆罕默德?阿里也從奧斯曼蘇丹手中獲取了克里特島的統(tǒng)治權(quán)。但希臘戰(zhàn)爭(zhēng)的慘敗,讓穆罕默德?阿里向朝廷獅子大開口,索要敘利亞(大致相當(dāng)于今天的敘利亞、巴勒斯坦、約旦、黎巴嫩,也被稱為沙姆地區(qū)或黎凡特地區(qū))的統(tǒng)治權(quán)作為補(bǔ)償。朝廷自然不愿滿足穆罕默德?阿里的野心。而兇悍的穆罕默德?阿里在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竟然派其子易卜拉欣揮兵自取。其實(shí),放在歷史的長(zhǎng)河中看,穆罕默德?阿里的野心并不奇怪,因?yàn)檫@幾乎是歷代埃及統(tǒng)治者的慣性。無論是古埃及的法老,還是中世紀(jì)時(shí)期的法蒂瑪哈里發(fā)、薩拉丁、馬穆魯克,抑或現(xiàn)代的納賽爾,只要他們有足夠的實(shí)力和精力,都會(huì)嘗試揮師東向,問鼎西亞。所以,穆罕默德?阿里可謂“前有古人,后有來者”,無外乎是延續(xù)埃及統(tǒng)治者的歷史傳統(tǒng)。
從1831年開戰(zhàn),不到兩年的功夫,埃軍就占領(lǐng)了地中海東岸的大片土地,甚至攻占了安納托利亞的科尼亞,也就是已經(jīng)打進(jìn)了今天土耳其的境內(nèi)。而且埃及還得到了法國(guó)七月王朝的支持。在此情況下,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岌岌可危。幸虧在沙俄的干預(yù)下,穆罕默德?阿里才被迫收手,退出安納托利亞。但兵強(qiáng)馬壯的他已經(jīng)從奧斯曼朝廷那取得了對(duì)克里特、漢志(阿拉伯半島的紅海沿岸地區(qū),有麥加和麥地那兩座圣城)和敘利亞的統(tǒng)治權(quán)。穆罕默德?阿里的帝國(guó)似乎已經(jīng)建立。
當(dāng)然,任何中央朝廷都難以容忍這樣的強(qiáng)藩,何況是這種可能取而代之的強(qiáng)藩。而穆罕默德?阿里父子也是欲壑難填。1838年雙方刀兵再起。但奧斯曼帝國(guó)再次慘敗,甚至奧斯曼艦隊(duì)還在亞歷山大向埃及投降。而此時(shí)一代英主馬哈茂德二世也含恨而終,16歲的阿卜杜勒?麥吉德即位,本來就已岌岌可危的奧斯曼帝國(guó)又處在了主少國(guó)疑的境地。
但英國(guó)人出于自己的利益考慮,“挽救”了奧斯曼帝國(guó)。
援土抑埃:帕麥斯頓的帝國(guó)考慮
塔奇曼對(duì)穆罕默德的“興趣主要不在于他震撼歐洲各國(guó)首都的功業(yè),而在于他將英國(guó)永久地拉入中東事務(wù)之中,并給英國(guó)人提供了一個(gè)為猶太人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國(guó)的機(jī)會(huì)。”當(dāng)然,沙夫茨伯里伯爵的“動(dòng)機(jī)是宗教的”,但外交大臣帕麥斯頓(他還有個(gè)令中國(guó)人熟悉的譯名——“巴麥尊”)的動(dòng)機(jī)則是“帝國(guó)的”,也就是利益。如此,沙夫茨伯里伯爵為了“忽悠”政府介入中東局勢(shì),就不能只談微言大義而不顧利害得失。在1838年第二次土埃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后,奧斯曼帝國(guó)與英國(guó)簽訂協(xié)定,“增加了(英國(guó))在耶路撒冷建立領(lǐng)事館的條款。”塔奇曼認(rèn)為這是沙夫茨伯里伯爵運(yùn)作的結(jié)果,他把這當(dāng)做“以色列復(fù)國(guó)的第一步。”此外,沙夫茨伯里伯爵把自己“崇高的動(dòng)機(jī)掩蓋起來”,向帕麥斯頓“灌輸把猶太用做插入奧斯曼帝國(guó)內(nèi)部楔子的理念”。帕麥斯頓并沒有讓沙夫茨伯里伯爵失望,他在給駐奧斯曼大使的信中表示:“如果猶太人是在蘇丹的邀請(qǐng)和保護(hù)下返回的,他們就會(huì)在未來阻止穆罕默德?阿里或其繼任者的任何惡毒企圖……”
同樣是“他者”的奧斯曼蘇丹和穆罕默德?阿里,英國(guó)人為何厚此薄彼,支持奧斯曼而敵視穆罕默德?阿里呢?根據(jù)塔奇曼的論述,可大致分為兩點(diǎn):遏制沙俄和維護(hù)印度通道。
首先就遏制沙俄而言,奧斯曼帝國(guó)面臨穆埃及大軍的兵鋒,不得已求助于自己的宿敵——沙俄。而穆罕默德?阿里的支持者——七月王朝時(shí)代梯也爾政府治下的法國(guó),對(duì)穆罕默德?阿里“取得的榮耀大家贊許,他此時(shí)看起來似乎也即將成為一個(gè)可與薩拉丁的帝國(guó)媲美的新帝國(guó)的主人,并掛上法國(guó)的三色旗。”如此,法國(guó)利用穆罕默德?阿里進(jìn)行的間接擴(kuò)張?jiān)獾缴扯淼牡种疲媛鼩w因于“沙皇極端厭惡帶著中產(chǎn)階級(jí)紳士派頭的法王路易?菲利普和他的民主思想。”當(dāng)然,意識(shí)形態(tài)之爭(zhēng)只是一個(gè)方面,沙俄還從奧斯曼帝國(guó)的恐懼獲取了很大的實(shí)惠。沙俄勢(shì)力迅速涌入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讓英國(guó)大使覺得“土耳其人已經(jīng)是俄國(guó)的傀儡了。”更要命的是,沙俄與奧斯曼簽訂條約,“規(guī)定一旦俄國(guó)要求,土耳其將封鎖達(dá)達(dá)尼爾海峽不允許任何其他國(guó)家的軍艦通過。”如此,英國(guó)便希望“化解土埃危機(jī)”,以阻止沙俄的擴(kuò)張。
而就“去印度的道路”而言,穆罕默德?阿里征服的地區(qū)關(guān)系到英國(guó)與印度的聯(lián)系,即便當(dāng)時(shí)蘇伊士運(yùn)河尚未開通。英國(guó)人覺得“一個(gè)年邁虛弱因而人人擺布的奧斯曼君主仍然比一個(gè)獨(dú)立親法的‘活躍阿拉伯君主’(帕麥斯頓語)更適合占據(jù)去印度的道路。”
當(dāng)然,或許法國(guó)支持的埃及擴(kuò)張過于猛烈,使得沙俄“放棄他的海峽特權(quán)”,與英國(guó)站在了一邊,共同反對(duì)穆罕默德?阿里的擴(kuò)張。這此背景下,英國(guó)得到了歐洲列強(qiáng)沙俄、奧地利和普魯士的支持。敘利亞爆發(fā)“反抗易卜拉欣的起義”后,英國(guó)和奧地利于1840年9月聯(lián)合炮轟貝魯特。11月,英奧聯(lián)合艦隊(duì)炮轟阿克,并在奧地利艦隊(duì)司令腓特烈(Archduke Friedrich)的率領(lǐng)下,英國(guó)、奧地利和奧斯曼聯(lián)軍占領(lǐng)阿克城堡。在聯(lián)軍的攻勢(shì)下,易卜拉欣“崩潰了”。與此同時(shí),英國(guó)與奧地利的聯(lián)合艦隊(duì)還封鎖了亞歷山大。在歐洲列強(qiáng)的炮口下,71歲的穆罕默德?阿里放棄了自己即將建立的帝國(guó),放棄了自己在亞洲的土地。

穆罕默德?阿里之子,易卜拉欣帕夏(1789-1848),1830年代敘利亞的實(shí)際統(tǒng)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