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張光年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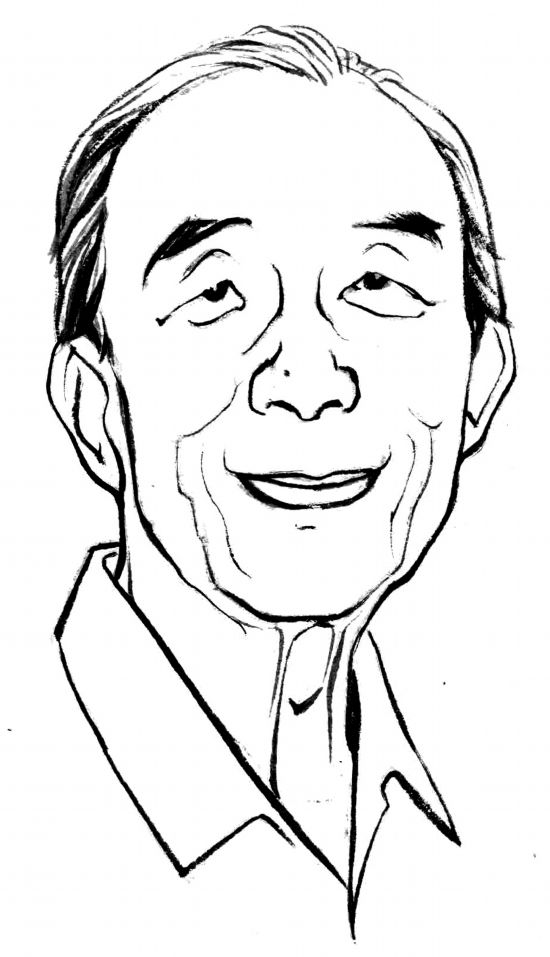
張光年肖像 羅雪村 作
我曾率隊(duì)走訪長(zhǎng)江水利委員會(huì),從武漢小住一夜即赴南水北調(diào)的水源地丹江口,車子經(jīng)過一處叫做老河口的鎮(zhèn)子,同行的高偉突然說道:“老河口是光年的家鄉(xiāng)呀!”于是話題自然轉(zhuǎn)到中國(guó)作協(xié)這位老領(lǐng)導(dǎo)的身上。
老河口有一條路以光年的名字命名。當(dāng)年他從這里走上革命的漫漫征途,我、高偉與光年同在一個(gè)創(chuàng)聯(lián)部黨支部,他是中國(guó)作協(xié)黨齡最長(zhǎng)的老黨員(1927年加入共青團(tuán),1929年加入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我們?cè)谒募抑卸冗^許多有意義的黨日,所以車過老河口喚起我諸多的回憶。
“風(fēng)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兩行經(jīng)典的詩(shī)句,把我領(lǐng)入到抗日戰(zhàn)場(chǎng),而光年的激情、才華、使命感,以時(shí)代為己任的責(zé)任意識(shí),也借助《黃河大合唱》留在了歲月的豐碑上。
那次走長(zhǎng)江,在秭歸的屈原祠,我在憑吊屈原之后寫一小詩(shī):“詩(shī)魂千載沉江底,孤忠一片浮日來。民心可用吊清烈,文章救國(guó)須捷才。”“清烈公”是宋代對(duì)屈原的封號(hào),詩(shī)中寫屈原的命運(yùn)時(shí),我其實(shí)是在潛意識(shí)里想到了光年先生的,他是文章和詩(shī)歌救國(guó)的榜樣,更是捷才。
巧的是我在《張光年文集》第一卷中偶然翻到他1986年10月25日寫的一首關(guān)于屈原的詩(shī):“熱淚滂沱瓊玉篇,文苑受惠兩千年。倘有詩(shī)人倡唯我,何來面目吊屈原!”(《屈原紀(jì)念館留字》)。光年憑吊屈原,我們紀(jì)念光年,冥冥中終有那么幾分巧合。“倘有詩(shī)人倡唯我,何來面目吊屈原!”這種口吻是光年典型的口吻,是他以詩(shī)人兼造詣精深的理論家雙重身份說出的極有分量的話。這是時(shí)代造就的堅(jiān)定不移的信念,說是信仰,也成。
其實(shí)早在40多年前云南從軍時(shí),我就知道光年,不,應(yīng)該說知道光未然。
因?yàn)樗?944年整理出一本極有名的云南彝族支系阿細(xì)族史詩(shī)《阿細(xì)的先雞》,后易名《阿細(xì)人的歌》,我在軍營(yíng)里拜讀過。我的營(yíng)房在宜良,與路南相鄰,而野營(yíng)拉練時(shí)常住在撒尼人的山寨里,與史詩(shī)中講述的故事背景十分吻合,故而親切萬分,同時(shí)為漢族詩(shī)人光未然對(duì)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尊重而感動(dòng)。他和提供詩(shī)歌原料的阿細(xì)族青年畢榮亮的友誼,也足以讓人稱頌不已。
真正知道張光年和光未然是一個(gè)人,是我1978年夏天從云南部隊(duì)轉(zhuǎn)業(yè)到《文藝報(bào)》之后了。光年是《文藝報(bào)》老主編,要當(dāng)好《文藝報(bào)》人,先熟讀歷期《文藝報(bào)》,這是編輯部主任謝永旺同志對(duì)每個(gè)新人的要求。永旺是光年的老下級(jí),也是“文革”前光年十分賞識(shí)的年輕人。當(dāng)永旺以剛復(fù)刊的《文藝報(bào)》骨干編輯的身份給我們這些新人(包括雷達(dá)、李炳銀、何孔周、臧小平、李維永……)講傳統(tǒng)時(shí),我才恍然大悟:光未然和張光年原來是同一個(gè)人!敢情《黃河大合唱》的作者、《五月的鮮花》歌者、《阿細(xì)的先雞》的整理改編者,居然是《文藝報(bào)》的老領(lǐng)導(dǎo),現(xiàn)任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的黨組書記!遙遠(yuǎn)頓時(shí)轉(zhuǎn)化為親近,說親切也行。
兩個(gè)身影與名字疊合在一起的光年,引領(lǐng)著當(dāng)時(shí)百?gòu)U待興的文藝界,以詩(shī)人的激情與理論家的睿智,加上一個(gè)老共產(chǎn)黨員對(duì)時(shí)代的敏感與責(zé)任,與他的戰(zhàn)友們一起,開啟了上個(gè)世紀(jì)80年代文學(xué)的輝煌。他或率團(tuán)出訪深圳特區(qū),或帶隊(duì)去大西北采風(fēng),更多的是組織評(píng)獎(jiǎng),編《人民文學(xué)》,應(yīng)對(duì)不時(shí)發(fā)生的突然事件。那個(gè)時(shí)候我只是《文藝報(bào)》一個(gè)年輕編輯,間接聽到一些因時(shí)代變革造成的觀念反差進(jìn)而產(chǎn)生的文壇糾紛,就讓光年煞費(fèi)苦心,當(dāng)然也讓具體執(zhí)筆的唐摯(達(dá)成)和唐因吃盡苦頭。可當(dāng)年光年肩上的壓力之重之大,也許只有《文藝報(bào)》的謝永旺同志多少能夠感知。
作為一名遠(yuǎn)觀者的我,正是因?yàn)楣饽瓿珜?dǎo)舉辦文講所七期的評(píng)論編輯班才成為魯院學(xué)員的。他對(duì)文學(xué)期刊評(píng)論與編輯的高度重視體現(xiàn)了文壇領(lǐng)導(dǎo)者的遠(yuǎn)見卓識(shí),與此同時(shí),他為當(dāng)時(shí)的作協(xié)所屬期刊制訂工作條例(即不嚴(yán)格坐班,要有讀書、調(diào)研和寫作的時(shí)間),造就了那個(gè)時(shí)期諸多的復(fù)合型人才。在《文藝報(bào)》一次會(huì)議上,我親耳聽到光年建議道:一年中12個(gè)月,編輯們可以一個(gè)月讀書,兩個(gè)月調(diào)研出差,9個(gè)月工作,后被簡(jiǎn)稱“129制度”。《文藝報(bào)》的同仁們應(yīng)是最大的受惠者。
事實(shí)上我與光年的接觸一直不多,遠(yuǎn)不如與馮牧、達(dá)成、羅蓀甚至文井、葛洛、朱子奇,還有舒群、管樺等前輩那么密切,但1985年底我突然受領(lǐng)《中國(gu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huì)的一項(xiàng)任務(wù):撰寫該書系“中國(guó)文學(xué)”卷“張光年”詞條,不到2000字的條目,在謝永旺同志的指點(diǎn)下,也在光年親自過問下,勉強(qiáng)完成了。其間我曾登門向光年求教過,也聆聽了他的醇厚湖北口音基礎(chǔ)上的普通話,講話慢條斯理、思路十分清晰的光年,講述著自己經(jīng)歷過的風(fēng)雨人生,講述著遙遠(yuǎn)的云南,講述著抗戰(zhàn)的烽火和寫作《黃河大合唱》的背景,你會(huì)感到充滿欽敬,你會(huì)仰視,你會(huì)為自己的年輕而慚愧,會(huì)產(chǎn)生一種愿意去追隨、去尋覓、去沖鋒陷陣的沖動(dòng)——也許這是所有年輕人的共性吧。
這就是我所理解的長(zhǎng)者、仁者和智者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