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的源頭在哪里
01
在一個消費主義盛行乃至猖獗的時代,飲水思源便顯得有些難能可貴了。純粹的消費是不問源頭的,重要的是快樂和享受;而文化則不同,它總是有傳統(tǒng)的,有傳統(tǒng)就有源頭。飲水思源既有感恩的意思,又有探尋揭秘的意思,這與消費主義背道而馳。設若文化與消費合二為一,文化的作用與意義也就幾乎消失殆盡了。因此,文化與消費不同,所謂消費文化或文化消費終究是一個矛盾的組合體。
我從事西方文學的教學和研究三十余年了,在心頭一直有一個縈繞不去的問題:西方文學的源頭在哪里?追根究底或者就是學者的本性。現(xiàn)當代西方文學愈蔚為大觀,追溯其源頭的意義也就愈為重要;尋本探源,對源頭的探究也更有利于認識當今西方文學的特質(zhì)和精神。所謂“源”和“流”總是裹挾在一起、彼此難分的,沒有“源”就沒有“流”,而有“流”就必有“源”。
因此,便有了“西方文學源頭考辨”的說法。當然,這只是一種比喻的說法,就是將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比作江河的源頭和流變。二者的可比性似乎是無可置疑的:任何文學現(xiàn)象無論多么繁榮復雜均有其源頭,正如任何江河湖海無論多么洶涌寬闊必有其發(fā)源地一樣。然而,考察文學的源頭正如考察江河湖海的源頭一樣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到源頭去飲水”,就是去飲用最純正的水,最潔凈的水,最沒有雜質(zhì)的水,而飲用源頭的水的前提是,我們必須首先尋找到源頭。
說到江河大川,對于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江河就是長江黃河了。它們都屬于中國的母親河,世世代代孕育著江河兩岸成千上萬的人民。長江黃河的源頭在哪里?現(xiàn)在人們通常認為,長江的發(fā)源地在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脈格拉丹冬峰西南側(cè)。黃河的源頭則在青藏高原的巴顏喀拉山脈。這里所說的源頭均只是大體位置而已,并沒有確切的源頭發(fā)生點。長江黃河的第一滴水出現(xiàn)在哪里?什么時間出現(xiàn)的?這類問題其實是很難考察的,甚至是根本沒法考察的。我們從“流”追溯“源”,最后會不知所終;我們從“源”順“流”而下,而“源”卻只能有大體的位置。大江大河如此,小江支流就更是如此了。
我們具體來說說汾河吧。汾河為黃河在山西境內(nèi)的支流,亦是黃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是山西最大的河流,被山西人稱為母親河,對山西省的歷史文化影響深遠。汾河全長713公里,流域面積39721平方公里。然而,它的源頭在哪里?有關汾河源頭的最早記載出自《山海經(jīng)》:“管涔之山,汾水出焉。”以后《水經(jīng)注》亦云:“汾水出太原汾陽北管涔山。”不過,汾河源頭具體在管涔山什么位置,史書的記載語焉不詳。1995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標明了汾河的具體發(fā)源地:山西省寧武縣東寨鎮(zhèn)西雷鳴寺泉。此處豎有“汾源靈沼”石碑一尊,被視為汾河之正源。不過,《山西河流》一書對汾河源頭的界定應該更為完整:“汾河發(fā)源于寧武縣東寨鎮(zhèn)管涔山脈樓子山下水母洞,和周圍的龍眼泉、象頂石支流匯流成河。”如此一來,汾河的源頭就不只是在一個點上,而是由多點匯合而成,汾河的源頭也就變得復雜起來。稍后出版的《汾河志》并不認同這種“正源”的說法:“其實汾河真正的源頭還應從正源雷鳴寺泉向北向西上溯16公里,至岔山鄉(xiāng)宋家崖村之西北與五寨縣交界處。”果然,現(xiàn)代的科技手段似乎證實了這一點。2011年山西省水文水資源勘測局經(jīng)過勘查,最后確定從神池縣延伸過來的一條溝道為汾河源頭,該地處于神池縣太平莊鄉(xiāng)西嶺村,位于雷鳴寺泉上游。“一條溝道”有多長?溝道如何可以成為源頭?溝道里的水又從何而來?這些籠統(tǒng)而模糊的說法似乎離汾河源頭的說法相去甚遠。總之,有關汾河源頭的諸種說法大抵如此。
02
現(xiàn)在我們來說說西方(歐洲)文學或文化的源頭。關于這個源頭,我們都知道所謂“兩希說”,即希臘和希伯來文學是西方文學的源頭。由鄭克魯主編的《外國文學史》在導論中寫道:“古希臘-羅馬文學和希伯來-基督教文學是歐洲文學的兩大源頭,文學史上稱之為‘兩希’的傳統(tǒng)。它們在歐洲文學漫長的歷史流變過程中呈矛盾沖突與互補融合之勢,歐洲近代文學的人文觀念和藝術精神的基本內(nèi)核,主要來自于這兩大傳統(tǒng)。”“兩希說”已經(jīng)成為外國文學史中的一種傳統(tǒng)了。這種說法相當于說汾河的源頭在“山西省寧武縣東寨鎮(zhèn)西雷鳴寺泉”,屬于“正源”說。然而,這個“說法”的源頭在哪里?這也是需要梳理和考證的。
茅盾在1930年出版的《西洋文學通論》中提及西方文藝思潮發(fā)生和發(fā)展的“兩個H”之說。所謂“兩個H”指的是Hebrism(希伯來主義)和Helenism(希臘主義)。“尤其是‘二希’,很被重視為歐洲文藝史的兩大動脈。”茅盾此說是自己的獨創(chuàng),還是援引他說?茅盾先生沒有注明。但茅盾僅僅只是提出了觀點,并沒有提供證據(jù)或進行論證,且茅盾也確非專門研究西方文學源頭的學者,因此茅盾的觀點很可能是援引自其他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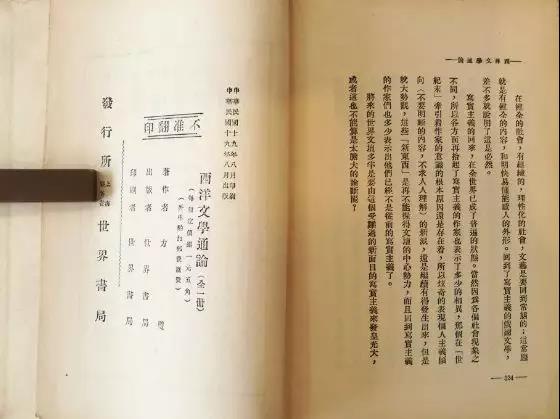
1930年版《西洋文學通論》書影
這樣一來,19世紀英國著名學者馬修·阿諾德(1822—1888)的觀點就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注意了。馬修·阿諾德是19世紀下半葉英國最重要的批評家。他一直被視為英美知識思想傳統(tǒng)或者說主流文化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他的重要著作《文化與無政府狀態(tài)》出版于1869年。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tài)》一書中,阿諾德明確指出:“希伯來文化與希臘文化,這兩者之間的影響推動著我們的世界。在一個時期,感受到它們中的這一個吸引力大些,在另一個時期,又感到另一個的吸引力大些;雖說從來不曾,但卻應當在它們之間保持適當和幸福的平衡。”阿諾德的這一關于西方文化源頭的說法影響久遠。因此,這一說法很可能影響到中國學者,然后又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到茅盾。我以為,這種推斷應該是有一定道理的。
當然,也有西方學者指出,西方文學的源頭還應加上哥特文學或文化:“歐洲文明的主流發(fā)源于古典文化和希伯來文化時代,隨后又因哥特人的入侵而加入第三個重要支流。”哥特人被認為是耳爾曼部落中最兇暴、最活躍的一支。哥特人的主要特點是躁動不安和激情好動。他們沒有在書面文學、藝術形式以及文化裝飾品方面做出貢獻,但是,“他們對個人自由理想的強調(diào)、對怪誕事物的迷戀、對婦女的神秘態(tài)度以及個人對首領的忠誠等觀念,在創(chuàng)造中世紀和后來的歐洲生活形態(tài)過程中也頗有影響力”。這便等于說汾河源頭雖然發(fā)源于“寧武縣東寨鎮(zhèn)西雷鳴寺泉”,但是,還應加上“周圍的龍眼泉、象頂石支流”等才算得上完整全面。不過,比較而言,作為西方文學的源頭,哥特文學出現(xiàn)較晚,希伯來文化則有些間接,作為西方文學最直接、最古老的源頭應當就是古希臘文學了。
古希臘文學是西方文學的開端,鑄就了西方文學的精神品格和基本走向。瓊·肯尼·威廉姆斯在《古代希臘帝國》一書中指出:“他們(古希臘人)的神話,經(jīng)荷馬傳誦,成為西方文學的源泉。”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近代世界就是希臘和羅馬世界的延續(xù)。現(xiàn)代西方人是羅馬人的孫輩,是希臘人的重孫。如果沒有希臘-羅馬文化,西方的現(xiàn)代文明將是不可想象的。西方文學的源頭在希臘,希臘文學的源頭為荷馬。荷馬是“當時唯一寫作的人”,但他的寫作并非只是一種消遣,有關特洛伊的戰(zhàn)爭也并非只是傳說,甚至荷馬根本就沒有“寫作”,他只是“吟唱”,當然還有整理或者改編。荷馬與西方文學源頭究竟為何種關系?如何能領略西方文學的精髓或精神?到古希臘文學那里去,大概是我們的必經(jīng)之路或理想之路,并且應該是我們最先的選擇。如有可能,我們就應該到源頭去飲水。這句話包含兩個意思:一是若想品味西方文學,就得首先品味古希臘文學;二是若想真正品味希臘文學,就得去閱讀希臘原著。但是,設若做到了以上兩點,我們是否就飲到了“源頭活水”呢?
03
事情并非如此簡單。西方文學的源頭并非一泓固定不變的“死水”,等待著我們隨時去“豪飲”。一旦我們誠心去追尋西方文學的源頭時,我們發(fā)現(xiàn)這個源頭其實并不確定,也并非可以輕易涉足其間。對于古希臘文學,我們現(xiàn)在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斷片或片面性的傳說。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文學作品,我們所掌握的約有百分之二十,而越往前我們所掌握的就越少。英國古希臘文學研究專家吉爾伯特·默雷說:“每一種文學作品,當人們想起要保存下來的時候,實際上大部分早已毀棄。”古代人最初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時并沒有想到要保存,而之所以想到保存,則是因為許多文學作品已經(jīng)永久消失,已無法保存了。我們保存下來的文學作品大都經(jīng)過書寫和印刷而定型,而文明之前的野蠻人的文學作品的保存卻只能通過記憶和傳承,在今天看來,這種保存方式自然是不可能精確可靠的。而文學的真正源頭顯然來自后者,而非前者。前者在經(jīng)過文字的記載和傳播后,已經(jīng)從“源”變成了“流”,且蔚為大觀。
周作人在《歐洲文學史》中寫道:“希臘古代文學最早者為宗教頌歌,今已不存。”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于1918年出版,迄今已逾百年。百年來有關希臘古代宗教頌歌的材料已有零星出現(xiàn),并非完全不存。不過,正因為這種宗教頌歌不復存在或難以尋覓,因此我們便以為希臘神話的最重要特征是“神人同形同性”。其實,所謂“神人同形同性”只能概括以荷馬為代表的世俗文學,真正的宗教文學恐怕并非如此。在以荷馬為代表的世俗文學存在之前,極有可能還存在著一種宗教文學,譬如俄爾甫斯和他的親屬繆薩埃阿斯創(chuàng)作的文學,據(jù)說古代許多宗教詩都是他們創(chuàng)作的。俄爾甫斯與神秘宗教及其儀式有著十分密切的聯(lián)系。
劉小楓在《俄耳甫斯教輯語》一書前言中寫道:“在古希臘的經(jīng)典作品中,我們的確經(jīng)常見到這個詩人的名,據(jù)說,他輩分比荷馬還高。可是,俄耳甫斯基本上沒有完整詩篇傳下來,如今能見到的,大多是古希臘經(jīng)典作家的文字中說到他的地方,而且都是一些片段而已。20世紀初,德國的古典語文學家Otto Kern將古希臘作品中所有提到俄耳甫斯的地方輯出來,編成‘俄耳甫斯輯語’,仍然見不到什么完整的詩章。從而,俄耳甫斯其人始終不過是西方詩人最為古老的魂影,令后世詩人不斷追憶的亡靈——如詩人里爾克在《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詩》中所唱的。品達的詩句‘這人是一個魂影之夢’雖未必說的一定就是俄耳甫斯,用在這位歷史面目如此模糊的詩人身上卻也實在恰如其分。很可能與這位俄耳甫斯相關,古希臘還盛行一種所謂‘俄耳甫斯教’,詩人俄耳甫斯在這個以秘儀為主要特征的宗教中身為神主,據(jù)說在古希臘影響最為廣泛,其重要意義越來越受當今學人重視——所謂‘俄耳甫斯教禱歌’就是這一宗教傳統(tǒng)的見證(今據(jù)古典語文學家考訂,共存87首,中譯見《俄耳甫斯教禱歌》,吳雅凌編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這就意味著,真正作為希臘文學源頭的宗教文學我們已經(jīng)不可知,而我們現(xiàn)在所知道的以荷馬史詩為代表的世俗文學已經(jīng)不是真正的西方文學源頭。這便等于推翻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汾河源頭說,另出新說:“其實汾河真正的源頭還應從正源雷鳴寺泉向北向西上溯16公里,至岔山鄉(xiāng)宋家崖村之西北與五寨縣交界處。”汾河的源頭在別處,我們?nèi)匀恍枰硇锌碧健?/p>
如此看來,真正的西方文學源頭,由于沒有文字記載下來,現(xiàn)已大多散失,我們已不可知。我們已知的最早的荷馬史詩所記載的神話,經(jīng)過數(shù)百年的重復、編輯、改動,已經(jīng)不可能是真正的源頭了。而我們今天通過文字——不論是那種文字,閱讀或吟誦的荷馬史詩,也已經(jīng)不可能是當年荷馬吟唱的史詩了。即便我們盡可能地將荷馬史詩還原,我們也不可能擁有荷馬時代的聽眾,況且,物是人非,時過境遷,吟唱荷馬史詩的自然環(huán)境和歷史情境早已不復存在了。沒有了古代的聽眾,荷馬史詩還是荷馬所講述的那個故事嗎?當代著名學者伊迪絲·漢密爾頓在《希臘精神》一書中指出:“希臘文學和希臘雕塑一樣都不尚雕琢,行文素樸、率直,實話實說。如果直譯的話,譯文往往顯得非常直白干癟……但如果我們不能欣賞直接的譯文,我們就永遠不可能知道希臘人的作品是什么樣子的,因為希臘語和英語非常不一樣,希臘語一旦譯成了英語,原文的風格就喪失殆盡了。”希臘語與英語如此不同,以至于任何翻譯都不可能獲得成功。如此一來,英語與中文又如此不同,希臘語與中文反倒可能有更多的相近或相通之處,希臘語一旦譯成中文,其原文的風格或者比英譯本保留更多?這倒是別有意味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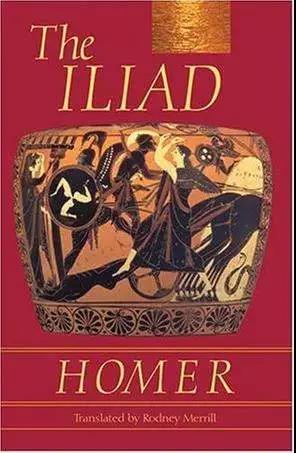
《伊利亞特》英文版書影
的確,我們渴望到源頭去飲水,我們相信“唯有源頭活水來”,但是,真正的源頭卻并不易發(fā)現(xiàn),或者永遠不可能被發(fā)現(xiàn)。歐洲文學的源頭在哪里?有沒有可稱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第一部作品——它孕育、培養(yǎng)或啟發(fā)了往后的所有作品?正如是否存在作為源頭的第一滴水,或者說是否有作為“零時”的時間的起點。文學的淵源較之國家、民族、文字的淵源似乎更為幽深錯綜、撲朔難辨,“沿波討源”,真“幽”則未必“顯”,無論我們多么努力,我們所飲之水,只不過是稍稍地接近了源頭而已。德裔美籍思想家漢娜·阿倫特認為,從詩歌的角度,我們不如說,歷史就是從俄底修斯在法雅西亞國王的宮廷里,傾聽他自己的事跡與他遭受的苦難的那一刻開始的。的確,許多人認為,荷馬就像《奧德賽》中的那位盲人歌人得摩多科斯(Demodocus)。“游蕩在古代希臘各地的人民歌手行吟詩人的詩歌一代代流傳下來。這些說唱者走進人們家里,用三角豎琴(cithara)伴奏,歌頌英雄們的功績,歌頌庇護他們的神以及很久前發(fā)生在他們故鄉(xiāng)的各種事情。”荷馬就是這樣一個盲人歌手行吟詩人。史詩《奧德賽》第八卷,俄底修斯漂落到法雅西亞國王阿爾基諾斯(Alcinoos)居住的海島。國王的女兒瑙西卡(Nausicaa)在海邊洗衣服時發(fā)現(xiàn)了他,并把他帶到王宮。國王設宴招待他,席間請來了這位盲人歌手:
你們再把神妙的歌人
得摩多科斯請來,神明賦予他用歌聲
娛悅?cè)说谋绢I,唱出心中的一切啟示……
傳令官回來,帶來了敬愛的歌人,
繆斯寵愛他,給他幸福,也給他不幸,
奪去了他的視力,卻讓他甜美地歌唱。
得摩多科斯歌唱特洛伊戰(zhàn)爭的故事和俄底修斯的英雄事跡,俄底修斯聽后不禁淚流滿面。當俄底修斯的生活故事變成了他自身之外的東西,成為了所有人看與聽的“對象”時,歷史也就從這里開始了。因為俄底修斯的故事是以詩歌的形式講述的,因此它就是詩歌的開始,即詩之源。于是,西方歷史從這里開始,西方文學從這里發(fā)源。如此看來,我們或許可以說,俄底修斯在法雅西亞王宮里傾聽說唱藝人得摩多科斯講述自己的故事大概便是西方文學的源頭了。至于說到汾河水的源頭,“站在那高處,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嘩啦啦地流過我的小村旁”。盡管有關汾河的源頭眾說紛紜,但我們還是寧愿相信它的源頭就在“寧武縣東寨鎮(zhèn)管涔山脈樓子山下水母洞”,因為這里包含的文化底蘊深厚:既有史書記載,又有民間傳說,還有神話故事。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