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福德談翻譯與“奇趣漢學(xu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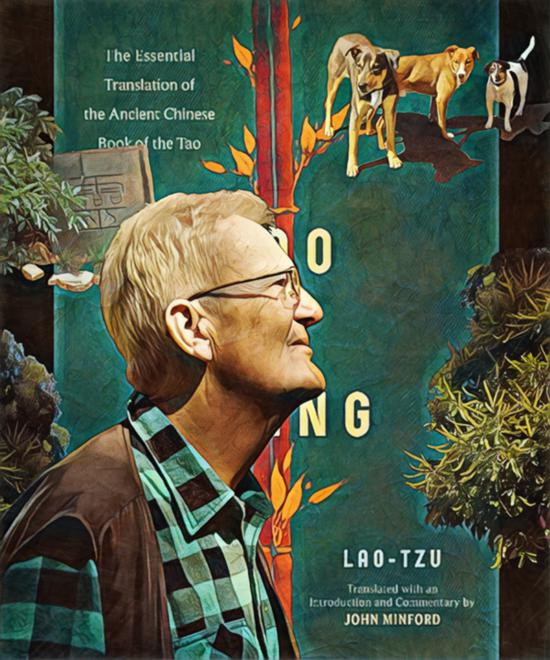
閔福德(澎湃新聞 蔣立冬 繪)
閔福德(John Minford),生于1946年,英國(guó)漢學(xué)家、文學(xué)翻譯家。曾于中國(guó)內(nèi)地、中國(guó)香港、澳大利亞及新西蘭任教,并將包括《紅樓夢(mèng)》《聊齋志異》《孫子兵法》《鹿鼎記》《易經(jīng)》在內(nèi)的多部中國(guó)文學(xué)經(jīng)典翻譯成英文。其岳父霍克思(David Hawkes)同為著名漢學(xué)家、翻譯家,二人合譯的《紅樓夢(mèng)》,前八十回由霍克思負(fù)責(zé),后四十回出自閔福德手筆。
去年,閔福德出版了最新譯作《道德經(jīng)》。《上海書評(píng)》今年7月在他位于法國(guó)南部的山莊采訪了他,請(qǐng)他談?wù)剮资陙淼姆g心得,以及“奇趣漢學(xué)”的理念。
去年12月,維京企鵝出版社出版了您翻譯的《道德經(jīng)》。您是如何與《道德經(jīng)》結(jié)緣的呢?
閔福德:我和《道德經(jīng)》的緣分從學(xué)生時(shí)期就開始了。我最早對(duì)道家思想的了解來自英國(guó)哲學(xué)家艾倫·沃茨(Alan Watts)的著作,從那時(shí)起我就成為了老莊之道的追隨者。六十年代牛津大學(xué)的中文課程還是以四書五經(jīng)為基礎(chǔ)的。我先跟隨雷蒙德·道森(Raymond Dawson)教授讀了《孟子》和《春秋左氏傳》,然后就選擇了《道德經(jīng)》和《莊子》這兩本書作為我的專修科目。《道德經(jīng)》也就從此一直伴隨在我身旁,但我從未想過要翻譯它。1998年我忽然收到維京企鵝(Viking-Penguin)紐約總編輯發(fā)來的邀請(qǐng),說希望我能新譯一版《孫子兵法》(于2002年出版)。之后他們又委托我翻譯了《易經(jīng)》(2014年出版) 以及《道德經(jīng)》。這三本書都是由美國(guó)的維京企鵝發(fā)行的。我和英國(guó)的企鵝出版社的合作可以追溯回1970年我和我的老師霍克思開始翻譯《紅樓夢(mèng)》的時(shí)候。從那時(shí)起,我便有幸能持續(xù)地與企鵝出版社合作,我的《聊齋志異》也于2006年由企鵝出版社出版。特別提一點(diǎn),《紅樓夢(mèng)》和《聊齋志異》都系屬“企鵝古典叢刊”(Penguin Classics)。這個(gè)系列自E. V. 里烏(E. V. Rieu)于1946年創(chuàng)辦以來,便竭力用流暢易讀的形式將世界古典名著呈現(xiàn)給英語讀者,強(qiáng)調(diào)在扎實(shí)的學(xué)術(shù)根基上,譯作的文學(xué)性和藝術(shù)性。這與我的翻譯理念恰巧相合。
您在《道德經(jīng)》的序文中提出了“靈讀” 的讀法,能稍作解釋嗎?
閔福德:“靈讀”(Lectio Divina)在拉丁文中的原意為“神圣的閱讀”。這是西方教會(huì)里一種古老的讀經(jīng)和禱告的方式,是一種緩慢的、冥想式的誦讀。我對(duì)“信達(dá)雅”中“達(dá)”有兩個(gè)層面的理解,首先你必須要“達(dá)到”,然后還需要“表達(dá)”。這是一個(gè)漫長(zhǎng)的過程。我花了好幾年為翻譯《道德經(jīng)》做準(zhǔn)備,包括收集不同的版本、注本,研究書中的詞匯和語言,閱讀古今中外學(xué)者們的研究等等。2016年,我旅居于羅馬的圣安瑟倫修道院 (Sant'Anselmo all'Aventino),在那里,我體驗(yàn)了幾天的隱修生活。這是一所本篤會(huì)(Order of Saint Benedict)的修道院和學(xué)院,每天清晨我步入教堂,和修道士們站在一起,聽他們吟唱從八世紀(jì)流傳至今的圣歌。與我同行的好友也是一名本篤會(huì)的修道士,他向我描述了他們每日需要進(jìn)行的“靈讀” 操練——分成誦讀(lectio)、默想(meditatio)、禱告(oratio)、靜觀(contemplatio)四個(gè)階段,通過反復(fù)誦讀《圣經(jīng)》中的某段文字,繼而進(jìn)入默想,對(duì)所讀的內(nèi)容進(jìn)行反思和發(fā)想,再以禱告的方式作為響應(yīng)。最后再靜靜地審查內(nèi)心的轉(zhuǎn)變,感受天人合一的樂趣。我忽然意識(shí)到這是我翻譯《道德經(jīng)》需要達(dá)到的境界。因?yàn)槲蚁嘈拧兜赖陆?jīng)》的雛形正是來自那些由道士們反復(fù)吟誦、默想,從而悟道的經(jīng)文。我便將此稱為L(zhǎng)ectio Sinica(中國(guó)式靈讀)。
當(dāng)我意識(shí)到了這點(diǎn),當(dāng)我聆聽到了《道德經(jīng)》的 “聲音”之后,一切就“靈”了。接下來我還需要在“表達(dá)”上下工夫,這又花去了兩年的時(shí)間。不管是翻譯也好,還是做其他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耐心,一定要給自己足夠的時(shí)間。現(xiàn)在的人總是太過急躁,你必須要等種子在地下生根發(fā)芽,它才能長(zhǎng)大,這都需要時(shí)間。我與霍克思先生合譯《紅樓夢(mèng)》一共花了十六年,這期間我們沒有申請(qǐng)任何一個(gè)項(xiàng)目或基金,完全是憑我們對(duì)這本書的喜愛堅(jiān)持下來的。我總是強(qiáng)調(diào)“情”的重要性,我覺得作為一名譯者如果你不熱愛你翻譯的東西,讀者很快能感受出來的。當(dāng)我在翻譯的時(shí)候,我總是將自我放下,用心去感受書中一切情感,再想辦法將我感受到的用另一種語言表達(dá)出來。我想,這是我和很多譯者最大的不同,我總是讓我的情感來引導(dǎo)我的翻譯。《道德經(jīng)》的有聲書是由美國(guó)演員愛德華多·巴萊里尼(Edoardo Ballerini)朗讀的,他曾寫信向我詢問過注意事項(xiàng),我回信和他解釋了“靈讀”這一概念。后來,我聽了他的朗誦,從中我可以感受到他傳遞出來的感情,這點(diǎn)我非常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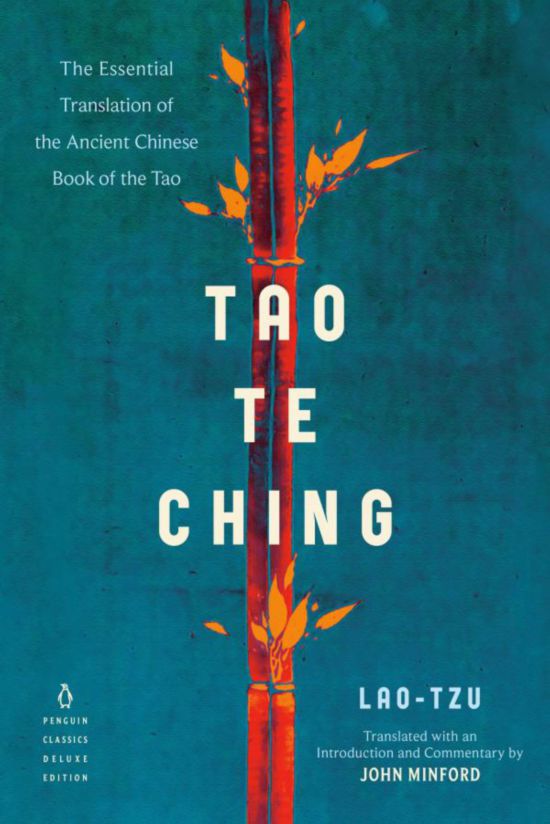
閔福德譯《道德經(jīng)》
您在您的《道德經(jīng)》譯本的每個(gè)章節(jié)后面都附上了一首中國(guó)詩,這點(diǎn)和其它的譯本很不同。您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
閔福德:這只是我當(dāng)時(shí)的一個(gè)想法,《道德經(jīng)》是一本只有五千字的書,而道家思想?yún)s與中華文化密不可分,所以我想用一種方式讓西方讀者更進(jìn)一步地了解這個(gè)博大而悠久的傳統(tǒng),不管是通過音樂、美術(shù)還是詩詞。再說,中國(guó)最好的詩人幾乎都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響,好像這是成為詩人必備的條件一樣。我收錄了好幾首謝靈運(yùn)的詩,他受了佛教和道教的影響,在詩中常以登山作為尋道的一種象征。就好像對(duì)李白來說,飲酒就代表了他對(duì)道的追求。我選擇加入詩也和排版有關(guān)。我花了很多時(shí)間來思考《道德經(jīng)》的排版。我請(qǐng)臺(tái)灣的朋友廖新田教授幫我寫了很多漂亮的篆書,放在每個(gè)章節(jié)的前面。譬如第六章我用了“谷神不死”這四個(gè)字,讀者首先看到的不是我的翻譯,而是這種古老的字體。這和《道德經(jīng)》一樣,有一種永恒的感覺。接下來才是我的翻譯及一些注語。可是到最后,我總覺得還少了些什么。那些批注《道德經(jīng)》的人個(gè)個(gè)都能長(zhǎng)篇大論,說得神乎玄乎,我覺得結(jié)尾還是需要一個(gè)簡(jiǎn)短的、實(shí)在的東西。所以我選了一些我喜歡的詩,不管是李白還是寒山,可以說這本書也是一本充滿道家思想的詩歌選集。我在書的最后面放入了一個(gè)“悟道集”(Florilegium)來代替?zhèn)鹘y(tǒng)的索引或者詞匯表。我還因此和出版社交涉了很久,他們不喜歡這個(gè)主意。我的目的是在最后用二十多頁歸納整理書中的主要意象,因?yàn)椤兜赖陆?jīng)》是一部混亂的、毫無秩序的書,我希望在最后能留給讀者們一些明確的、總結(jié)性的東西。很少有譯者會(huì)談排版的問題,可這很重要。中國(guó)所有的古典文獻(xiàn)都沒有標(biāo)點(diǎn),也沒有分段。當(dāng)你在翻譯這些典籍的時(shí)候,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排版。這個(gè)過程可以很有趣。我也非常感謝我的出版社,我和他們合作了二十年,知道他們是對(duì)細(xì)節(jié)十分有要求,在排版、字體、封面設(shè)計(jì)上都很講究,也肯花時(shí)間。他們用了將近一年才將此書出版。
您覺得《道德經(jīng)》以及其它的傳統(tǒng)典籍對(duì)新一代的中國(guó)讀者還有任何吸引力嗎?
閔福德:年輕一代的中國(guó)讀者或許喪失了閱讀《道德經(jīng)》原文的能力,但是我相信他們?cè)谧非笪镔|(zhì)條件外,依然保有內(nèi)在的、心靈上的追求。就我接觸到的年輕學(xué)生來說,他們不僅對(duì)傳統(tǒng)文化和思想充滿興趣,甚至有些如饑似渴。我想任何體制或者教育都無法改變我們作為人對(duì)更高的精神層面的追求,就這點(diǎn)而言,中國(guó)和西方國(guó)家都是一樣的。
您覺得一個(gè)好的譯者或一部好的翻譯需要具備什么樣的特質(zhì)?
閔福德:我覺得“靈”就是一個(gè)很好的象征。這個(gè)字的意象很古老,“雨”字底下三個(gè)“口”,然后是一個(gè)“巫”字。這代表遠(yuǎn)古時(shí)代巫師與天地萬物溝通的神秘力量。其實(shí)翻譯與通靈十分相似,我妹妹就是一個(gè)靈媒,一旦她“出神”,便可以與靈魂溝通。同樣,譯者也需要聆聽來自另一個(gè)世界的聲音。翻譯是一個(gè)很奇怪的過程,你往往在召喚一個(gè)死去已久的、來自異國(guó)他鄉(xiāng)的靈魂。身為譯者,我們要想盡辦法與這個(gè)靈魂溝通,聽到他的聲音。“靈” 在吳語和一些其它方言中依然屬于日常用語,一個(gè)電燈泡如果能用,那么就 “靈”了。到最后,一個(gè)翻譯好不好,其實(shí)就看它靈不靈,有沒有感情。這和翻譯理論一點(diǎn)關(guān)系也沒有。
作為《紅樓夢(mèng)》后四十回的譯者,您如何看待高鶚的續(xù)書?
閔福德:這個(gè)問題我在我的博士論文中反復(fù)申訴過(當(dāng)時(shí)我答辯的主考官是紅學(xué)家吳世昌,副考官是楊憲益——另一位《紅樓夢(mèng)》的英譯者),我深信高鶚是一名認(rèn)真負(fù)責(zé)的編輯。是他將曹雪芹殘損的手稿修補(bǔ)成輯,使得《紅樓夢(mèng)》可以完整地流傳。《紅樓夢(mèng)》中許多動(dòng)人心弦的情節(jié)也都出自后四十回,這里林語堂、夏志清、余國(guó)藩、白先勇都曾撰文討論過。我的老師霍克思在他的《紅樓夢(mèng)翻譯筆記》中也曾經(jīng)好幾次對(duì)高鶚的修改表示贊賞。我想高鶚身為漢軍旗人能比一般人更加了解曹雪芹筆下所描繪的清代特有的旗人貴族世界。
您從事翻譯工作已將近半個(gè)世紀(jì),除了上述提到的先秦哲學(xué)經(jīng)典和明清小說以外,您也翻譯了許多現(xiàn)代的作品,譬如金庸的《鹿鼎記》、八十年代的朦朧詩歌,以及香港詩人也斯的作品等等。您是如何將這樣不同的語言與風(fēng)格翻譯出來的呢?
閔福德:這些年來我確實(shí)翻譯了許多不同歷史時(shí)期、風(fēng)格題材迥異的文學(xué)作品。身為譯者,我總是喜歡接受新的挑戰(zhàn)。多數(shù)時(shí)候,這些挑戰(zhàn)帶給了我不一樣的視角,也提升了我翻譯的功底。我相信做任何工作都需要有勇于嘗試、不斷探索的精神。我發(fā)表的第一篇譯作是四川大學(xué)繆鉞教授的《論詞》,那是1979年我還在讀博士的時(shí)候。當(dāng)時(shí)身在香港的翻譯家、文學(xué)評(píng)論家宋淇先生寫信給我的指導(dǎo)老師、在澳大利亞國(guó)立大學(xué)任教的柳存仁教授,問他有沒有適當(dāng)?shù)娜诉x。他們兩個(gè)是老朋友,柳存仁教授向他推薦了我。我那時(shí)對(duì)詞的了解并不深,好在有柳教授的細(xì)心指導(dǎo),我花了將近一年來學(xué)習(xí)、品味詞的境界。正因如此,詞在接下來的四十年里帶給了我無限的樂趣。也因?yàn)槲业倪@篇翻譯,在2000年我收到了宋緒康先生的邀請(qǐng),希望我將他父親宋訓(xùn)倫(宋訓(xùn)倫與國(guó)畫大師張大千、溥心畬,篆刻家吳昌碩等人均為好友)的詞翻譯成英文。我因此和宋緒康先生成為了摯友。這都是文字因緣。
八十年代初,我在天津教書,在朋友龐秉鈞教授的推薦下讀了一些二十世紀(jì)初的新詩,于是我對(duì)現(xiàn)代詩發(fā)生了興趣。后來朦朧詩人興起,有的詩人也成了我的朋友,他們獨(dú)特的語言風(fēng)格對(duì)于我來說無疑是一種新的挑戰(zhàn)。1982年我在宋淇的邀請(qǐng)下前往香港中文大學(xué)擔(dān)任翻譯期刊《譯叢》的編輯。在這期間,我和宋淇合編了《山上有木》(Trees on the Mountain:An Anthology of New Chinese Writing),里面首次收錄了來自兩岸三地的新詩、散文、小說以及戲劇的翻譯,為的是向西方讀者展示中國(guó)新文學(xué)的多樣性。我們的楔子是仿照《紅樓夢(mèng)》開頭而寫成的,宋淇更是效仿脂硯齋在里面加入了批注。后來,在這本書的基礎(chǔ)上,我和我的好友白杰明(Geremie Barmé)又于1987年推出了《火種》(Seeds of Fire: Chinese Voices of Conscience),收錄了當(dāng)時(shí)最新銳、最具爭(zhēng)議性的詩人、作家、編劇及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這本書的靈感來自魯迅的“石在,火種是不會(huì)絕的”,這句話放到現(xiàn)在依然適宜。我和白杰明的合作與友誼也一直持續(xù)至今,2017年我們?cè)谛挛魈m共同創(chuàng)辦了一所名為“白水書院”的私人學(xué)院。
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里,我和香港詩人也斯從相識(shí)逐漸成為知己。我翻譯了很多他的小說和詩歌,有時(shí)候他讀完我的英文翻譯又對(duì)自己的詩有了新的想法,回頭重新修改。我從這樣的合作中品嘗到了創(chuàng)作的樂趣。同時(shí)期,我在宋淇的介紹下認(rèn)識(shí)了香港女作家西西,我又和同事朋友們一起將《像我這樣的一個(gè)女子》翻譯成英文。也斯不僅帶我走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更向我展示了香港文學(xué)獨(dú)特的一面。我因此在2012得到香港藝術(shù)發(fā)展局的資助,擔(dān)任“香港文學(xué)與翻譯”系列圖書的總編輯。這個(gè)系列即將在明年陸續(xù)出版,包括也斯、劉以鬯、西西、鐘玲、李歐梵五位作家的作品的選譯本,和一部四五十年代的作品集。
您的中文名字還是宋淇取的,能談?wù)勀銈冎g的友誼嗎?
閔福德:我將我翻譯的《詞論》寄給宋淇后不久便收到了他的來信。在通信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他是少有的誠(chéng)心喜歡與作家和譯者們交換意見的編輯。我也從中感受到了他對(duì)文學(xué)和翻譯的癡迷,為了將中國(guó)文學(xué)以最完美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他可以不惜一切。當(dāng)我偶爾有不同看法的時(shí)候,他也十分尊重我的意愿。我第一次見到宋淇本人是1980年的8月,我經(jīng)由香港前往天津任教的時(shí)候。我們可以說是一見如故,因?yàn)槲覀兌挤浅O矏邸都t樓夢(mèng)》。我剛到天津的那會(huì),物資還十分貧乏,宋淇經(jīng)常寄東西給我,我就是在他寄給我的好利獲得(Olivetti)打字機(jī)上完成了一部分《紅樓夢(mèng)》的翻譯。1982年他邀請(qǐng)我前往香港與他一起共事。在接下來的四年多,我們幾乎每天都會(huì)碰面,我從他身上學(xué)到了太多的東西。他從未在大學(xué)里任教,不是狹義上的學(xué)者,相反,他是二十世紀(jì)初文人的典范,不僅擁有扎實(shí)的國(guó)學(xué)基礎(chǔ),又精通西方語言和文化。這和他的家學(xué)也有關(guān),他的父親宋春舫是王國(guó)維的表弟,早年曾留學(xué)瑞士,以戲劇研究和藏書聞名。
宋淇一生最熱愛的三樣?xùn)|西就是翻譯、《紅樓夢(mèng)》和詞。他不僅是一個(gè)很好的翻譯家,也可以算是研究《紅樓夢(mèng)》英譯的第一個(gè)人。他在《紅樓夢(mèng)西游記》里展現(xiàn)出作為文學(xué)評(píng)論者的敏銳和作為譯者對(duì)中西文化的熟諳,可謂是翻譯批評(píng)的上乘之作。宋淇也曾經(jīng)擔(dān)任過編劇,在香港影劇圈十分活躍。記得有一次我在深夜致電向他請(qǐng)教《紅樓夢(mèng)》第九十一回末寶玉與黛玉那段令人費(fèi)解的禪語。他后來回電向我詳細(xì)說明了一番。但是第二天一早,他又在辦公室里把這段對(duì)話從頭到尾演了出來,從房間的一端踱步到另一端,不停地重復(fù)那幾句禪語,直到他覺得他把作者的意思全部都表達(dá)了出來為止。后來我再見到他的妻子鄺文美女士的時(shí)候,她告訴我說宋淇那晚幾乎徹夜未眠,一直在他的書房里面喃喃自語,想象著書中人物的動(dòng)作神情和作者的用意。這就是嚴(yán)復(fù)所謂“達(dá)”的最高境界吧。宋淇在《譯叢》主編的最后一本書就是有關(guān)古典詩詞的。書的中文名稱我們決定叫做“知音集”,英文名則是A Brotherhood in Song,出自英國(guó)詩人濟(jì)慈的寫給朋友的信:
詩詞固然美妙
然而分享使其美妙加倍
Sweet are the pleasures that to verse belong,
And doubly sweet a brotherhood in song.
我想宋淇這一生就在與中外讀者分享他讀書的樂趣吧。
您提到您從澳大利亞國(guó)立大學(xué)退休后,與漢學(xué)家白杰明先生在新西蘭創(chuàng)辦了“白水書院”。在書院的網(wǎng)站上,您提出了“奇趣漢學(xué)”的說法,能談?wù)剢幔?/span>
閔福德:“奇趣漢學(xué)”(Nouvelle Chinoiserie)這個(gè)中文名稱是由我的好友白杰明翻譯的,取自圓明園中的“諧奇趣”。當(dāng)時(shí)我正好讀到十八世紀(jì)英國(guó)的一個(gè)叫做“慕雅會(huì)”(Society of Dilettanti)的團(tuán)體,里面的成員大多都是貴族,他們對(duì)歐洲大陸的藝術(shù)、建筑、歷史很感興趣,經(jīng)常組織去歐洲的考古活動(dòng),回來后與成員分享他們的收獲與樂趣。他們的座右銘是Seria Ludo,意思是 “游戲地學(xué)術(shù)”。這也是奇趣漢學(xué)的座右銘,更是我一生追求,那就是把中國(guó)文學(xué)的樂趣分享給西方的讀者。我也因此遭到抨擊,甚至有學(xué)者說我翻譯的《聊齋志異》是“西方消費(fèi)主義”。可是我為什么不能讓我的書讀來是有意思呢?蒲松齡、曹雪芹他們不都是風(fēng)雅游戲,悅己娛人嗎?奇趣漢學(xué)可以被看作是對(duì)當(dāng)前學(xué)界主流思潮的一種反抗,它很容易被貼上 “消費(fèi)主義”“東方主義”“殖民主義”的標(biāo)簽,但我不在乎。因?yàn)橘N標(biāo)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連“Chinoiserie”(中國(guó)風(fēng))現(xiàn)在也被看作是一個(gè)負(fù)面的詞,說它視中國(guó)為“玩物”,這是誤解。我曾經(jīng)撰文為“東方主義”辯護(hù),因?yàn)楸慌険魹椤皷|方主義”的學(xué)者都是些真正熱愛他們所研究的文化的人。亞瑟·韋利(Arthur Waley,1898-1966)就是一個(gè)典型。你看他翻譯的《西游記》,選的都是他覺得有趣的部分,題目也索性換成“Monkey”(美猴王)。還有他有關(guān)白居易和袁枚的書,全部都是因?yàn)樗蕾p這兩個(gè)人的個(gè)性為人。他的翻譯不僅詼諧幽默,更是充滿了人性。奇趣漢學(xué)的出發(fā)點(diǎn)就是以人為本,提倡人的文學(xué),反對(duì)將文學(xué)和藝術(shù)當(dāng)作說教或是宣傳的工具。
白水書院的辦學(xué)理念是什么?
閔福德:去年我們的白水書院舉辦了一場(chǎng)由二十多位中外學(xué)者參加的“雅集”。我們刻意打破學(xué)術(shù)會(huì)議的規(guī)范和流程,效仿魏晉時(shí)期的蘭亭雅集還有竹林七賢,在會(huì)議當(dāng)中融入了音樂、戲曲和藝術(shù)鑒賞等項(xiàng)目,更有美食和美酒助興。當(dāng)中的亮點(diǎn)來自我的朋友、收藏家宋緒康先生帶來的一系列的名人字畫和手跡。宋先生不僅給我們講解了這些字畫背后的文化底蘊(yùn),更向我們展示了他自身作為一名鑒賞家的修養(yǎng)。“藝術(shù)的修養(yǎng)”就是雅集的主旨之一。此外,我們還有幸邀請(qǐng)到了由鄧宛霞女士所指導(dǎo)的香港京昆戲劇團(tuán)為我們表演。其中很令我難忘的一幕就是排練的過程中,兩個(gè)年青年的花旦跟著年邁的老師練唱,老師唱一句學(xué)生學(xué)一句。這是口傳最好的例子,也是中國(guó)藝術(shù)能夠一代一代地傳承下來的原因。幸好這一切都有錄像記錄。雅集的另外一個(gè)主旨就是“文化的傳承”。我們的參與者是一些二三十歲的年輕學(xué)者和能夠“從心所欲”的老一輩的學(xué)者,可以說是“群賢畢至,少長(zhǎng)咸集”。這樣年輕人能有機(jī)會(huì)跟老一輩的學(xué)者交流,老一輩的學(xué)者也很樂意與年輕人分享他們的心得。我們注重的就是這種自我的修養(yǎng)以及文化的傳承,這是做任何有關(guān)中國(guó)的研究都不可或缺的。我不明白現(xiàn)在的學(xué)者怎么能只專注于研究廣東小工廠的就業(yè)率或是西北農(nóng)村婦女的權(quán)益之類問題,當(dāng)然不是說這些不重要,而是說作為一名學(xué)者你必須從更高、更長(zhǎng)遠(yuǎn)的視角來看待事情,你需要了解中國(guó)的文化、歷史、文學(xué)、美術(shù)還有音樂。畢竟這些才是真正流傳下來的東西啊。我們現(xiàn)在對(duì)宋朝的煤產(chǎn)量知道多少?但是我們都知道宋朝的詩詞、話本小說,還有書法和繪畫。這就是我們舉辦雅集的原因,也是白水書院的辦學(xué)理念。我們將學(xué)術(shù)、文學(xué)和翻譯視作人文教育的一部分,秉持四海之內(nèi)“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精神。
您繼續(xù)談?wù)劇翱趥鳌边@個(gè)概念嗎?翻譯也可以“口傳”嗎?
閔福德:我年輕的時(shí)候花了很多年學(xué)習(xí)鋼琴,你可以從書中閱讀大量有關(guān)鋼琴的技法,但這些都比不上坐在一名真正的鋼琴大師旁邊,觀察他的指法,聆聽他的演奏。當(dāng)我翻譯《紅樓夢(mèng)》的時(shí)候,我每周都會(huì)去見我的老師霍克思先生。我們總會(huì)在他的書房里談上兩三個(gè)小時(shí)。在這過程中,我學(xué)習(xí)到的總是比我們談?wù)摰膬?nèi)容多得多。有的時(shí)候這不僅僅是口頭上的傳授,更是一種身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問我:“你知道我們?yōu)槭裁匆g《紅樓夢(mèng)》嗎?”我說:“我不知道。”他回答道:“因?yàn)槲覀兙褪歉吲d。”(We’re just doing it for the hell of it.)這就如同禪宗里禪師和學(xué)生之間的關(guān)系,很多時(shí)候禪師是通過棒喝的形式來幫助學(xué)生覺悟。口傳在中國(guó)的傳統(tǒng)教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也是為什么人們會(huì)問你的老師是誰而不是你的學(xué)校,就要看你繼承了哪一個(gè)學(xué)派。這種傳承也不僅局限于中國(guó),這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基本方式,是一種化學(xué)反應(yīng),就像戀愛一樣。有的時(shí)候?qū)Ψ街恍枰f上幾句話就能觸動(dòng)你內(nèi)心深處的情緒,這種感覺非常奇妙。這也是我為什么這么反對(duì)翻譯理論,理論家們總有大量東西可以說,但他們都只是自顧自說,他們是典型的有口無傳。
最后非常榮幸可以來到您在法國(guó)南部的山莊。這間坐落在山谷里葡萄園內(nèi)的石屋充滿了有趣的東方元素:從大門口的兩座石獅,到院子里噴泉內(nèi)打著太極拳的小人兒。這座房子是否也是奇趣漢學(xué)的一種延伸呢?
閔福德:我和我的夫人雷切爾(Rachel,霍克思的長(zhǎng)女)于1995年買下了這座房子,算起來也快二十五年了。里面很多的家具和裝飾是我們?cè)谔旖蚝拖愀劬幼〉臅r(shí)候購(gòu)得的,包括門口的石獅還有瓷墩,所以這里的裝飾是自然形成的,并非刻意為之。同時(shí)我們也在房子里也加入了西方的元素,像門上掛著的羅馬神像等等。這片山谷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羅馬時(shí)代,公元一世紀(jì)就有退役的羅馬士兵在這里種葡萄、釀葡萄酒。這座房子也許可以代表我這一輩子的追求吧,那就是將中西文化打通,并且將中國(guó)文學(xué)以有趣的方式呈現(xiàn)給西方讀者。奇趣漢學(xué)強(qiáng)調(diào)趣味性,同樣地,這座房子是用來休閑,用來招待朋友們的,這里有足夠的空間可以同時(shí)容納十幾個(gè)人呢!現(xiàn)在我在屋后的空地上修建了一座“中式園林”,叫做“思樸園”。里面有一個(gè)拱門,一張小板凳,還有一座小橋。另外還有一塊頑石,是前幾周從山上滾落下來的,真是渾然天成。橋底下沒有水,或者說有看不見的水,因?yàn)槲覀冎赖氐紫率怯猩饺摹_@個(gè)地方原本的名稱是“Fontmarty”,也就是“水源” 的意思。要是沒有水源,那就不會(huì)有這里的一切。此外,這所房子的一切都是依靠太陽能。也可以說,這是一個(gè)充滿道家意味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