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科學(xué)的罪與罰:《臨界》第一輯評(píng)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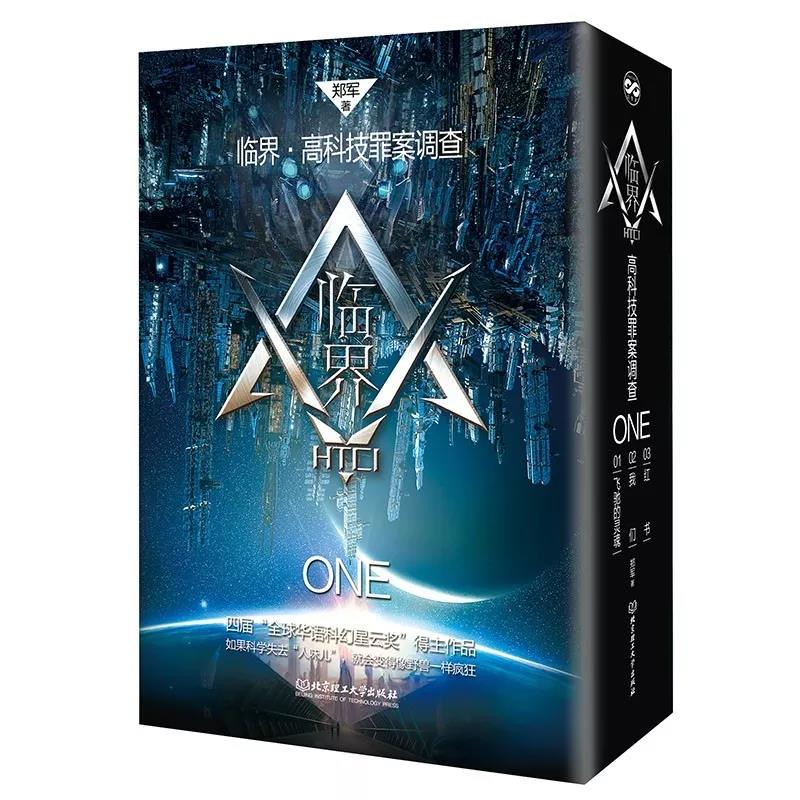
《臨界·高科技罪案調(diào)查》第一輯
作者:鄭軍
北京理工大學(xué)出版社
2019年1月
《臨界·高科技罪案調(diào)查》第一輯的三本書,將科幻與罪案這兩種類型密切結(jié)合,以故事為引領(lǐng),在情節(jié)、人物、場(chǎng)景等文學(xué)因素都下了較大功夫,既能引人入勝,也傳達(dá)了科學(xué)理念。
《臨界》第一輯所關(guān)注的科學(xué)技術(shù),都集中于人的內(nèi)心世界,諸如改造人類大腦而制造的超人,以及由心理因素而激發(fā)的人體超常能力,在當(dāng)下的科幻小說(shuō)中,的確是別具一格。
《飛馳的靈魂》
不少人莫名其妙失蹤了,他們都有一個(gè)共同特點(diǎn):吸毒,而且都是身無(wú)分文、被人厭棄的最低層吸毒者。這一組案件被警方定名為“旌旗嶺專案”。
自然,失蹤了卻又唯一被發(fā)現(xiàn)的幸存毒販,便成了警察重點(diǎn)關(guān)注的對(duì)象。不過(guò),在圍捕過(guò)程中,既販且吸,本該弱不禁風(fēng)的癮君子卻變得力大無(wú)窮、迅捷無(wú)比,徒手擊斃兩條兇猛的警犬,從容地從十?dāng)?shù)名警察的包圍網(wǎng)從容脫身……
《臨界》第一輯,貫穿始終的人物是女主角楊真。她作為一個(gè)實(shí)驗(yàn)心理學(xué)專業(yè)的大學(xué)生,畢業(yè)后加入高科技犯罪調(diào)查處。對(duì)于書中出現(xiàn)的一系列瘋狂的、違背人類倫理道德的高科技,她不僅是見(jiàn)證者,也是親歷者,甚至是受害者。
在第一本《飛馳的靈魂》中,反派李文濤是一個(gè)塑造得不錯(cuò)的角色。他是楊真的老師、曾經(jīng)的戀人,也是一名嚴(yán)謹(jǐn)?shù)膶?shí)驗(yàn)心理學(xué)專家。不過(guò),他最后卻成了一名突破倫理和法律底線,非法進(jìn)行人體實(shí)驗(yàn)的罪犯。
小說(shuō)用一種逆向法,將這個(gè)反派塑造得有血有肉。所謂逆向法,是指人物在出現(xiàn)開頭和結(jié)尾的巨大反差——舉個(gè)例,比如《三體》中的羅輯,在最初是個(gè)連一夜情人名字都不知道的浪子,而最后卻變成了一個(gè)對(duì)整個(gè)地球負(fù)責(zé)的人。用好萊塢的術(shù)語(yǔ)來(lái)說(shuō),便是完成了人物的“成長(zhǎng)弧”。當(dāng)然,正如有“負(fù)能量”一樣,劇中人“成長(zhǎng)”的方向也可以是負(fù)向的,本書中的李文濤即是如此。他最終的成長(zhǎng)值,前面得加上一個(gè)巨大的負(fù)號(hào)。
對(duì)于男主人公的成長(zhǎng)路徑,當(dāng)然需要作者下筆時(shí)就了然于胸,但是在寫作過(guò)程中,他卻必須巧妙地將路上的痕跡掩蓋起來(lái)——就像主人公在書中掩蓋自己的身份一樣——直到故事快結(jié)束的時(shí)候才揭開蓋子。男主人公最初的理性和最后的瘋狂,是一脈相承的,都源于對(duì)科學(xué)的熱愛(ài),和對(duì)人類好奇心的極致放縱。從寫作技術(shù)上來(lái)說(shuō),這是“意料之外”的“情理之中”。
《臨界》第一輯三本小說(shuō),都在探討科學(xué)技術(shù)與人倫的關(guān)系。而在《飛馳的靈魂》中,大量的討論是通過(guò)書中人之口來(lái)進(jìn)行的,比如反科學(xué)主義者與李文濤的相互駁詰。不是通過(guò)故事性的沖突,而是以對(duì)白來(lái)傳達(dá)理念,對(duì)本書來(lái)說(shuō)是主要失分之處。
《我們》
也是失蹤,但這一次不是吸毒者,而是可以提供巨大能量的原堆。然后,失蹤的是一些社會(huì)精英、各個(gè)行業(yè)最頂尖的專家……
現(xiàn)實(shí)世界中存在的學(xué)者、鏡象神經(jīng)元的發(fā)現(xiàn)者里佐拉蒂,在《臨界·我們》中擔(dān)當(dāng)了一個(gè)角色。這也是以鏡象神經(jīng)元為點(diǎn)子展開的一個(gè)故事——里佐拉蒂的兩名弟子、一對(duì)科學(xué)伉儷,主持了一項(xiàng)人腦實(shí)驗(yàn),通過(guò)手術(shù)將人的大腦并聯(lián)了起來(lái)……
第二冊(cè)《我們》,僅從名字,對(duì)科幻有一定了解的讀者都會(huì)知道,這個(gè)故事致敬的是反烏托邦小說(shuō)、扎米亞金的《我們》——一部關(guān)于集體與個(gè)體,共性與個(gè)性的小說(shuō)。
將人腦進(jìn)行并聯(lián),好處當(dāng)然是巨大的。進(jìn)入“人聯(lián)網(wǎng)”之后,每一個(gè)個(gè)體所擁有的知識(shí)和信息,可以立即為這個(gè)群體中的所有個(gè)體共享,甚至感情,甚至情緒。這樣的好處,帶來(lái)的是巨大的誘惑。因此書中的那些精英人物,進(jìn)去之后,不僅不想出來(lái),還拼命想把更多的人拉進(jìn)去。
然而,代價(jià)就是個(gè)性的抹殺。很難想象,不同的個(gè)體,在“我們”體內(nèi)如何讓個(gè)體的欲望與整體的目標(biāo)相洽?因此,“我”與“你”的邊界只能模糊、消失,不同的訴求只能放棄,只剩下唯一的利益目標(biāo)——“我們”。
1000個(gè)1相加,大于10億——這可能是“我們”設(shè)計(jì)者的初衷,但研究大眾心理的學(xué)者龐勒可能并不同意,他在著作《烏合之眾》中說(shuō),“群體的產(chǎn)品不管性質(zhì)如何,與孤立的個(gè)人產(chǎn)品相比,總是品質(zhì)低劣。”
人腦并聯(lián),帶來(lái)的一定是更高級(jí)的意識(shí)嗎?實(shí)未可知。而關(guān)于泯滅個(gè)性的危害,乃至罪惡,已有的反烏托邦小說(shuō)說(shuō)得太多。在扎米亞金的《我們》,以及奧威爾的《1984》里,集體主義的陰影無(wú)處不在,籠罩著人們的生活和心靈。而《臨界·我們》,更從技術(shù)的角度,描繪了“我們”建立、運(yùn)作和滅亡的細(xì)節(jié)。
集合了眾多精英的智力,“我們”便成了一個(gè)人擋殺人、佛擋殺佛的超級(jí)怪物。它的建立、運(yùn)作和滅亡的全過(guò)程,使故事變得十分驚悚刺激,具有一種“反烏托邦+好萊塢”的走向。
前面提到,在《飛馳的靈魂》中,反派李文濤這個(gè)人物其實(shí)是塑造得不錯(cuò)的。遺憾的是,他在第一本中已經(jīng)死了。《我們》中又要重新下功夫來(lái)塑造人物。相對(duì)于第一本,這本的人物形象要單薄一些,特別是一些正面的配角,來(lái)來(lái)往往,卻并不能讓人產(chǎn)生深刻的印象。之所以給了比上一本要高的分,是因?yàn)樗矣谔魬?zhàn)“反烏托邦”這種題材,并能將其“好萊塢化”。
《紅書》
印度,某警察分局,身體衰弱、行將就木的老年畫家突然發(fā)力,在3分鐘之內(nèi)擊倒分局內(nèi)的所有人,其中5人當(dāng)場(chǎng)死亡,7人重傷入院……
同《我們》借用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心理學(xué)家里佐拉蒂相似,《紅書》也借用了現(xiàn)實(shí)世界里的因素——心理學(xué)家榮格的心理學(xué)筆記“紅書”。
在小說(shuō)中,榮格“紅書”的筆記及圖畫具有通靈的魔力,可以通過(guò)心理活動(dòng)激發(fā)人的生理潛能。通靈畫家夏爾馬借助“紅書”,使他的畫具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并通過(guò)賣畫成為巨富。有一天,夏爾馬突然發(fā)狂,刺死自己的經(jīng)紀(jì)人,將其鮮血混合顏料,繪成了一幅能迷亂人心的畫作。
奇異的開頭,暗示了這本書的風(fēng)格。心理類的小說(shuō)對(duì)于讀者來(lái)說(shuō),往往具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但與此同時(shí),對(duì)寫作技術(shù)的要求也相當(dāng)高。
《紅書》在這方面做得不錯(cuò),因此,可以說(shuō)是一本接近神作的小說(shuō)。何謂“神作”?寫得好不是充分條件,甚至不是必要條件。關(guān)鍵是,要寫人之所未寫,言人之所未言。
這本小說(shuō)以“紅書”為意象,雜以神秘的宗教色彩、異域風(fēng)情,以及波瀾起伏、詭譎奇異的情節(jié),讓故事具有非同尋常震撼力。可以說(shuō),在科幻小說(shuō)中,很難找到同類型的作品。
作者簡(jiǎn)介
何大江,作家、新聞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