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諜戰(zhàn)特工跨界文學(xué)的作家,讓人生閃光的是想象力與觀察力
世界文學(xué)史里,有這樣一群有著各種奇怪職業(yè)打掩護的作家,他們曾親自扮演過這些角色,之后在寫作中游刃有余地構(gòu)建起具有說服力的人物形象,事實上,很大程度上他們就是在寫自己。
今天想介紹這樣幾個作家,擁有神秘職業(yè),被職業(yè)所眷顧或困擾,很難說這份職業(yè)決定了文學(xué)之路,但他們每當(dāng)坐在書桌前想寫點什么的時候,記憶角落里散發(fā)的光芒,總是令人難以抵擋,不費吹灰之力的素材,為什么要故意忽視呢?
記得電影《王牌特工》里,主角科林·費爾斯飾演的特工人員,給人最大的印象不是身懷絕技,會破譯奇怪密碼,而是,一柜子正裝。
是的,如紳士一般的著裝和舉止,成就了這個系列電影的典型特工形象,主角有個口頭禪,“manners maketh man”,這句話引用自牛津大學(xué)新學(xué)院的院訓(xùn),翻譯過來,我們的孔夫子也曾說過類似名言——
不知禮,無以立。
實際上,英國情報部門還真有這個習(xí)慣,在募集工作人員時,英國情報部門遵循的主要原則之一就是,“凡是紳士都是可以信賴的”。英國作家約翰·勒卡雷這樣評價自己曾供職過的情報部門,“你必須先引起別人注意,讓他們主動過來挑選你……想要被選上,那你得有天生的好運。你必須上好學(xué)校,最好是私立的,然后上大學(xué),最好是牛津劍橋。”
難道,注重自我形象、充滿想象力和觀察力的作家真的天生適合從事情報諜戰(zhàn)工作?約翰·勒卡雷、威廉·薩默塞特·毛姆、格雷厄姆·格林這些作家會給出什么樣的回答呢?
等等,大洋彼岸的作家塞林格也申請加入回答,他或許有著截然相反的感受。
約翰·勒卡雷:我遇到了比編輯更懂遣詞造句的上級
提到作家約翰·勒卡雷,許多諜戰(zhàn)小說愛好者會對他的作品以及影視改編了如指掌。
他18歲時就被英國軍方情報機構(gòu)招募,退役后在牛津大學(xué)攻讀現(xiàn)代語言,之后于伊頓公學(xué)教授法文與德文。1959年進入英國外交部,同時開始憑借寫作享譽文壇。這段經(jīng)歷的細節(jié)他一直嚴守秘密,直到許多年后的2016年,他出版了回憶錄性質(zhì)的作品《鴿子隧道》,詳細講述了情報工作與文學(xué)寫作之間的轉(zhuǎn)換。

年輕時的勒卡雷
那時候,他還不叫約翰·勒卡雷這個筆名,他的真名是大衛(wèi)·康威爾,父親是一個英國商人,他從小被送進伊頓公學(xué)求學(xué),那是英國著名的貴族學(xué)校,學(xué)費高昂,但他又常常為學(xué)費中斷而擔(dān)憂,因為父親的債務(wù)累積,他很快熟練掌握了各種躲避債主的招術(shù),這些經(jīng)歷使他成為了日后秘密情報機構(gòu)理想的招募對象。
他先后在軍情五處和六處工作,那段時間,他利用業(yè)余時間創(chuàng)作完成了自己的處女作《召喚死者》。由于軍方規(guī)定間諜不可以用真實姓名發(fā)表出版物,“約翰·勒卡雷”這個名字才得以閃亮登場。“我的名字,約翰·勒卡雷,以及我的小說人物喬治·史邁利于1958年同時誕生在我的第一部小說的第一頁上。”
1963年,約翰·勒卡雷用了6周時間,寫完了日后給他帶來名聲、財富以及麻煩的《柏林諜影》。付梓前,情報機構(gòu)領(lǐng)導(dǎo)審讀了全書,確保他寫出的是一個與現(xiàn)實情報世界無關(guān)的虛構(gòu)故事,才給這本書放行。
后來,勒卡雷特別提到情報工作的經(jīng)歷給予了自己的寫作最大的優(yōu)勢是接受上級的文辭教育,每當(dāng)他把報告交給總部頂樓那些受過古典式教育的高級官員之后,他明白,事情不算完,這只是開始,接著他被叫上去,
報告上許多地方毫無必要被劃掉!
“他們一副幸災(zāi)樂禍的老學(xué)究模樣,抓起我的報告,對我那些炫耀式的從句和毫無必要的副詞表達了極力的藐視。然后在我朽木不可雕也的文章頁邊空白處打上分數(shù),以及諸如‘行文累贅——注意省略——論證缺失——結(jié)論草率——你真的是這個意思嗎?’之類的評論。我遇到過的編輯們都沒他們這般嚴苛,或者說沒他們這般正確。”
正是因為自己的真實體驗,勒卡雷的小說才不會兜售虛假的過度浪漫化的諜戰(zhàn)故事,他賦予人物的是堅強與脆弱、信念與困惑、真實與虛無的矛盾一體,他們首先是具體的、脆弱的、血肉豐盈的人,其次,才是從事諜報工作的專業(yè)人員。
而這些,也都曾如此深刻的在年輕的勒卡雷內(nèi)心涌現(xiàn)過,因而,勒卡雷最后會在回憶里說,“我心想,我們的情報組織是不是應(yīng)該感謝感謝我們這些轉(zhuǎn)向文學(xué)界的叛徒。與其他任何可能掀起腥風(fēng)血雨的方式相比,寫作簡直像小孩玩積木一樣人畜無害。”
毛姆、格林:寫作太真實甚至成為工作手冊
在作家毛姆面前,勒卡雷與格林,算得上是晚輩了。
毛姆生前一度是全世界最暢銷的英語作家,并且在加入情報工作前,他已經(jīng)是知名的作家了。小時候的毛姆就有著驚人的閱讀量,他成績很好,本可以走約定俗成的牛津劍橋之路,但他最后選擇去德國上大學(xué),在大學(xué)里他喜歡上了叔本華和易卜生。1897年畢業(yè)后,他成為一名婦產(chǎn)科醫(yī)生,處女作《蘭貝斯的麗莎》也隨之應(yīng)運而生。不過,大約10年之后,毛姆才開始聲名大噪,并且還是因為一部喜劇劇本《弗雷德里克夫人》。
之后“一戰(zhàn)”爆發(fā),毛姆加入了英國情報部門,先到日內(nèi)瓦做諜報,后又當(dāng)密使,到俄國去勸阻戰(zhàn)爭。事實上,毛姆的大部分工作并不在一線,而是聽取其他間諜的匯報,下達指令和發(fā)工資。他把搜集到的信息加上自己的評論,寫成報告用密碼發(fā)送出去,他不止一次抱怨說,“沒有比編碼和解碼更沉悶的事了”。

寫作中的毛姆
工作之余,熱愛旅行的毛姆走訪了許多地方,出版了小說代表作《月亮和六便士》。1919年他還到訪過中國,最后創(chuàng)作了3部作品來紀念:一部戲、一本小說《面紗》、一本游記《在中國屏風(fēng)上》。
1928年,小說《英國特工阿申登》面世,毛姆稱“這是對我在戰(zhàn)時情報經(jīng)歷的真實記述”。據(jù)說這一系列本來有31篇小說,但當(dāng)毛姆把手稿拿給朋友丘吉爾看時,后者堅持要求他刪掉其中的14篇,認為這些小說違反了官方保密法案。有幾年,這本小說甚至成為情報工作手冊,被列入軍情五處與六處新人必讀書目,還啟發(fā)了蘇聯(lián)軍事情報部門對英國間諜小說的立項研究。
然而,當(dāng)毛姆離開情報工作專職于寫作時,他又十分懷念這個工作的好處了,毛姆的朋友、藝術(shù)史家肯尼斯·克拉克回憶,毛姆常說起自己非常喜歡情報工作,“我想,他喜歡它照進人性的那束光”。
還有個插曲是,到了“二戰(zhàn)”時期,六十多歲的毛姆繼續(xù)發(fā)揮著余熱,到美國去宣傳,他推銷國防債券,走訪軍隊作報告,甚至還按要求寫文章,鼓勵美國往英國寄蔬菜種子。
毛姆在美國宣傳的時候,年輕的作家亨利·格雷厄姆·格林差不多進入了英國情報部門工作。加入前,格林也寫已過多部作品,比如《斯坦布爾列車》(后來被改編成電影《東方快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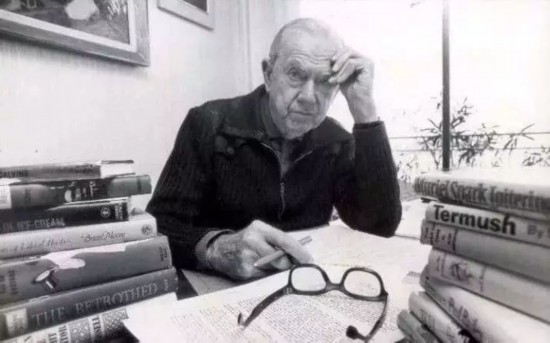
格雷厄姆·格林
格林年輕時就不是個安分的人,對情報工作很感興趣,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加入了英國軍情六處。經(jīng)過培訓(xùn)后,他成為代號“59200”的特工,被派往非洲的塞拉利昂。因為愛好寫作,格林選擇了一本小說作為自己專用的密碼本。
從非洲回來后,他換了一個負責(zé)葡萄牙方面情報工作的部門,他的上級菲爾比后來回憶說起格林的工作表現(xiàn),“他在寄來的信件中發(fā)表的尖刻的評論,使我每天在精神上得到些恢復(fù)”。
情報工作顯然沒有讓格林感到滿足,他發(fā)現(xiàn)許多同事編寫的報告充滿了錯誤和虛假,只是為了騙報酬,這些細節(jié)最后在十幾年后的小說《我們在哈瓦那的人》里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xiàn)。
寫作中并不避諱職業(yè)細節(jié)的行為,讓格林曾差點因為“精準描繪了英國大使館情報主管與外勤特工之間的關(guān)系”而遭情報組織起訴。對此,格林的反擊是二十年后送給他們一本《人性的因素》,書中描繪的情報組織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愚蠢無比的形象。
格林在1945年就離開了情報機構(gòu),一系列的經(jīng)歷讓他變得沉默,此后,他在眾人眼里變得愈發(fā)神秘。
J.D·塞林格:很遺憾,這段經(jīng)歷最終反噬了自己
美國作家塞林格一向給讀者以隱士的形象,他的人生后期躲避世人躲避媒體。他存世的作品并不多,但每本都是暢銷讀物,影響了好幾代讀者,今年在他百年誕辰紀念活動里,他的兒子馬特·塞林格先生來到中國,為大家?guī)淼囊粋€好消息是,他還有遺作會整理出版。
1942年塞林格在加入軍隊前,已經(jīng)努力了許多年在寫作上,不斷收到退稿信,最后總算在《紐約客》上發(fā)表了幾個短篇小說。這是大多數(shù)文學(xué)青年開始寫作的常見模式,他可能在醞釀寫一部長篇,但還不夠勇氣開始。那個叫霍爾頓的年輕人倒是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他的小說稿里了,很快,他會成為《麥田里的守望者》的主角,成為流行文化的偶像。

軍隊里不忘寫作的塞林格
23歲那年,塞林格入伍了,服役18個月之后,軍方為塞林格找了個地方,成為一名反情報組織的特工,即軍中間諜,監(jiān)視部隊在愛國方面的可信度。塞林格的任務(wù)是和其他特工一起,深入基層部隊,不僅與士兵們并肩作戰(zhàn),也要注意他們的言行舉止,以便盟軍順利實施登陸歐洲的行動。在軍隊期間,塞林格一直沒有忘記對出版商的承諾,他會把霍爾頓的故事繼續(xù)寫下去,直到形成一個長篇,他寫信對朋友說:“要寫的書我還沒忘。”
1944年6月6日,塞林格參與了歷史上最著名的“D Day”——諾曼底登陸。其后11個月的連續(xù)作戰(zhàn),在塞林格身上造成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后來一次次從他的作品里顯現(xiàn)出來,他反復(fù)提到諾曼底登陸,但對細節(jié)又三緘其口。
一封當(dāng)時寫給作家海明威的信件保留了下來。塞林格當(dāng)時在德國紐倫堡,負責(zé)甄別戰(zhàn)犯,遣送難民,“并沒有什么大的狀況,但總是有一種持續(xù)的沮喪感籠罩著我。”他這樣寫道。
更大的沮喪感還在等待著塞林格。
戰(zhàn)爭后期,塞林格的任務(wù)是搜集情報,所以他更加知道這次戰(zhàn)爭造成的終極恐怖。反情報部門向特工轉(zhuǎn)發(fā)了一份秘密報告:《德國的集中營》,列出德國14座重要的集中營,其名字、簡介和位置,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100個小型集中營。
塞林格和戰(zhàn)友驚得目瞪口呆,他們還以為戰(zhàn)爭即將結(jié)束,他們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最惡劣的事件,沒想到還有這么多令人發(fā)指的罪行。塞林格的傳記作家坎尼斯·斯拉文斯基后來形容說,1945年的塞林格,變了一個人,他不僅見證了大批無辜者的死亡,還見證了他珍視的所有事物被肢解。那是一場噩夢。
戰(zhàn)爭震壞了塞林格的大部分聽力,也傷害了他的精神,他的抑郁變得越來越嚴重,最后因精神問題住進醫(yī)院,離開了戰(zhàn)場。
唯一能拯救他的只有寫作,只有那個年輕人霍爾頓。1950年7月,《麥田里的守望者》面世。
塞林格正面描寫的戰(zhàn)爭經(jīng)歷的文字并不多,但從《魔術(shù)般的貓耳洞》《一個在法蘭西的小伙子》《陌生人》《艾絲米》等短篇里可以感受到,戰(zhàn)爭對他的反噬。
我們當(dāng)然也可以說,正因為戰(zhàn)爭,因為他在第一線的情報工作,讓他充實了成就了《麥田里的守望者》,讓戰(zhàn)后的年輕人以此為精神偶像,一起撫平,一起質(zhì)疑。
他們的熱情反響與塞林格最后選擇的隱居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每當(dāng)讀到小說里霍爾頓臨別的那句話:“你千萬別跟任何人談任何事情。你只要一談起,就會想念起每一個人來。”我們或許會更理解塞林格的選擇。
像情報諜戰(zhàn)這樣的特殊職業(yè),多多少少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作家也不例外,但是,他們的人生卻有幸借助文學(xué)變得更為強大,假裝無視黑暗并不能帶來力量,直面自己經(jīng)受成長的代價,才不會被世界輕易擊垮。
最終的回答很簡潔,無論此刻的你在扮演何種角色,隨時隨地,保持對自身和世界的敏感與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