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記錄》:千禧一代天才作家的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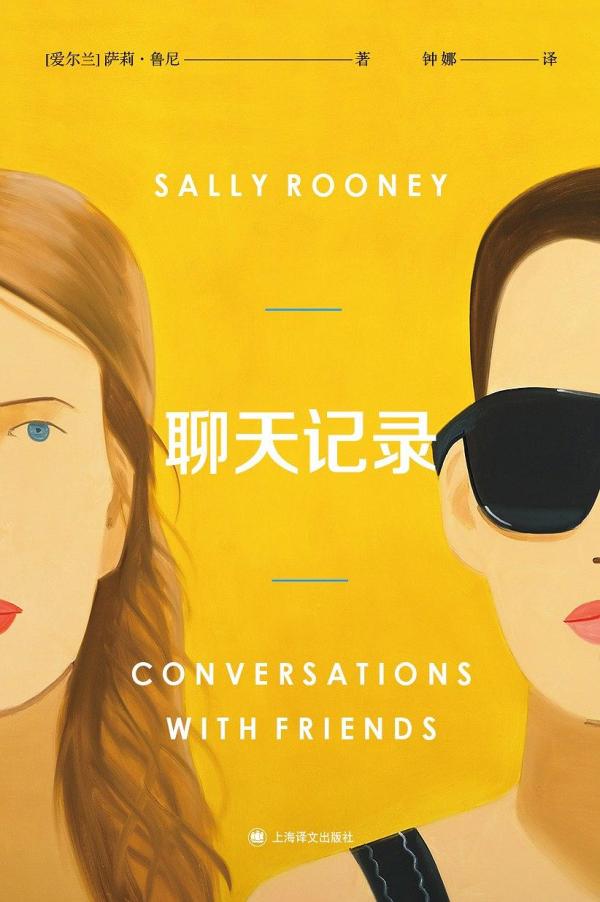
《聊天記錄》,[愛爾蘭]薩莉·魯尼著,鐘娜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304頁,49.80元
通常來說,在西方語境里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s”(1981-1996)不算特別正面的形象。他們重度依賴社交媒體和現代化通信手段,離開智能手機和筆記本電腦基本無法生活。寫過《美國精神病人》的布雷特·伊斯頓·艾利斯(Bret Easton Ellis)是位六零后同志,和一個小他二十多歲的千禧一代小男友同居多年,他在新書《白》(White)中揶揄千禧一代都是“軟蛋”(Generation Wuss),極為刻薄地勾勒了千禧一代的性格特寫:
我最愛談論的是千禧一代的過度敏感,他們的權利意識,他們總是堅持自己永遠是對的——哪怕有時反面證據排山倒海,他們拒絕把任何事放在具體語境里考量,他們幾乎都有遇事過度反應以及消極抵抗的積極性,順帶說一句,所有這些小毛病都是偶爾發(fā)作,他們并不總是那樣,而且很有可能被濫用的藥物加重了病情,要知道他們這年紀的孩子們從小到大的每一步都被保護欲過強的直升機父母控制著。這些父母,要么是嬰兒潮一代(1946-1964)的尾巴,要么是X世代(1965-1980),好像要反抗他們自己的叛逆性,因為他們感覺從來沒有被他們自己那自私、自戀、出生在真正的經濟繁榮年代的父母愛過,于是他們反過來要用愛悶死孩子,不教他們如何面對困難,不告訴他們真相:別人不一定會喜歡你,你愛的人不一定會愛你,小孩都很殘忍,工作很辛苦,要把事情做好很難,你的生活會充滿失敗和失望,你沒什么天分,人會受苦,會變老,會死。“軟蛋一代”的反應就是崩潰然后陷入感傷,滋生各種受害者敘事,而不是去掙扎著理解冰冷的現實然后繼續(xù)前行,做好準備在這個冷漠且時常有敵意、根本不鳥你個人存在的世界里摸索生存。
……
空虛和焦慮成了“軟蛋一代”的標志,當世界不再提供任何金融儲備,你就得全靠社交媒體過活了:維持人設,保持品牌競爭力,努力去被喜愛,被喜愛,被喜愛,當個好演員。而這制造了更進一步且無止盡的焦慮,當有人尖銳批評這一代人時就會被罵成一個混蛋——討論結束。負能量是不許有的:我們只能邀請別人來欣賞。但這問題就更大了,因為它限制了爭論。如果我們都被噤聲到只能喜歡一切(千禧一代之夢),是不是就只能無聊地討論啊一切多么好,你在Instagram上經常被點贊嗎?2014年春天他們的神級網站BuzzFeed宣布不會再上線任何“負面”內容——要是這種勢頭持續(xù)下去,還會有對話和辯論嗎?如果改善自身境況的經濟之路被堵死了,那么受眾度就會成為通用貨幣,所以你想要有成千上萬的人在Twitter, Facebook, Instagram, Tumblr還是別的什么上為你點贊,所以你會像演員一樣拼命地想被別人喜歡。你在社會中唯一的上升途徑是通過個人品牌,你的人設,你的社交媒體地位。我的一個二十出頭的朋友最近說,千禧一代更像是策展人而不是藝術家,一群“美學家”,任何上Tumblr的年輕藝術家,并不想創(chuàng)造藝術——只想偷別人的藝術,或者把自己變成藝術。
……

《白》
讀完愛爾蘭女作家薩莉·魯尼(1991年生)的處女作《聊天記錄》,你看不到太明顯的千禧一代軟蛋通病,女主人公弗朗西絲只要碰到不順心的事,就會用利器割傷自己,而且從來不喊疼。她的小說里沒有千禧一代最常見的玻璃心,沒有媽寶男,雙女主都是在校大學生,卻有著異乎尋常的成熟心智,向往那些小有名氣的成年人更為世故的社交世界。也許正因為魯尼能夠超越自己身處的世代局限,去關心更為普遍永恒的人類境況和人際關系,她被英美一眾高眉文學刊物譽為千禧一代最天才的作家,左翼圈也很興致勃勃地稱她為新型馬克思主義小說家。唯一彌漫在小說中的千禧特質是弗朗西絲的不上進,但她的不上進并不是不動腦筋的懶散,而是刻意選擇的“消極抵抗”(passive aggressive):
我不想找工作。關于未來財務的可持續(xù)性我沒有任何規(guī)劃:我從沒想過做什么事來賺錢。之前幾個夏天里我打過很多份最低工資的零工——發(fā)郵件,打推銷電話,諸如此類——畢業(yè)后我估計還會干更多類似的活。盡管我知道我終將全職工作,我從未幻想過一個光芒四射的未來:我參與金錢活動,從而獲取報酬。有時,這讓我覺得我對自己的人生不感興趣,于是感到很低落。另一方面,我感覺我對財富的漠不關心在意識形態(tài)上來說是健康有益的。我會去查如果把全球總產值按人頭平均分配,平均年工資是多少;據維基百科答案是16100 美元。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我都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掙超過這個數字的錢。
你要問薩莉·魯尼怎么寫一本馬克思主義小說,她八成會說不知道,畢竟寫《聊天記錄》時她才二十五歲,小說里七次提到“資本主義”的地方都是象征性的道具,沒有什么特別讓人眼睛一亮的深刻表述,當然這也因為人物設定是女大學生而不是理論家。但魯尼對階級差異造成的張力明顯很感興趣。敘述者弗朗西絲出身中下階層,父母離異,酗酒的父親經常失聯、不給撫養(yǎng)費,她有一陣窮得叮當響,不得不接受有婦之夫尼克的食物接濟;弗朗西絲的同性戀前女友博比可以算得上白富美,她在社交場合特別討人喜歡,與時常有自卑感、外表冷淡的弗朗西絲形成了互補;梅麗莎和尼克是一對文藝圈小有名氣的夫婦,梅麗莎是作家,尼克是演員,家庭環(huán)境是標準中產階層——弗朗西絲從來不會錯過描述他們家里用的好餐具、埃及棉的被套、尼克穿的名牌外套,以及自己第一次吃牛油果(多么切題的中產標配)的感受。小說的主線是弗朗西絲和尼克的婚外情,不過不同于爛俗的蘿莉大叔套路,這場婚外情的文化背景是千禧年之后流行的“聰明是新式性感”(濫觴是2007年開播的美劇《生活大爆炸》,主角謝爾頓是個性格乖僻但聰明絕頂的年輕科學家),二十一歲的弗朗西絲在智性上是強勢的一方,足以碾壓三十多歲的半過氣演員尼克。
魯尼并沒有滿足于簡單的階級對比,她把地位的對比也加入其中,使得故事的層次感更強,動態(tài)更豐富,人物關系更微妙。弗朗西絲和博比作為初出茅廬的大學生文青,處于文化圈食物鏈的最底層,而食物鏈中端的梅麗莎看中她倆聰明美貌(借小說人物之口的評價就是“她們也很具備裝飾性”),時不時邀請她們來家里做客,多半是為了給無聊的生活增加點新鮮感和刺激;梅麗莎的丈夫尼克雖然出身優(yōu)渥,但性格軟弱(梅麗莎說他是那種哪怕知道她在策劃謀殺他也會聽任她殺的弱雞),演藝事業(yè)也不順利,能領到的都是些龍?zhí)捉巧佒荡蟾攀撬ㄒ坏挠餐ㄘ泿牛ā盎ㄆ坷瞎保喲灾A級高地位低的典型人物。小說中有一個著墨不多但地位重要的人物,是身世顯赫、在出版界可以呼風喚雨的老女人瓦萊麗。她明顯刻薄又可怕,說話是那種討人厭的有錢人腔調,從來不顧忌聽者的感受,但每次她來梅麗莎家里做客時,都會得到“皇室嬰兒般的接待規(guī)格”。梅麗莎會特別緊張,她早早打發(fā)尼克去采購,讓博比打掃客房疊床單,還提醒她不許說任何挖苦富人的話。花瓶里要有剛剪的鮮花,不配套特別丑的桌椅都得拿走:
剩下的下午,梅麗莎打發(fā)我們做各種瑣事。她覺得杯子不夠干凈,于是我在水槽里把它們重洗了一遍。德里克拿了一瓶花去瓦萊麗的房間,還在床頭柜上放了瓶氣泡水和一只干凈的杯子。博比和伊夫林一起在客廳熨了幾只枕套。尼克出去買了檸檬,后來又出去買了方糖塊。傍晚剛剛降臨時,梅麗莎在做飯,德里克在擦銀器……
梅麗莎并不喜歡瓦萊麗,之所以要如此費心討好,全是因為沒有瓦萊麗的幫助她就沒法出新書。在晚餐時,瓦萊麗當面輕慢尼克,梅麗莎不響,卻引起了弗朗西絲的極度不滿,幫尼克說話,頂撞了瓦萊麗。妙就妙在,這女大學生的出格舉動卻引起了瓦萊麗的興趣,之后表示愿意讀一讀弗朗西絲的作品。“我居然給瓦萊麗留下了持久的印象,這讓我充滿了惡狠狠的勝利感。”后來弗朗西絲的新小說正是在瓦萊麗的推薦下得到都柏林重要文學刊物的青眼,讓在她最窮的時候(“只剩大概六歐元時”)突然賺到了一筆八百多歐的巨額稿費和一點薄名。雖然這小說是弗朗西絲“賣友求榮”的惡例,寫的全是前女友/閨蜜博比家的事,不過對青春無敵的人來說,最后也沒有什么一封情真意切的道歉信和好好上床不能解決的事。

薩莉·魯尼
除了階級、地位等傳統小說要素之外,作為性別意識流動性極強的千禧一代,魯尼為小說中主要四人的性別身份設定也加了調料,弗朗西絲是雙性戀,博比是女同性戀,梅麗莎是已婚雙性戀,出軌對象不分男女,尼克則是純直男。一個老派直男,妻子和小情人都是雙性戀,動態(tài)系統中有了不少可以咀嚼的新鮮變量。
弗朗西絲和尼克的婚外情有一點戴維·黑爾的名劇《天窗》的影子,年輕而貧窮的女主人公是智力優(yōu)越的一方,對與有婦之夫的情感中的權力關系看得非常透徹,但也并非銅墻鐵壁完全沒有脆弱的時刻。魯尼很會寫性關系中各方的小心思和沖突,調情也寫得很好:
討論時,我說的笑話尼克都笑了。我告訴他我很容易被喜歡我笑話的人誘惑,他說他很容易被比他聰明的人誘惑。
我猜你只是不常遇見比你聰明的,我說。
瞧,互相奉承是不是感覺非常好?
在這段關系里,尼克處處處于下風,弗朗西絲比他聰明,跟她辯論幾乎沒有勝算,而且他是有婦之夫,自帶原罪,弗朗西絲對他亂發(fā)脾氣他也只能忍受,何況他生性是受虐型,逆來順受是常態(tài)。梅麗莎在發(fā)現他們偷情后,給弗朗西絲寫了一封長信,刀刀見血地總結了她自己和尼克的關系,以及弗朗西絲和尼克的關系,算是小說中的一個小高潮。
弗朗西絲從這段關系里想要什么,并不是特別清楚。身體的欲望、掌控欲、嫉妒、憤怒、猜疑、自卑、自信、被需要、不斷試探邊界等種種復雜的情緒糾纏在一起。小說的結尾,是尼克和弗朗西絲在分手一個月后又通了一次長電話,尼克說了弗朗西絲久等的情話,弗朗西絲跟尼克分享了自己的近況包括很不愿面對的醫(yī)院診斷結果(子宮內膜異位癥),兩人決定立刻見面。弗朗西絲:
我閉上雙眼。物和人在我周圍轉動,在模糊復雜的等級制度里占據不同位置,加入我現在不知道并永遠都不會知道的系統。一個由事物與概念組成的復雜網路。要明白生活你需要先經歷它。你不能總是做一個分析的人。
很難說之后兩人的關系會有什么實質性的改變,不過反正能吵的架都吵過了,婚外情中能分析的也已經分析完了。魯尼說過她不認為一個人可以獨活,她喜歡寫親密關系,寫人如何在彼此的關系中互相建構。這不就是馬克思名言“人是社會的動物”的千禧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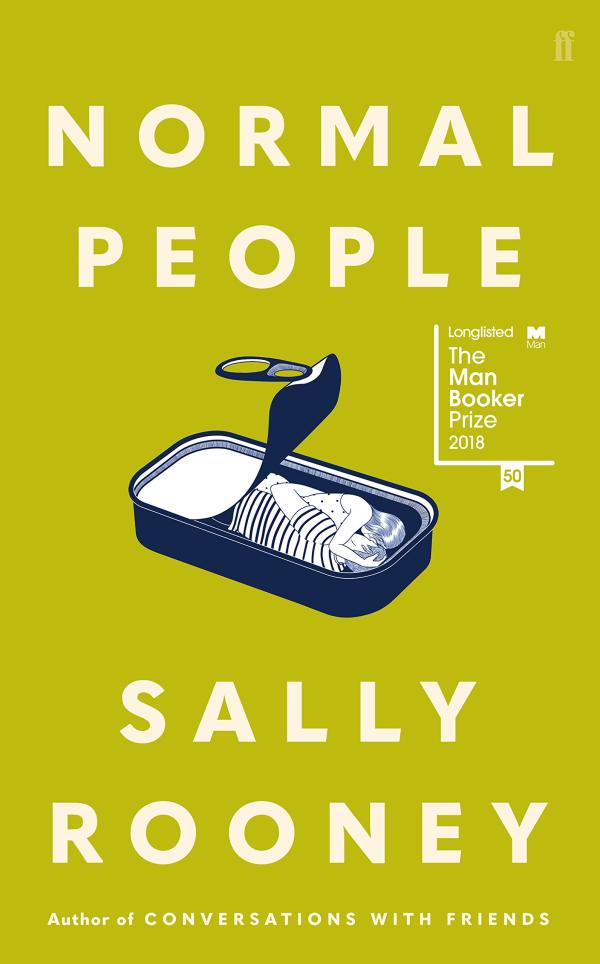
《正常人》
很多小說家的處女作都是回憶錄。魯尼的這部處女作要成熟得多,完成度甚至超過她的第二部小說《正常人》。盡管魯尼多次否認弗朗西絲是她自己,但她也不得不承認,許多不合時宜、政治不正確的話,只要安在小說人物身上就一點問題都沒了。比如她本人對本國文學偶像葉芝的反感,被安放在弗朗西絲的一次令人極度不適的網絡約炮橋段中,這位炮友很愛葉芝,使得這種反感被立刻放大了十倍。
我熱愛詩歌,他說。我愛葉芝。
沒錯,我說。要說法西斯有什么優(yōu)點,那就是它產出了不少好詩人。
然后他對詩歌也沒什么可說的了。喝完酒,他邀請我回他的公寓,我讓他解開了我的襯衣。我心想:這很正常。這件事再正常不過。他的上身很嬌小柔軟,和尼克的截然不同,而且他也沒做任何尼克做愛時會做的事,好比撫摸我很久,低聲說話。一切馬上就開始了,幾乎沒有什么前戲。生理上我?guī)缀跏裁锤杏X都沒有,只是有輕微不適。我感覺自己變得僵硬沉默,我等待羅薩意識到我的僵硬,然后停下他在做的事,但他沒有。我想叫他停下來,但又真切地覺得他會忽略我,雖然情況并不一定如此。不要給自己惹上什么法律麻煩,我心想。我躺在那兒,任他繼續(xù)。他問我想不想來點粗的,我告訴他我不喜歡,但他還是扯了我的頭發(fā)。我想笑,笑過后又恨自己感到高人一等。
《聊天記錄》的大部分內容是以對話推動的,魯尼筆下的對話體是千禧一代毫無隔膜的網絡風格,能用簡短的“推特體”進行自曝和自嘲,不給別人留批評的機會。她和她筆下的人物愛看愛讀的是莉娜·鄧納姆(Lena Dunham,自編自導自演美劇《都市女孩》)、格蕾塔·葛韋格(Greta Gerwig,出演過《弗朗西絲·哈》,導演過《伯德小姐》)、帕特麗夏·洛克伍德(Patricia Lockwood,女詩人)——全都是千禧一代女權主義者;少女時代的弗朗西絲曾在日記里寫下這些思考: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我有權力不去愛任何人。
有采訪者愛把魯尼與希拉·赫提、本·勒納相提并論,她用不卑不亢的口氣表示了很榮幸能與他們比較,但是,她堅持自己的小說并沒有顛覆形式的實驗野心,依然注重傳統小說的那些要素:人物關系、性格、結構等等。“許多評論人注意到我的小說基本就是套著當代服飾的十九世紀小說。”
與布雷特·伊斯頓·艾利斯眼中拼命表演以獲得關注度的“千禧軟蛋”不同,魯尼在成名后刪掉了自己的社交媒體賬號,因為過度的關注令她不適,她覺得小說家被過譽了,媒體應該多報道護士和公交司機。很多人好奇她會如何處理小說暢銷帶來的財富和名氣,她的做法也許能給千禧一代馬克思主義者帶來示范意義,可以肯定的是,她不會去買奢侈品或者五星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