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大作家為何都是“樂迷”?
作家們總有一些特別的愛好,如巴爾扎克寫作的時(shí)候嗜咖啡成癮,福樓拜白天休息,夜晚寫作,海明威喜歡站著寫作,馬克·吐溫喜歡航海冒險(xiǎn)。在這些愛好中,又有一些頻繁出現(xiàn)的,如對(duì)音樂的愛好。作家與“樂迷”身份兼于一身的情形實(shí)在是太常見了,村上春樹迷戀爵士樂,米蘭·昆德拉、赫爾曼·黑塞喜歡古典音樂,余華也曾狂熱迷戀古典音樂,更不必說中國(guó)古代那些精通音律的大詞人們。作家們?yōu)楹稳绱讼矚g音樂?音樂與文學(xué)之間有什么關(guān)系呢?
作為“樂迷”的作家們
喜歡音樂的外國(guó)作家很多,其中村上春樹應(yīng)該是中國(guó)讀者非常熟悉的一位。據(jù)統(tǒng)計(jì),從他的處女作《且聽風(fēng)吟》到2005年出版的《東京奇譚錄》,他的作品中出現(xiàn)音樂曲名、音樂家名字達(dá)近八百次。他非常喜歡直接援引樂曲作為小說的題目,如大熱的作品《挪威的森林》出自英國(guó)搖滾樂隊(duì)披頭士的同名歌曲,《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中隱含了李斯特的鋼琴組曲《巡禮之年》,《國(guó)境以南 太陽(yáng)以西》、《舞舞舞》與《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也都是出自音樂曲名。

村上春樹書房里的唱片墻
村上春樹最愛爵士樂,曾經(jīng)寫過《爵士樂群英譜》,專門介紹爵士樂史上的樂手們。他對(duì)上世紀(jì)六七十年代的搖滾和古典音樂也很偏愛,《與小澤征爾共度的午后音樂時(shí)光》是他與日本著名指揮家小澤征爾的對(duì)談錄。

《爵士樂群英譜》
村上春樹在他的音樂隨筆集《沒有意義就沒有搖擺》(是的,這一題目也是出自一首爵士樂曲)中提到,“書和音樂在我的人生中是兩個(gè)關(guān)鍵物”。他屢次談及音樂對(duì)于他創(chuàng)作的影響,尤其是音樂的節(jié)奏運(yùn)用對(duì)于他小說創(chuàng)作的啟發(fā)。他將爵士樂自由的節(jié)奏和即興的創(chuàng)作手法運(yùn)用到小說中,讓小說的節(jié)奏快慢相間,并十分重視小說中的即興創(chuàng)作。他如此重視小說的節(jié)奏,以至于認(rèn)為如果一個(gè)人缺乏節(jié)奏感,連成為作家的資質(zhì)也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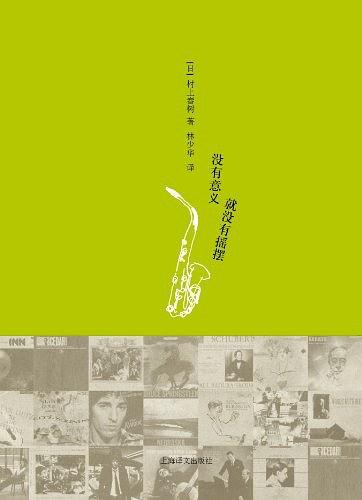
《沒有意義就沒有搖擺》
相較于村上春樹音樂愛好者的身份,米蘭·昆德拉差一點(diǎn)就踏上了專業(yè)從事音樂的道路。他的父親是鋼琴家、音樂教授,從小便教他彈鋼琴,他后來還師從捷克著名的作曲家保爾·哈斯學(xué)習(xí)作曲。對(duì)于音樂的熱情同樣深刻地影響到了米蘭·昆德拉的創(chuàng)作,他曾經(jīng)在《小說的藝術(shù)》中談到過音樂對(duì)于他的小說結(jié)構(gòu)創(chuàng)作的影響:“我小說中的每一部分都可以標(biāo)上一種音樂標(biāo)記:中速,急板,柔板,等等。”幾乎每一部米蘭·昆德拉的長(zhǎng)篇小說中,都能看到音樂對(duì)他的創(chuàng)作的影響,他將小說的主題性詞語類比為音樂中的“音列”,將小說的多線敘事類比為音樂的復(fù)調(diào),將小說的不同部分類比為音樂的各個(gè)段落,音樂的節(jié)奏變化對(duì)于他的創(chuàng)作有巨大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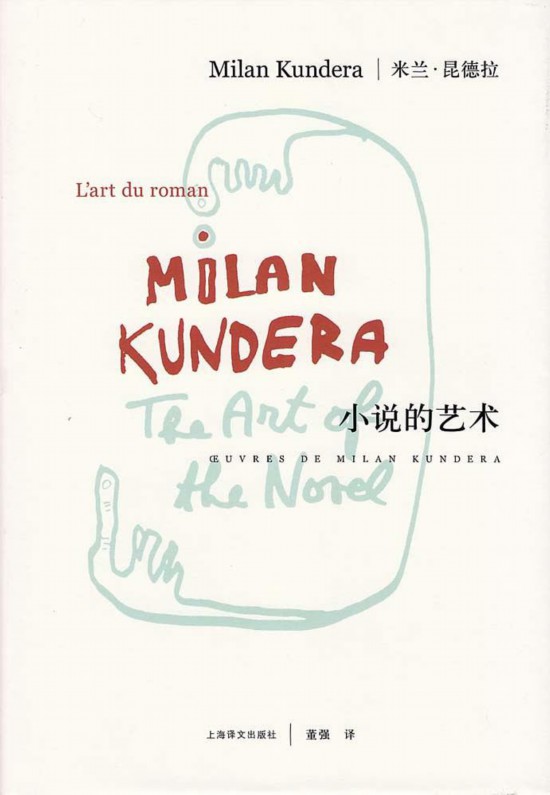
《小說的藝術(shù)》
盡管在文學(xué)上成名很早,但在音樂方面,中國(guó)作家余華完全是半路出家。按照他在隨筆集《文學(xué)或者音樂》中的描述,直到三十三歲時(shí),音樂才真正走入了余華的世界,半年的時(shí)間里,他買了差不多四百?gòu)圕D,余華自己描述道:“音樂一下子就讓我感受到了愛的力量,像熾熱的陽(yáng)光和涼爽的月光,或者像暴風(fēng)雨似的來到了我的內(nèi)心。”

《文學(xué)或者音樂》
對(duì)于音樂的熱愛很快影響到了余華的創(chuàng)作,他從音樂的敘述中學(xué)到了小說的敘述,這根本上都是藝術(shù)的敘述,他從音樂的敘述中理解藝術(shù)的民間性和現(xiàn)代性,從加德納指揮的巴赫《馬太受難曲》中領(lǐng)會(huì)到“敘述的豐富在走向極致后其實(shí)無比單純”,從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交響曲》中,他“聽到了敘述中‘輕’的力量”。
這些熱愛音樂的作家們,都談到了音樂對(duì)于他們創(chuàng)作的影響,那么,這種影響何以發(fā)生呢?音樂與文學(xué)之間究竟有怎樣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呢?
同源異流的音樂與文學(xué)
如《禮記》中所言,“詩(shī),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dòng)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音樂與文學(xué)(詩(shī))在人類文明的最初其實(shí)是同源的,在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里都不可分割,無論是西方的史詩(shī)還是中國(guó)的《詩(shī)經(jīng)》,最初都是用來吟唱的。朱之謙先生在《中國(guó)音樂文學(xué)史》中寫道:“文學(xué)史和音樂史是同時(shí)合一并進(jìn)的。”

《中國(guó)音樂文學(xué)史》
詞是音樂與文學(xué)緊密結(jié)合的產(chǎn)物,葛曉音在《唐詩(shī)宋詞十五講》中談到了詞的起源問題:“詞的濫觴最早可追溯到隋唐之際的民間曲子詞”,不同于樂府詩(shī)“選詩(shī)入唱”,詞是“倚聲填詞”,詞的句式、用韻等體制方面的特點(diǎn)與曲調(diào)曲式密切相關(guān),因而與音樂的關(guān)系也更為緊密。兩宋詞壇的大家如柳永、周邦彥、姜夔等,都是精通音律的音樂家。周邦彥執(zhí)掌大晟府時(shí),規(guī)范了詞的調(diào)式,創(chuàng)造了《六丑》等新的詞牌,他十分注重字句與音律的和諧,使詞的聲律進(jìn)一步緊密化,開啟了“格律詞派”的先河。如今我們雖推崇蘇軾等人的豪放詞風(fēng),但在當(dāng)時(shí),周邦彥為代表的格律詞才是詞學(xué)正宗。蘇軾開拓詞的境界,有時(shí)不甚注重詞與音樂的諧和,成為“曲子中縛不住者”,在當(dāng)時(shí)常常為恪守詞學(xué)正體的詞人們所詬病,李清照便批評(píng)蘇軾雖“學(xué)究天人”,然而所作的詞“皆句讀不葺之詩(shī)爾”。可見,詞與音樂關(guān)系之緊密。
在西方音樂史上,尤其是歌劇創(chuàng)作領(lǐng)域中,歌詞與音樂的關(guān)系更是音樂家們常常爭(zhēng)論的話題,就像漢斯立克所說,“音樂與歌詞永遠(yuǎn)在侵占對(duì)方的權(quán)利或作出讓步”。莫扎特是堅(jiān)持音樂原則的典型,他認(rèn)為好的音樂可以使人們忘記最壞的歌詞,他的歌劇中,歌詞很可能不是最杰出的。格魯克等人與他相反,更加重視歌劇中詩(shī)的地位,柏遼茲更是在他著名的《幻想交響曲》演奏前,給觀眾們分發(fā)了兩千份樂曲解說。這可能是柏遼茲的得意之作,然而在門德爾松的眼中,評(píng)價(jià)就變成了“他是一位有教養(yǎng)、有文化、可親的君子,可是樂曲卻寫得很糟”。
浪漫主義音樂時(shí)期,文學(xué)對(duì)于音樂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文學(xué)在唱詞文本、腳本來源、標(biāo)題內(nèi)容等方面深刻影響著音樂,柏遼茲的《浮士德》和《羅密歐與朱麗葉》、舒伯特的藝術(shù)歌曲都借用了文學(xué)作品來表達(dá)音樂主題。音樂與歌詞地位孰高孰低的問題在音樂史上引發(fā)如此多的爭(zhēng)議,不也恰恰證明了音樂與文學(xué)互相影響之深,聯(lián)系之緊密嗎?
我們也似乎可以理解作家們?yōu)楹稳绱藷釔垡魳罚⑶夷軌驈囊魳分屑橙∧敲炊鄤?chuàng)作的智慧了。音樂與文學(xué)或許傳情達(dá)意的手段不同,但都給讀者/聽眾以相似的感動(dòng),而在敘述的技巧上,又有那么多可供相互借鑒的地方。音樂與文學(xué)對(duì)于彼此,都是有著致命吸引力的寶藏。
參考文獻(xiàn)
1.《中國(guó)音樂文學(xué)史》,朱謙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沒有意義就沒有搖擺》,【日】村上春樹/著 林少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
3.《文學(xué)或者音樂》,余華/著,譯林出版社2017年
4.《小說的藝術(shù)》,米蘭·昆德拉/著 孟湄/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