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的短篇里,有“失重”后的輕盈 ——評(píng)新近出版的《格雷厄姆·格林短篇小說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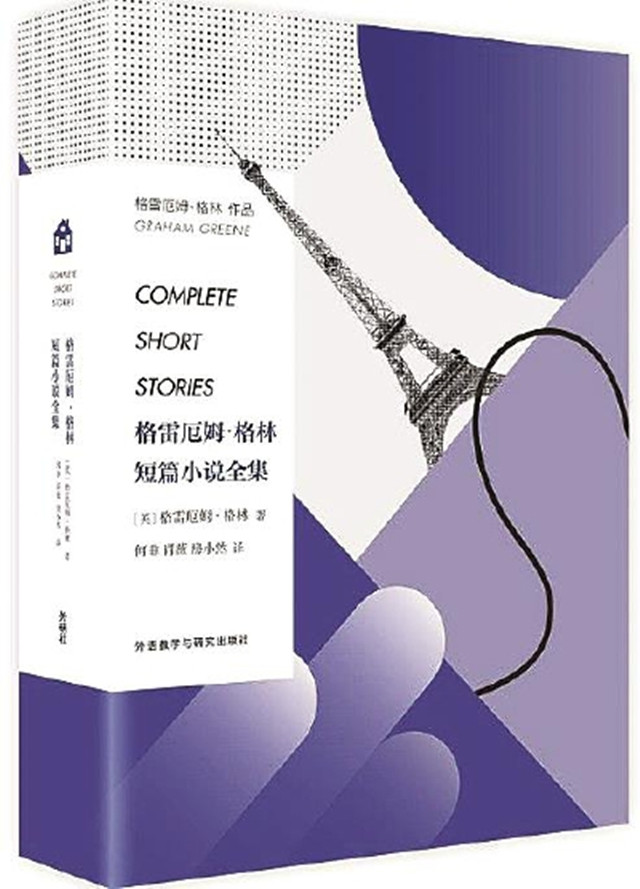
作家的長(zhǎng)篇和短篇?jiǎng)?chuàng)作并不總“相向而行”,更多的實(shí)驗(yàn)、摸索和闡釋,被安放在短篇故事的“海灘”上。
格林長(zhǎng)篇里的沉重,在短篇里正變得“失重”,這種輕盈才是迷人眩惑。怪誕幻想,黑色幽默,就像格林的“側(cè)顏”,在長(zhǎng)篇里他很少顯露,因?yàn)闀?huì)打亂嚴(yán)肅現(xiàn)實(shí)感。在短篇里,卻隨性而至。
沒有長(zhǎng)篇小說問世的作家,總像打了折扣,魯迅先生就吃了這種虧。我們總愛幻想文壇那些“短篇圣手”,如果寫出長(zhǎng)篇作品會(huì)是什么風(fēng)貌。其實(shí),長(zhǎng)篇太高產(chǎn)、太有名的作家也有失落:他們的短篇故事常被淹沒,仿佛從未寫過一樣。
格雷厄姆·格林就是如此。他是真正的無冕之王,被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提名21次,也沒得到。文學(xué)界甚至用“格林國(guó)度”標(biāo)榜其風(fēng)格,這意味著一位嚴(yán)肅的作家,光靠講故事就能搭建王國(guó),寫出人性萬象。
格林的人生本就像小說,也許只有毛姆的經(jīng)驗(yàn),才能與之比擬。他們都當(dāng)過特工,沉迷異域,都善講故事,能把通俗和消遣寫出嚴(yán)肅深刻的境況。同時(shí),他們也都有缺陷,毛姆的口吃,格林的躁郁癥,放在小說藝術(shù)里,倒成了壓抑的激情:更敏感、世故、也更機(jī)警。不同的是,格林的天主教信仰帶來一種視角,那就是強(qiáng)烈的道德感,讓他對(duì)墮落、背叛、誘惑與救贖的主題無比醉心。那種不動(dòng)聲色的優(yōu)越性,對(duì)主人公愚蠢且憂傷的嘲諷,完全有種俯瞰的哀矜。
《格雷厄姆·格林短篇小說全集》呈現(xiàn)了作家短篇藝術(shù)全貌。如果借用格林的書名來概括,就是他總在捕捉“戀情的終結(jié)”時(shí)刻(“戀情”代表純真詩(shī)意的退場(chǎng)),使“問題的核心”自然敞開,剝離各種“人性的因素”,戳給你看。這正是亨利·詹姆斯所謂“現(xiàn)實(shí)登臨的絕妙時(shí)刻”。《往昔純真》里,“我”后悔搭上酒吧偶識(shí)的羅拉,一起回到兒時(shí)鄉(xiāng)下。“我”想起兒時(shí)喜歡的女孩,發(fā)現(xiàn)原先畫過的畫。“我根本認(rèn)不出這畫是我畫的……我心中只記得當(dāng)年的純真、彼此的親密”。當(dāng)“我”看到那張畫感到尷尬的瞬間,就意味純真不再。這種情緒在諸多作家青澀之作里都留有痕跡。馬丁·艾米斯的《雷切爾文件》,寫年少時(shí)的騷動(dòng)卻映透清純,寫放縱狂野又流溢迷惘。在身體的激情酣暢后,最終發(fā)現(xiàn)青春之愛始終被丑陋驚醒,在庸俗現(xiàn)實(shí)里無以安放。在厄普代克短篇集《鴿羽》中,也大多是少年們萌動(dòng)的青春紀(jì)事。
只不過,格林會(huì)否定、懷疑青春的可靠性。《花園之下》里,兄弟二人的記憶“大相徑庭,這讓他很吃驚。他們談?wù)摰暮孟袷峭耆煌牡胤剑耆煌娜恕薄!澳莻€(gè)伴隨他周游世界的夢(mèng),其來源很可能只是他為校刊胡亂編造的一個(gè)故事,而這個(gè)故事已被自己遺忘”。作家描述的正是小說的視差之見——虛構(gòu)和記憶混同的錯(cuò)覺,想象力和現(xiàn)實(shí)間的斷裂,就是藝術(shù)的魅力。他隱晦模擬了“世俗聲音”——維爾迪奇太太把想象力斥為“愚蠢幻想”,對(duì)神秘事物極端反感,對(duì)屈從于“宗教教育”的苗頭高度警惕。這顯然是格林的焦慮:作為一個(gè)天主教作家,他既離不開虛構(gòu),也放不下宗教情感。主人公“校準(zhǔn)”否定回憶,改寫童年舊夢(mèng),它的動(dòng)機(jī)就像格林親自示范怎么“改小說”。這擺脫了格林常有的“雙軌模式”:既不是驚險(xiǎn)消遣,也不是宗教探討。它像一種心理小說,影射作家的精神現(xiàn)實(shí)。這種“出神狀態(tài)”與薇拉·凱瑟的《花園小屋》的幽深柔膩,有種契合。在童年生活、家庭成員和心理類型的沉浸里,通往潛意識(shí)的秘境。
在短篇中,格林不必總是穿插錯(cuò)綜復(fù)雜的情感與政治,他能騰挪更多講故事的天性。《無罪開釋》中,謀殺案庭審現(xiàn)場(chǎng),證人指認(rèn)嫌疑人,法庭后座卻出現(xiàn)與被告一模一樣的人。“沒有一個(gè)證人愿意發(fā)誓他看到的那人就是被告。”結(jié)果無罪釋放。格林給的尾巴才是“爛尾的不安感”。孿生兄弟出庭后,一人被車撞死,“沒人能說清楚他到底是那個(gè)兇手還是那個(gè)無辜的人。”
創(chuàng)作短篇的格林,更像一個(gè)“世情小說家”。他寫的都是卑微、瑣碎的小人物,情節(jié)也多是些出軌偷情、背叛不忠的荒誕現(xiàn)實(shí),又偽裝成一些輕喜劇的悲傷故事(如《借夫記》及其他喜劇)。“對(duì)忠誠(chéng)的背叛,對(duì)人物內(nèi)心沖突的挖掘,是格林的拿手好戲”。正如張愛玲的短篇,總在平凡里發(fā)現(xiàn)傳奇,相比契訶夫?qū)θ宋锬骋恍愿窈颓榫w的夸飾性嘲諷,歐·亨利式的經(jīng)典反轉(zhuǎn),格林的短篇藝術(shù),更像是參差對(duì)照、權(quán)衡強(qiáng)弱的力的解析。
格林總能寫出人物間復(fù)雜合力對(duì)事件的隱在導(dǎo)向,施壓與抵抗、作用與反作用,讓你理解人們是如何自然而然,不知不覺地滑向千百條罪惡迷途。《當(dāng)騙子遇上騙子》挖苦了詭計(jì)世界的“完美結(jié)構(gòu)”,當(dāng)每個(gè)人都在欺騙,騙術(shù)自然會(huì)失效。假校長(zhǎng)想騙錢,假貴族要文聘,反而被雙方晚輩所欺騙,促成兩個(gè)年輕人相愛結(jié)合。短篇小說需要發(fā)現(xiàn)平庸里的驚奇感、戲劇性,既然不能像長(zhǎng)篇小說去編織生活大網(wǎng),就要在事件的“截面”里挖掘人性縱深。正是一種來自深淵的凝視,悲觀的窺伺,給了格林感受恐懼、暴力和背叛,冷峻掀開平庸之惡,危險(xiǎn)邊緣的藝術(shù)知覺。如《破壞者們》里一群少年們的“拆屋計(jì)劃”,就是并無緣由的破壞欲展示。多克托羅《威利》,也寫過兒童破壞欲的古怪莫名、獰厲狂亂。
格林對(duì)暴力和悲觀的展示,讓人很容易聯(lián)想到奧康納。《好人難尋》中,一個(gè)多事的老太太,在假日旅行途中,心血來潮,非要繞道去看年輕時(shí)的老宅。結(jié)果出了車禍,路遇逃亡歹徒,又多嘴指認(rèn),惹來全家身亡。有趣的是,老太太企圖用宗教感化歹徒,反而被連射三槍,死得更快。奧康納就和殺手一樣,不僅讓宗教在暴力面前失效,還用三個(gè)槍子兒崩掉了愚蠢、嘮叨和假模假式。
事實(shí)上,作家的長(zhǎng)篇和短篇?jiǎng)?chuàng)作并不總“相向而行”,更多的實(shí)驗(yàn)、摸索和闡釋,被安放在短篇故事的“海灘”上。如格林用童話思維來對(duì)夢(mèng)境挖掘,對(duì)潛意識(shí)和精神疾患的自我診斷,正如精神分析對(duì)小說的轉(zhuǎn)碼編譯。那種“格林式悲觀”也常常變成機(jī)謹(jǐn)嘲諷的喜劇性沖兌。換言之,格林長(zhǎng)篇里的沉重,在短篇里正變得“失重”,這種輕盈才是迷人眩惑。怪誕幻想,黑色幽默,就像格林的“側(cè)顏”,在長(zhǎng)篇里他很少顯露,因?yàn)闀?huì)打亂嚴(yán)肅現(xiàn)實(shí)感。在短篇里,卻隨性而至。
《唉,可憐的馬林》里主人公患上了腸鳴癥,不可思議的是他的肚子,好像裝上了耳朵,能模擬發(fā)出接收到的外部聲音。馬林先生把公司會(huì)議給搞砸了,他的腸子竟然發(fā)出了空襲警報(bào),他只好揣著明白裝糊涂,跟著董事一起躲在地下室。“他那肚子不知道是什么品味,空襲警報(bào)的音調(diào)學(xué)得無比神似,可空襲解除的音調(diào)卻從沒學(xué)會(huì)”。這種諧趣寓意,往往在絕壁處推向高潮。相比這種“有去無回”,能去能回更是一種環(huán)島效應(yīng)。“偷走埃菲爾鐵塔并不太難,難在如何悄悄放回去,還不被人察覺”(《偷埃菲爾鐵塔的人》)。格林寫出這樣一個(gè)夢(mèng)話般的幻想小說,是罕見的。怎么拆卸鐵塔,卡車搬運(yùn),迷惑游客,避免報(bào)警……格林就像幻術(shù)大師,策劃轉(zhuǎn)移人們注意力。“我確定那么做幾乎毫無風(fēng)險(xiǎn),因?yàn)榘屠枞诵哂诔姓J(rèn)埃菲爾鐵塔在眼皮底下消失了五天,而他們竟然毫不知情,這就好像讓熱戀的情侶承認(rèn),情人不見了,自己竟然不知道”。
格林在訪談中曾強(qiáng)調(diào),一個(gè)作家必須受到一種“支配的激情”,才能提供一種持續(xù)性,給予眾多小說“統(tǒng)一體系”。“因?yàn)槿绻贿@樣,就只能依賴他的天賦了;而天賦,即使有極高的天賦,也不足以使你佳作不斷”。這種激情也支配了這些短篇故事,那就是描寫人類普遍狀況,“我筆下的人物身處這種狀況,只有信仰能救贖他們,不過救贖的真正方式常常不是立即顯現(xiàn)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