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鳴:對(duì)北京人藝的愛和責(zé)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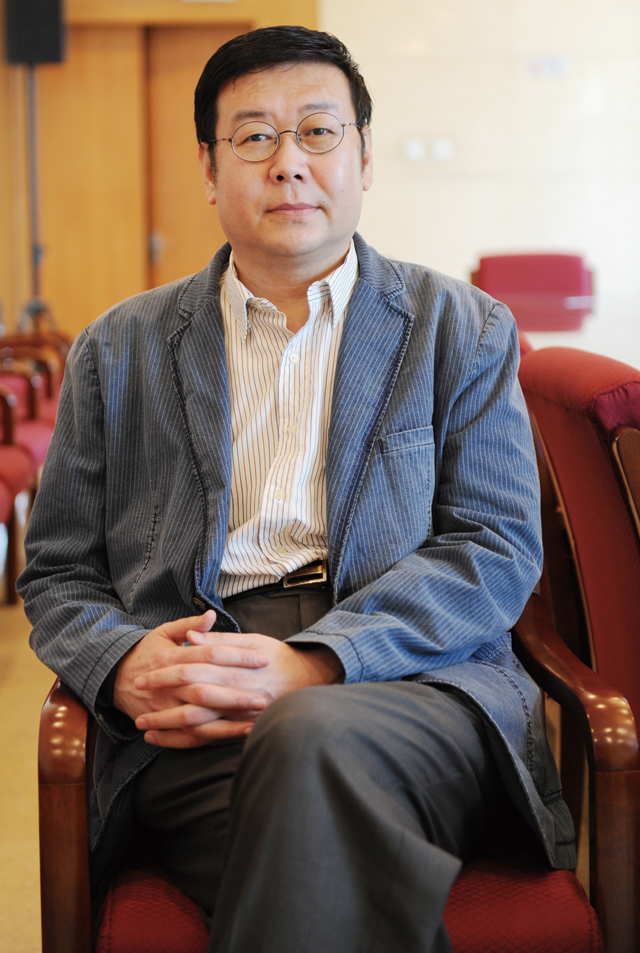

《回歸》

《北京大爺》

《名優(yōu)之死》

《風(fēng)雪夜歸人》
18歲啟航夢(mèng)想,41年執(zhí)著堅(jiān)守,92部舞臺(tái)作品……這背后是任鳴對(duì)戲劇的癡迷與難舍。任鳴常說(shuō):“我的人生第一個(gè)幸運(yùn)是考上中戲,第二個(gè)幸運(yùn)就是來(lái)北京人藝當(dāng)導(dǎo)演。”而1982年和1987年,正是改變?nèi)硒Q命運(yùn)的兩個(gè)時(shí)間點(diǎn),也是他戲劇人生大幕的開啟與真正的起步。進(jìn)入北京人藝后的任鳴依舊是幸運(yùn)的,29歲進(jìn)入北京人藝藝委會(huì),31歲有了自己獨(dú)立執(zhí)導(dǎo)的大戲,34歲成為劇院最年輕的副院長(zhǎng),54歲擔(dān)任北京人藝院長(zhǎng)……在外人看來(lái),任鳴的藝術(shù)成長(zhǎng)和發(fā)展之路似乎格外順利,缺少波折,但很少有人知道任鳴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的勤奮和付出、踏實(shí)與堅(jiān)定。“我不希望走捷徑,就愿意簡(jiǎn)單、本分、老實(shí)地走。”或許就是這種本分和老實(shí),才有了他戲劇匠人的定力和恒心,才結(jié)出了一個(gè)個(gè)他稱之為“幸運(yùn)”的藝術(shù)果實(shí)。在新中國(guó)成立70年之際,本報(bào)記者再次采訪了任鳴。在回顧自己創(chuàng)作歷程的同時(shí),任鳴多次強(qiáng)調(diào)自己對(duì)北京人藝的愛和責(zé)任,戲是演給觀眾看的,努力做北京人藝風(fēng)格的繼承者、發(fā)展者。這是一個(gè)管理者的擔(dān)當(dāng)與魄力,更是一個(gè)藝術(shù)家的純粹與初心。
“來(lái),我和人藝的未來(lái)干一杯”
記者:從1987年27歲進(jìn)入北京人藝工作到1994年34歲成為劇院最年輕的副院長(zhǎng),這期間在北京人藝除了獨(dú)立執(zhí)導(dǎo)大戲《回歸》外,您大多數(shù)的時(shí)間都是擔(dān)任副導(dǎo)演或者作為聯(lián)合導(dǎo)演參與劇目排演,而且參與排演的劇目類型不一、風(fēng)格多樣。這7年對(duì)您此后的創(chuàng)作帶來(lái)了哪些影響?
任鳴:這是我從事導(dǎo)演工作非常重要的學(xué)習(xí)期、積累期。1987年我中戲畢業(yè)剛剛進(jìn)入北京人藝的時(shí)候,老一代的大藝術(shù)家都在,我給自己定的目標(biāo)就是要好好學(xué)習(xí),認(rèn)真吸收人藝優(yōu)秀表演藝術(shù)家的優(yōu)點(diǎn)和長(zhǎng)處。這期間,院領(lǐng)導(dǎo)一方面給我創(chuàng)造了很多與國(guó)外優(yōu)秀導(dǎo)演合作的機(jī)會(huì),另一方面安排我同林兆華等人藝的優(yōu)秀導(dǎo)演合作、學(xué)習(xí),更為重要的是還給了我獨(dú)立導(dǎo)演實(shí)踐的機(jī)會(huì)。7年里,我做過助理導(dǎo)演、副導(dǎo)演、聯(lián)合導(dǎo)演,可以說(shuō),導(dǎo)演的培養(yǎng)之路走得很穩(wěn)健。到1991年劇院給了我單獨(dú)排戲的機(jī)會(huì),那是我第一個(gè)獨(dú)立執(zhí)導(dǎo)的大劇場(chǎng)戲《回歸》。當(dāng)時(shí),我是去呂齊老師家里請(qǐng)他參加演出,呂齊老師說(shuō):“本來(lái)我是不想演了,但是你來(lái)邀請(qǐng)我,而且你是年輕導(dǎo)演,第一次排戲,我支持你。我接了。”進(jìn)劇組后,呂齊老師又跟劇組其他演員說(shuō):“任鳴是年輕導(dǎo)演,而且是第一次排戲,我們都應(yīng)該支持他。”全劇發(fā)生在一個(gè)寫實(shí)景里,地點(diǎn)則是一個(gè)老頭的家里,但那時(shí)我排的時(shí)候沒有走寫實(shí)的路子,而是采用了以旋轉(zhuǎn)的大唱片為主的象征、寫意的景。其實(shí),當(dāng)時(shí)于是之老師還是希望做一個(gè)寫實(shí)的景,他覺得為什么要做一個(gè)老唱片在舞臺(tái)上,而且唱片一旋轉(zhuǎn),演員在上面表演有點(diǎn)暈。我就使勁給他解釋這樣做景的好處,最終是之老師同意了我的構(gòu)思。我想他內(nèi)心深處可能并不認(rèn)同這樣的處理方式,但是作為支持、鼓勵(lì)年輕導(dǎo)演大膽創(chuàng)作,他還是同意了。由此看出是之老師的胸懷和大度。其實(shí),剛進(jìn)劇院的那些年,我并不著急獨(dú)立排戲,就想多積累、多參加藝術(shù)實(shí)踐,把自己看作一名藝術(shù)的學(xué)徒。1989年2月11日,是之老師提名29歲的我成為了北京人藝藝委會(huì)成員。那時(shí)藝委會(huì)里全是德高望重的藝術(shù)家,他們?cè)谝黄饘徔磩”尽⒂懻搫∧俊⒁?guī)劃劇院發(fā)展方向等,我有幸參加了藝委會(huì)每一次討論。藝委會(huì)上,我只是認(rèn)真學(xué)習(xí),不敢發(fā)言,但是之老師卻經(jīng)常點(diǎn)名讓我發(fā)言,就想聽聽年輕人的看法。慢慢地,我也從拘謹(jǐn)?shù)礁矣趯?duì)一些問題發(fā)表自己的看法。我知道這是院領(lǐng)導(dǎo)在想盡一切辦法培養(yǎng)我。按照是之老師的說(shuō)法就是要“熏”我,“這孩子得‘熏’”。記得在《海鷗》演出完的慶功酒會(huì)上,是之老師來(lái)到我旁邊敬酒說(shuō):“來(lái),我和人藝的未來(lái)干一杯。”那個(gè)時(shí)期我很努力,就是不想辜負(fù)劇院對(duì)我的培養(yǎng)。
記者:這7年也是話劇發(fā)展的一個(gè)重要時(shí)期。一方面,上世紀(jì)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話劇遭遇了生存的危機(jī),另一方面,以牟森、孟京輝為代表的實(shí)驗(yàn)戲劇漸成氣候,以全新的藝術(shù)語(yǔ)匯進(jìn)行著迥異于傳統(tǒng)的探索。身處這樣一個(gè)觀念碰撞的時(shí)代,您又是如何給自己的導(dǎo)演風(fēng)格進(jìn)行定位的?
任鳴:上世紀(jì)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戲劇創(chuàng)作的思維還是很活躍的,那時(shí)有各種各樣的戲劇觀念、戲劇流派、探索戲劇、實(shí)驗(yàn)戲劇。我看了不少這樣的探索作品,也在觀察、思考我應(yīng)該走一個(gè)什么樣的道路?但當(dāng)時(shí)我很明確,這些肯定不是我的路子。我看到了一些實(shí)驗(yàn)戲劇作品藝術(shù)表達(dá)、舞臺(tái)呈現(xiàn)上的閃光點(diǎn),同時(shí)我也產(chǎn)生了疑問,那就是這些作品能不能持久?畢竟那個(gè)年代的創(chuàng)作還沒有那么商業(yè)化,不用考慮太多的票房和市場(chǎng)壓力。但我不屬于顛覆戲劇、前衛(wèi)戲劇那一類型的導(dǎo)演。我比較適合北京人藝的路子,也在自覺地研究北京人藝的作品和風(fēng)格。這跟一個(gè)人的世界觀、人生觀有很大的關(guān)系。我覺得應(yīng)該走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相結(jié)合的創(chuàng)作之路,舞臺(tái)上既有傳統(tǒng)的東西,同時(shí)也不放棄創(chuàng)新探索。
“戲首先應(yīng)該活在當(dāng)下,然后再求永生”
記者:1995年,您獨(dú)立執(zhí)導(dǎo)的話劇《北京大爺》可以看作是您的成名作。該劇至今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僅僅是林連昆的表演,還有德仁貴一家人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大潮沖擊下,內(nèi)心世界、傳統(tǒng)觀念產(chǎn)生的震動(dòng)。當(dāng)時(shí)是如何發(fā)現(xiàn)這個(gè)劇本的?
任鳴:《北京大爺》的劇本是劉錦云老師給我的。那時(shí),他是第一副院長(zhǎng)。是之老師也看了劇本說(shuō)很好。我拿到劇本一看,發(fā)現(xiàn)這正是我一直在尋找的京味兒話劇劇本。這是我獨(dú)立排的第一個(gè)京味兒話劇。談劇本階段,是之老師、錦云老師和我跟編劇中杰英老師一塊兒談。由此可見,這個(gè)戲得到院領(lǐng)導(dǎo)相當(dāng)大的支持。等劇本修改好了,錦云老師問我,你想讓誰(shuí)演啊?我說(shuō)希望邀請(qǐng)林連昆老師演德仁貴。那個(gè)時(shí)候,林連昆老師的身體不是特別好。我也不知道最終能不能實(shí)現(xiàn)合作。正巧,林連昆老師在劇院演出一個(gè)戲,我就親自去后臺(tái)找他,跟他說(shuō)有一個(gè)特別好的劇本,希望他能來(lái)演。林連昆老師說(shuō):“我知道有這么一個(gè)本子,是《北京大爺》,藝委會(huì)也討論了。我就是身體不是特別好,但我還是要演出,要支持年輕導(dǎo)演。”我沒想到林連昆老師答應(yīng)得這么爽快,這么支持我的工作。
《北京大爺》前前后后排了近半年,因?yàn)橹虚g趕上演員的兩次外出演出,無(wú)形中增加了排練的周期,這讓我對(duì)這個(gè)戲也有了很長(zhǎng)時(shí)間的思考。《北京大爺》講的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剛剛起步時(shí)期的北京,也是我特別喜歡的京味兒題材,故事性特別強(qiáng)。這個(gè)戲的優(yōu)點(diǎn)在于很好地記錄了時(shí)代,提出了深刻的社會(huì)及人的問題,猶如一面鏡子。舞美的景也做得特別寫實(shí)、精致,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的環(huán)境。這部作品是我的成名作。后來(lái),我們?nèi)メt(yī)院看望曹禺院長(zhǎng),他握著我的手說(shuō):“聽說(shuō)《北京大爺》演得很好,是京味兒戲,又帶有北京人藝風(fēng)格。”接著,他說(shuō)了對(duì)我此后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的三句話:“首先,戲是演給觀眾看的,一定要讓觀眾懂;其次,北京人藝一定要有自己的風(fēng)格,不斷地繼承和發(fā)揚(yáng)才能走下去;最后,要好好學(xué)習(xí)焦菊隱。”有這些話劇前輩的支持和鼓勵(lì),我感到既幸運(yùn)又幸福。我常常說(shuō),我的人生第一個(gè)幸運(yùn)是考上中戲,第二個(gè)幸運(yùn)就是來(lái)北京人藝當(dāng)導(dǎo)演。
記者:從這個(gè)劇本的選擇看,您特別重視戲劇與時(shí)代之間的關(guān)系,注重演出與當(dāng)代觀眾的交流,這是不是跟您的戲劇觀有直接的關(guān)系?
任鳴:任何劇本都是為當(dāng)下的觀眾服務(wù)的,戲首先應(yīng)該活在當(dāng)下,然后再求永生,如果你連活在當(dāng)下都做不到,何談?dòng)郎N夷玫饺魏蝿”臼紫纫磳?duì)今天的觀眾是否有意義和價(jià)值,不單單是滿足個(gè)人的需要。導(dǎo)演必須明白作品的時(shí)代和他自己所處的時(shí)代,在兩個(gè)時(shí)代之間尋找到通道,尋找到共同點(diǎn)。落后時(shí)代與超前時(shí)代都會(huì)被拋棄、被淘汰。只有同步是最能產(chǎn)生共鳴,最能存在下去的。落后與超前是一個(gè)命題,而導(dǎo)演把握這個(gè)分寸是非常重要而關(guān)鍵的。脫離時(shí)代,就會(huì)喪失觀眾,太超前的作品往往也不被時(shí)代和觀眾所理解。當(dāng)然話劇作品是需要時(shí)間來(lái)檢驗(yàn)和證明的,但也不能講我們的戲是為20年、50年之后的觀眾看的,只有50年之后的觀眾才能看懂,這也是故弄玄虛,無(wú)法證明的,是形而上學(xué)的表現(xiàn)。藝術(shù)上想不朽的東西往往會(huì)速朽,想在歷史上見的東西常常煙消云散。自己是決定不了的,只有時(shí)間才能夠回答和證明。我們必須認(rèn)真研究自己所處的時(shí)代,讓作品與時(shí)代同行。
記者:從《北京大爺》開始,到后來(lái)的《金魚池》《北街南院》《全家福》再到如今的《玩家》,您實(shí)際上也在持續(xù)探索“京味兒”在不同時(shí)代的表達(dá)方式。您是如何理解話劇的“京味兒”特色的?《玩家》中您又是如何在求新上進(jìn)行實(shí)踐的?
任鳴:由于我生長(zhǎng)在北京,對(duì)京味兒文化有著特殊的感情,看不膩、導(dǎo)不膩、研究不膩。記錄北京,記錄北京的變化、北京人的變化、北京景的變化、北京語(yǔ)言的變化,是我排演京味兒話劇的主要目的,也體現(xiàn)了我對(duì)京味兒話劇的思考。而在這類風(fēng)格話劇的探索上,有兩部作品是比較重要的,一個(gè)是《王府井》,這個(gè)戲更強(qiáng)調(diào)民族化,另一個(gè)是《玩家》,這個(gè)戲有很多表現(xiàn)主義、象征主義、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東西,用的現(xiàn)代因素比較多。從內(nèi)容上看,《玩家》表現(xiàn)的東西是豐富的,特別表現(xiàn)了外地人在北京的特點(diǎn),展現(xiàn)北京的開放性、國(guó)際性。過去的不少京味兒作品更多是講述老北京的往事。我要努力記錄的是新北京,記錄北京近年來(lái)的新變化、新精神、新面貌。過去我的創(chuàng)作強(qiáng)調(diào)的是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結(jié)合,通過《玩家》等新京味兒話劇的探索,我今后要追求更多的是傳統(tǒng)與更加開放的現(xiàn)代相結(jié)合。一個(gè)劇院如果想生存有活力,必須有一種開放的、現(xiàn)代的胸襟。人藝不是古玩店,更不是博物館。所以為什么《玩家》最后,我讓靳伯安把所有假的花瓶都砸碎,并說(shuō)了“把假的都砸了,真的就來(lái)了”這樣一句極富寓意性的臺(tái)詞,原因之一是為了求真,原因之二為了證明靳伯安的魄力、一種“破”的精神。只要是假的或者不好的東西,我都要去打碎。不破不立,這代表一種一往直前的勇氣。所以《玩家》代表了新京味兒話劇的開放性和現(xiàn)代性。當(dāng)然,它還有批判性,講收藏,又超越收藏,講玩家,又超越玩家,這也是這部作品的深刻所在。
“把中國(guó)話劇的經(jīng)典作品排好,
建立起我們自己的經(jīng)典體系”
記者:2009年,49歲的時(shí)候,您導(dǎo)演了歷史劇《知己》。在這之前,似乎您很少在大劇場(chǎng)涉獵歷史劇,這跟您的人生閱歷和藝術(shù)體驗(yàn)有關(guān)嗎?又是什么動(dòng)力推動(dòng)您把《知己》搬上舞臺(tái)?
任鳴:在《知己》之前,我確實(shí)沒有排過歷史劇,這個(gè)可以追蹤到我在中戲?qū)W習(xí)的5年。我在中戲就沒有排過歷史劇。我那時(shí)對(duì)歷史劇沒有那么濃厚的興趣,總覺得歷史劇的節(jié)奏緩慢,沒有發(fā)現(xiàn)歷史劇的妙處。進(jìn)入北京人藝后,我也很少去觸碰這類劇目。我所說(shuō)的歷史劇,主要是古典戲或者再具體一點(diǎn)就是中國(guó)的古典歷史劇。除了節(jié)奏問題,我覺得歷史劇的難度還在于,你要有非常多的歷史積累,需要研究大量的歷史資料。這些都不是我的強(qiáng)項(xiàng)。直到郭啟宏先生把《知己》這個(gè)劇本給我。我本來(lái)是抱著試試看的態(tài)度去嘗試的。因?yàn)檫@是一個(gè)好劇本,但是我依然沒有太大的把握。于是,前期下了很大的工夫,把能看的、能夠搜集到的歷史資料都看了。《知己》講的是朋友、友誼,是個(gè)典型的文人戲、知識(shí)分子戲,是個(gè)相對(duì)來(lái)說(shuō)比較高級(jí)的戲。但排完后呈現(xiàn)在舞臺(tái)上的效果出乎意料,沒想到受到了觀眾的歡迎。通過這個(gè)戲,我發(fā)現(xiàn)歷史劇也能夠排得非常深刻,而且還可以特別民族化。也是從《知己》開始,我對(duì)歷史劇的看法發(fā)生了巨變。《知己》也為我今后的創(chuàng)作打開了另一扇門。我發(fā)現(xiàn)歷史劇里面有那么多的東西可以借著中國(guó)歷史和文化去表達(dá)。
記者:從《知己》到后來(lái)的《我們的荊軻》《司馬遷》,連續(xù)三部歷史劇,三種歷史的表達(dá)方式,但在舞臺(tái)呈現(xiàn)上,都體現(xiàn)了您一脈相承的風(fēng)格。我也注意到您把這些作品的探索稱為“東方戲劇”。如何理解東方戲劇的內(nèi)涵,與《蔡文姬》《武則天》等劇作相較,這些作品在民族化的追求上又有哪些新的突破?
任鳴:從《知己》開始,我就在有意識(shí)地探索歷史劇表達(dá)的東方化問題。在我看來(lái),“東方戲劇”應(yīng)該是具有東方的戲劇思想、戲劇美學(xué)、哲學(xué)思想和表現(xiàn)手段,以民族化為基礎(chǔ),能夠更廣泛代表東方文化精髓的舞臺(tái)表現(xiàn)風(fēng)格,是東方美學(xué)精神與舞臺(tái)戲劇的結(jié)合。同時(shí),這一審美風(fēng)格不應(yīng)與舞臺(tái)表達(dá)的現(xiàn)代精神構(gòu)成沖突。歷史劇同樣可以在內(nèi)容上使作品深刻。此外,通過排演歷史劇,我也在逐漸解決節(jié)奏的問題。繼承傳統(tǒng)的、民族的東西很重要,發(fā)展傳統(tǒng)的、民族的東西更為重要。《蔡文姬》是焦菊隱先生民族化的寶貴實(shí)踐,到了我們這一代人,一方面要繼承好,另一方面要對(duì)戲劇有新的發(fā)現(xiàn)、新的認(rèn)識(shí)和新的發(fā)展,尋求一種藝術(shù)觀念和境界上的突破。我們不僅要在戲劇中表現(xiàn)中國(guó)傳統(tǒng)戲曲的元素,更應(yīng)該探索一種涵蓋東方戲劇的美學(xué)精神和戲劇追求,甚至在其中表達(dá)一種東方的哲學(xué)精神。總之,我在創(chuàng)作上有兩個(gè)是永不放棄的,一是對(duì)京味兒戲的探索,二是從民族化到東方化的實(shí)踐,追求歷史劇創(chuàng)作的新高度,向著新的經(jīng)典邁進(jìn)。
記者:重新復(fù)排、搬演中外經(jīng)典作品也是您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一個(gè)重要領(lǐng)域。像《日出》《風(fēng)雪夜歸人》《名優(yōu)之死》等都是搬演經(jīng)典中值得關(guān)注的作品。這些作品給我的感覺是“老戲不老”、“常演常新”,特別是最新演出的《名優(yōu)之死》。您是如何看待經(jīng)典作品的示范作用的?
任鳴:經(jīng)典是歷史文化的積累,中國(guó)話劇一定要保持傳承自己經(jīng)典作品的傳統(tǒng)。所以我希望把中國(guó)話劇的經(jīng)典作品排好,建立起我們自己的經(jīng)典體系。否則舞臺(tái)上總是莎士比亞、莫里哀、契訶夫、奧尼爾等外國(guó)戲劇家的作品,從世界看,這些劇作家當(dāng)然是寶貴財(cái)富,但我們自己也有寶貴財(cái)富,像曹禺、老舍、田漢、吳祖光等等。把我們民族好的傳統(tǒng)、經(jīng)典拿出來(lái),通過加工、改造、再創(chuàng)造,使其更有生命力和活力,這也是經(jīng)典作品示范作用的一種表現(xiàn)。而對(duì)待經(jīng)典作品不能盲目照搬,必須有很高的藝術(shù)性去創(chuàng)造、呈現(xiàn)。《風(fēng)雪夜歸人》和《名優(yōu)之死》是我在經(jīng)典新排方面做的比較成功的例子。《風(fēng)雪夜歸人》既忠實(shí)原作又創(chuàng)新,走的是唯美的路子。《名優(yōu)之死》在原有的故事、人物、語(yǔ)言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了新的再創(chuàng)造,使這個(gè)老劇本獲得新生。它沒有走老戲的路子,從導(dǎo)演構(gòu)思到舞臺(tái)呈現(xiàn)都有原創(chuàng)思維和理念,不落套路。它不像任何一個(gè)戲,只像它自己,是一個(gè)孤立的存在。它無(wú)論是內(nèi)容和形式都是新生的,有一種老戲獲新生的重生感。此外,在話劇的民族化和借鑒戲曲精粹上,該劇也做到了極致。話劇中見京劇,京劇中見話劇,二者高度有機(jī)地融合于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wú)法分離;戲中唱、念、做、打及鑼鼓經(jīng)都得到充分運(yùn)用,大量的京劇元素和技法,包括京劇的美學(xué)原則和程式,既讓觀眾感到京劇的博大精深,又符合現(xiàn)代觀眾的審美和欣賞特點(diǎn)。《名優(yōu)之死》也為我今后打開了又一扇創(chuàng)作的大門。
“人藝要有大的格局和精神境界”
記者:縱觀您的創(chuàng)作,雖然根據(jù)文學(xué)作品改編的劇目特別少,但您又是與作家合作最多、對(duì)劇本的文學(xué)性重視最多、對(duì)演出的思想性思考最多的導(dǎo)演,這應(yīng)該看作是北京人藝話劇創(chuàng)作的一個(gè)寶貴傳統(tǒng)。您是如何看待文學(xué)與戲劇之間關(guān)系的?
任鳴:的確像你說(shuō)的,我改編文學(xué)作品的劇目特別少,僅有《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心靈游戲》兩部作品。其實(shí),我是特別想走這條路,但是難度很大。到目前為止,我看到的文學(xué)作品改編話劇最成功的例子是曹禺先生的《家》和梅阡先生的《駱駝祥子》。其他的改編作品不是沒有成功,而是很少達(dá)到上述作品的藝術(shù)高度。我也一直在通過各種渠道尋找這類創(chuàng)作的契機(jī),卻又找不到很好的改編路徑。后來(lái),每次跟小說(shuō)作者談的時(shí)候,我就有一個(gè)結(jié)癥,總是抱著這么一個(gè)想法:好的小說(shuō)改成話劇后,極少數(shù)是能比原著好的。當(dāng)你的小說(shuō)寫得已經(jīng)很成功了,再怎么改也不如小說(shuō),因?yàn)閼騽∫呀?jīng)不是第一創(chuàng)作了。真正在舞臺(tái)上成功的戲應(yīng)該是第一創(chuàng)作的。我希望作家能直接給我劇本,而不是讓小說(shuō)的原作壓著。當(dāng)然,您的問題也啟發(fā)了我,可能會(huì)在今后嘗試打通這條道路。
我特別看重劇本的文學(xué)性。我始終認(rèn)為,劇院的傳承靠的是劇目,《茶館》《雷雨》《天下第一樓》等經(jīng)典作品是一代一代演員在傳承,而不是靠某一個(gè)人在傳。跟京劇的流派不同,劇院依靠的是保留劇目和經(jīng)典劇目。每一版演員表演會(huì)有自己的風(fēng)格,但劇目是永遠(yuǎn)在那里的,而能成為保留劇目的作品都有深厚的文學(xué)底蘊(yùn)和扎實(shí)的文學(xué)功底。如果劇本的文學(xué)性不強(qiáng),只是借名演員勉強(qiáng)支撐,一旦名演員不演了,這個(gè)戲的生命就結(jié)束了。在某種程度上,話劇既是表演的藝術(shù),也是劇本的藝術(shù)。
記者:今年是新中國(guó)成立70周年,也是北京人藝成立67周年。北京人藝可以說(shuō)是與新中國(guó)一同成長(zhǎng)的劇院。對(duì)于今天的話劇人而言,把前輩藝術(shù)家奠定的優(yōu)秀傳統(tǒng)繼承好、發(fā)展好,就是對(duì)歷史的最大尊重。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您認(rèn)為,當(dāng)下的演員應(yīng)該從老一代藝術(shù)家身上汲取哪些經(jīng)驗(yàn)?
任鳴:首先要學(xué)習(xí)對(duì)藝術(shù)的熱愛和敬畏精神。人藝的精神第一是戲比天大,第二是對(duì)藝術(shù)永遠(yuǎn)懷有敬畏之心,第三是在藝術(shù)上精益求精。人藝有自己的風(fēng)格,也有自己的精神。其次,從藝術(shù)上的繼承看,永遠(yuǎn)要講究對(duì)人物形象的塑造,永遠(yuǎn)追求臺(tái)詞的藝術(shù)性。當(dāng)然,我們也要講深厚的生活積累、深刻的生活體驗(yàn)等,但是更重要的還是要抓住人物和語(yǔ)言。這是人藝所有優(yōu)秀表演藝術(shù)家的特點(diǎn)。當(dāng)年,在排演《北京大爺》的時(shí)候,我受益最大的就是林連昆老師的表演。他多次跟我談,人物是最重要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戲劇是有長(zhǎng)久生命力的。戲劇最重要的是演人物。林連昆老師是優(yōu)秀的表演藝術(shù)家,跟他合作我看到了表演的高度。讓我體會(huì)到一個(gè)好演員是如何攀登表演的高峰的,看到了高級(jí)的表演是什么,懂得欣賞優(yōu)秀的表演是什么樣的。我希望北京人藝新一代的演員一定要善于鉆研角色,研究人物,要培養(yǎng)自己的藝術(shù)個(gè)性和風(fēng)格。
記者:近20多年,圍繞北京人藝風(fēng)格的探討已經(jīng)非常多了,其中也不乏爭(zhēng)鳴,有對(duì)北京人藝風(fēng)格在當(dāng)下傳承的質(zhì)疑聲音。傳統(tǒng)對(duì)您而言,是包袱還是財(cái)富?
任鳴:人藝風(fēng)格絕對(duì)是財(cái)富。對(duì)于有創(chuàng)造的、勇敢的藝術(shù)家來(lái)說(shuō),當(dāng)他的前輩能有那么豐厚的風(fēng)格和藝術(shù)積累的話,這絕對(duì)是金山銀山,關(guān)鍵是如何吸收好、發(fā)展好和創(chuàng)新好。任何的繼承都不是為了繼承而繼承,都是為了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而繼承。藝術(shù)家一定要具有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的能力。如果死守著傳統(tǒng)不放,保守而不創(chuàng)新,北京人藝的發(fā)展是沒有活力的。在這方面,《名優(yōu)之死》的實(shí)踐比較好的解釋了這個(gè)問題。人藝是豐富的,不能狹隘,要有大的格局和精神境界。人藝的發(fā)展不在于喊口號(hào),而是用一部部作品來(lái)證明你的格局和精神。追求新的經(jīng)典作品是我們最大的奮斗目標(biāo)。要拿優(yōu)秀作品說(shuō)話,把培養(yǎng)演員跟創(chuàng)作新經(jīng)典結(jié)合起來(lái)。
記者:您把戲劇集的第一本書命名為《導(dǎo)演的思想》,提出“導(dǎo)演最重要的是——思想”。其實(shí),不僅導(dǎo)演需要“思想”,戲劇也是需要“思想”的。您是如何理解“思想”與“形式表達(dá)”之間的關(guān)系的?作為院長(zhǎng),未來(lái)在劇院建設(shè)方面,您又有怎樣的思考和規(guī)劃?
任鳴:一個(gè)劇院應(yīng)該有自己的思想性,而不是單純的藝術(shù)性。戲劇之所以能出現(xiàn)偉大的劇作家,就在于他們的作品不但有藝術(shù)的東西,還有深刻的思想。而導(dǎo)演是一臺(tái)演出的組織者和靈魂,你不能想象一個(gè)沒有思想的導(dǎo)演能排出好的作品。導(dǎo)演的思想決定了他的藝術(shù)高度,而藝術(shù)高度是決定作品品格和品質(zhì)的關(guān)鍵。高度決定了作品的存在價(jià)值。只有特立獨(dú)行,才會(huì)橫空出世脫穎而出。藝術(shù)創(chuàng)作需要千里走單騎的精神,永遠(yuǎn)是在孤獨(dú)中前行的。我們現(xiàn)在的很多戲劇作品藝術(shù)呈現(xiàn)是不錯(cuò)的,但在思想層面缺少深刻性。沒有精神能量的作品是無(wú)力的,而能量的匯聚是由美學(xué)和哲學(xué)的思想構(gòu)成的。我希望人藝是一個(gè)有思想的劇院,把深刻的思想融入到完美的藝術(shù)呈現(xiàn)當(dāng)中。2021年,北京人藝屆時(shí)將有5個(gè)劇場(chǎng),2400個(gè)座位。這些劇場(chǎng)會(huì)在人藝風(fēng)格的總體構(gòu)架下有不同的功能定位。那時(shí),人藝的劇場(chǎng)將演出各種各樣的戲劇,還會(huì)組織各種各樣的戲劇普及活動(dòng)。這也意味著人藝的胸懷和格局會(huì)更大、更寬廣。進(jìn)入新時(shí)代的人藝,前景將是非常美好的,對(duì)此我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