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長:扎迪·史密斯的小細節(jié)和大手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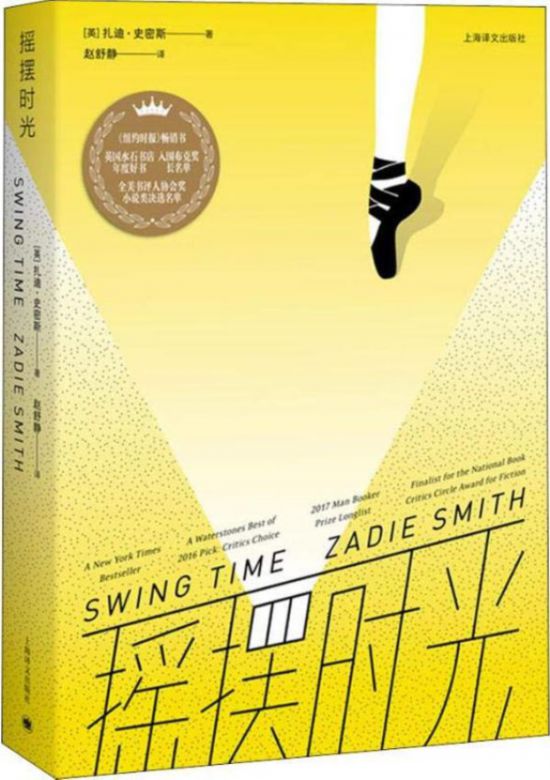
《搖擺時光》,[英]扎迪·史密斯著,趙舒靜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出版,456頁,65.00元
有一段時間,我不太愿意讀扎迪·史密斯的小說。
種族、膚色、階級以及多元的文明沖突,變成正確的文學(xué)修辭之后,對我來說并不是具共鳴乃至共情的因子。一個人對不曾經(jīng)歷過的事情,要生出切身且準(zhǔn)確的體驗,光靠文學(xué)想象是不夠的。被賦予的文學(xué)意義,也因為缺乏生命感受,變成了隔鞋撓癢的附麗。扎迪·史密斯并不像奈保爾和康拉德那樣具有強大的原生力量,足以讓人忘記背井離鄉(xiāng)和不同民族的文明在文字上打上的烙印。當(dāng)然,她也沒有身份剝離和彌合的深刻體驗。
就像扎迪·史密斯出生在倫敦這一基本情況,常被人提起,做一些額外的文化分析。父親是白人,母親是黑人,她是混血兒。諸如不同膚色的融合會產(chǎn)生什么故事?倫敦街區(qū)混血兒的成長隱藏著多少隱為人知的秘密?文化的沖突怎樣影響著他們與社會建立聯(lián)系?如果可以不談這些,那我對她白人父親與黑人母親的婚姻故事更感興趣,對小扎迪作為普通孩子的成長更感興趣。父親所遇到的難處,比作為小孩子的扎迪,可能還要復(fù)雜,也更富戲劇性。
遇見《搖擺時光》,我嘗試回到小說本身,去到人物身邊,感受小說細節(jié),我發(fā)現(xiàn)了扎迪的奇妙之處。這是一種放棄尋找文學(xué)意義、沉浸于閱讀本身的愉悅。當(dāng)我忘記作者是誰,忘記她被人談?wù)摰哪w色標(biāo)簽,我獲得的是有別于他人的閱讀體驗,這是忠于自己的補償。
如此一來,我就漸漸理解詹姆斯·伍德的毒舌了,他就忠于自己的閱讀感受。在他眼里,扎迪·史密斯的《白牙》呈現(xiàn)出了部分歇斯底里現(xiàn)實主義的特征,譬如故事套故事,讓人目不暇接,永不停歇。這向哪兒說理去?伍德的這一飛刀,來得力道十足。好在真誠的伍德先生也承認,扎迪的作品當(dāng)然不是全無是處,最好的地方,是她接近人物,并賦予他們?nèi)诵裕≌f細節(jié)往往具有說服力,既有趣,又感人。這是伍德的可愛之處,批評歸批評,好的地方不能一并抹掉。真誠又準(zhǔn)確的批評不是以毀掉作品為己任,相反應(yīng)該努力提供一種方法,以便讓讀者更好地理解一部作品,靠近一個小說家,繼而形成自己的判斷。不然的話,批評家辛苦的工作,變成了替讀者嘗嘗菜,也了無生趣。
在《搖擺時光》中,我感受到了扎迪·史密斯筆下具有的伍德提到的這種能力。扎迪不僅有能力捕捉和刻畫細節(jié),寫人物可以做得跟蠟像一樣纖毫畢現(xiàn),更有能力在尋常的細節(jié)上往前多走一步。就這一小步就體現(xiàn)出了她的小說才華。
舉一個例子:“彈鋼琴的人叫布思先生。他彈琴時我響亮地跟著哼唱,哼唱時加了不少顫音,希望有人聽見。”
這個小小的細節(jié),不是什么大事件,在寫作技巧而言,就是喬伊斯·卡洛爾·奧茨所言的大手筆。小說家寫一個小女孩,參加跳舞班,跳得并不出色,但她會唱歌,唱得很不錯,于是就有了這個細節(jié)。多在哪一步?最后一句,加了顫音,為的是“希望有人聽見”。將一個小女孩的內(nèi)心寫得隱秘又到位,以這樣微小的動作,希望被人注意,被人發(fā)現(xiàn)。寫到顫音,是很多小說家可以做到的,這是小說細節(jié)鋪設(shè)的基本功。多一句“希望有人聽見”,就捕捉到了孩子、少年身上較為普遍的心事。一個內(nèi)心再驕傲的孩子,都期望獲得肯定。我們的小時候不是一樣?為了引人注意,故意大聲說話,假裝無意地表達,這是共鳴的基礎(chǔ)。
這是一個極小的細節(jié),細微到你一不留神就可能錯過去了,完全不會影響閱讀整部小說。差別在于,若是體會到其中精微的奧妙,會收獲更多的閱讀愉悅。別小看這個細節(jié),理解了小說人物身上的這個細節(jié),就可能理解她的性格、心事和長大后的個人生活。小說生活的確如此,小女孩長大了,直到三十多歲,小半生都在小心翼翼地發(fā)出自己的“顫音”,期望有人聽見,期望得到回應(yīng)。
再舉一個例子。孩子放學(xué)后,父母總要假裝親切地問,今天學(xué)校里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小說中的孩子說不出來,說不出父母就不放她一個人去玩,就開始無師自通地編撰:“我把他們想象成兩個孩子,比我還天真無辜,我有責(zé)任保護他們,讓他們不舒服的事情我就不說,省得他們胡思亂想(我媽)或多愁善感(我爸)。”
這樣的小說細節(jié)具有生活質(zhì)地,以及一種普遍的概括性。如果停留于說學(xué)校的事,或者抵抗不說,與父母產(chǎn)生對抗,就顯得一般了。扎迪·史密斯反其道而行之,往前多走了一步,不但要說,還是以保護家長的方式,虛構(gòu)地說,而且報喜不報憂,省得兩個大人胡思亂想。這樣一來,家長和孩子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發(fā)生了對調(diào),父母成了被安慰的對象,孩子成了主角。
這樣的細節(jié)還有許多,扎迪·史密斯的教科書般的小說技術(shù),與生俱來的敘事天賦,以及對生活河流的流向,在這部小說中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如果有心,每一段都值得細讀。正如伍德所提醒的,一旦意識到扎迪賦予小說人物的人性,便能體會到小說家施工過程的樂趣,借助這些細微的小說細節(jié),我們得以看清扎迪的搭建技術(shù)。這份樂趣是屬于小說本身的,是獨立于小說故事之外閃亮的掛件,惟有在專注的閱讀中,才可能獲得這份禮物。
一個人閱讀小說的能力,就在于是否能從尋常的細節(jié)中捕捉到樂趣,這也需要訓(xùn)練和提升,好在有專業(yè)讀者伍德先生,無償?shù)靥峁┓铰浴H绾慰创榈聦υ系脑u論,倒成了一種考驗了。歇斯底里的說法誠然具有喜劇性。是否真有讀者奉之為圭臬,天真地拿去衡量扎迪小說的藝術(shù)性,我是存疑的。事實上,大部分讀者在乎的還是人物性格和被伍德吐槽的故事。那些負責(zé)承擔(dān)意義的小說人物,得到更多的關(guān)注也就毫不意外了。
就像扎迪小說《搖擺時光》中的黑人母親,一個大器晚成的奮斗者,看書學(xué)習(xí),瘋狂考學(xué),勵志向上,變成了一個社會活動家,參政議政,從社區(qū)一步步走上政壇。將改變命運的機會握在手里,即便身染重病,也要表現(xiàn)得生機勃勃。與這樣的人生活在一起,自然辛苦。父親則要懶散得多,不思進取,不愛讀書,談不上事業(yè)心,本來做到了經(jīng)理,坐辦公室,卻申請重回到街上去當(dāng)郵遞員。凌晨三點起床,下午一點干完活兒回家。與母親的關(guān)系自然分崩離析。一個向上,一個往下。一個充滿斗志,一個安于庸常。
扎迪小說中的這對父母形象是否來自生活,并不是我們關(guān)心的重點所在。閱讀的愉悅并不都在將小說生活和真實生活進行對比。天天向上的母親,和不思進取的父親,一個黑人,一個白人,兩者之間的對照就自然地生成了張力。要考證這樣的父親和母親的象征意義,以及與倫敦的關(guān)系,也實在犯不著。就像布魯姆在《巨人與侏儒》中說的,“人是其處時代及場所中權(quán)威意見的囚徒,一切人由此開始,大多數(shù)人也在此結(jié)束”。小說生活同樣如此,如此顯而易見的事情沒有必要去求證,到底怎么個囚徒法兒。有瘋狂的囚徒,就有隨波逐流的囚徒。一本正經(jīng)的母親,和無所事事的父親,不過是兩種囚徒方式而已。為什么不單純地享受下這兩個小說人物身上可樂又分裂的性格和行事方式呢?
至于小說主角“我”的故事,偏于成長的記憶,以及成長中對未來的迷途。“真相顯露在我面前:我總是依附于別人的光,我從未有過自己的光。我的生活是影子。”這是《搖擺時光》中的句子。基本上就是這部小說要表達的主題。依附于別人的光,自己的生活是影子,這是怎樣的生活?我對此很好奇。如此“自傳”般的敘事,必然地會遵循一種敘事法則,就是從我出發(fā),去展示自己的生活和想象別人的生活。它不可回避地會染上迷茫的色調(diào),比如影子生活的比喻。這的確是趨于普遍性的人生描述,大多數(shù)人似乎都經(jīng)歷過這樣的童年和青年時光。小時候別人家的孩子,長大后別人家的青年,過得像背景一樣。
“你得知道你想要什么。你得去想象,然后去實現(xiàn)。”這是小說中成功人士的話。這話說對了一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般可以做到。去想象,去實現(xiàn),卻未必能夠可以。人總會走很多彎路。活出自我,不止取決于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更取決于能否實現(xiàn),實現(xiàn)不了應(yīng)當(dāng)如何面對,否則就是一句空話。
閱讀小說的魅力不止在于感受教益,或獲得某種精神支撐,更多的是觀看一段生活,或者將看別人如何生活。大部分的樂趣在于被描述的具有普遍性的生活細節(jié),如果毫無共鳴的可能,僅僅提供一個故事,也就顯得寡淡無趣了。hhhh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