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伊·麥金納尼:將生活的真相澄清為一種支離破碎

杰伊·麥金納尼(Jay McInerney),美國作家。1955年生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曾任職于美國《紐約客》雜志。1981年師從雷蒙德·卡佛和托拜厄斯·沃爾夫學習寫作。1984年,短篇小說集《如此燦爛,這個城市》出版,創(chuàng)造了口碑奇跡,暢銷至今,被譽為“1980年代的《麥田里的守望者》”。此后,他又陸續(xù)出版了《贖金》《我生活的故事》《最后一個野蠻人》《他們是怎樣玩完的》等著作,均大獲好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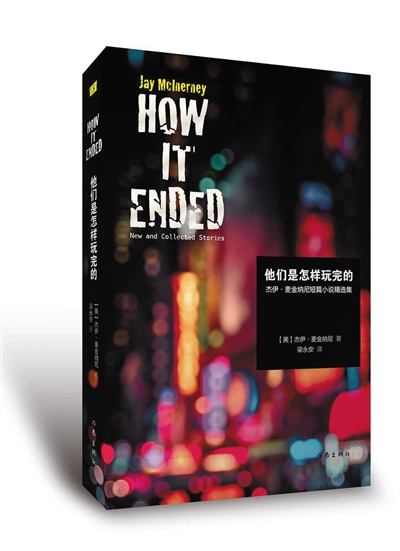
《他們是怎樣玩完的》 作者:(美)杰伊·麥金納尼 譯者:梁永安 版本:S碼書房|作家出版社 2019年1月
貝爾納·皮沃在《理想藏書》美國小說一欄下,將美國作家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以玄學作為回答,如麥爾維爾、弗蘭納里·奧康納和厄普代克”,第二類“打著最日常的現實主義牌,今天他們的代表是格雷斯·培利和雷蒙德·卡佛”,第三類是“去歐洲尋求出路,他們中不僅有1916年取得英國國籍的詹姆斯,以及不知不覺中獲取了波德萊爾式榮耀的愛倫·坡。他們中還有‘迷惘的一代’”。誠如唐·德里羅對歐洲與美國的比較,如果說歐洲是精裝書,那么美國僅僅是前者的平裝本;在文學上兩者的差異便表現在“美國小說家一般比歐洲同行更不拘于體裁限制”。一種標新立異的沖動使得在兩個時期的作品之間,除了它們保持的斷裂以外,人們找不到任何相似性。因為這個原因,皮沃對美國作家的分類就顯得不太準確:奧康納的玄學與厄普代克的玄學之間缺乏可茲比較的基礎,德萊塞的現實主義與卡佛的現實主義也毫無共通之處。也許唯一妥當的是第三類作家,但這也無非是因為戰(zhàn)后一代的美國作家,自羅伯特·佩恩·沃倫開始,他們對歐洲文學的認同便已然不再需要去分享那巴黎的盛宴。質而言之,用歷時性的眼光去看待美國文學史或者更為可靠。同一時期的作家之間也許有“家族相似性”,但不同時期的“文學家族”之間總是有著最大程度的斷裂和差異。現在言歸正傳。我們如何評價杰伊·麥金納尼呢?
最日常的現實主義
在他的短篇小說精選集自序中,麥金納尼供出了自己的文學師承:“我相當幸運能夠師從兩位精通小說形式的大師:卡佛和沃爾夫。”他在雪城大學專門進修過這兩位作家開設的寫作課程。除此以外,他對卡佛與沃爾夫的認同,他們發(fā)表小說的渠道,以及他們共有的經歷,似乎也決定了他們之間的家族相似性因素。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不只提到了他眼中美國作家的形象:他們“總忘不了聽從自己的直覺:他們不斷地鼓吹他們自己的想象,過分地擴展它,使之達到巨人的高度”,也提到了他對民主社會之于藝術創(chuàng)作影響的思考:“模仿美德是每一時代皆然的;但偽奢侈卻比較特別地屬于民主時代……藝術家的產品日見其多,每一件產品的價值卻在降低。藝術不再能飛升到偉大藝術的領域”。如果說托克維爾眼中的美國作家尚且還落實于霍桑、庫珀這些早期的奠基者身上,那么他對民主時代媚俗現象的觀察,則可以視為在將近一個半世紀之后徹底實現的預言。前者適用于從麥爾維爾到福克納這一派試圖以小說體裁去模仿史詩的作家(布魯姆稱之為“散文史詩”),但并不適用于生活在后一種預言徹底實現的社會中的那些人:英雄精神對他們筆下那些過早陷入生活泥潭的人來說,著實為遙不可及的一件事。
在接受《巴黎評論》采訪時,卡佛曾談到了生活對寫作的影響:“從來沒有人請我當作家,但在付賬單、掙面包和為生存而掙扎的同時,還要考慮自己是個作家并學習寫作,這實在是太難了。”某種程度上,這些人之所以喪失了托克維爾所謂的巨人的想象力,正因為他們的生活如此,而他們的寫作悖論似的成為挽救這種生活的方式。福克納同樣沉湎于酒精,會一邊灌威士忌一邊敲打字機,但他不會像卡佛那樣用筆記錄這些處在崩潰邊緣的人或事:一些借爛醉遺忘現實的人,一些整夜開著電視,無休無止地交談卻難以擺脫沮喪的人。這就是兩個文學家族之間的斷裂。卡佛也許會羨慕福克納這樣有地域感的作家,可是他也清楚自己“絕大部分小說都和特定的場所無關”。這些小說通常在室內展開(家宅、酒吧、格子間),然而這些地方終究不是“意義深重的土地”,而只是那被連根拔起的一代展開生活之處,同時也是美國藍領階層被生活壓迫得失去了歷史的地方。他們不僅喪失了得自于現代性早期的直覺與想象力,也無從抵抗自己的生活在現代性完成的時刻成為一出不斷上演的肥皂劇,就像約翰家的電視機每晚都會準時打開一樣。歸根結底,寫作對他們而言就是將生活的真相澄清為一種具體的支離破碎。在我看來,皮沃指出的晚近以來“打著最日常的現實主義牌”的美國作家,在他們身上盡管秉持著福樓拜的日常性一端,也大多意識到此時此地缺乏創(chuàng)造傳奇的必要,但主要原因卻無法歸入“日常生活正是全部”這一遁詞,而恐怕要更多地聯(lián)系到這一時代在他們身上造就的宿命論觀念。一言以蔽之,在他們這里,福樓拜曾經憎恨的中產階級生活,被從容地接納為一種先天正當的存在方式,甚至是夢想。
史詩寫作夢碎后的寫作
在麥金納尼的這本短篇小說集里,諸如此類的無可奈何與承擔比比皆是,然而無疑是比那個文學家族中諸位前輩涉及的領域更廣,且在層次上有著較為豐富的幻想性因素。他的筆下不僅容納了最底層無產者的呼喊,也涵蓋了各個階層、不同角色的現實生活景觀:政壇競選者身邊的人(《我的公職生涯》《池塘畔的潘妮洛碧》),監(jiān)獄醫(yī)生(《假醫(yī)生》),社交界的名媛(《簡易判決》),好萊塢編劇(《生意》)等等。縱向來看這一創(chuàng)作光譜,就會發(fā)現麥金納尼是從醉酒者不知歸處的迷惘出發(fā),一路寫到了更多看似也并不屬于他本己經驗以外的困惑。首先,在展示中產階級生活這一方面,他擅長處理兩性之間的細微情感,尤其是對于出軌通奸這一題材的偏愛,麥金納尼已然可以引厄普代克為同道。這一批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要遠遠優(yōu)渥于卡佛筆下的人物:餐廳女招待、倒霉的推銷員、頑劣的孩童、旅館清潔員、汽車修理工、失業(yè)者……可是也毫無疑問的,當欲望滿足之后,人們就會陷入精神危機的險境。上世紀60年代的《兔子,跑吧》如此,1985年的《抽煙》與2008年的《我愛你,甜心》亦然。在前一篇中,作者巧妙地將戒煙/復吸同忠誠/出軌對應起來,其中細膩之處,可堪擊節(jié);后一篇里,作者則是將主人公的出軌同“9·11”事件耦合在同一時間,大概只有在讀過之后人們方能理解那被摧毀的大廈同時也是忠誠的象征。
其次,在關于身體或心靈的流浪者的部分篇什中(《現在清晨六點,你知道你在哪嗎?》《皇后與我》),麥金納尼先前的平和心緒,轉瞬又被一種布考斯基式的激情所取代,即用命來迎接這個世界的一切恩賜與損害。事實上,這就是麥金納尼給我的最初感受:他的寫作雖然始于對卡佛與沃爾夫的禮贊,但最終呈現出來的形態(tài),卻介于厄普代克與布考斯基之間,他比后者彬彬有禮,但又比前者暴力一些。布考斯基曾經在《破商品》這篇小說里寫到過一個藍領弗蘭克,他的妻子每天例行公事般與他吵架,辦公室也有個助理經理不時尋釁開除他。弗蘭克在開車回家路上的一段感想非常富有代表性:“也許不需要那么趕。就算弗蘭在等著。一邊是弗蘭,另一邊是麥爾斯。他唯一需要獨處的時刻,唯一不會被壓迫的時刻,就是開車上下班的時候,或睡著的時候。”然而,這種對一塊緩沖地帶的要求,或者說對上岸喘口氣的渴望,在《看不見的籬笆》《火雞節(jié)日圣母》等篇章里,已經轉化為一種傳統(tǒng)意義上的家庭倫理的崩潰跡象。換言之,反諷、反抗、感傷、逃離、戲謔在此皆變得無關緊要,因為秩序正在不可逆地發(fā)生崩潰。
以此觀之——“就像大部分小說家,我寫短篇小說是為了練筆”——他在自序里說的這句話恐怕是誠實的,而這一點保證了麥金納尼在選擇題材時能夠持一種相對游刃有余的心境,同時也保證了他的寫作同時代精神之間的即時呼應。2015年謝世的E.L.多克托羅大概是美國最后一位“散文史詩”作家,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英雄精神已然早于多克托羅的謝世而成為這個時代(布魯姆稱之為“混亂時代”)中不合時宜的事情。不管怎樣,美國作家都曾經共享著同一個夢想,而時至今日,無論人們怎樣對它重新命名,亦無論如何重新確定這個詞的所指,至少從麥金納尼這部橫跨二十六年寫成的作品來看,那個夢已然無可懷疑地碎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