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人說中國 ——撰述《吾國與吾名》的2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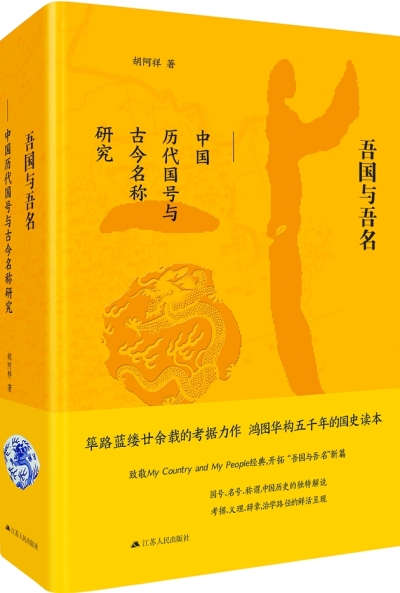
《吾國與吾名——中國歷代國號與古今名稱研究》 胡阿祥 著 江蘇人民出版社

“鎮(zhèn)國之寶”何尊的銘文中首次出現(xiàn)了“中國”一詞。圖片選自《吾國與吾名——中國歷代國號與古今名稱研究》
從1994年動筆寫作開題立意的《中國古今名號尋源釋意》,到2017年完成總結(jié)之作《吾國與吾名——中國歷代國號與古今名稱研究》,我在這個領(lǐng)域斷斷續(xù)續(xù)地耕耘,竟然已經(jīng)持續(xù)了24個年頭,其間出版了尤重考據(jù)與義理的《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面向大眾的《中國國號的故事》《正名中國:胡阿祥說國號》《中國名號與稱謂的故事》《祖國的名稱》,又在《百家講壇》主講了“國號”“國之名稱”兩個系列節(jié)目。回想起稿時節(jié),我還剛過而立之年,待到告別之時,我已年近耳順。一個研究領(lǐng)域與宣講課題,何以伴隨著我如此之長的學(xué)術(shù)生涯呢?
從兩個坊間流傳的故事說起
先說兩個坊間流傳甚廣、主角為中國人的外國國號“故事”。
晚清,在維新洋務(wù)人士的大力鼓噪下,西風(fēng)勁吹,西學(xué)猛漸。一位略聞新知的童生請教私塾先生:“何謂伽利略意大利人?”私塾先生回答:“伽利略的意思就是賺大錢的人。”
這位私塾先生望文生義,將“意大利”妙解為“意思就是賺大錢的人”;而頗涉洋務(wù)的李鴻章竟也鬧出笑話,當(dāng)他聽說“葡萄牙”時,驚訝地問道:“怎么葡萄也有牙?”
李鴻章沒有去過葡萄牙,而且葡萄牙這類譯名確實離奇古怪,難免李大人有此千古一問。不過值得肯定的是,李大人畢竟勇于提問,而勇于提問正是求得真知的途徑。筆者時常感到難解的是,在我已經(jīng)30多年的大學(xué)教書經(jīng)歷中,卻幾乎沒有大學(xué)生、碩士生、博士生提問這類問題。反之,筆者在課堂上常常問學(xué)生:“啟為什么用夏作為國號?劉邦為什么定國號為漢?時時接于目、聞于耳的華夏、中國、中華、China又是什么意思?”滑稽的是,如此等等的相關(guān)問題,同學(xué)們往往語焉不詳;再問英吉利、不丹、伊拉克、土耳其、美利堅、法蘭西、烏干達(dá)……同學(xué)們就更加啞口無言了!
英吉利、不丹、伊拉克等,暫且不去管它。起碼我們自己的夏、商、周,以至元、明、清,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些國號的來源取義,還是應(yīng)該知道的。畢竟,我們的遠(yuǎn)祖生長在夏、商、周,我們的祖先生長在元、明、清,我們生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我們的子孫也要生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此,對于這一連串的國家大號,我們豈可不知,焉能不解!
其實,即便不談學(xué)問,探求中國歷代國號的來源取義,也是一件特別富有趣味的事情。夏、商、周等以至元、明、清,中國、華夏、中華等等,也許我們太耳熟能詳了,往往想不到要對它們“打破砂鍋問到底”,而一旦“打破砂鍋問到底”,以我的切身感受,那是奧妙無窮、極有意思的。這種情況,似可比附一下東漢劉熙的《釋名》。昔劉熙撰《釋名》,其自序云:“夫名之于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義”,所以《釋名》的目的,在于辨明上則天地陰陽、下至宮室車服種種名稱的“所以之意”。而就“中國”歷代國號與古今名稱來說,也與此相仿。本來,創(chuàng)造了方塊漢字的中國人,歷來就有講究名稱字號的傳統(tǒng),人名都是如此,關(guān)涉國家的大號當(dāng)然更不例外,道理很簡單:人名不過一己的代號,國家大號則關(guān)系到億兆斯民,而如果這億兆斯民都不關(guān)心這國家大號的“所以之意”,是不是有點說不過去?
利瑪竇解說中國國號的“故事”
相較于私塾先生妙解“意大利”為“意思就是賺大錢的人”、李鴻章訝異于葡萄牙“怎么葡萄也有牙”,這里不妨再說一個確實可信的、主角為外國人的、解說中國國號的“故事”。
400多年前的1582年,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人利瑪竇(1552-1610年)從印度啟程,登陸澳門,開始了他的中國傳教之旅。利瑪竇在中國傳教、工作和生活了28年,逝世后安葬于大明京師(今北京)。利瑪竇晚年撰寫而又經(jīng)由比利時耶穌會士金尼閣增修的《利瑪竇中國札記》,1615年在德國奧格斯堡出版。由于“書中初次精確地、忠實地描述了中國的朝廷、風(fēng)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務(wù)問題”,所以一經(jīng)問世,就在歐洲引起了轟動,歷史悠久、地大物博、繁榮富庶的中國,也因此而真實地、立體地呈現(xiàn)在歐洲人的眼前。
在《利瑪竇中國札記》第一卷第二章中,利瑪竇這位與中國士大夫頗多交往、直接掌握了中國語文、并對中國典籍進(jìn)行過鉆研的西方“中國通”,第一次相當(dāng)詳細(xì)地解說了其時的歐洲人尚覺模糊不清的“關(guān)于中華帝國的名稱”問題。
“中華帝國的名稱”紛繁復(fù)雜,利瑪竇則聰明地將之區(qū)別為三類。
關(guān)于第一類名稱,利瑪竇認(rèn)為:“這個遠(yuǎn)東最遙遠(yuǎn)的帝國曾以各種名稱為歐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稱是Sina,那在托勒密的時代即已為人所知。后來,馬可·波羅這位最初使歐洲人頗為熟悉這個帝國的威尼斯旅行家,則稱它為Cathay。然而,最為人所知的名稱China則是葡萄牙人起的”;“我也毫不懷疑,這就是被稱為絲綢之國(Serica regio)的國度,因為在遠(yuǎn)東除中國外沒有任何地方那么富饒……在中華帝國的編年史上,我發(fā)現(xiàn)早在基督誕生前2636年就提到絲綢工藝,看來這種工藝知識從中華帝國傳到亞洲其他各地、傳到歐洲,甚至傳到非洲。”
關(guān)于第二類名稱,利瑪竇寫道:“中國人自己過去曾以許多不同的名稱稱呼他們的國家,將來或許還另起別的稱號……因此我們讀到,這個國家在一個時候稱為唐,意思是廣闊;另一時候則稱為虞,意思是寧靜;還有夏,等于我們的偉大這個詞。后來它又稱為商,這個字表示壯麗。以后則稱為周,也就是完美;還有漢,那意思是銀河。在各個時期,還有過很多別的稱號。從目前在位的朱姓家族當(dāng)權(quán)起,這個帝國就稱為明,意思是光明;現(xiàn)在明字前面冠以大字,因而今天這個帝國就稱為大明,也就是說大放光明。”
又第三類名稱,即利瑪竇所謂“這個國家還有一個各個時代一直沿用的稱號”——中國(Ciumquo)或中華(Ciumhoa),中國這個詞表示王國,中華這個詞表示花園,放在一起就被翻譯為“位于中央”,“我聽說之所以叫這個名稱,是因為中國人認(rèn)為天圓地方,而中國則位于這塊平原的中央”。
平心而論,利瑪竇這位老外對“中華帝國的名稱”的解說,或者正確,或者接近正確,或者有些正確的影子,總之,比我們的私塾先生說“意大利”、李鴻章問“葡萄牙”的風(fēng)馬牛不相及,顯得進(jìn)步得多。而尤其可貴的是,利瑪竇還分析了中國為什么會有如此之多的名稱:“這個國度從遠(yuǎn)古時代就有一個習(xí)慣,常常是統(tǒng)治權(quán)從一個家族轉(zhuǎn)移到另一個家族,于是開基的君主就必須為自己的國家起一個新國號。新統(tǒng)治者這樣做時,是根據(jù)自己的愛好而賦予它一個合適的名稱”。然而,“與中國接壤的國家中,很少有知道這些不同名稱的,因此中國境外的人民有時就稱它這個名稱,有時又稱它另一個”——外國人有關(guān)中國的各種稱謂,正是因此而起。
蘊含深意的中國歷代國號
由以上中國人解說外國國號的“故事”、外國人解說“中華帝國的名稱”的故事,我們應(yīng)該能夠感受到:外國國號、“中華帝國的名稱”的“所以之意”,都是非常復(fù)雜、牽連甚廣的學(xué)術(shù)問題;而方塊漢字為主的“中華帝國的名稱”與拼音文字為主的外國國號,又各有復(fù)雜之處。比如拼音文字的外國國號,由于歷經(jīng)演變、屢有發(fā)揮,其意往往十分難解,我們所見只是一堆字母的組合。至于方塊漢字的“中華帝國的名稱”,其望文生義的方便之處,卻也正是容易導(dǎo)致臆解、誤解乃至瞎解的關(guān)鍵原因,又漢字意義的引申、擴(kuò)展、假借等,也會造成“中華帝國的名稱”解說中本義、引申義、附會義等等的混淆。以上述利瑪竇“夏”等于偉大、“商”表示壯麗、“周”就是完美、“漢”的意思是銀河、“大明”就是大放光明一類說法為例,所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本義、引申義、附會義等的混淆。
然則正本清源,系統(tǒng)全面地探討中國遞更的國號、眾多的名號、繁雜的域外稱謂之形成過程、來源取義、使用情況與復(fù)雜影響,正是筆者鍥而不舍24年、并且漸次拓寬加深的追求所在。即以集大成的《吾國與吾名》為例,對話1615年出版的《利瑪竇中國札記》的三類“中華帝國的名稱”,本書以40余萬言的篇幅,得出了諸多學(xué)術(shù)價值與現(xiàn)實意義兼具的認(rèn)識,姑引“結(jié)語”中的三段為例:
以言歷代國號之美……夏國號的最終擇定,與蟬所代表的居高飲清、蛻變轉(zhuǎn)生等的美義有關(guān);取美義為國號,也成為后世中國歷史上命名國號的一種常用方法。由夏而下,商、周、秦、漢、新、晉、隋、唐、周、宋、大元、大明、大清這些王朝或皇朝所用的國號,同樣具有或顯或隱的美義,并成為各自國家的政治文化符號。這種符號,于商為鳳,于周為重農(nóng)特征,于秦為養(yǎng)馬立國,于漢為“維天有漢”,于新為“應(yīng)天作新王”,于晉為巍巍而高,于唐為道德至大,于宋為“天地陰陽人事際會”,于大元為“大哉乾元”,于大明為“光明所照”,于大清為勝過大明,總之,都屬于“表著己之功業(yè)”“顯揚己于天下”“奄四海以宅尊”“紹百王而紀(jì)統(tǒng)”的“美號”。這些“美號”,既與君主的統(tǒng)治息息相關(guān),也照應(yīng)了所統(tǒng)治的部族民眾之心理要求,并進(jìn)而使政權(quán)蒙上了濃重的順天應(yīng)人的色彩。至于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則書寫出國號歷史的新篇章,即既區(qū)別于以往天下社稷一家一姓的國號,又表明了國家的主權(quán)屬于中國各民族,屬于中華民族,此種意義,更是“美”之大矣!
以言古今名號之偉,可以“中國”名號為例。“中國”名號,歷史久遠(yuǎn),先秦時即已存在。雖然地域概念的中國是多變的,文化概念的中國是模糊的,但中國的地域范圍在不斷放大,中國的文化意義在不斷加強(qiáng)……至于后起的政治概念的中國——“18世紀(jì)50年代清朝完成統(tǒng)一之后,19世紀(jì)40年代帝國主義入侵以前的中國版圖,是幾千年歷史發(fā)展所形成的中國的范圍。歷史時期所有在這個范圍之內(nèi)活動的民族,都是中國史上的民族,他們所建立的政權(quán),都是歷史上中國的一部分”——既與地域概念的中國、文化概念的中國相輔相成,又較之更加客觀與全面,而且政治概念的中國,無論時間、空間都指稱相當(dāng)明確。由中國概念的流變,我們又可以明了這樣的史實:中國的歷史是中國境內(nèi)各民族——無論文化高低、地域遠(yuǎn)近,是漢族抑或非漢民族——共同締造的,中國的版圖是由中原和邊疆共同組成的,現(xiàn)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繼承和發(fā)展。
以言域外稱謂之妙……記得有種說法,比喻中國的物質(zhì)文明就是一塊泥巴、一片樹葉、一只蟲子,泥巴燒成了瓷,樹葉喂養(yǎng)了蠶,蠶蟲吐出了絲,而瓷與絲,就在中國的域外稱謂China、Serice中得到了形象的體現(xiàn)。至于既是自稱也是他稱的漢與唐、龍與獅,漢、唐是中國歷史上充滿正能量的代表性皇朝,它們共同寫照了巍巍中國的歷史地位,龍、獅是體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近代政治歷程的典型化動物,它們一并烘托了泱泱中華的文化形象。
要之,“美哉,變動不居而又蘊含深意的中國歷代國號!偉哉,延用不衰而又凝重氣派的中國古今名號!妙哉,來源不一而又呈現(xiàn)特征的域外有關(guān)中國的稱謂!”——可謂從獨特的側(cè)面、別樣的角度,生動形象地反映了中國文化中的名稱情結(jié),淋漓盡顯方塊漢字的無窮魅力、中華民族的心理認(rèn)同、中外交通的艱難歷程以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表現(xiàn)出的泱泱大國氣度……
中國人共同關(guān)注之事
1999年國慶節(jié),卞孝萱師在《〈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序言》中感慨:“中國古今稱謂,既是中國人共同關(guān)注之事;《“中國”古今稱謂研究》,應(yīng)為天地間必不可少之書。”拙著《偉哉斯名》以及在此基礎(chǔ)之上“大事增補(bǔ)修訂而成”的《吾國與吾名》,自然遠(yuǎn)當(dāng)不起“天地間必不可少之書”的先師期望,但“中國歷代國號與古今名稱”的來源取義、來龍去脈,作為“中國人共同關(guān)注之事”,卻是毫無疑義的,因為這些國號、名號與域外稱謂,伴隨著我們民族的成長、我們國家的歷史、我們疆域的變遷、我們與世界的交往與交流、我們以及我們的祖先與后代的生命,推而廣之,如果我們立足于“名實互證”的視角、“聞‘名’識中國”的思路,那么這些國號、名號與域外稱謂,又能豐富、強(qiáng)化與鮮活我們對歷史中國與現(xiàn)實中國的理解,并油然而生對中華文化與華夏傳統(tǒng)的自認(rèn)、自信與自豪。
正是基于對中國歷代國號、古今名號、域外稱謂的這種切身認(rèn)識、這份真摯感情,我從篳路藍(lán)縷的10萬字的《中國古今名號尋源釋意》做起,歷時24年,終于完成了總結(jié)集成的50余萬言的《吾國與吾名》,雖然滿頭的濃密黑發(fā),已經(jīng)稀落漸衰為謝頂而兩鬢斑白,卻依然“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畢竟為“中國人”說“中國”,值得這樣的無悔付出!
(作者:胡阿祥,系南京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教授、六朝博物館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