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珍珠的三位中國合作者
近代來華作家、學(xué)者翻譯了不少中國的著作,也寫了大量關(guān)于中國的書。他們在翻譯和寫作過程中常常會在語言文化方面或者對實(shí)際情況的了解方面,從中國人那里得到大量幫助。在很多情況下,可以說,如果沒有中國人的幫助,這些近代來華人士的翻譯或著述就很難完成或者質(zhì)量會大打折扣。魯迅和季羨林日記中都提到艾克 (又名艾鍔風(fēng),Gustav Ecke),據(jù)季羨林后來回憶說他不懂中文,季羨林的這個說法不太可信,但是可能艾克在清華大學(xué)教季羨林德語時(shí)中文水平確實(shí)很有限。但是艾克卻寫了世界上第一本關(guān)于中國家具的學(xué)術(shù)專著,艾克在寫作過程中得到楊耀等中國人的很多幫助。瑞典藝術(shù)史學(xué)者喜仁龍40歲左右才開始研究中國藝術(shù),中文水平很有限,在研究和翻譯著述的過程中得到楊周翰等中國助手的很多幫助。王世襄說外國人用英文所寫的關(guān)于北京鴿哨的著作對中國古代文獻(xiàn)的理解反而比中國人的著述中的理解更加準(zhǔn)確,原因不是外國人的中國古文水平更高,而是他們更愿意向中國的內(nèi)行高人求教。英國著名藝術(shù)史學(xué)者蘇立文的中國妻子吳環(huán)和瑞典漢學(xué)家馬悅?cè)坏闹袊拮雨悓幾娑荚谒麄兊姆g、研究和著述過程中給予他們巨大的幫助。賽珍珠的翻譯和著述過程也證明了這一點(diǎn)。
趙雅南
賽珍珠雖然自小生活在中國,但是在她生長的年代,中文不受重視,大多數(shù)傳教士學(xué)習(xí)漢語和中文的目的不過是把漢語和中文當(dāng)做傳教的工具而已(王賡武教授語)。

金陵女子學(xué)院難民營職員、志愿者和來訪者合影,第二排站立者右起第三人為趙雅南
賽珍珠雖然在晚年的回憶錄中聲稱她小時(shí)候在鎮(zhèn)江曾經(jīng)跟一位孔先生學(xué)習(xí)儒家經(jīng)典。但是對于她父母為什么會請一位儒家學(xué)者教她中國經(jīng)典,她一直沒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況且她的父母并非那種癡迷于中國文化的人。賽珍珠的同時(shí)代人楊步偉在自傳中提到她早年在上海就讀的中西女塾時(shí)說:“我的同學(xué)大多是來自基督教新教徒家庭或?yàn)橥鈬竟ぷ鞯纳倘思彝ァM鈬?dāng)然不會上我們的學(xué)校,因?yàn)樗齻兩贤鈬藶橥鈬⒆娱_辦的學(xué)堂,目的是為了在成長過程中不諳中文讀寫。”(《趙元任全集》第15卷上冊頁93)有意思的是,楊步偉的自傳最早還是在賽珍珠的建議下寫作并且由賽珍珠的第二個丈夫經(jīng)營的出版公司出版的。
而根據(jù)1934年2月26日晚章伯雨寫的《勃克夫人》一文,賽珍珠1934年在南京時(shí),“家里請了一位教中文的老塾師,這位老塾師教了她好多年的中國文學(xué),現(xiàn)在仍在她的家里,每天教讀她的五齡次女”。根據(jù)章伯雨1934年譯的賽珍珠1930年代早期寫的自傳,賽珍珠在該自傳結(jié)尾時(shí)說:“我抱歉,我好像沒有想到別的什么事情好寫,只是我有兩個小女兒。一個是在學(xué)校里,一個五歲了,是陪著我們住在家里。她每天跟著她的老中文塾師學(xué)習(xí)讀寫中文。這位老塾師當(dāng)了我的中國文學(xué)教師好多年了。”賽珍珠在她1930年代早期尚未返回美國定居時(shí)所寫的這篇自傳中從未提及她小時(shí)候曾經(jīng)在鎮(zhèn)江跟孔先生學(xué)中國經(jīng)典。而胡愈之的弟弟胡仲持在《文學(xué)》1933年第一卷第五期發(fā)表的《〈大地〉作者賽珍珠重來中國》也說:“她后來同卜克教授到南京金陵大學(xué)任課,在課余之暇學(xué)習(xí)中文,研讀 《紅樓夢》、《水滸》、《三國》等中國小說。”而當(dāng)時(shí)賽珍珠居住在南京,南京離鎮(zhèn)江很近,當(dāng)時(shí)身邊熟悉賽珍珠早年生活的人肯定有不少,因此她這時(shí)寫的自傳更加可信。
另外根據(jù)1940年代早期國民政府教育部編輯的《專科以上學(xué)校教員名冊》第二冊,頁三七四(1971年10月臺灣傳記文學(xué)出版社影印出版),章伯雨,1909年生,安徽來安人,金陵大學(xué)農(nóng)學(xué)士,曾任金陵大學(xué)助教、講師、副教授,專長科目是農(nóng)村社會經(jīng)濟(jì)及農(nóng)業(yè)教育。據(jù)《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史志》頁89及90,章伯雨曾任金陵大學(xué)農(nóng)學(xué)院農(nóng)業(yè)推廣部教員及農(nóng)業(yè)專修科主任。據(jù)《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教育史》頁71,章伯雨1953年任南京農(nóng)學(xué)院教授。我們知道賽珍珠丈夫卜凱長期在金陵大學(xué)任教,賽珍珠也長期居住在金陵大學(xué),因此章伯雨的敘述應(yīng)該是可信的。胡仲持(筆名宜閑)是中國較早在《東方雜志》等刊物上介紹翻譯《大地》的人,胡仲持的敘述應(yīng)該不是空穴來風(fēng)。當(dāng)賽珍珠晚年在美國寫回憶錄時(shí),熟悉她早年生活的人大多已經(jīng)凋零,即使有極少數(shù)還活著,也生活在中國大陸,而當(dāng)時(shí)時(shí)值冷戰(zhàn)高潮,中美對立,根本無法找人對證。賽珍珠寫
回憶錄也就無所顧忌,信筆揮灑,有意無意的為她早年生活增添傳奇色彩,同時(shí)也等于是向費(fèi)正清等瞧不起她的中國通們宣示:“你們算什么,我小時(shí)候就打下了漢學(xué)童子功!”賽珍珠在她早年寫的自傳中倒是提到了她的中國老奶媽。客觀地說,不少在中國長大的傳教士子女倒是會說中國話的,傳教士林查理(Charles Henry Riggs)的長子Fred W.Riggs從小跟他家的福州阿媽的兒子一起玩耍,學(xué)會了說一口流利的福州話(http://www2.hawaii.edu/~fredr/autobio1.htm#1)。但是他們的中文閱讀能力大多不好。復(fù)旦大學(xué)英語系退休教授孫驪在《外語教育往事談(第二輯)》頁123提到加拿大傳教士文幼章(James G.Endicott)時(shí) 說:“他 本 人 的語言能力又極能引起學(xué)生學(xué)語言的興趣,因?yàn)樗刚Z之外還能講一口流利的四川話。如果不看見人,還真會以為是一個四川人在講話。我對此非常好奇,有一天課下見他在讀學(xué)生的壁報(bào),以為他讀中文與講中文一樣行,就隨便問問他怎么學(xué)的中文。他說他講四川話行,因?yàn)槭浅运拇棠锏哪涕L大的(他的父親曾長期在四川傳教),但讀中文就不具備同樣的能力,只能半讀半猜。我當(dāng)時(shí)當(dāng)然并不懂什么語言與文字的差異,聽到這一回答頗感奇怪,也使我多少知道一點(diǎn)學(xué)語言的復(fù)雜性。”根據(jù)這段敘述,我們可以對傳教士子女的中文能力略見一斑。
那么這位在南京教了賽珍珠好多年中國文學(xué)的老塾師到底是誰呢?
既然教了賽珍珠很多年中國文學(xué),并且還被聘請教賽珍珠的次女,那么這位老塾師一定是教得很好了,否則不會長期聘用的。
1949年至1950年金陵大學(xué)哲學(xué)系教授芮陶庵(Andrew T.Roy)夫婦在他們的朋友金陵女子大學(xué)教師Eva Spicer的推薦下聘請大概已經(jīng)70余歲的老先生趙雅南教他們的兩個兒子中文。趙雅南當(dāng)時(shí)大約已經(jīng)教了外國人40年中文,并且也教過Eva Spicer。在Suping Lu編輯的一本英文書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 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 -38(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ios Press,2008)中的金陵女子大學(xué)難民營管理人員集體照片中站立的第二排右起第三人就是趙雅南,圖片說明上說是Mr.Djao,而Djao也是“趙”羅馬化拼寫的一種方式。書中的索引部分簡略地提到這位Mr.Djao,并聲稱他是金陵女子大學(xué)教師Eva Spicer的Private language tutor(私人語言教師)。趙雅南不是金陵大學(xué)的教師,也不是金陵女子大學(xué)的教師,他是位自由職業(yè)者,專門教外國人漢語和中文,他不會說英語,大概也不懂英語,他教外國人漢語和中文用的是直接教學(xué)法。近60年之后,芮陶庵的長子回憶起他來,還說他是一位優(yōu)秀的教師。芮陶庵的兩個兒子后來成為美國大名鼎鼎的中國通。一位是著名的中國古代文學(xué)研究者和《金瓶梅》翻譯家芮效衛(wèi)(David T.Roy),另 一 位 是曾經(jīng)擔(dān)任美國駐華大使的芮效 儉(James Stapleton Roy)。趙雅南告訴芮效衛(wèi),他曾經(jīng)幫助賽珍珠翻譯過《水滸傳》。趙雅南說賽珍珠能夠閱讀一些中文,但是卻依靠他把《水滸傳》口頭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然后她自己再看原文,然后翻譯成英文。
根據(jù)以上資訊,我們可以推斷,這位在南京教了賽珍珠好多年中國文學(xué)的老塾師很可能就是趙雅南。首先教了賽珍珠自己好多年中文,后來又被聘請教她次女中文,說明這位老塾師教得很好。而塾師翻譯成英文恰好是private tutor或private teacher。另外趙雅南在1949年時(shí)已經(jīng)70多歲了,并且已經(jīng)教了外國人漢語大概40年了,那么他在1930年代早期教賽珍珠次女時(shí)說是老塾師,當(dāng)之無愧。根據(jù)芮效衛(wèi)教授的說法,趙雅南是專門依靠教外國人漢語為生的自由職業(yè)者,而且本人不說英語,他怎么會認(rèn)識賽珍珠,并且還幫助賽珍珠翻譯過《水滸傳》呢?那一定是他曾經(jīng)在賽珍珠家里教過漢語了。
龍墨薌
過去有人認(rèn)為這位老塾師是龍墨薌,但是龍墨薌是金陵神學(xué)院的專職秘書。而章伯雨和賽珍珠早期自傳提到的老塾師不但教過賽珍珠很多年中國文學(xué),并且每天還教賽珍珠五歲的次女(養(yǎng)女Janice)讀寫中文。根據(jù)龍墨薌子女的說法,龍墨薌是金陵神學(xué)院的專職秘書,是不可能去做一個每天教五歲小女孩中文的老塾師(而塾師一般是指專職私人教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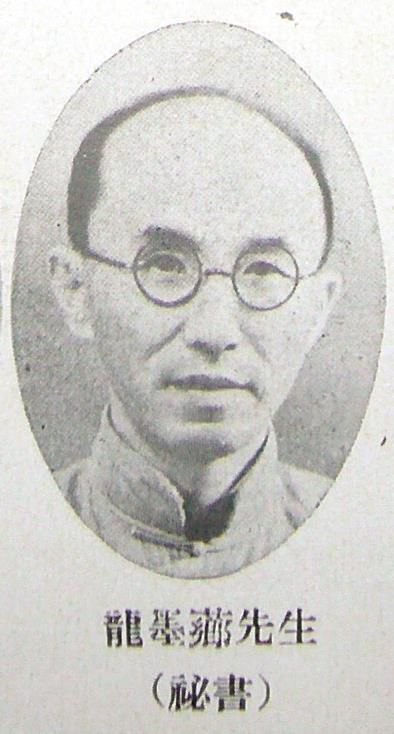
龍墨薌是賽珍珠的一位中國合作者,曾寫過《英譯〈水滸傳〉序》。
不過龍墨薌確實(shí)是賽珍珠的一位中國合作者。筆者的友人姜慶剛先生最近發(fā)現(xiàn)了1935年11月9日南京《中央日報(bào)》文學(xué)周刊上刊載的一篇龍墨薌寫的《英譯〈水滸傳〉序》。在該文結(jié)尾時(shí)龍墨薌說:“我的學(xué)識與經(jīng)驗(yàn)俱感缺乏,今勉應(yīng)卜凱夫人(即賽珍珠,葉公平注)之約,助譯此書,我自己常怕不能勝任,幸有邵仲香(即邵德馨,葉公平注)先生肯犧牲精神,代為校正。又幸虧卜凱夫人擅長文學(xué),所以才沒有發(fā)生困難。惟其中尚有謬誤之處,至希海內(nèi)外讀者不吝教正。”
賽珍珠在其英譯的All Men are Brothers導(dǎo)論中也提到Mr.M.H.Lung,并且稱其為 合 作 者(co-worker)和 老 師(teacher)。龍墨薌如果用當(dāng)時(shí)盛行的威妥瑪拼寫法并且根據(jù)西洋習(xí)慣把姓放在名字之后,就是Mo Hsiang Lung,名字再用首字母縮寫就成了M.H.Lung。有人可能會因?yàn)橘愓渲樵诖颂幏Q龍墨薌是老師,就認(rèn)為賽珍珠早年自傳中的曾經(jīng)教過她多年中文并且當(dāng)時(shí)還每天教她的五歲的養(yǎng)女中文讀寫的老塾師是龍墨薌。其實(shí)凡是對人有所教益和幫助的人,都可以被稱為老師的。估計(jì)賽珍珠之所以會認(rèn)識龍墨薌大概跟她父親賽兆祥有關(guān)。賽兆祥晚年一直在金陵神學(xué)院任職。胡仲持1933年7月15日在為開明書店1933年《大地》中譯本寫的譯序《評〈大地〉》中也提到幫助賽珍珠搜集中國小說史材料的中國朋友龍墨薌(參看《賽珍珠評論集》頁27)。
龍墨薌在抗戰(zhàn)時(shí)西遷四川,窮困潦倒,曾經(jīng)寫信向賽珍珠求助,但沒有收到回音。
邵德馨
賽珍珠的第三位中國合作者是邵仲香,又名邵德馨。筆者已經(jīng)有專文談他。日軍侵入南京時(shí),邵德馨和趙雅南都留在南京。章開沅《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里面多次提到金陵大學(xué)農(nóng)場主任邵德馨,不過因?yàn)樯鄣萝懊麣獠皇呛艽螅摃质嵌嗳朔g,有時(shí)把Shao Tehhsing翻譯為邵德星,有時(shí)又翻譯為邵鐵興。舊的西方文獻(xiàn)中提到朱德一般都用Chu Teh,舊時(shí)用Teh來拼寫“德”是很常見的,另外林語堂的《當(dāng)代漢英詞典》說馨既可以讀“Shing(Xing)”,也可以讀“Shin(Xin)”。現(xiàn)在很多人說普通話還是分不清 “ing”和“in”的讀音。而且姜慶剛發(fā)現(xiàn)的金陵大學(xué)農(nóng)學(xué)院教員名冊上有邵德馨,旁邊注的英文是Shao,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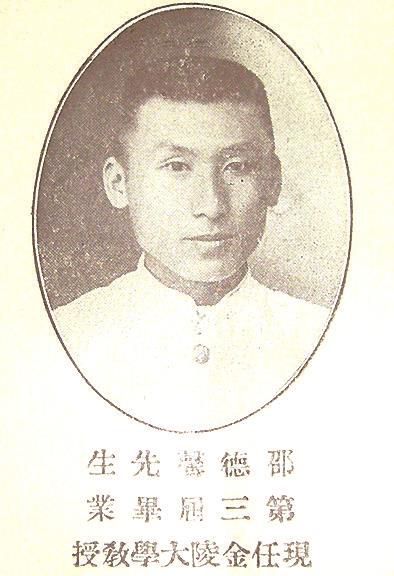
邵德馨與陶行知是金陵大學(xué)校友。后來他幫陶行知辦過曉莊師范。
邵德馨與陶行知是金陵大學(xué)校友。后來他幫陶行知辦過曉莊師范。曉莊師范被查封后,邵德馨回到金陵大學(xué)。《陶行知全集》有多處提到邵德馨(邵仲香)。1934年陶還寫信給邵請他在金大咨詢林業(yè)專家關(guān)于苗圃方面的問題。1981年6月24日邵仲香給南京市政協(xié)編輯的《史料選輯》寫了篇《我所了解的南京金陵大學(xué)農(nóng)學(xué)院》,后來發(fā)表在《史料選輯》第三輯上。由于那時(shí)還不方便對卜凱和賽珍珠做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jià),所以邵的文章中沒有提到他們。邵在該文中提到他是金陵大學(xué)農(nóng)科第一屆學(xué)生,對金陵大學(xué)農(nóng)學(xué)院的所作所為還是語多肯定。姜慶剛幫我找到了署名Shao Teh-Hsing與Pearl S.Buck的 《農(nóng) 民 老 王》(“Lao Wang,the Farmer”,發(fā)表在《教務(wù)雜志》[The Chinese Recorder]1926年4月號)和Shao Teh-Hsing(即邵德馨)著,Mrs.J.L.Buck(即卜凱夫人賽珍珠)英譯的《老王的老牛》(“Lao Wang’s Old Cow”,發(fā)表在《教務(wù)雜志》1932年2月號)。據(jù)姜慶剛說他曾經(jīng)見到過該文的中文版。另外姜慶剛還在民國二十年5月15日的《金陵大學(xué)校刊》上找到了一篇邵仲香寫的《藝術(shù)化的老王》。另外,姜慶剛還幫我在《農(nóng)林新報(bào)》上找到了很多邵仲香寫的小文章,從這些文章看,邵仲香的白話文寫得很不錯。最近出版的《上海圣約翰大學(xué)》中收錄的圣約翰大學(xué)農(nóng)學(xué)院教員名冊上也提到邵仲香。《鼓樓區(qū)志》《南京人物志》和《南京農(nóng)林人物志》上有他的小傳。據(jù)《南京農(nóng)林人物志》說:邵德馨“在金大執(zhí)教十五年,有多次出國深造機(jī)會,每次都推薦別人,受到贊許”。
(作者為常州工學(xué)院藝術(shù)與設(shè)計(jì)學(xué)院講師,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xué)研究青年基金項(xiàng)目“近代來華藝術(shù)史學(xué)者研究[15YJC760117]”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