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fēng)流圖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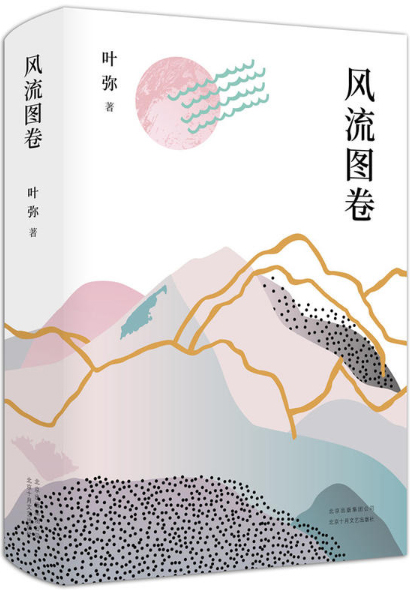
《風(fēng)流圖卷》葉彌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ISBN:9787530218808 定價:49.90元
“111”軍醫(yī)院東邊,有一條巷子叫憐花巷,憐花巷住著一些有本事的人。譬如那位磚雕大師,他用十塊方磚拼接出一朵大牡丹,看不出接縫在那里。他的一個弟子說,師傅用大方磚拼出過一個裸體西洋女人,倒是有縫的。這就是本事,該有就有,該沒有就沒有。磚雕大師隔壁住著一個核雕師傅,這師傅是個瞎子,擅刻《紅樓》里的金陵十二釵。人家問他怎么瞎子也有如此本領(lǐng),他就說,這是鬼教他的。一位做硯臺的女子,從來不出大門,求硯的文人、高官和商人踏破門檻,人家說她是硯田名家顧二娘的傳人,她不露齒地淡淡一笑,既不否認(rèn)也不承認(rèn)。她的隔壁住著一位書籍收藏家,家中三萬多冊書,清版、元版的書多得沒地方放,睡覺時嫌枕頭低,放在枕頭底下作墊子。就是宋版的,也有一大箱,傳說他還藏有曹雪琴的八篇詩稿。巷子里的訓(xùn)詁大師,每回他去上海的大學(xué)講學(xué),都是轎車來回接送,孩子們很少看見轎車,每次看見車子,全都涌過去,圍得水泄不通地看新鮮。還有一位修古籍的,一位做檀香扇的,一位蟋蟀大玩家。一位自稱無國籍僑民者,會赤腳從火上走過而不受傷。一位前妓女,是書寓小姐,現(xiàn)今有兩個男人和她一起住,住了若干年了,也不知和她是什么關(guān)系,兩個都是西裝筆挺,氣宇軒昂,一個為她買菜燒飯,一個為她遞煙打扇。這種生活,她過了二十幾年了。
但大家公認(rèn)的最有本事的一位,是個裁縫,姓范,自稱是范仲淹的后代,他爹是“榮昌”縫紉機修理店的老板,前店后坊,也裝配,也代銷。代銷上海縫紉機廠的“無敵”和“鴛鴦”牌縫紉機。三個兒子,只有這個喜歡做手工,大家都說他沒出息。這裁縫不做別的,只做女人的胸罩,而且只用“鴛鴦”牌縫紉機。他有他的說法,他說胸罩是西方傳來的文明之物,他就是一個文明的使者。他最風(fēng)光的年代是四十年代在上海灘的日子,幾乎所有上海灘的電影、戲劇女明星,紅極一時的舞女,貴婦,新潮女學(xué)生,“青紅幫”頭子們的年輕家屬,都到他這里訂做胸罩。他做胸罩不用量身,前后左右看一看,再輕輕摸一下肩胛骨,就行了。他的老婆原先在胡徐巷口三十二號做鈕扣,嫁給他以后,不去做鈕扣了,給他當(dāng)下手,在他做好的胸罩里繡上一只小手,這只小手長得和范裁縫的手一模一樣,小拇指有點朝外彎,只是小了若干倍。他老婆也是個有趣的人,每當(dāng)繡小手,總是笑了又笑,止不住,說:“你們范家老祖宗的臺,都被你坍光了。”范裁縫說:“人和人是不一樣的,老祖宗范仲淹歡喜風(fēng)云人生,我呢,喜歡門窗里的日子。只要過得好,都一樣的。”范裁縫家里有個大院子,他不做胸罩的時候,就會四下走動視察,一只手在酸疼的后背上輕輕捶,院子里的書帶草、蛇莓、鴨跖草、香草、芥菜、土參、野蔥、野蒜……不管是野生的還是家生的,一棵一棵都被他看個遍。他心情好時,嘴里唱著周璇的歌:好花不常開……他一唱,左右隔壁人家的大孩子小孩子一起跟著唱起來。在許多年里,他唱歌,孩子們和歌,是憐花巷的可愛節(jié)目。他如此得人心,所以憐花巷里的居民都說他才是這里最有本事的人。
話劇里并沒有寫后來的事,后來范裁縫參加了“保派”,就是保全吳郭市革命委員會的意思,簡稱“保派”,又稱“保皇派”。某一天,有人發(fā)現(xiàn)他死在了河里,不知是自殺還是他殺。他的老婆是個明白人,不敢大聲哭泣,垂著淚,叫了自家弟兄,悄悄地抬到城外亂墳灘里埋了。他可愛的小手藏在冰冷的土里,永遠(yuǎn)不可能再出現(xiàn)在女人的布胸罩里。他是吳郭第一個死亡的手藝人,他的死仿佛拉開了一個大幕,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昔日安靜的吳郭城內(nèi)變得無比喧鬧,鑼鼓聲時不時地響起,慶祝“停課鬧革命”,慶祝“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慶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慶祝“打倒一切”,慶祝本市“毛澤東思想?yún)枪懈锩瘑T會成立”,慶祝各個區(qū)的革命委員會成立……再后來連砸爛某中學(xué)的一塊勸學(xué)匾、憐花巷改成反修巷、剪爛某演員的高跟鞋也要敲鑼打鼓慶祝一番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的深夜,吳郭城多處火光沖天,溫良的吳郭人拿起了刀槍,互相爭斗,為了捍衛(wèi)自己一方的思想。我沒有加入什么派別,屬于“消遙派”,我不知道這些人的思想誰對誰錯,我自己的思想還沒理清楚。
不管什么樣的夜,總有人睡不成覺的,譬如舊軍裝和破棉襖,譬如王來恩。王來恩在常寶住過的房子里娶了一位妻子,從此他散發(fā)油條味的枕頭上多了一個人。妻子是位大齡姑娘,中學(xué)數(shù)學(xué)課老師,精瘦刻薄,腫脹的細(xì)眼睛,大鼻子上架了一副眼鏡,大大的嘴唇慘淡無血色。對于王來恩,她打心眼里看不起,一來二去,王來恩就得了不應(yīng)之癥。兩人剛仰天躺下,老婆就把王來恩拖到她的大褲衩上,王來恩圖省事,也不脫掉她的大短褲,只把她短褲的褲腳撩起來,與往常一樣,剛動幾下,就沒了動靜。老婆氣呼呼地把他掀下身去,并踢了他一腳。王來恩趕緊閉上眼就睡著了。突然他醒了過來,說:“好像聽到一聲槍響。”老婆被王來恩胡混了幾下,滿心不足和懊惱,靠在床架子上還沒睡,聽見他這么說,拍著床刻薄地罵道:“你也怕吵?莫非進(jìn)化了?”
偏偏邊上住著一對老夫婦,兩個人都是中醫(yī)名家,精于養(yǎng)身之道,陰陽之道也是常常研習(xí),真是老當(dāng)亦壯。墻體不隔音,每當(dāng)夜里從隔壁傳來老夫婦演習(xí)陰陽之道的聲音,王來恩和他的老婆總是聽得干瞪眼。王來恩偏過耳朵,沒有再聽到槍聲,卻聽見了隔壁又一次傳出歡快之聲,當(dāng)然王來恩老婆也聽到了,她忍不住了,陰陽怪氣地說道:“平時只看見他們買點青菜吃吃,不知道為什么有這么大的力氣?有些人吃油條,吃了多少年下來,那東西還不如剛炸的油條有力氣,倒好像出鍋的油條,被西北風(fēng)一吹就冷了,就軟了。”王來恩起身拿了拖把,對著聲音傳來的地方一頓猛搗。也許是沒聽見吧,那邊繼續(xù)歡快有力地響,或者聽見了不予理睬。這兩種情況都是王來恩不能容忍的。王來恩只穿了褲衩就竄到隔壁去敲門。門開了,開門的老頭一愣,王來恩便說:“你想找死嗎?”那老頭倒也沉得住氣,不卑不亢地說:“活得好好的,我為啥要找死?”王來恩說:“你家好像夜里在砸地板嘛,聲音很響的。”老頭臉上紅了一下,他也沒想到這墻這樣不隔音,沒多思量,就犟了一句:“我在家里干什么,別人是管不著的。”就是這句話把他和老妻子推上了絕路。王來恩,這時已經(jīng)是副院長了,他那只眼睛也能視物了,不再貼著膏藥,他簡潔地說:“你們明天去‘對敵斗爭學(xué)習(xí)班’報到。”老中醫(yī)愣住,臉上悲戚,卻不服軟,笑著對王來恩說:“不就是要我死嗎?我六十歲了,活得夠本了。不怕死。”當(dāng)著王來恩的面,他不客氣地把門碰上。老太太坐在床上,向他豎起大拇指,笑著夸獎他說得好,她佩服他,就是到了陰宅地府也要拉著他的手。
王來恩回到家里,老婆對他使了一個眼色,他就拿出一串鞭炮和七、八個炮仗,在大院里一通亂放,深更半夜的,周圍人家居然沒有一個提抗議。老中醫(yī)夫婦兩個人聽了,當(dāng)下就決定自己了結(jié)生命,服了安眠藥,一起走到常寶跳河的地方,干凈利落地跳河赴了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