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羊走在村莊的上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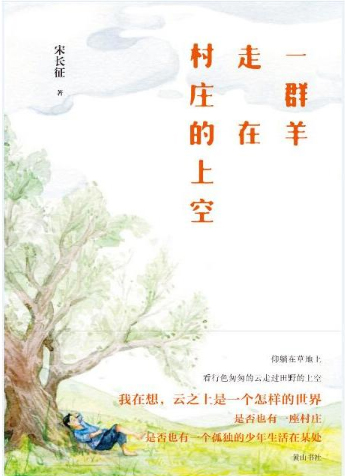
《一群羊走在村莊的上空》
作者:宋長征
出版社:黃山書社
出版時間:2018年11月
ISBN:9787546176765
定價:39.80元
結露為霜
很多時候,我不得不自己尋找路口。在荒蕪的大地上,在茂密的野草的家園,所有的路,一定是野草走出來的。你看它們不需要召喚,經(jīng)過一個季節(jié)的休眠,突然點亮荒野。野兔奔跑其間,田鼠開鑿洞口,鳥兒在天空飛翔,無不以草的盛衰枯榮作為旅程的航標。
父親告訴我,我可以自己出門了,去二姑家。話說的不容置疑。我是懷疑自己的,一直都是,沒有人告訴我什么路可以走下去,什么路就算走到白頭也還一無所有。我會茫然地站在田野上,妄圖聽見歲月深處傳來的神諭。沒有。除了一股又一股刮過曠野的風,看不見星光出現(xiàn),也聽不見啟迪靈魂的智者回聲。那些草,還在自由生長。仿佛來到這個世界上,大地母親就完成了所有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它們從此要自己面對新生坎坷疾病風雨和死亡。有一些能在烈火中永生。有一些,將從此寂滅,潸然告別這個荒蕪的世界。沒有天堂,天堂也是一條路,這條路上荊棘叢生,這條路上烏云密布。最重要的是,這條路的路口不知所蹤。有的人終其一生也尋找不到。
父母生養(yǎng)了我們七個子女;其間,還有一個溺斃的孩子。母親說過。說的時候表情淡然,卻又害怕忽略每一個細節(jié)。母親說那個午后,我不該讓水生去洗澡。天熱的出奇,大地出了很多汗,到處彌漫著潮濕的空氣。水生應該和你小的時候長得差不多。母親說話時眼睛一眨不眨地看著我,仿佛我就是他的水生。從那年夏日的小河里又回到了家,白白的,真像你。母親說完,在老祖母留下的紅木椅上閉上眼睛,仿佛諳熟了老祖母的那條生命之路。祖母在前,母親在后,一個家庭就是這樣一個接著一個走進虛無的時間,在村莊的視野里消失,在草和樹木觀望的眼神里消失。有時候我會想起那個溺斃的孩子,他該多么幸運啊,從此走上一條永遠天真無邪的路,知了的嘶鳴留不住,茂密的野草留不住,天上的鳥兒極力挽留,他還是頭也不回地走了下去。在小河里,在一個漩渦預謀的句號里,簡單而極致地過完了自己小小的一生。
由此,我斷定死者的痛,往往來自于生者的感知。他們看不得失去一個熟悉的面孔,他們覺得生命的某一根神經(jīng),猛然被人扯斷,他們哀傷的淚水贖罪般河水一樣流淌。在懺悔,為何不能早早發(fā)現(xiàn)一個人走到了路的盡頭。從此,將再也難看上一眼。
每個人的眼里都有回憶。我站在荒野上,把自己當成一個圓心。其實每個人都是一個圓心,緊緊圍繞在你身旁的是天地萬物與親人。我在回憶往日的細節(jié)時,像走進一個巨大的漩渦,大哥和二哥為什么在正好的年紀遠走他鄉(xiāng)?大姑為何遠嫁偏僻的不毛之地?還有二姑,像一個斷了線的風箏,一個人走到黃河邊上,沿著她自己選擇的那條路,找到一個可以托付生死的人。橫向,是每個親人親切而溫熱的臉,有笑容有淚痕,有一千個思念;縱向,是每個人的那條路,從腳下伸延,從大地上某個無名的村落,從村落里一座矮小的土屋里,線索密密匝匝,情節(jié)糾糾纏纏。
闊別家園四十年的大哥回來了,木訥像一個孩子,母親問一句他就回答一句。問家里都還好吧?好。問這么多年你就不想家?想。問怎么過了整整四十年這才想起來回家一趟,不如等我死了。母親的慍怒顯而易見。而大哥點燃一支煙,瞇著眼睛開始回憶自己走過的那條路。
那條路實在太遠,風一程雨一程,大哥一定以為自己走在通向死亡的旅程。唯一的舅舅在關外,而家園天災人禍,父母不愿看見自己的孩子病死餓死,只好在荒草叢中撥開一條若有若無的小徑。走吧,走到天邊也別回頭。我懷疑母親慍怒時是不是想起當年那句冰冷的話,當走在路上的大哥遠望荒涼一片時,心底涌出如何的感傷。路一旦走下去,不要輕易回頭。這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在遠離故鄉(xiāng)遠離親人的屋檐下,不知大哥打沒打過退堂鼓;或者,重重地立下一個念頭:走吧,無論多遠,總還是一條生路,而停頓,將是饑餓與死神緊緊的包裹。
那樣的茅草屋,我真正見過。多年以后,當我擅自決定選擇了自己的那條路時,執(zhí)拗地想走一走大哥二哥走過的路。陌生的北方小鎮(zhèn),陌生的語言和陌生的面孔。當我怯生生打問路人時,村子里的人當即說宋老大宋老二是吧?就在不遠的前面,一左一右兩架茅草屋。甚至,那人還說出舅舅的名字。一條路只走過一個人的時候,野草會很快淹沒原來的足跡。當兩個人,三個人,很多人沿著那條荒蕪的小徑走下去,就走出了一條隱約的羊腸小路。舅舅已經(jīng)死去,他的兒女遍布這個小鎮(zhèn)的每個角落。還有他的外甥——我的大哥二哥。你要知道,在這個世界上誰都不欠你什么,父母給了你生命,親人們給予你關切的目光,而路是自己走出來的。兩座低矮而典型的東北農(nóng)村的院落,前院是糧食和馬車,馬廄和豬圈建在一旁。后院是一片地,夜晚盛滿月光,白天是幾畦青菜和幾行玉米。他們選擇了腳下的那條路,大哥踩著舅舅的腳步,二哥踩著大哥的足跡,從一個關內(nèi)人成功過渡到一個典型的東北漢子。
我理解母親的慍怒,幾十年的光陰就是一段結露為霜的想念之路。沿著這條虛無的線索,母親常常會不期然地落下淚來,總是一次次地問,為什么,為什么大哥一去多年不想返鄉(xiāng)?為什么當初就狠心下了那個決定,讓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踏著冰雪迎著寒風走向未知的遠方?我能理解大哥的沉默,轉瞬一望,竟然望去了半生的光陰,臉上刻滿了皺紋,頭發(fā)結滿冰霜,牙齒像在一次次咀嚼鄉(xiāng)愁之后,覺得盡是苦澀,干脆老了去,凋落如一片片風中的葉子。
我接過母親遞來的點心,也接過母親的囑告,千萬別犯饞偷吃。我是一個聽話的孩子,同樣認為人一旦落地生根必是一株草。鳥兒有鳥兒的軌跡,盡管飛過天空不曾留下痕跡,而季節(jié)照樣更迭。草芥,草民,草根,一個人不可能生就的鳳胎龍種,你選擇了一條星光大道,而我只能走過狹窄的野草小徑,你用你的情懷與抱負擁抱世界,而我用我的卑微與萬物交流。
低矮的草叢,間或竄出一只野兔在草間藏匿身形。這是我一個人的時光,也是我一個人的荒原之路。從家到二姑所在的村莊很遠,穿過一片又一片草叢,走過一個又一個破舊的村落。最醒目的記憶就是一條彎曲的柏油路,黃河水在門前流淌,柏油路在屋后蜿蜒。路太遠了,二姑往往這樣說。這樣說的時候,我就領悟了二姑的意思:別回了,好好住幾天,看汽車。
每天,在嘹亮的汽車喇叭聲中醒來,我驚訝于為何只能在二姑的村莊才能看見如此新奇的事物。有時是一輛漆了綠漆的敞篷車,上面坐了很多人。我想他們的路可能更加遙遠吧,遠到自己的一雙腳不能勝任身體的負累。村莊在他們的眼前一閃而過,路旁的狗在呆立中被撇下很遠。不識相的孩子們,在追趕一輛車時,顯示出無比的快樂與激情,在追上的剎那一躍而起,像一只風中的蜘蛛,懸掛在車廂上走出很遠。后來,還是悵然地留下,看著遠去的汽車,若有所思。
我在二姑家的后窗上看見那輛敞篷車,汽車經(jīng)過這里時速度緩慢。那是一輛老邁的解放牌汽車,發(fā)動機獅吼般轟鳴,而車輪依舊如蝸行。車上有一個很好看的小女孩,也就是十幾米的距離,和我的目光對接。我忘乎所以地對著那輛車招手,好像遇見一群分別多年的親人。而那個女孩,曾經(jīng)和我一起在小河里玩泥巴,在月亮底下捉蛐蛐。女孩是快樂的,從揮舞的紅領巾上,讓我知道那是在朝向一個不能遠行的少年揮舞,而不是向著一座簡陋的老屋。她要去哪里?她的家鄉(xiāng)在哪里?是不是將要踏上一段長長的路,從此離開故鄉(xiāng),而一別經(jīng)年之后,再也想不起曾經(jīng)的家園。
二姑小腳,從我第一眼認識她開始,就好像已經(jīng)年邁。而她的皮膚竟然依舊白皙,這讓人多少有些詫異。想必年輕時的二姑一定很漂亮,像許多蹩腳的劇本那樣,一個藏著心上人的美麗姑娘,愛上一個遠方的后生,狠心的爹娘從中作梗,妄圖生生拆散兩個苦命的鴛鴦。可那時候的我實在太小,想不清楚一個如此復雜的命題。只是斷斷續(xù)續(xù)聽母親說,二姑說走就走,不顧家人的反對,沒有像樣的衣衫,也沒有足夠的盤纏,腰里揣了一把剪子,走上荒蕪的原野。路,或者根本就沒有路。腳下的青草蔓延,像一片渺無人煙的荒原。她的小腳是否在走過坑坑洼洼時,磨出水泡與血水,天色已近黃昏,坐在一根樹樁上自哀自憐。她的眼里是否有一條星光之路,撥開叢生的野草一直延伸,延伸到黃河灘上那座無名的村莊。她灑落的淚珠,落在荊棘叢中,是否荒蕪的原野就像沾滿了露水。人就像一只蟲子,為了活命與愛情,只能不管不顧向前。二姑坐在蒲草團上紡棉線,嚶嚶的紡車聲伴我入眠。
我那陌生而熟悉的親人啊,有時我只能默默念叨你們的名字。父親,姊妹兄弟五個,走到最后只剩下二伯,和我家毗鄰而居。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我不曾聽見看見過一次真正的攀談。人世間的路千條萬條,為什么情同手足的兄弟卻南轅北轍。荒野就是荒野,不會告訴你一句人生箴言,也不會坦露給你命運的答案。你只能一個人,從踏上荒野的第一步開始堅定信念,無論對錯,無論平坦與坎坷,無論悲喜,只能在走過漫長的歲月時回頭一望,露水凝集在離離的荒草之上。
二姑夫性木訥,常年在黃河灘上結網(wǎng)打魚。夕陽斜斜地打在平靜的水面,沒有浪花也無魚躍。他的木船已經(jīng)破敗不堪,腐朽的洞口被打上一塊又一塊難看的補丁。他們沒有子嗣,沒有。這個膚色黑鐵一樣的男人不知用什么打動了二姑的芳心,讓這個遠年的小腳女子,死心塌地地追隨一生。我的到來,仿佛給他們平靜的水面上泛起幾絲生動的漣漪,姑父只要出船打漁必定把我?guī)稀6谜驹诎渡线h遠地看著,看小船漸漸消失在蒼茫的蒹葭深處。
沒有人教我如何才能平安抵達二姑所在的村莊,父親也只是遙遙地向遠方一指,像在指認一枚遙遠的星辰。身后的草叢在我走過之后,復又合攏,我能聽見它們迅速歸位的聲音,一切是這樣默契,默契到滴水無痕。我懷疑在每次返回的路上,是不是從來不會踏上相同的足跡,只是在野草叢中辟開另外一條道路,悄然折返。一只流浪狗,在我草草吃過午飯時尾隨。我走,窸窸窣窣的聲音響起,它也開始行走。我停下時,它便躲進一片杞柳叢,半蜷半臥。所謂的午飯不過是母親包好的野菜團子,給二姑帶的點心,是斷然不能偷食的,這源自于我小時候天性里的自尊因子。在村子里我的極度自尊早就傳為笑柄。貓眼的媳婦將一枚熟透的地瓜給我,在我剛要下嘴的一刻,說了一句不知羞。地瓜便完美地劃了一個弧形,飛進旁邊的糞坑。那只執(zhí)拗的流浪狗,將我內(nèi)心的恐懼放大到千倍,在這個渺無人煙的荒野,我想我會不會變成一幅森森的白骨,任父親和母親喊破喉嚨,再也找不回他們最小的孩子。幾乎哭泣著,二姑竟然顛著小腳遠遠地迎來,當我一頭扎進她的懷里,終于可以肆意地放聲大哭,以釋放漫漫荒野所帶來的無邊恐懼。
路,終究會走到盡頭,每個人腳下的路都會有終點。多年以后的那個秋天,二姑在一個秋露結滿草尖的清晨逝去。時令已近深秋,遠遠的幾棵樹上只剩下幾片翻飛的黃葉。葉子的路也到了終點,在秋天之上,萬物都不能脫凋零的宿命。親人們一個個消失在漫長的時光路上,而我的血脈也一層一層結上冰冷的秋霜。沒有人能安撫彼此內(nèi)心的憂傷,哪怕最親近的那個人坐在你面前,也不能猜透層層結痂的光陰,最后包裹的那個小小謎團。在那個有著黑鐵一樣肌膚而訥言的黃河漢子面前,我成了他們唯一的孩子,披麻戴孝摔老盆,以一種最為古老的儀式為二姑送行。黃河邊上那座孤零零的老屋,后窗正對著一條彎曲的柏油路,我喊不住任何一個匆匆趕路的人,包括綠漆敞篷車上在那個揮舞紅領巾的小女孩。
結露為霜。連天的秋草像大地斑駁的鬢發(fā),蔓延無邊的憂傷。淚水結晶的剎那,透過無邊的荒野,我看見每一個親人熟悉的笑容,化作秋夜里漫天閃爍的星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