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視域下的科幻地形圖
《給孩子的科幻》有一個頗為冷酷的開篇。想要提早見到哥哥的美麗女孩偷乘了要執(zhí)行救援任務(wù)的急遣船,卻不知道這類飛船沒有任何富余燃料,等待她的命運是被拋出船外,在距離哥哥工作星球咫尺之遙的地方變形為一具丑陋的尸體。
讓湯姆·葛德溫這篇極富爭議的代表作率先出場,可能有編排上的偶然,但《冷酷的等式》一文在中國科幻視域中所處的特殊位置,卻已然標(biāo)識了劉慈欣和韓松編選全書的思想坐標(biāo)和深層邏輯。按照研究者王瑤的分析,《冷酷的等式》(又譯《冷酷的方程式》)是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科幻小說核心意象“理性鐵籠”的原初文本,幾乎所有當(dāng)代中國科幻作者都嘗試過對它進(jìn)行模仿、變奏、顛覆或突圍。也就是說,在這樣一本“給孩子系列”的開頭,編者就以超越日常的殘酷,給出了中國科幻的關(guān)鍵問題與焦慮核心。

▲《冷酷的方程式》早期出版時的封面
以這樣的方式向孩子打開科幻,聯(lián)系著編者對“孩子”和“科幻”不同尋常的理解。在韓松看來,孩子和科幻本身就是一種同義反復(fù),“科幻本身就等同于年輕和夢想,代表了人類這個物種目前正在經(jīng)歷的童年時代。我們接受它,就是肯定我們自己,從而樹立起對當(dāng)下和未來的信心”。也就是說,這本選集并不意在為刻板印象里無辜無知的孩子提供某種定制低幼的“潔本”,而是希望經(jīng)由科幻來召喚和牽引一批屬于(代表)人類未來的孩子。
《太陽風(fēng)》中意外不斷發(fā)生卻仍要駕著光帆駛向遠(yuǎn)方的豪情,《霜與火》里對嚴(yán)酷生存環(huán)境和僅有八天的生命周期的超脫,《追趕太陽》中遭遇意外的幸存者以繞月球表面一周的腳印寫下的生命意志的頌歌,都是科幻文類以最具體可感的方式對人類精神的想象和再現(xiàn)。而這些仿佛《地心引力》《火星救援》前身的故事,也應(yīng)和著我們通過好萊塢科幻大片習(xí)得的對于科幻的日常想象。但編入這幾篇小說和阿瑟·克拉克、雷·布拉德伯里等英美科幻大師的名字,并不意味著韓松和劉慈欣在搬運復(fù)制英美世界中某種“天然的”、抽象的、無國別的人類,他們的選擇是坐落在中國科幻視域之中的。這是一份中國科幻共同體的核心索引,當(dāng)我們順著《給孩子的科幻》進(jìn)入一個科幻議題時,我們其實已經(jīng)在這份地形圖的導(dǎo)引下,體認(rèn)著(疊加起)不同時期中國科幻人對同一主題差異性的閱讀和思考。
最為有趣的一組例子是圍繞“進(jìn)化/演化”的三篇小說(《雪山魔笛》《熊發(fā)現(xiàn)了火》和《水星播種》)。童恩正的《雪山魔笛》用一種報告文學(xué)的筆觸,講述考古調(diào)查隊在喜馬拉雅山區(qū)的古剎旁意外發(fā)現(xiàn)了神秘生物的痕跡,在科學(xué)集體的縝密設(shè)計下,揭示和發(fā)現(xiàn)了一支存留至今的猿人,以“活化石”見證(填補)了從猿到人的人類進(jìn)化鏈條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小說滿懷社會主義式的對自然沒有恐懼的好奇和激情,宗教和傳說在故事里只是佐料和調(diào)味劑,真正的滿足與歡喜來自印證(或補完)達(dá)爾文進(jìn)化論、赫胥黎人類起源說,科學(xué)軌道仿佛更加完整的那個時刻。
這份因科學(xué)“完成”而歡欣的情緒并不為《熊發(fā)現(xiàn)了火》分享,特里·比森描繪的是一個怪誕得多的情境。這一情境就是小說的標(biāo)題——熊發(fā)現(xiàn)了火,這個在日常語境中荒誕不經(jīng)、在幻想語境下又好像平淡無奇的事件之所以詭異,用劉慈欣的概括就是“地球的智慧文明本來有各種可能性,這一種似乎早就該發(fā)生了”。也就是說,特里·比森正好逆轉(zhuǎn)了童恩正的思維實驗,展示了如果進(jìn)化論/科學(xué)假定的可能性(準(zhǔn)確地說必然性)在當(dāng)下被印證,當(dāng)學(xué)會了使用工具、使用火的熊“入侵”現(xiàn)實人類世界,面對這種奇特景象普通人的生活將怎樣被改變(或不被改變)。換言之,科學(xué)不再是一種有待印證的必然性,而是召喚奇特狀態(tài)、創(chuàng)造新關(guān)系和新連接的可能。而這正是自認(rèn)“新左派”的特里·比森通過“后新浪潮”式的寫作對另類可能性的想象與再現(xiàn)。
頗有意思的是,這兩篇小說對科學(xué)自身的必然性和帶來的可能性的對位呈現(xiàn),也在無意識中打動了設(shè)計者,選集的封面圖畫就是“舉著火把的熊隱身在巍巍雪山之后”——可能性高擎火炬藏身于必然性之后。當(dāng)然,無論《雪山魔笛》還是《熊發(fā)現(xiàn)了火》都并非當(dāng)代中國科幻討論“進(jìn)化”的主流范式,更多故事中人類已經(jīng)取代了大自然來操弄必然性和偶然性。描繪這種“僭越”的代表作者就是王晉康,而《水星播種》正是最成功的一篇。故事并沒有平鋪直敘地描繪一種人造的硅錫鈉生命從低級形式向智慧生命演化的過程,相反,它將相隔億萬年的兩種生命視角(人類和索拉星人)穿插交互,外星人面對的神秘情境通過當(dāng)下的人類故事獲得詮釋。更為震撼的是人類企業(yè)家的縝密計劃遭遇了毀滅性的意外,故事結(jié)束在(被創(chuàng)造的)外星人自身的歷史邏輯中。
殘疾的人類想要彌補自身的缺憾,最終卻導(dǎo)向了后人類的結(jié)局。王晉康講述進(jìn)化的方式已經(jīng)在不經(jīng)意中顯現(xiàn)了現(xiàn)代主義發(fā)展邏輯的悖論,也把我們引回當(dāng)代中國科幻的核心關(guān)切——人類該如何存續(xù)于這個資源有限的地球/宇宙(中國在資源有限的地球該如何發(fā)展的升級版本)。而這也讓我們進(jìn)入了該選集中最具戲劇性的場景,劉慈欣和韓松——中國當(dāng)代最重要的兩位科幻作家互選對方的作品,韓松挑選了劉慈欣的《微紀(jì)元》,劉慈欣則選擇了韓松的《宇宙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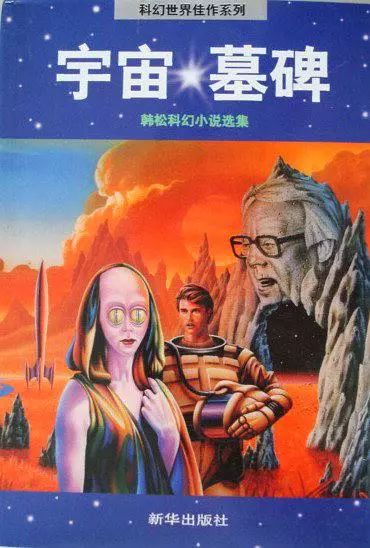
▲《宇宙墓碑》早期出版時的封面
熟悉劉慈欣的創(chuàng)作和言說會知道他是太空技術(shù)和“星辰大海”的虔信者,在劉慈欣的作品中困守一般絕沒有好下場,《三體》系列里通過讓光都無法逃逸進(jìn)行自我防護(hù)最終導(dǎo)致自我湮滅的“光墓”就是對困守立場的形象化諷刺。然而《微紀(jì)元》卻并不分享這種“開著地球去流浪”的豪情,作為劉慈欣序列中相對早期也極為特殊的一部,面對極端的災(zāi)難狀態(tài),人類社會選擇了用基因技術(shù)將個體縮小 10 億倍。由此,人類社群得以保存,而消耗資源極少的“微人”也創(chuàng)造出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烏托邦。這里最動人心魄的一幕是從太空中歸來的唯一“宏人”在見證了微紀(jì)元的完美生活后,主動焚化了所有留存的宏人胚胎細(xì)胞。用滅亡高耗費人類的方式來完成對另類“后人類社會”的認(rèn)同。這種決絕的姿態(tài),以極高的強度顯影了危機的深重,而這也是二十世紀(jì)末中國科幻作為文明預(yù)警的自我期許。
相比而言,韓松的晦暗從來都是更為徹底的。《宇宙墓碑》作為整本選集最神秘莫測的一篇,是一個來自現(xiàn)實也抵抗現(xiàn)實的隱喻——凡記憶的必將被遺忘,無論人類進(jìn)行了多少建設(shè),宇宙都將恢復(fù)它作為一座大墓的狀態(tài),然而在最后的黑暗來臨之前也許還會留有一些格調(diào)迥異的存在。

▲作家劉慈欣
作為一種舶來文類,科幻在中國有著漫長的發(fā)展史,但某種科幻亞文化圈卻是八九十年代以來才漸次形成的。很多著名科幻作者都是通過閱讀外國科幻(主要是美國黃金時代科幻)獲得了最初的靈感,開始自己的本土寫作的,到 2015 年劉慈欣的《三體》獲得雨果獎,可謂完成了一個驚人的旅行和翻轉(zhuǎn)。
而更為奇特的是,促成這一翻轉(zhuǎn)的譯者劉宇昆也是一名華裔。當(dāng)然如果僅僅將劉宇昆理解為中國科幻面向美國、面向世界的譯介者和推手,則忽略了他自身寫作的成就。在選集收錄的《宇宙之春》中,劉宇昆以陌生化的筆調(diào),描繪了一個宇宙春節(jié)的到來。在結(jié)尾莊嚴(yán)的訴說中,新生的宇宙將幻化為北京西站的模樣——“太空中群星組成的一個圖案——那是一座長方形橋梁,層層疊疊的塔樓為頂,道道裙檐累累下?lián)洌麄儠⑵涿麨椤鞲呙钡陌┲搿R驗樗麄兝響?yīng)知曉些先輩的事跡,知曉他們自己來自何方。”這是一份經(jīng)由科幻中介的深情,身處離散狀態(tài)的華人對于中國不滅的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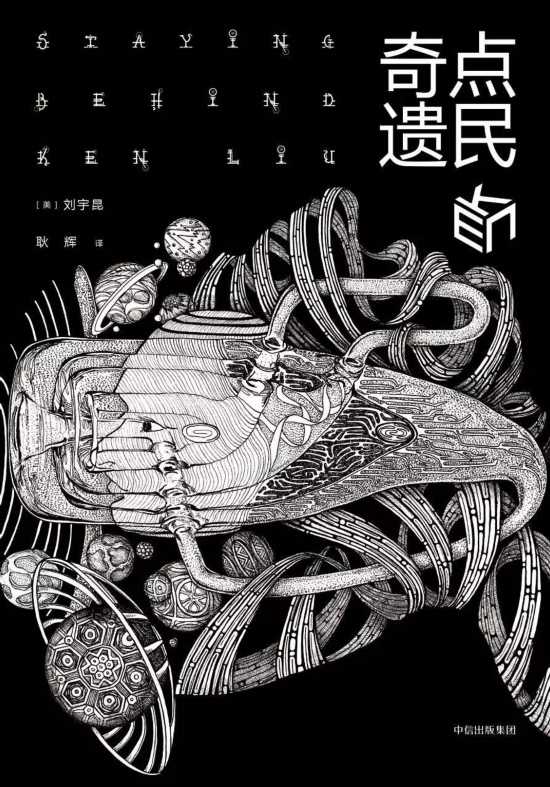
《奇點遺民》
[美] 劉宇昆 著
耿輝 譯
中信出版社 出版
比劉宇昆更具知名度的華裔科幻作家是特德·姜。作為當(dāng)代最優(yōu)秀的短篇科幻小說家,特德·姜的每一篇小說都極為精彩,《巴比倫塔》更堪稱他最完美的作品。相比被改編為電影《降臨》的《你一生的故事》,《巴比倫塔》通過一磚一石構(gòu)筑了一個更加完整生動的世界,驚奇感灌注于每一行和每個場景的轉(zhuǎn)換中。當(dāng)鑿穿拱頂?shù)臅r刻到來時,讀者會和小說中的礦工們一樣屏息以待。也是借由這樣一篇違反所有科學(xué)常識、卻充滿工程細(xì)節(jié)的“巴比倫人的科學(xué)幻想小說”,編者重申了科幻中想象力的力量——科幻絕非現(xiàn)有科技的推論,而是想象另一個世界的權(quán)力。而這可能也是編入潘海天《偃師傳說》的原因,由科幻打開對中國神話的重新闡釋。

▲電影《降臨》劇照
選集收束于陳楸帆的《造像者》,經(jīng)歷了中外漫游的讀者回到了中國科幻自身的脈絡(luò)。作為更新代的代表作家,陳楸帆有著對于中國現(xiàn)實和技術(shù)現(xiàn)實的雙重敏感,他在處理近未來題材時不是將其放置在一個有別于當(dāng)下的時空。相反,《造像者》這類故事極有可能就發(fā)生在此時此刻。他所做的是捕捉這種寓于此刻的未來,以描繪在新的媒介技術(shù)形態(tài)下普通中國人將如何生活、如何思考。而這可能也是面對“未來已至”——科幻小說中最狂悖的夢想紛紛實現(xiàn)而手足無措的我們更需要的思想準(zhǔn)備。
當(dāng)然,僅僅十五篇小說所能形塑的也只是一個充滿遺憾的輪廓,單一的性別、兩三種國別都提示著這是一份理應(yīng)擴展可供批判的地形圖。手持這份導(dǎo)覽的孩子或大人,理應(yīng)望向更遠(yuǎn)的遠(yuǎn)方。然而可貴的可能也是這種極簡和狹隘,允許我們在路程的開始一窺位于中國科幻視域中心的癥結(jié)和洞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