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逝世二十周年:“錢氏神話”為何不可復(fù)制?
那時候知識分子在淪陷的上海,真不知“長夜漫漫何時旦”。但我們還年輕,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過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開日出。
——楊絳
錢鍾書在上海居住多年。1933到1935年,他在上海光華大學(xué)就任外文系講師。1939年夏,在西南聯(lián)大度過一段不愉快的短暫時光后,他受父親錢基博之命赴湖南藍(lán)田國立師范學(xué)院任教,兩年后離開,暫居上海,住拉斐德路609號(現(xiàn)復(fù)興中路573號),楊絳的娘家則在霞飛路來德坊(現(xiàn)淮海中路899弄)。二人本打算休整幾月就回內(nèi)地,沒想到碰上珍珠港事件,上海淪陷,他們就困著出不去了。此后八年,錢鍾書留在上海,中途搬到蒲石路蒲園(現(xiàn)長樂路570弄1-9號的12幢西班牙式花園洋房),一直到建國前夕。
想起淪陷時期,楊絳心有余悸:
“我們淪陷上海,最艱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變之后,抗戰(zhàn)勝利之前。鍾書除了在教會大學(xué)教課,又增添了兩名拜門學(xué)生。但我們的生活還是愈來愈艱苦。”
錢鍾書也曾作詩排解自己的苦悶情緒,詩云《古意》,內(nèi)有一聯(lián):“槎通碧漢無多路,夢入紅樓第幾層。”又有另一首《古意》,“心如紅杏專春鬧,眼似黃梅詐雨晴”。
錢鍾書在上海暫無工作,經(jīng)楊絳介紹,他做起震旦女子文理學(xué)院授課的鐘點(diǎn),靠給學(xué)生補(bǔ)課掙點(diǎn)家用。《家庭教師錢鍾書》一文對此有過詳細(xì)記載。錢鍾書博聞強(qiáng)識,學(xué)生又沒有太多考試任務(wù),補(bǔ)課對他來說,不過大材小用,占不了多少時間,好不容易閑下來,錢鍾書燃起寫長篇小說的興趣。1944年,在楊絳的鼓勵下,錢鍾書開始寫長篇小說《圍城》,他每天寫五百字,晚上給楊絳看,修修改改,直到1946年小說寫完。《圍城》最開始連載于《文藝復(fù)興》雜志,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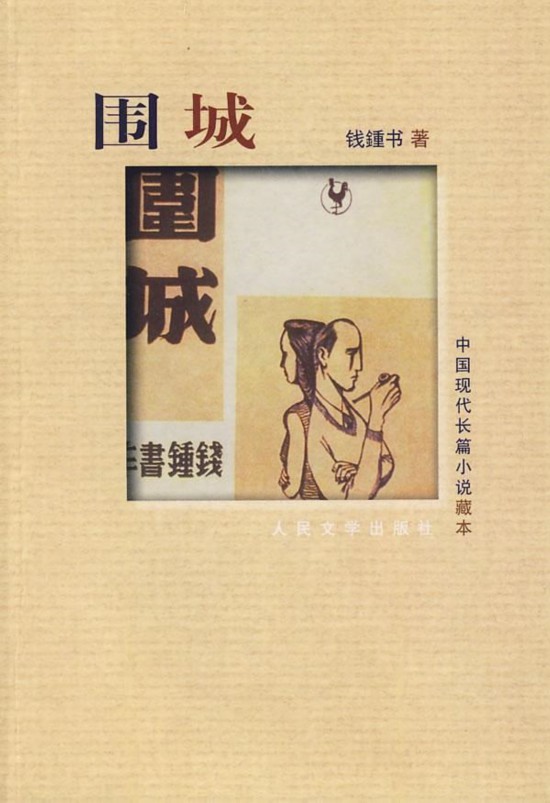
1991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的《圍城》
《圍城》是一部“錙銖必較”的小說,取材自錢鍾書的生活,譬如小說中的三閭大學(xué),就有藍(lán)田國立師范學(xué)院的影子,方鴻漸和他的朋友們,也多剪切、拼接自錢鍾書的友人,但絕不等于原型。小說對知識分子有鞭辟入里的描寫,對婚姻、家庭、求學(xué)等人生問題,也有清醒的看法,剛一發(fā)表,就在上海引起一些影響,于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三版,此后30年不得重印,到1980年才重見天日,引起震動。
創(chuàng)作《圍城》期間,錢鍾書還寫一些短篇,被收錄進(jìn)小說集《人·獸·鬼》,于1945年出版。其中,《貓》影響力最大,1944年,李健吾和鄭振鐸策劃出版文學(xué)雜志《文藝復(fù)興》,二人找錢鍾書約稿,原想連載《圍城》。到創(chuàng)刊號組版時,錢鍾書以來不及抄寫為由,沒有把《圍城》交付,而是把短篇《貓》交給二人。由于疑似影射林徽因、沈從文、林語堂等作家,《貓》受到了文壇的一些非議。
《人·獸·鬼》的另外三篇小說《上帝的夢》《靈感》和《紀(jì)念》被談?wù)摰幂^少。《靈感》寫一個“有名望的作家”荒唐的一生,是和《圍城》異曲同工的作品。《紀(jì)念》一改同題小說的俗套,寫小布爾喬亞的生活和婚外戀,卻不聚焦于批判,而是略帶蒼涼的把三個主角的交集娓娓道來,留下一絲灰燼的余味。讀后倒讓人想起同在上海的張愛玲。《上帝的夢》則是一部寓言體小說,小說中的上帝實(shí)際上是錢鍾書對人類進(jìn)化到極致的遐想,上帝是看似完美的人,卻成為整個世界的獨(dú)裁者,他繼承了人性的善惡,又因失去約束而將惡的一面發(fā)揮出來,他的自私、驕縱、虛榮,并沒有因為力量的強(qiáng)大而改變。錢鍾書在此戲仿了上帝造人的神話,用戲謔的姿態(tài)解構(gòu)了神的神圣性,小說同時是對進(jìn)化論的質(zhì)疑,在錢鍾書看來,線性上升的歷史敘事并不可靠,現(xiàn)代人存在自以為是的性格。然而,《上帝的夢》表意過直,模仿痕跡也較重,有錢鍾書自己的風(fēng)格,但遠(yuǎn)未成熟。誠如夏志清所說,是“有著法郎士風(fēng)格的輕浮”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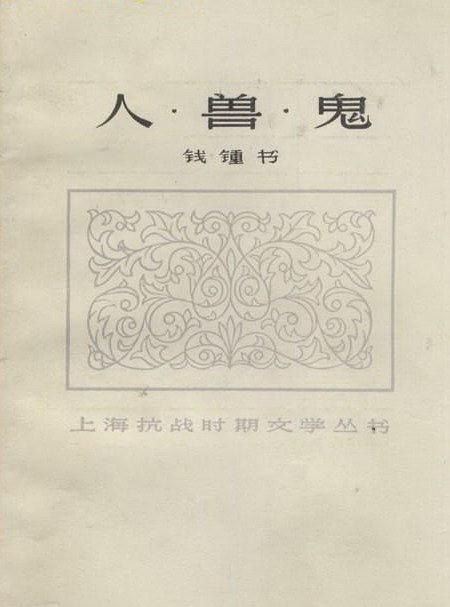
《人·獸·鬼》
錢鍾書的小說常常不拘于型,夾敘夾議,反諷連連,似隨筆,卻又有故事的要素,他的小說和散文出于同路,都是作者觀察某個群體,有什么道理想說出來,于是寄托文字,以虛入實(shí)。所以,他筆下的人物具有典型性,是某個群體的化身,譬如方鴻漸之于孤島時期的小知識分子、建候之于歸國讀書人、上帝之于想主宰一切的獨(dú)裁者。小說成為錢鍾書的傳聲筒、諷刺劇。
錢鍾書深受新古典主義影響,他的小說里有英國通俗文學(xué)的影子。上個世紀(jì)二三十年代,英國文學(xué)盛產(chǎn)以毫無畏懼的年輕人為主角的小說,語言幽默、諷刺,折射世相百態(tài),錢鍾書在牛津期間讀了大量這樣的小說。另外,留洋經(jīng)歷讓他能夠掌握世界文學(xué)的新潮流,當(dāng)一批民國作家還在為白話與文言之爭絞盡腦汁,錢鍾書已經(jīng)在探索現(xiàn)代主義的技法。他在小說中影射了當(dāng)時歐美文壇當(dāng)紅的作家,比如T.S.艾略特。《圍城》里,蘇文紈后來的丈夫曹先生就是研究艾略特的學(xué)者,小說還諷刺了一把艾略特,從譯名就可看出。錢鍾書把艾略特譯成“愛利惡德”,就是愛好利益,厭惡道德。這其實(shí)代表了當(dāng)時新古典主義對現(xiàn)代派詩人的偏見。
不過,《圍城》延續(xù)的還是《儒林外史》的路子,諷刺和比喻性的語言是它的精髓。有人統(tǒng)計《圍城》有600多個比喻,這些比喻或是尖酸,或是幽默,個個不重樣,讓讀者在捧腹之余,感受到世相的多樣面貌。錢鍾書利用比喻寫出一部諷刺大戲,偽造學(xué)歷的方鴻漸、飽讀詩書的蘇文執(zhí)、輕聲抱怨的孫柔嘉、婀娜多姿的鮑小姐,還有在她身后嘴饞的海歸讀書人等,都被納入到這部諷刺大戲中,映射出抗戰(zhàn)時期孤島知識分子的不同心態(tài)。
也是在淪陷時期,耳聽刺刀劃過墻壁的呲呲聲,每日活在警報響起的紛擾中,錢鍾書耐心完成了《談藝錄》的創(chuàng)作。這是一本談?wù)撝袊娢牡恼撍噷V彩清X鍾書第一部有分量的學(xué)術(shù)著作。與此同時,他還從事散文創(chuàng)作。他并不是一個專職散文寫作者,寫散文是“一種業(yè)余消遣者的隨便和從容”。得益于多年學(xué)術(shù)生活,錢鍾書的散文引經(jīng)據(jù)典,富于辯證,充滿書袋氣。學(xué)者范培松統(tǒng)計過,《寫在人生邊上》不到3萬字的篇幅,錢鍾書引經(jīng)據(jù)典多達(dá)60余個。這些文章寫在抗戰(zhàn)時期,涉及戰(zhàn)爭的篇幅卻少之又少,文壇上時興的階級、主義、革命、小資等,都不是錢鍾書的主題。他既不依附潮流,也不刻意反對潮流,而是專注于他學(xué)者似的消遣,談?wù)勚R分子的家常。后人喜歡把《寫在人生邊上》稱為小品文,錢鍾書“名之曰家常體(familiar style)”,因為“它不衫不履得妙,跟‘極品’文的蟒袍玉帶踱著方步,迥乎不同”。
錢鍾書曾把上海和這里的人寫進(jìn)文字里,早在1934年,他有一篇散文就叫“Apropos of the Shanghai Man”(《關(guān)于上海人》),文中寫道:
“正如‘北京人’(化石)代表著過去的中國人,‘上海人’代表著現(xiàn)在的中國人,說不準(zhǔn)還代表著未來的中國人。在當(dāng)下的中國語境里,‘上海人’這個詞匯一直被用來形容一種白璧德式的人物,精明、干練、自負(fù),自命清高。”
彼時的錢鍾書推崇上海人,30年代上海人“精明、干練、自負(fù),自命清高”的氣質(zhì)給他好感,到40年代,在上海待久了,錢鍾書對上海人的認(rèn)識更加具體,《圍城》里很多人物都有上海人的影子,比如女主角之一的孫柔嘉、點(diǎn)金銀行的行長,唐曉芙的父母等,上海人的精明與克制、市民與物質(zhì)的一面,都在里面了。
此外,錢鍾書還借上海與北京的對比諷刺了一把京派文人的自我優(yōu)越感。在小說《貓》中,他寫道:
“那時候你只要在北京住家,就充得通品,就可以像南京或上海的朋友夸耀,仿佛是個頭銜和資格。說上海或南京會產(chǎn)生藝術(shù)和文化,正像說頭腦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會思想一樣的可笑。周口店‘北京人’遺骸的發(fā)現(xiàn),更證明了北平居住者的優(yōu)秀。”
抗戰(zhàn)勝利后,上海光復(fù),錢鍾書受聘擔(dān)任中央圖書館的英文總纂,兼英文館刊《書林季刊》的主編,不必再為收入發(fā)愁。1946年9月到1949年5月,他又兼任上海暨南大學(xué)外文系教授(楊絳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xué)院外文教授),在上海和南京兩地跑。楊絳后來在《我們仨》中回憶道:“鍾書每月要到南京匯報工作,早車去,晚上老晚回家。”
到此,四十年代走入尾聲。可以說,四十年代是錢鍾書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黃金時期,其中大半時光都在上海,上海是摩登與傳統(tǒng)結(jié)合的巨型城市,亂世中的一葉孤島,給予了錢鍾書紛飛無窮的靈感。《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等作品的完成,標(biāo)志著他的小說、散文創(chuàng)作走向成熟。
錢鍾書在1949年回到清華任教,這個決定影響了他的后四十年。實(shí)際上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是留在內(nèi)地迎接新政權(quán)的工作,還是隨一批學(xué)者遠(yuǎn)赴香港或海外,錢鍾書和楊絳都仔細(xì)考慮過這個問題。他們當(dāng)時已經(jīng)名揚(yáng)學(xué)界,要出去并非難事。錢之俊回憶道:
“1948年,香港大學(xué)就曾邀請錢鍾書去任文學(xué)院院長,1949年,教育部長杭立武邀他去臺灣大學(xué)任教授,朱家驊許給他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牛津大學(xué)也約他去任Reader。”
但錢鍾書都拒絕了。他愛好中國古典文化,不愿離開父母之邦,遭受漂泊之苦,為此,他甘愿枯坐板凳,收斂鋒芒。
余論
錢鍾書在建國后就不寫小說,《圍城》重印時,楊絳問他想不想再寫小說。他說:
“興致也許還有,才氣已與年俱減。要想寫作而沒有可能,那只會有遺恨;有條件寫作而寫出來的不成東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遺恨里還有哄騙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學(xué)的西班牙語里所謂‘面對真理的時刻’,使不得一點(diǎn)兒自我哄騙、開脫、或?qū)捜莸模兜啦缓檬堋N覍幒尬慊凇!?/span>
上個世紀(jì)八十年代,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要重版《圍城》,錢鍾書對此不是很積極,他覺得好作品自然會被時間保留,不需要作者費(fèi)力呦呵,出版社編輯好說歹說,他才答應(yīng)重版。錢鍾書的身上有一種二重性,他重視名節(jié),但不追求虛名,《圍城》再版之前,他的姿態(tài)都很低調(diào),不急著出書,不卷入潮流,依然像古老士人一樣手抄筆記,密密麻麻幾百頁紙,寫完就放進(jìn)柜中,很少人看。
隨著小說《圍城》重版、劇版《圍城》熱播,海內(nèi)外掀起一股“錢鍾書熱”,打破了錢楊夫婦寧靜的家庭生活,成麻袋的信寄往他們住處,各種活動邀請錢鍾書,令他無法專心學(xué)問,以至于他說“浮名害我”。不過,錢楊夫婦還是客氣地給讀者回信,學(xué)者周絢隆說:
“錢先生和楊先生屬于老輩的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講老理,所有的信都力所能及要給別人回,有些讀者冒失地直接找到他們家去敲門,想跟他們交談,給他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擾,但是他們也很開心。”
“錢鍾書熱”成為世紀(jì)末的奇觀,也讓研究錢鍾書成為一時顯學(xué),錢鍾書在他生命中作品寥寥的最后二十年,反而收獲了前所未有的熱度,這是歷史的玩笑,也是值得觀察的現(xiàn)象。
放在傳統(tǒng)士人的邏輯里理解,錢鍾書并不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尤其是在那個新舊之交的劇變時代,仍然有一些老先生和錢鍾書一樣,在學(xué)術(shù)上考據(jù)嚴(yán)謹(jǐn)、筆記繁復(fù),在生活里不媚權(quán)威、待人平和,堅持自己的風(fēng)骨。然而,為什么是“錢鍾書”熱,而不是其他與他性格相似的學(xué)者?為什么錢鍾書能夠成為大眾眼中的文化偶像,其熱度能跳出文學(xué)或?qū)W術(shù)圈子的束縛?究其原因,除了《圍城》的長銷不衰,圍繞錢鍾書構(gòu)建的“記憶神話”“美好愛情”等也是關(guān)鍵所在。經(jīng)由多方友人的回憶、著書,擺在大眾面前的是一個看書過目不忘、讀遍全校圖書館書籍、擁有“最賢的妻,最才的女”的錢鍾書,它滿足了大眾對知識分子的一種理想,這種理想不是兼濟(jì)天下、經(jīng)世救民,而是在智慧和人格上的高貴,書籍、媒體等共同構(gòu)建的錢鍾書“人設(shè)”,是這么一個高貴的化身。盡管他和真實(shí)的錢鍾書有所出入。

錢鍾書和楊絳夫婦
錢鍾書的存在必須放在特殊的時代語境去理解,新千年后的時代產(chǎn)生不了錢鍾書,或者說,即便出現(xiàn)語言功力和記憶力堪比錢鍾書的學(xué)者,他也斷斷不可能復(fù)制“錢鍾書神話”,如文化偶像一般被萬千讀者景仰,煜煜生輝又如在霧中。錢鍾書和魯迅一樣成為轉(zhuǎn)型中國的稀有動物,只有在新舊變革的時代才能醞釀那樣的現(xiàn)象,在古士人之風(fēng)遺存、歐美先進(jìn)知識傳來的交匯之中,在知識分子占據(jù)言論中心、互聯(lián)網(wǎng)尚未誕生的歷史縫隙中,錢鍾書憑借淵博學(xué)識和非凡記憶力滿足大眾對知識分子的想象。但這種想象正隨著大數(shù)據(jù)而被動搖,恰恰是在新千年后,對錢鍾書的推崇已經(jīng)分化為擁躉與質(zhì)疑者的對立,依然會有許多人敬仰錢鍾書,但這種知識神話已經(jīng)愈發(fā)失去效力。與此同時,錢鍾書在建國后的緘默也成為眾矢之的,盡管批評者身處風(fēng)口浪尖未必比他更勇敢。
放在如今,若有一人孜孜不倦地抄錄古文,放在朋友圈,他不會引起太大的反響,甚至?xí)池?fù)“賣弄才學(xué)”“裝X”的名號。錢鍾書再能背書,背不過人工智能,有再多的筆記,在互聯(lián)網(wǎng)面前也如滄海一粟。大數(shù)據(jù)讓記憶神話不再耀眼,草根群體的崛起、市民口味的變化和互聯(lián)網(wǎng)對權(quán)威的消解,也讓學(xué)者、知識分子不復(fù)往日地位,從社會發(fā)言的頂層位置滑落至邊緣,錢鍾書式學(xué)者失落的同時,掌握算法規(guī)律、精通草根心理的作者成為時代寵兒,他們所代表的正是一種技術(shù)神話和市民趣味的結(jié)合,反權(quán)威、反精英,崇尚技術(shù)和消費(fèi)的力量,用取悅消費(fèi)文化和技術(shù)壟斷者的姿態(tài)走入市場。于是,在此刻的潮流中回望錢鍾書,仿佛民國時讀書人對晚清遺老的紀(jì)念,多少有點(diǎn)欣賞珍奇古物的玩味。
參考資料:
錢鍾書:《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
楊絳:《我們仨》《記錢鍾書與<圍城>》
范培松:《論四十年代梁實(shí)秋、錢鍾書和王了一的學(xué)者散文》
周絢隆、陸建德:《錢鍾書寫作<圍城>之前,被稱作“楊絳的丈夫”》
錢之俊:《家庭教師錢鍾書》《錢鍾書為什么沒有被打成右派?》《編輯錢鍾書》
端木異:《錢鍾書是怎樣煉成的:前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知識管理術(shù)》
宋丙秀:《<圍城>的版本變遷及修改》
龔剛:《錢鍾書談上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