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地書(shū)、博物志與史詩(shī) 阿來(lái)作品國(guó)際研討會(huì)在京舉行
1982年,24歲的阿來(lái)發(fā)表詩(shī)歌《振響你心靈的翅膀》,從此踏上漫長(zhǎng)的文學(xué)旅程,將近40年的時(shí)間里,中國(guó)乃至世界漸漸認(rèn)識(shí)了這樣一位穿行于漢語(yǔ)和藏語(yǔ)之間,將富有魅力的自然情志與心靈景觀傳達(dá)給讀者的優(yōu)秀作家。
11月17日,由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主辦,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創(chuàng)作研究部、四川省作家協(xié)會(huì)、北京師范大學(xué)國(guó)際寫(xiě)作中心承辦的“邊地書(shū)、博物志與史詩(shī)——阿來(lái)作品國(guó)際研討會(huì)”在京舉行。中國(guó)作協(xié)主席鐵凝出席開(kāi)幕式并致辭,中國(guó)作協(xié)黨組成員、副主席吉狄馬加主持開(kāi)幕式。中國(guó)作協(xié)副主席、北師大國(guó)際寫(xiě)作中心主任莫言,四川省作協(xié)黨組書(shū)記、常務(wù)副主席侯志明,瑞典漢學(xué)家、翻譯家陳安娜等出席活動(dòng)。

鐵凝在開(kāi)幕式上致辭
“民族、自然、文化等等這些都是我們進(jìn)入阿來(lái)文學(xué)世界的路標(biāo),但是,我以為,阿來(lái)的意義絕不限于此。”鐵凝在致辭中說(shuō),阿來(lái)的作品,真正的落腳點(diǎn),仍然是中國(guó),以及生活在中國(guó)大地上的普普通通的人。我們從中看到了一個(gè)中國(guó)作家穿越紛繁復(fù)雜的信息與各式各樣的觀點(diǎn)的洪流,以文學(xué)的方式建立與中國(guó)的血肉聯(lián)系、創(chuàng)造史詩(shī)的努力。鐵凝認(rèn)為,舉辦阿來(lái)作品國(guó)際研討會(huì)的意義就在于此,借阿來(lái)的作品重新認(rèn)識(shí)生機(jī)勃勃的中國(guó),也可以由此討論種種重要而有趣的話題,譬如,地域、民族給一個(gè)作家的寫(xiě)作帶來(lái)怎樣深遠(yuǎn)的影響,史詩(shī)在今天的文學(xué)書(shū)寫(xiě)中有著怎樣的新的可能性,一個(gè)中國(guó)作家可以給世界文學(xué)提供怎樣的經(jīng)驗(yàn)等。她相信這樣的共同探討和相互學(xué)習(xí),定會(huì)取得豐碩的收獲。

莫言在開(kāi)幕式上致辭
莫言尤其贊同研討會(huì)的題目“邊地書(shū)、博物志與史詩(shī)”,認(rèn)為這三個(gè)名詞比較完整地概括了阿來(lái)的創(chuàng)作和他大半生的生涯,但同時(shí)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上沒(méi)有邊地或中心之說(shuō),阿來(lái)把一個(gè)相對(duì)偏僻的地理位置變成了在文學(xué)上引人注目的地點(diǎn)。“中國(guó)很多作家都經(jīng)歷了同樣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就是從寫(xiě)自己的家鄉(xiāng)那一方土地開(kāi)始,由此慢慢深入、擴(kuò)大,最終讓這個(gè)地方通向世界。”他認(rèn)為,研討會(huì)的召開(kāi)非常必要和及時(shí),“我們對(duì)這個(gè)作家閱讀了幾十年,批評(píng)家對(duì)這個(gè)作家研究了幾十年,翻譯家翻譯了幾十年,確實(shí)應(yīng)該有一個(gè)階段性的總結(jié)。”他希望通過(guò)研討讓讀者更加全面地理解阿來(lái),讓批評(píng)家從更新更獨(dú)特、更深入的角度來(lái)理解阿來(lái),讓翻譯家從更準(zhǔn)確的角度翻譯阿來(lái)。

吉狄馬加主持開(kāi)幕式
吉狄馬加認(rèn)為阿來(lái)是一位在精神層面上和文本形式上都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開(kāi)拓者,一位給我們提供了精神建構(gòu)的作家,一位跨文化的卓越寫(xiě)作者。他說(shuō),“今天阿來(lái)作品研討會(huì)沒(méi)有在他的故鄉(xiāng)阿壩舉辦,而是選擇在北京召開(kāi),這明白地告訴我們,在這個(gè)不對(duì)稱的世界,所謂的中心和邊緣似乎永遠(yuǎn)存在,只是對(duì)于文學(xué)和精神創(chuàng)造而言,與時(shí)間的搏斗不會(huì)輕易結(jié)束,若干年后總會(huì)發(fā)現(xiàn),某一個(gè)人的文字將改變我們對(duì)邊緣所下的定義。”

陳安娜在開(kāi)幕式上致辭
陳安娜代表與會(huì)外國(guó)專家學(xué)者致辭,直言相比于已經(jīng)被翻譯成20多種語(yǔ)言,、獲得世界范圍關(guān)注的“大作品”《塵埃落定》,自己更偏愛(ài)阿來(lái)的短篇小說(shuō)。“讀阿來(lái)的短篇小說(shuō)集《阿壩阿來(lái)》時(shí),印象最深的是‘靜’。這種‘靜’使讀者能專注于文本,讀得更加細(xì)致,而不像閱讀喧囂、激烈躁動(dòng)的文本那樣。”她感覺(jué)阿來(lái)作品對(duì)自然的關(guān)切,特別適合北歐的口味,“因?yàn)槲覀円彩歉笞匀魂P(guān)系比較密切的,而印象里中國(guó)作家好像大多不夠關(guān)注自然。”她呼吁與會(huì)翻譯家同行,多翻譯阿來(lái)的短篇小說(shuō),而不止盯著長(zhǎng)篇、歷史小說(shuō),讓世界上更多讀者看到阿來(lái)的那份特別的“靜”。
阿來(lái)以詩(shī)人身份步入文壇,作為小說(shuō)家被廣泛關(guān)注和喜愛(ài),同時(shí)也創(chuàng)作了大量散文作品。近日,阿來(lái)的《成都物候記》《一滴水經(jīng)過(guò)麗江》《大地的階梯》《人是出發(fā)點(diǎn),也是目的地》和《讓巖石告訴我們》5部散文集,由陜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在開(kāi)幕式現(xiàn)場(chǎng)舉行了五卷本《阿來(lái)散文集》揭幕儀式,鐵凝、莫言、麥家以及陜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總社社長(zhǎng)劉東風(fēng)共同為阿來(lái)新書(shū)揭幕。
開(kāi)幕式后,賀紹俊、孟繁華、陳曉明、張清華、潘凱雄、施戰(zhàn)軍、何向陽(yáng)、邱華棟、謝有順、穆濤、何平、陳思廣、張莉、季進(jìn)、張學(xué)昕、梁海、劉大先、叢治辰、岳雯等近20位評(píng)論家,與來(lái)自13個(gè)國(guó)家的翻譯家、學(xué)者山口守(日本)、李莎(意大利)、墨普德(印度)、娜佳(烏克蘭)、李點(diǎn)(美國(guó))、金泰成(韓國(guó))、林幸謙(馬來(lái)西亞)、魯博安(羅馬西亞)、馬海默(德國(guó))、鳳玲(俄羅斯)、羅賓(英國(guó))、月月(法國(guó))等展開(kāi)研討,從鑒賞、感悟、理論、直覺(jué)等不同路徑進(jìn)入,共同探秘阿來(lái)的文學(xué)世界。

阿來(lái)作品國(guó)際研討會(huì)現(xiàn)場(chǎng)
從奇異經(jīng)驗(yàn)到普遍感受
“36年來(lái),阿來(lái)以《塵埃落定》《空山》《格薩爾王》《瞻對(duì)》《機(jī)村史詩(shī)》等一系列作品為我們深描了一個(gè)美好的所在,對(duì)于中國(guó)文學(xué)來(lái)說(shuō),藏區(qū)和那片土地上的風(fēng)光、人民不再是作為奇觀,而是作為實(shí)在的人世風(fēng)景來(lái)到我們的文學(xué)里。”北京師范大學(xué)教授張莉說(shuō),“優(yōu)秀的作家應(yīng)當(dāng)具備跨越民族、地域、血脈和文化,抵達(dá)人類的普遍感受、構(gòu)建情感共同體的能力。”
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主任陳曉明嘗試用二元悖反的結(jié)構(gòu)來(lái)理解阿來(lái)的創(chuàng)作,其中重要一點(diǎn)就是“大文明的視角與藏地的獨(dú)特眼神”,“比如機(jī)村,它是大文明展開(kāi)中的一種情狀,是非常特殊的人類生活中的一個(gè)村落,在消失前最后歲月的那么一片時(shí)光。”陳曉明認(rèn)為,阿來(lái)一直從非常大的文明視角來(lái)看待故鄉(xiāng)生活,看待嘉絨地區(qū)、阿壩地區(qū),這種文本上的大文明視角,不止是一種主題性的理念,重要的是一種時(shí)間和空間在敘事中形成的氛圍。
誠(chéng)然阿來(lái)有著天然的族群和多元文化背景,阿來(lái)的寫(xiě)作也從不回避他的族群性或地域性身份,“但是顯然,他的寫(xiě)作自覺(jué)不自覺(jué)地追求著共通性或者公約性的情感、觀念和普泛化內(nèi)涵。”中國(guó)社科院研究員劉大先感覺(jué),這在阿來(lái)的創(chuàng)作語(yǔ)言上多有直觀體現(xiàn),“他的語(yǔ)言排除過(guò)于地方性的少數(shù)民族成分,是經(jīng)過(guò)自我翻譯的,這種攜帶異質(zhì)文化元素的可譯性語(yǔ)言,甚至悄然豐富了現(xiàn)代中文的表述,形成了可以普遍接受的清通流暢的美學(xué)風(fēng)格。”
“我只感到世界撲面而來(lái)”是阿來(lái)很多年前在一個(gè)小說(shuō)家論壇上的演講題目,而這句話在本次研討中被反復(fù)提及和引用,成為解讀阿來(lái)的一個(gè)入口。大連理工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教授梁海說(shuō),“我覺(jué)得這不僅僅是阿來(lái)感受世界的目光,也是阿來(lái)一以貫之的敘事策略。在阿來(lái)看來(lái),藏地這樣一個(gè)遠(yuǎn)離先進(jìn)文明中心的地帶,其歷史進(jìn)程都是在世界撲面而來(lái)中完成的,這些變化包括自然、生態(tài)、傳統(tǒng)文化、倫理,也包括人的精神世界,沒(méi)有選擇也無(wú)法逃避。”由此他認(rèn)為,研究阿來(lái)必須要騰挪出藏地這個(gè)定語(yǔ)的桎梏,在世界的遼闊空間中審視這位作家,“畢竟一位作家的全部努力是為在整體的文化脈絡(luò)當(dāng)中獲得他的意義。”
阿來(lái)中篇小說(shuō)集《遙遠(yuǎn)的溫泉》德文版譯者馬海默,引用阿來(lái)自己的表述 “異族人過(guò)的并不是異類的人生”,他表示,阿來(lái)可以代表全人類聲音的藏地書(shū)寫(xiě),在西方社會(huì)能夠找到很多“沒(méi)有偏見(jiàn)的或者說(shuō)愿意克服自己偏見(jiàn)的讀者”。
幾位西方學(xué)者、翻譯家不約而同地談到,阿來(lái)作品以充滿生命多樣性又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藏地世界,祛除著西方對(duì)西藏的符號(hào)化想象,提供了另外的參照,這個(gè)意義超越文學(xué)本身,同西方對(duì)西藏的慣常想象產(chǎn)生抵抗、悖反與博弈,為西方世界理解西藏帶來(lái)了突破。
藉由歷史和自然的不朽力量,從現(xiàn)實(shí)中超拔出來(lái)
如果說(shuō)“建立起一種超越性的國(guó)家共識(shí)”的文學(xué)書(shū)寫(xiě),是阿來(lái)作為小說(shuō)家自覺(jué)、理性的部分,那么從感知層面又該如何感受阿來(lái)的文學(xué)呢?“黃色的報(bào)春、藍(lán)色的龍膽、紅色的點(diǎn)地梅,野百合、蒲公英、小杜鵑、李樹(shù)、櫻桃數(shù)、油菜花、土豆苗、豌豆花,我們的文學(xué)中有多久沒(méi)有這些鮮活的形象了?”中國(guó)作協(xié)創(chuàng)研部主任何向陽(yáng)從阿來(lái)小說(shuō)的自然觀切入,闡述自己的觀點(diǎn),“‘萬(wàn)物有靈,且平等’,這是打開(kāi)阿來(lái)文學(xué)之門(mén)的另一把鑰匙。”何向陽(yáng)談到,穿越了“自覺(jué)”達(dá)至“自在”之境的阿來(lái),是擁有完整世界觀的詩(shī)人小說(shuō)家,進(jìn)行著人與萬(wàn)物之間的相互理解和深層對(duì)話。她朗誦起古羅馬詩(shī)人奧維德《變形記》中的古老詩(shī)句,感慨其與阿來(lái)的《機(jī)村史詩(shī)》仿佛是一次相隔兩千多年的邂逅,“這兩千多年來(lái),人類和自然發(fā)生了太多的變化,但是當(dāng)中總有些不變的東西,如果一個(gè)作家觸到改變中的不變,并虔誠(chéng)地呈現(xiàn)它,那就是他用他的文字對(duì)這個(gè)涌動(dòng)而恒久的宇宙法則的尊重。”
中山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謝有順對(duì)此有同感,“文學(xué)如果迷信一種變化,光有世俗性而沒(méi)有超越性,寫(xiě)作就會(huì)匍匐在地上,站不起來(lái)。”在謝有順看來(lái),歷史與自然的不朽,是文學(xué)中最為重要的兩個(gè)不變的價(jià)值根基,阿來(lái)的寫(xiě)作記下了這個(gè)世界所具有的這種不朽的品質(zhì),他寫(xiě)歷史中的人、自然中的人,這兩個(gè)角度的建立為阿來(lái)筆下的人物構(gòu)建起一個(gè)超越性的背景,所以他筆下的人有一種從現(xiàn)實(shí)中超拔出來(lái)的力量。這個(gè)超越性的力量,恰恰不是宗教的力量,而是人文的力量。
“阿來(lái)小說(shuō)的開(kāi)頭常常有意無(wú)意地表述他的時(shí)間觀,這種時(shí)間觀有點(diǎn)類似于歷史循環(huán)論,不是進(jìn)化論,和古老的中國(guó)式運(yùn)命之道遙相呼應(yīng),內(nèi)容上與古今之變心有靈犀,那種進(jìn)化論認(rèn)識(shí)基礎(chǔ)上的現(xiàn)代性對(duì)阿來(lái)來(lái)說(shuō)只是容納囊括。”《人民文學(xué)》雜志主編施戰(zhàn)軍提出,評(píng)價(jià)阿來(lái)的創(chuàng)作應(yīng)該著眼于兩個(gè)維度:一個(gè)是百年新文學(xué)中近些年才被重新擦亮的傳統(tǒng),即非線性、非進(jìn)化的時(shí)間認(rèn)知系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從周作人到沈從文到汪曾褀一路而來(lái),可以追溯到老子、莊子的時(shí)間觀念,是對(duì)人的現(xiàn)世和未來(lái)更寬厚的審視和擔(dān)憂。第二個(gè)維度,是世界文學(xué)中的大生態(tài)關(guān)切,即人在其中的自然文學(xué)。不是西方自然文學(xué)里面的荒野,也不是傳統(tǒng)的中國(guó)山水畫(huà),而是今生今世的生命與中國(guó)先哲曾經(jīng)定義的自然相遇,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這就是阿來(lái)的小說(shuō)。
研究、譯介與傳播,共同成就“經(jīng)典”
從《瞻對(duì)》的非虛構(gòu)文體意義,《機(jī)村史詩(shī)》中的風(fēng)景政治,《塵埃落定》中的女性書(shū)寫(xiě),阿來(lái)文本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現(xiàn)代性、懷舊抒情性到如何從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整體發(fā)展中考量阿來(lái)小說(shuō)、阿來(lái)對(duì)我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東西格局平衡的貢獻(xiàn)等,都成為大家熱議的話題,其中不乏觀點(diǎn)的交鋒。
“不能認(rèn)為阿來(lái)是地方主義者,也不能認(rèn)為他是古典主義者,他不是傳統(tǒng)主義者,也不是現(xiàn)代主義者,多種線條構(gòu)成了復(fù)雜的網(wǎng)絡(luò),他的游移恰恰是文學(xué)的價(jià)值所在,反映思考的深度,也真實(shí)反映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的精神狀況。”中國(guó)作協(xié)創(chuàng)研部副研究員岳雯如是說(shuō)。這樣的研討又一次告訴我們,作家的創(chuàng)造跟批評(píng)的闡釋共同建構(gòu)起文學(xué)的世界與生態(tài)。
魯迅文學(xué)院常務(wù)副院長(zhǎng)邱華棟介紹說(shuō),魯迅文學(xué)院每年培訓(xùn)800到1000名寫(xiě)作者,一直把阿來(lái)的多重文體作為范例來(lái)教學(xué)、研究,“我就問(wèn)學(xué)員們能不能從中獲得啟發(fā),打開(kāi)自己的寫(xiě)作,讓更多文體在筆下呈現(xiàn)出更多的可能性。”邱華棟表示,他自己也猜不到阿來(lái)的文體邊界還有多遠(yuǎn),總覺(jué)得阿來(lái)還會(huì)在文體上帶來(lái)更多的驚喜。
四川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陳思廣回顧了他編《阿來(lái)研究》雜志這些年的體會(huì),他編了九期的《阿來(lái)研究》,粉碎了很多唱衰論調(diào),這本刊物可能是唯一一個(gè)仍在出版的有關(guān)某一當(dāng)代作家研究的專門(mén)期刊。
今年是《塵埃落定》出版20周年,中國(guó)出版集團(tuán)公司副總裁潘凱雄回憶說(shuō), 1998年阿來(lái)寫(xiě)出《塵埃落定》的時(shí)候,正是中國(guó)文學(xué)出版開(kāi)始走向市場(chǎng)的時(shí)候,當(dāng)時(shí)他所在的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認(rèn)為這是一部非常優(yōu)秀的作品,但是對(duì)它的市場(chǎng)前景存在分歧。但事實(shí)證明,這部作品初版5萬(wàn)冊(cè)很快銷售一空,當(dāng)年即加印5萬(wàn)冊(cè),現(xiàn)在這本書(shū)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一共有15個(gè)版本,同時(shí)被將近30個(gè)國(guó)家翻譯成不同語(yǔ)種傳播到世界各地。“經(jīng)過(guò)時(shí)間檢驗(yàn),優(yōu)秀文學(xué)作品借助好的出版和傳播,同樣能夠有非常好的讀者市場(chǎng)。”《塵埃落定》從暢銷到長(zhǎng)銷的成功之路,讓作為出版人的潘凱雄對(duì)缺乏暢銷特質(zhì)的經(jīng)典品質(zhì)文學(xué)創(chuàng)作充滿信心。
意大利翻譯家李莎、韓國(guó)學(xué)者金泰城、烏克蘭翻譯家娜佳等都談到了阿來(lái)作品乃至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在其國(guó)家的譯介情況,發(fā)現(xiàn)中國(guó)的文學(xué)作品通過(guò)英文或者法文等其他語(yǔ)種作為中介再翻譯的現(xiàn)象不是個(gè)例。蘇州大學(xué)海外漢學(xué)研究中心主任季進(jìn)對(duì)此也有擔(dān)憂,“當(dāng)代文學(xué)通過(guò)不同語(yǔ)言的相互轉(zhuǎn)譯之后,能夠保留多少中國(guó)元素、中國(guó)經(jīng)驗(yàn)?”但他同時(shí)不無(wú)欣喜地談到,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傳播由政治性向?qū)徝佬赞D(zhuǎn)變,很多專業(yè)性、審美性的評(píng)價(jià)也越來(lái)越多,“《塵埃落定》的海外傳播中有很多報(bào)道文章關(guān)注作品的可讀性、文學(xué)性和文本價(jià)值,也為本土研究提供新的視野,應(yīng)該充分尊重海外研究,建立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與西方對(duì)話的關(guān)系,推動(dòng)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認(rèn)知與接受。”

阿來(lái)在研討會(huì)上傾聽(tīng)大家的研討
“我用寫(xiě)作回答我自己的問(wèn)題”
在研討會(huì)最后,作為主角的阿來(lái)作了答謝發(fā)言,真誠(chéng)地感謝大家的研討。“在13歲之前,我根本就沒(méi)聽(tīng)說(shuō)過(guò)文學(xué)、作家這些詞”,至于為什么要寫(xiě)作,阿來(lái)坦言,他的文學(xué)書(shū)寫(xiě)就是進(jìn)入空白的沒(méi)有經(jīng)驗(yàn)的地方,藏族人雖然有藏文,可是藏文過(guò)去主要是在寺院使用,普通老百姓并不掌握這種語(yǔ)言,對(duì)于文學(xué)來(lái)講它就是完全沒(méi)有經(jīng)驗(yàn)的地帶。
阿來(lái)追憶自己在家鄉(xiāng)進(jìn)行歷史文化調(diào)查的細(xì)節(jié),以及寫(xiě)作《塵埃落定》《瞻對(duì)》《機(jī)村史詩(shī)》的緣起。他透露,“我寫(xiě)這些作品是首先回答我自己的問(wèn)題。比如西藏問(wèn)題到底是什么問(wèn)題。因?yàn)楝F(xiàn)成的知識(shí)系統(tǒng)沒(méi)有提供可以解決我的那些問(wèn)題的辦法,我自己通過(guò)寫(xiě)作解決更簡(jiǎn)單,用文學(xué)的方式進(jìn)入到社會(huì)生活當(dāng)中。”對(duì)于研討會(huì)上專家、學(xué)者針對(duì)文體的剖析,阿來(lái)回應(yīng)道,自己腦子里面沒(méi)有文體的分別。“寫(xiě)詩(shī)、寫(xiě)小說(shuō)、寫(xiě)非虛構(gòu)、寫(xiě)散文,那是我當(dāng)時(shí)的情緒、當(dāng)時(shí)的思考,要表達(dá)這些情緒跟思考,拿到的材料,它適合用什么體裁就用什么體裁,可以講故事就變成小說(shuō),講不了但能抒發(fā)某種情緒就是詩(shī)歌,如果想做更理性的分析就是散文。”
阿來(lái)由衷地表達(dá)了自己在寫(xiě)作中對(duì)世界和事實(shí)的尊重之意,“就像非虛構(gòu)寫(xiě)作所代表的一種更縝密的、對(duì)基本世界跟事實(shí)保持的莊重態(tài)度,我特別喜歡‘莊重’這個(gè)詞,這種書(shū)寫(xiě)是我們應(yīng)該提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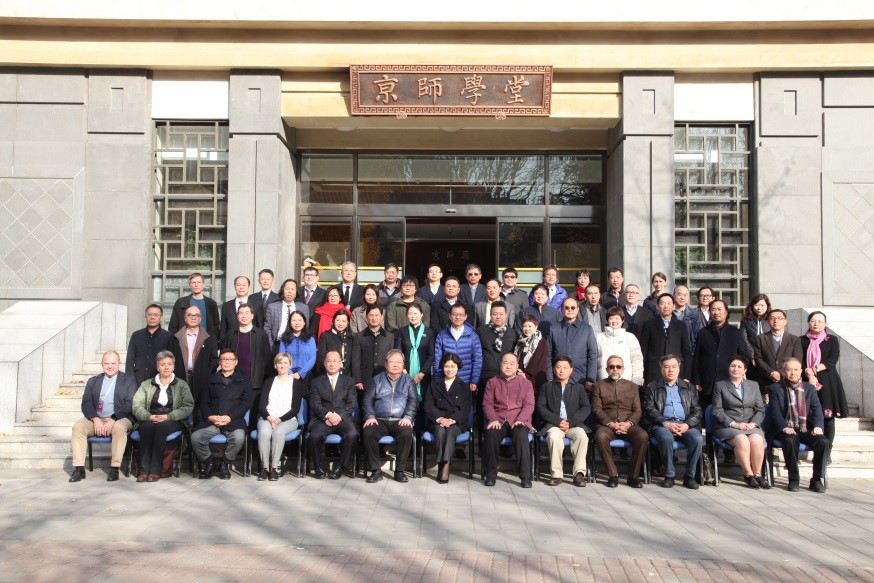
與會(huì)人員合影
(攝影:李幸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