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街九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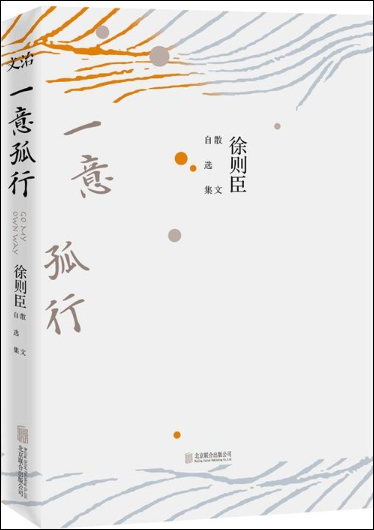
《花街九故事》 徐則臣 著 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 2018年10月
老默把錢留給了藍(lán)良生
1.老默
修鞋的老默死在下午。據(jù)負(fù)責(zé)處理這件案子的警察說,老默死的時(shí)候在下午一點(diǎn)左右,開雜貨鋪的老歪從床上爬起來,迷迷糊糊地披著衣服要去廁所,開了門驚得他睡意全無,他看見老默倒在他的修鞋攤子上,腦袋歪在一堆修鞋的家伙里,一半的屁股還坐在倒下的小馬扎上,吃了半邊的饅頭從飯盒里滾到了老榆樹底下。老歪喊了一聲老默,老默一動不動,又喊了一聲,還是不動,再喊了一聲,他就叫了起來:“老婆,不好了,修鞋的老默死了!”
老歪是個(gè)大嗓門,他的叫聲把一條街都驚動了。沿街的板門凌亂地打開,吱吱啞啞響成一片,一雙雙穿著拖鞋的腳陸續(xù)從花街兩頭奔湊過來,到了榆樹底下就不動了,他們把老默的修鞋攤子圍成一圈。他們不敢上前,站在一邊把兩只手握成拳頭抱在胸前看,我祖父和老歪走上前去,一人拽著老默的一條胳膊把他從修鞋攤子上架起來,他們想讓他站直了。可是老默站不直,腳沒法堅(jiān)實(shí)地著地,整個(gè)人像一只僵硬的蝦米,總也抬不起頭來。祖父試探一下老默的鼻孔,臉一下子拉長了,擺擺手對大家說:“沒用了。”
老歪的老婆從斜一側(cè)的樹根處撿起老默吃剩下的那半個(gè)饅頭,又冷又硬,像一捧粗砂做成的,一碰就向下掉饅頭渣子。“這個(gè)老默,做飯時(shí)我說給他熱一下,他不愿意,說喜歡吃冷的,”她把饅頭展示給大家看,抹著眼睛說,“這下好了,連冷饅頭都吃不上了。”
附和她的是我祖母,她那樣子好像是因?yàn)樯鷼獠诺粞蹨I的,她在我祖父旁邊指指點(diǎn)點(diǎn),主要針對老默單薄的衣服。“你看這該死的老默,給了他好幾條褲子他都不穿,就穿兩條單褲,連毛褲都不穿,大冷的天。”老默穿得的確很少,一件老得袖口露出棉花的小棉襖,上面套著藍(lán)灰色的中山裝,褲子是打著補(bǔ)丁的灰色單褲。還光著腦袋,而我們花街上頭發(fā)少的老人在冬天都戴著呢子或者毛線織成的帽子。祖母的話引起了大家的共鳴,很多人都跟著說老默的不是。你想想,一年到頭在花街?jǐn)[攤修鞋,三三兩兩地積累下來,老默的日子應(yīng)該過得很不錯才對。又不是沒錢,吃飯也省,穿衣也省,還要省成個(gè)百萬富翁啊。大家議論得很起勁,把老默已經(jīng)死了這事都給忘了。
“別咋呼了,人都死了,”我祖父說,想找個(gè)合適的地方把老默放下,他不能和老歪就這么一直抱著他。“男人留下,女人快回去找警察!”
女人們一哄而散,慌慌張張地不知要往哪兒跑。
祖父和一幫男人留下來收拾老默和他的修鞋攤子,雜七雜八的東西都撿起來放到他的三輪車?yán)铩@夏纳眢w僵了,祖父他們折騰了半天也沒能把他弄直,只好就讓他彎著睡在草席上,說不出來的別扭姿勢。草席是開豆腐店的藍(lán)麻子讓兒子良生從家里拿來的,沒用過的新席子。老默生前最喜歡吃藍(lán)麻子的豆腐腦,幾乎每天早上都吃,這些年來沒少給他送錢。剛收拾好,警車就到了,車停下來警笛還響著。尖銳的警笛聲不僅把花街上的居民全吸引過來了,周圍幾條街巷的人也循著聲音聚來了。人們源源不斷地向老榆樹底下涌來,都知道一定出大事了,否則警車不會鉆進(jìn)花街這樣狹窄的小巷子的。
警察的程序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復(fù)雜。他們拍拍打打把老默試探了一遍,掀開他的眼皮,撬開他的嘴,祖父他們剛剛沒發(fā)現(xiàn),老默的嘴里還有一塊沒嚼碎的冷饅頭。警察抱著他的臉左右端詳,又簡單地看了一下老默的周身,解開他的衣服又給他穿上,折騰來折騰去,就檢查完了。我祖父問一個(gè)戴眼鏡的警察怎么回事,警察說,還能怎么回事,他是猝死,與別人無關(guān)。這個(gè)結(jié)論多少讓我們有點(diǎn)失望。
老默對我們花街來說,其實(shí)是個(gè)熟悉的陌生人,因?yàn)闆]人知道老默的底細(xì)。他整天在這里擺攤修鞋,但是誰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家里還有什么人。什么都不知道,我們不知該把他送到哪個(gè)地方,只好由警察先收著。警察們同意了,他們也要作進(jìn)一步的調(diào)查。警察讓祖父他們幫個(gè)忙,把老默的尸體抬上車,正要塞進(jìn)車?yán)飼r(shí),那個(gè)戴眼鏡的警察在老默的上衣口袋里發(fā)現(xiàn)了一張紙。他打開那張因折疊時(shí)間過久而發(fā)絨泛黃的紙片,看了一眼就專注地讀出了聲:
“我叫楊默,半生修鞋,一身孤寡,他們叫我老默。我已經(jīng)老了,算不透自己的死期,所以早早立遺囑如下:我愿意將僅存的積蓄兩萬元整送給花街藍(lán)麻子豆腐店的藍(lán)良生,已將款額存到了他的名下,請發(fā)現(xiàn)此遺囑者代為轉(zhuǎn)達(dá)。老默感激你了。”
2.花街
從運(yùn)河邊上的石碼頭上來,沿一條兩邊長滿刺槐樹的水泥路向前走,拐兩個(gè)彎就是花街。一條窄窄的巷子,青石板鋪成的道路歪歪扭扭地伸進(jìn)幽深的前方。遠(yuǎn)處攔頭又是一條寬闊慘白的水泥路,那已經(jīng)不是花街了。花街從幾十年前就是這么長的一段。臨街面對面擠滿了灰舊的小院,門樓高高低低,下面是大大小小的店鋪。生意對著石板街做,柜臺后面是床鋪和廚房。每天一排排拆合的店鋪板門打開時(shí),炊煙的香味就從煤球爐里飄搖而出。到老井里拎水的居民起得都很早,一道道明亮的水跡在青石路上畫出歪歪扭扭的線,最后消失在花街一戶戶人家的門前。如果沿街走動,就會在炊煙的香味之外辨出井水的甜味和馬桶溫?zé)岬臍馕叮€有清早平和的暖味。
老默跟著一條水跡進(jìn)了花街,多少年來都是這樣。三輪車的前轱轆軋著曲折的水線慢騰騰地向前走,走到榆樹底下,拎桶的人繼續(xù)向前,老默停下了。他把修鞋的一套家伙從車上拿下來,一樣樣井井有條地?cái)[好,然后聞到了藍(lán)麻子家的豆腐腦的香味。他扔下攤子循著香味來到豆腐店里,在柜臺里邊固定的靠窗的長條凳上坐下,對著在熱氣升騰里忙活的麻婆說:“一碗豆腐腦。你不是知道嗎,香菜要多多地放。”然后他對從豆腐缸后走出來的藍(lán)麻子說:“生意好啊,麻哥,老默又來了。”
藍(lán)麻子給他抹一下桌子,說:“饅頭帶了嗎?”
“帶了,”老默從口袋里拿出昨天晚上買的饅頭,生硬地掰開,“麻哥你看,冷了吃才有饅頭味。”
麻婆一直不說話,只有藍(lán)麻子陪著老默天南海北地瞎說一通。吃過一碗熱乎乎的豆腐腦,老默就一頭大汗,抹抹嘴遞上錢,開始向藍(lán)麻子和麻婆告辭,一路點(diǎn)著頭往回走。他從不在豆腐店里長時(shí)間待。走過我家的裁縫店時(shí),不忘和我祖父、祖母打個(gè)招呼,說兩句天氣什么的無關(guān)緊要的話。回到榆樹底下他的修鞋攤子前,在小馬扎上坐下來,摸出根香煙獨(dú)自抽起來,等著第一個(gè)顧客把破了的鞋子送過來。這時(shí)候花街才真正熱鬧起來,各種與生活有關(guān)的聲響從各個(gè)小院里傳出來,今天真正開始了。懶惰的小孩也從被窩里鉆出來,比如我,比如藍(lán)麻子的孫女秀瑯,比如老歪的孫女紫米。
我和秀瑯、紫米常在一起玩。走過修鞋攤子時(shí),我們都會停下來擺弄那些修鞋的工具,錘子、剪子和修鞋的縫紉機(jī),老默一點(diǎn)都不煩,做著示范告訴我們這些東西怎么用,在什么時(shí)候用。
節(jié)選自《花街》
內(nèi)容簡介
修鞋的楊默死了,一生孤寡的他留下遺囑,把身后僅存的財(cái)產(chǎn)留給藍(lán)麻子豆腐店的藍(lán)良生。當(dāng)警察把老默的尸體送到豆腐店門口,良生和鄰里因毫無頭緒的遺產(chǎn)歸屬發(fā)生爭執(zhí),良生的媽媽麻婆,一個(gè)對誰都和風(fēng)細(xì)雨的女人,在眾人面前喝斥良生把老默留下……一場死亡,牽引出花街幾十年的舊憶。花街像一艘悠久的沉船,在命運(yùn)的河流上,飄飄蕩蕩……
花街儼然成為一條越走越漫長的街巷,并且正在成為世界。《花街九故事》以花街為谷,乘載由人生悲喜與人情溫涼匯聚而成的河流……
作者簡介
徐則臣
1978年生于江蘇東海,畢業(yè)于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供職于人民文學(xué)雜志社。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過中關(guān)村》《青云谷童話》等。曾獲老舍文學(xué)獎、莊重文文學(xué)獎、華語文學(xué)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馮牧文學(xué)獎,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2015年度中國青年領(lǐng)袖”。《如果大雪封門》獲第六屆魯迅文學(xué)獎短篇小說獎,長篇小說《耶路撒冷》獲第五屆老舍文學(xué)獎、第六屆香港“紅樓夢獎”決審團(tuán)獎等。長篇小說《王城如海》被香港《亞洲周刊》評為“2017年度十大中文小說”、被臺灣《鏡周刊》評為“2017年度華文十大好書”。部分作品被翻譯成德、英、日、韓、意、荷、俄、阿、西等十余種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