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分份:革命時代“學者”與“文人”的歧途 ——對顧頡剛與魯迅沖突的另一種探討
內(nèi)容提要:
本文借助當事人日記、書信及相關(guān)史料,探討了顧頡剛、魯迅沖突之緣起的“內(nèi)面”及其潛在的思想對話。在“學者”顧頡剛看來,“文人”魯迅的品性和作風,是導致自己與之沖突的主要原因;而在魯迅的斗爭經(jīng)驗中,顧頡剛、陳西瀅等“學者”“文人”黨同伐異的手段,則是使自己憎惡他們的根源所在。顧頡剛在國民革命和北伐戰(zhàn)爭時期,對“學者”身份及使命的認識,雖然有所觸動與反省,卻未曾真正動搖;而此時的魯迅,不僅拒絕“文學家”“文人”的稱號,反思文人學者對“革命”貢獻的有限性,而且向往實際“戰(zhàn)士”的身份。顧、魯沖突的“內(nèi)面”,既展現(xiàn)了當事人信仰、情感的差異性,也呈現(xiàn)了后五四時代文化場域中知識分子思想分化、身份認同、“占位”競爭的復雜性。
本文原刊香港《中國文學學報》2015年第6期,感謝北京師范大學林分份老師授權(quán)發(fā)布。

顧頡剛與魯迅沖突之時,恰好處在國民革命和北伐戰(zhàn)爭時期,也是新文化陣營分化的重要階段。有關(guān)顧、魯沖突的緣由,除了學界聚焦的彼時顧氏傳播魯迅“抄襲”鹽谷溫一案,以及相關(guān)人事紛爭、派系傾軋、政治立場差異[1]之外,也與“五四”之后二者的文化立場、思想旨趣、身份定位等多所關(guān)涉。本文在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依據(jù)對顧頡剛、魯迅的日記、書信中有關(guān)二者關(guān)系的私人言說,以及其他相關(guān)史料文獻的梳理,試圖考察顧、魯沖突之緣起的另一面,勾勒二者之間可能存在的思想對話,進而剖析后五四時代知識分子思想立場、身份認同的差異,以及文化場域中“占位”競爭等問題。
一 “整理國故”與“欣賞藝術(shù)”
從學術(shù)史的角度看,顧頡剛與魯迅沖突之際,正是古史辨派在中國學界迅速崛起的時期。而作為與胡適、錢玄同齊名的古史辨“三君”[2]之一的顧頡剛,當他與魯迅這位新文學創(chuàng)作、新文化思想的領(lǐng)軍人物沖突時,其所強調(diào)的側(cè)重點往往與對方有別。這不僅源于顧氏早先對職業(yè)、身份的自我定位,對學術(shù)研究與文學創(chuàng)作(文藝批評)的具體評價,也源于他后來對魯迅的為人、文風的個人觀感。
1920年大學畢業(yè)之際,顧頡剛即表示:“我所求的職業(yè),乃是于我學問上可以進步的職業(yè)。”[3]因而,工作頭幾年,盡管生活拮據(jù),對于外界報酬豐厚的任教、講演等邀約,他一概回絕,為的是讓自己能有更多的時間專注于研究,由此成為一位純粹的學者。1922年4月,在給李石岑的信中,顧氏提出“學術(shù)界生活獨立問題”,李石岑將其轉(zhuǎn)發(fā)給多人,引來鄭振鐸、沈雁冰、胡愈之、郁達夫、嚴既澄、常乃惪諸人的討論[4]。1924年元旦,李石岑致吳稚暉信中,特意稱贊“我友顧頡剛先生,可謂最富于為學問而學問的趣味者”[5]。李石岑同時把信寄給顧氏,而顧氏在回信中也承認:“先生許我為‘最富于為學問而學問的趣味者’,實為知我之言,我決不謙讓。”[6]


魯迅(上)與顧頡剛(下)
顧頡剛“為學問而學問”的姿態(tài),也體現(xiàn)在與不同陣營人物的交往方面。1926年,顧氏寫道:
我們交往的人,也許有遺老、復辟黨、國粹論者、帝國主義者,但這決不是我們的陳舊的表征。我們的機關(guān)是只認得學問,不認得政見與道德主張的。只要這個人的學問和我們有關(guān)系,或者這個人雖沒有學問,而其生活的經(jīng)歷與我們的研究有關(guān)系,我們?yōu)檠芯康谋憷嫞斎缓退咏N覀兯咏脑皇撬恼麄€的人格,而是他與我們發(fā)生關(guān)系的一點。[7]
這一主張與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觀念實無二致。而在實際上,顧頡剛“只認得學問,不認得政見與道德主張”的態(tài)度,正是陳西瀅諸人大力捧贊的重點所在,也是顧氏人脈比較廣達的主要因素。由于沒有家派之別,顧氏雖是《語絲》所公布的十六個撰稿人之一,卻也參與“現(xiàn)代評論派”的宴請和陳西瀅、凌淑華的婚禮,并受陳西瀅和徐志摩之邀,頻頻在《現(xiàn)代評論》和《晨報副刊》上發(fā)表有關(guān)古史方面的文章。這也是后來顧氏被魯迅認定為“現(xiàn)代評論派”的原因之一。
在對待學問派別方面,顧頡剛主張必須改變從前學問家“以己學為正學,必使天下惟我是從,定我為一尊而后快”[8]的態(tài)度。具體到整理國故方面,他批評從前的人用“家派”的態(tài)度整理國故,還是一種“宗教的態(tài)度”,而“現(xiàn)在我們就不然了。我們是立在家派之外,用平等的眼光去整理各家派或向來不入家派的思想學術(shù)。我們也有一個態(tài)度,就是:‘看出他們原有的地位,還給他們原有的價值’”。考慮到未必所有人都熱衷整理國故,顧氏在這篇文章的末尾寫道:“整理國故是新文學運動中應(yīng)有的事,但歡喜文學的人中,盡有專從藝術(shù)上著眼,不想做歷史的研究的,也有不耐做整理的功夫的,這一班人只須欣賞藝術(shù),不要一同整理國故。”[9]

顧頡剛著《古史辨》第一冊
雖然承認新文學運動中“欣賞藝術(shù)”的一派,但在顧頡剛心目中,“欣賞藝術(shù)”與“整理國故”的分量明顯不同。在幾年后有關(guān)康有為與王國維的比較文字中,顧氏指出:
他自己說,“三十五歲以后,學問沒有進步,也不求其進步。”所以學術(shù)界上的康有為,三十六歲就已死了。……至于靜安先生,確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進步的:三十五歲以前,他在學問上不曾做過什么大貢獻,他的大貢獻都在三十五歲以后。[10]
將康有為三十五歲以后的“通經(jīng)致用”與王國維三十五歲以后不斷追求學問的“進步”對照,再次看出顧氏“為學問而學問”的立場;同時,極力突出王國維三十五歲后的學術(shù)貢獻(“整理國故”),顯然也暗含著對其早年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學批評(“欣賞藝術(shù)”)成就[11]的有意漠視。
實際上,顧頡剛對“整理國故”與“欣賞藝術(shù)”的態(tài)度,一開始就涇渭分明。“五四”之后至大學畢業(yè)前夕,在寫給傅斯年、羅家倫的信中,顧氏屢屢表達了研究史學的志向:“你的意思,學問要從歷史上做起,我一向也這樣想,而且深愿照此做去。”[12]“我于學問上,很愿做史學的功夫。便是我入哲學門,也是想打好史學的根柢。因為哲學是人類精神的觀察,史學是人類精神的表章,原是在一個方向的。”[13]而在“五四”運動爆發(fā)之前,顧氏與傅斯年談及《新潮》雜志最近幾期的稿件時,對文學作品和人生觀(思想)論文的取向煞是分明:“這幾期你同志希(按:羅家倫)都傾向文學方面去,我有些失望。因為我們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文學是表現(xiàn)思想的形式;人生觀是創(chuàng)建思想的實質(zhì),實質(zhì)自然是形式的根本。”所以他寄望傅斯年能繼續(xù)撰寫《人生問題發(fā)端》或者談?wù)撍枷雴栴}、介紹西洋各個哲學家的人生觀的文章[14]。之所以特別重視人生觀(思想)的文章,是因為在顧氏看來,只有“科學常識同精密確當?shù)娜松^”,才是他們這一輩從事啟蒙或“使人起自覺心”的“根本”,“拿這二件建設(shè)得完備,再行發(fā)布這極端主義的鼓吹,方不使人凌亂失序,躐等進行”[15]。然而關(guān)于這兩方面的建設(shè)并非易事,尤其是當他看到《新潮》第三號有關(guān)“思想問題”的學術(shù)文章只有寥寥二篇時,即大發(fā)感慨:“可見研究學問,實非易事;最便當?shù)氖虑椋皇菍⑸鐣F(xiàn)象說說罵罵罷了。”[16]因而,在顧氏那里,是不懼艱難從事史學、哲學等關(guān)乎“人類精神”的學術(shù)研究,還是趨時就便寫寫文學批評或者社會評論,二者的價值明顯不同。
1921年初,顧頡剛留校任圖書館編目員不久,校長蔡元培囑其查看胡樸安所編《俗語典》。在寫給蔡元培的第一封匯報信中,顧氏談到,上海“最穩(wěn)重的文人”胡樸安,其所編《俗語典》實多缺點,故而覺得“他們與其為抄錄刪改的生涯,為有無不足輕重的事業(yè),不如勸他們在古書上做些功夫”[17]。在第二封匯報信中,顧氏則說:
胡君從前常在《國粹學報》作文,雖不見有精彩,然總是傾向樸學方面,所以我常以為他是一個帶有學問氣息的文人。近年來不甚見到他的文字,而他的弟寄塵(名懷琛)方趨時髦為新文學批評(記不真切,未知是此名否?)及大江集等書,彼亦不見有所論列,故疑為穩(wěn)重一流。[18]
顧氏言下之意十分明了,一個“文人”是否“帶有學問氣息”,以及是否屬于“穩(wěn)重一流”,乃在于其作文是“傾向樸學方面”,還是“為新文學批評”。
這樣的判斷標準,也影響了顧頡剛對新文學作家的評價。1923年6月,在給葉圣陶的信中,談及樸社的情況,顧氏寫道:“上海方面,雁冰是最好的辦事才,振鐸是最好的活動分子……”“振鐸是發(fā)起這社的第一人,而欠繳社費已有三月,成不得不使人失望。眼看再過三月,就要出社了。我們社里少一達夫之類的沒有什么可惜,而少一振鐸則大可惜”[19]。此時已因出版白話短篇小說集《沉淪》在文壇聲名鵲起的郁達夫,被拿來與鄭振鐸比較,其結(jié)果,前者自然是屬于“沒有什么可惜”、非“穩(wěn)重一流”的一類。1924年6月,在與妻子談到自己與新文化陣營諸君的區(qū)別時,顧氏舉出錢玄同《孔家店的老伙計》一文有關(guān)“孔家店有老牌的和冒牌的二種,這二種都該打”的劃分方法,表示十分認同錢玄同將他與胡適二人作為“打老牌的二人”,而“打冒牌的六人”則是陳獨秀、易白沙、魯迅、周作人、胡適之、吳稚暉。當然,顧氏的重點在于其中的區(qū)別:“打冒牌的孔家店,只要逢到看不過的事情加以痛罵就可,而打老牌卻非作嚴密的研究,不易得到結(jié)果,適之先生和我都是極富于學問興趣的……”“別人既怕讀書,又無膽量,能作文的多半是抱出風頭主義,故這個工作是擔任不了的(我現(xiàn)在也并不是擔任得了,只是秉著這個態(tài)度向前走去,將來不怕?lián)尾涣耍!盵20]而這,正是顧氏評價周作人、魯迅等新文學家的主要依據(jù)。
1922年6月,在一封致劉經(jīng)庵的信中,顧頡剛寫道:“歌謠研究會事,一言難盡。先是這會由劉半農(nóng)先生擔任,他出洋后,由周先生接下去。數(shù)年來無聲無臭,沒有作一點事。”顧氏據(jù)此認為,在北大的新文化運動大家中,除了蔡元培、胡適兩位在“真實做事情外”,其他人則不可靠,“大家看了虛名的可以招致外邊的信仰,大家努力造名望:自己職務(wù)上的事情不做,專做文章去發(fā)表。”因而,他對周作人的印象是:“周先生最壞的皮氣,就是職街盡管擔任,事務(wù)盡管不做。”[21]后來,在參與編撰《語絲》周刊期間,顧氏也屢屢在日記中寫下對魯迅、周作人兄弟行事、為文的觀感:
《語絲》近來文甚少,屢邀予作,未之應(yīng)。昨來函,謂將以無文停刊,想不忍見其夭折。因以舊日筆記一則抄與之。予今日對于魯迅、啟明二人甚生惡感,以其對人之挑剔詬誶,不啻村婦之罵也。今夜《語絲》宴會,予亦不去。(1926,01,17)[22]
昨語絲社宴會,予仍未去。此后永不去矣。魯迅等在報上作村婦之罵,小峰又以《言行錄》事屢慫恿魯仲華來找麻煩,均可厭。(1926,03,14)[23]
由在語絲社共事時嫌惡魯迅(及周作人)對人“挑剔詬誶”和在報上作“村婦之罵”,到后來擬與魯迅對簿公堂而購買其全部著作來閱讀,在顧氏看來,魯迅“乃活現(xiàn)一尖酸刻薄、說冷話而不負責之人”[24]。
實際上,顧頡剛所嫌惡者,正是魯迅以雜文作批評武器的文風及其“文人”身份。對于自己與魯迅之間的沖突,顧氏幾經(jīng)思考,認為主要原因在于:
按,魯迅對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陳通伯,《中國小說史略》剿襲鹽谷溫《支那文學講話》。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別人指出其剿襲為不應(yīng)該,其卑怯驕妄可想。此等人竟會成群眾偶像,誠青年之不幸。他雖恨我,但沒法罵我,只能造我的種種謠言而已。予自問胸懷坦白,又勤于業(yè)務(wù),受茲橫逆,亦不必較也。(1927,02,11)[25]
魯迅對于我排擠如此,推其原因,約有數(shù)端:
(1)揭出《小說史略》之剿襲鹽谷溫氏書。
(2)我為適之先生之學生。
(3)與他同為廈大研究教授,以后輩與前輩抗行[衡]。
(4)我不說空話,他無可攻擊。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話提倡科學者自然見絀。
總之,他不許別人好,要他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第一人,永遠享有自己的驕傲與他人的崇拜。這種思想實在是極舊的思想,他號“時代之先驅(qū)者”而有此,洵青年之盲目也。我性長于研究,他性長于創(chuàng)作,各適其適,不相遇問可已,何必妒我忌我!(1927,03,01)[26]
從以上《日記》內(nèi)容看,除了有關(guān)沖突起因之數(shù)端外,顧頡剛尤其突出自己與魯迅的諸多品性區(qū)別:我“胸懷坦白”,“勤于業(yè)務(wù)”,“不說空話”,“性長于研究”;而彼“卑怯驕妄”,“造我的種種謠言”,“以空話提倡科學”,“思想極舊”,“性長于創(chuàng)作”。如此種種不同,與顧氏此前對“整理國故”之“學者”與“欣賞藝術(shù)”之“文人”所設(shè)身份、專長的區(qū)隔標準,顯然若合符節(jié)。
此外,在給友人的信中,顧頡剛尤其指出:
若要排擠魯迅們來成全自己,更無此想。老實說,他的文學是我及不來的,他的歷史研究是我瞧不起的,及不來則不必排擠,瞧不起更不屑排擠。我豈無爭勝之心,但我的爭勝之心要向?qū)砜梢詣龠^而現(xiàn)在尚難忘其項背的人來發(fā)施。例如前十年的對于太炎先生,近來的對于靜安先生。我要同他們爭勝,也是‘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站在學術(shù)上攻擊。[27]
結(jié)合顧氏對自身學問個性的定位,以及后來在古史領(lǐng)域長達數(shù)十年的研究工作看,這樣的解釋并非虛言。或者,在顧氏看來,與他所要爭勝的對象相比,作為“剽竊”且“不知學”的“文人”魯迅,即使不是“不值得的”也是“道不同的”那一類,根本沒有爭勝的必要——而這,與他極力突出王國維后來“整理國故”的貢獻,而忽略其早年“欣賞藝術(shù)”的成就,自有其相通之處。
二 “學者”“文人”的“黨同伐異”
對于“學者”與“文人”,魯迅在1927年曾作如此區(qū)分:“研究文章的歷史或理論的,是文學家,是學者;做做詩,或戲曲小說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文人,此刻所謂創(chuàng)作家。創(chuàng)作家不妨毫不理會文學史或理論,文學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詩。”[28]在魯迅其他場合的表述中,“文人”所對應(yīng)的稱呼還有“作家”“文藝家”“詩人”“文家”等,“學者”所對應(yīng)的稱呼還有“學士”“研究家”“教授”等。此外,在具體文章中,魯迅經(jīng)常使用“文士”“文人學者”“學士文人”“學者文家”等合稱,另外也用“天才”“正人君子”“智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等來指稱相關(guān)的文人和學者。
與顧頡剛執(zhí)著于“整理國故”與“欣賞藝術(shù)”何者更為“根本”、抑或“學者”與“文人”何者更為“穩(wěn)重”不同,魯迅除了梳理中國歷代文人學者的“無特操”、附庸風雅、沽名釣譽、幫閑等特質(zhì)外,更為關(guān)注當下“學者”“文人”投機逐利、變化神速、善于造謠、卑劣陰險等方面的共同屬性[29]。在魯迅看來,尤其那群宣稱“搬進藝術(shù)之宮”或者“踱進研究室”的文人學者,不僅逃避現(xiàn)實,插科打諢,教人做順民,而且打著各種“公理”“公正”的旗幟,給對方貼上各種稱號和標簽,由此打壓那些與他們處于對立面的斗士。為此,魯迅揭開他們各種稱號和標簽背后的巧計:
如果開首稱我為什么“學者”“文學家”的,則下面一定是謾罵。我才明白這等稱號,乃是他們所公設(shè)的巧計,是精神的枷鎖,故意將你定為“與眾不同”,又借此來束縛你的言動,使你于他們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險性的。[30]
魯迅進而揭露了文人學者聯(lián)合起來打擊對手的嘴臉:
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至今還塞在書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據(jù)說都是講公話,談公理,而且深不以“黨同伐異”為然的。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幾下,——但這自然是為“公理”之故,和我的“黨同伐異”不同。[31]
此等“黨同伐異”的手段,正源于文人學者的狹隘與專制,因為“倘有人說過他是文士,是法蘭斯,你便萬不可再用‘文士’或‘法蘭斯’字樣,否則,——自然,當然又有‘某籍’……等等的嫌疑了”[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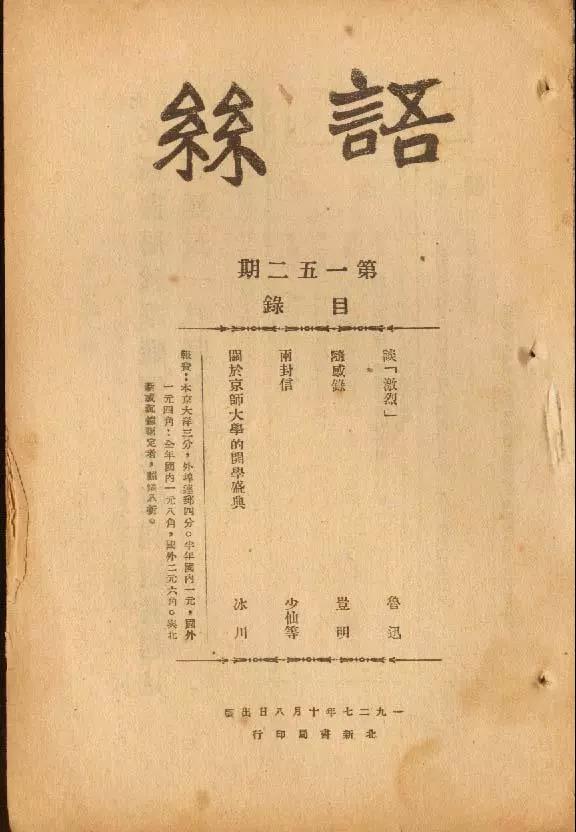
《語絲》雜志書影
魯迅的判斷,來自他當時與陳西瀅、徐志摩等《現(xiàn)代評論》諸公論戰(zhàn)的體驗。陳西瀅曾稱贊徐志摩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來與胡適、郭沫若、郁達夫、周氏兄弟等并列的“稍有貢獻”的人之一:“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體制方面,他的詩及散文,都已經(jīng)有一種中國文學里從來不曾有過的風格。”而徐志摩也撰文稱贊陳西瀅“就他學法郎士的文章說,我敢說,已經(jīng)當?shù)闷鹨痪涮旖蛟挘骸懈恕!睂τ陉悺⑿於换ハ啻蹬酢⒙?lián)袂作戰(zhàn)的把戲,魯迅予以拆穿:“中國現(xiàn)今‘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總算已經(jīng)互相選出了。”[33]此外,陳西瀅在評價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作品(實際評價了十一部)時,對顧頡剛不吝贊詞:“在學術(shù)方面,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的價值是不容易推崇過分的。他用了無畏的精神,懷疑的態(tài)度,科學的方法去整理一篇幾千年以來的糊涂賬,不多幾年已經(jīng)開辟了一條新路,尋到了許多大漏洞。”而對于魯迅,除了肯定《孔乙己》、《風波》、《故鄉(xiāng)》、《阿Q正傳》等小說外,則認為:“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的價值。”[34]對于陳西瀅抑此揚彼的修辭策略,魯迅后來指出:“陳西瀅也知道這種戰(zhàn)法的,他因為要打倒我的短評,便稱贊我的小說,以見他之公正。”[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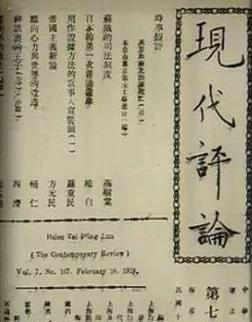
《現(xiàn)代評論》雜志書影
與陳西瀅等人的論戰(zhàn),使魯迅看清了文人學者披著“公理”“公正”的外衣進行“黨同伐異”的真面目。故此,后來在與顧頡剛的沖突中,魯迅除了不滿對方“只講學問,不問派別”的“學者”面孔外,尤其批判他作為“現(xiàn)代評論派”或“研究系”一員[36]所采取的“派系”手段。而這,也正是讓魯迅在奔赴廈門、廣州任教的過程中,對顧頡剛屢生惡感,以至于與對方交惡的關(guān)鍵因素。
仔細考察二者交往的過程,魯迅對顧頡剛的態(tài)度,在兩三年間有著較為明顯的變化。據(jù)《魯迅日記》載,他與顧頡剛之間的交往,最早始于1924年10月,當時顧氏等到魯迅家請其設(shè)計《國學季刊》的封面圖案;以后除幾次書信往來外,顧氏先后給魯迅送(寄)過《古史辨》第一冊、《孔教大綱》和《諸子辨》等書;當魯迅要離開廈大時,顧氏也參加了歡送宴會[37]。但魯迅對顧氏的不滿,在廈大時就已開始了。剛到廈大,魯迅多次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指出:
在國學院,顧頡剛是胡適之的信徒。另外還有兩三個,似乎是顧薦的,和他大同小異,而更淺薄。
看廈大的國學院,越看越不行了。顧頡剛是自稱只佩服胡適陳源兩個人的,而潘家洵陳萬里黃堅三人,皆似他所薦引。
他所薦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此人頗陰險,先前所謂不管外事,專看書云云的輿論,乃是全部為其所欺。[38]
經(jīng)此,魯迅將顧氏當作“現(xiàn)代評論派”在廈大的代表,而將顧氏力薦熟人到廈大國學院的做法看作是“拉幫結(jié)派”的舉動,并將這種局面當作是北大的派系斗爭在廈大的延續(xù)[39]。因而,魯迅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在廈大久待下去。
觀諸魯迅此時的文字,其對顧頡剛的個人觀感尚未有更劇烈之處,但接下來的兩件事大大刺激了魯迅。其一,魯迅想推薦章廷謙到廈大任教,開始顧氏持反對意見,但當獲得通過時,顧氏為“討個人緣”[40],又先行通知章氏。因此,魯迅大怒:“我實在熬不住了,你給我的第一信,不是說某君首先報告你事已弄妥了么?這實在使我很吃驚于某君之手段,據(jù)我所知,他是竭力反對玉堂邀你到這里來的,你瞧!陳源之徒!”[41]顧氏的做法,使魯迅對其惡感加深。其二,顧氏為胡適的書記程憬謀取代替孫伏園在廈門佛學院所兼職務(wù)一事的做法,更使魯迅覺得“你看研究系下的小卒就這么陰險,無孔不入,真是可怕可恨”[42]。這兩件事的是非曲直,或者不一定都如魯迅所想的那樣,但種種遭遇都讓其聯(lián)想在北京時與《現(xiàn)代評論》諸公的不愉快經(jīng)歷,因而在人格上將顧氏視為與陳西瀅同是“陰險”的一類。而章廷謙的遭遇,也使得魯迅在接下來的日子里,將其視為一起遭受顧氏排擠的受害者,因而屢屢在寫給章氏的信中強烈譴責顧氏,乃至用生理缺陷加以諷刺和丑化。
后來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在解釋自己離開廈大并擬接著離開中大的原因時,魯迅寫道:
我在廈門時,頗受幾個“現(xiàn)代”派的人排擠,我離開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為從北京請去的教員留面子,秘而不說。不料其中之一(按:顧頡剛),終于在那里也站不住,已經(jīng)鉆到此地來做教授。此輩的陰險性質(zhì)是不會改變的,自然不久還是排擠,營私。我在此的教務(wù),功課,已經(jīng)夠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閑氣。所以我決計于二三日內(nèi)辭去一切職務(wù),離開中大。[43]
在此,魯迅突出的正是自己遭受排擠的境遇[44]。如果說,在廈大時,因顧及林語堂和北京諸教員的面子,魯迅沒有將矛盾公開化,那么到了中大以后,他則毫不猶豫地表達不與顧頡剛共處一校的立場。在給孫伏園的信中,魯迅寫道:
我真想不到,在廈門那么反對民黨,使兼士憤憤的顧頡剛,竟到這里來做教授了,那么,這里的情形,難免要變成廈大,硬直者逐,改革者開除。而且據(jù)我看來,或者會比不上廈大,這是我新得的感覺。我已于上星[期]四辭去一切職務(wù),脫離了中大了。[45]
顧頡剛4月18日到中大,魯迅4月21日提出辭職,這顯然是一種公開的對立姿態(tài)。在致友人的另一封信中,魯迅表明了自己所受的聯(lián)手排擠:
不過事太湊巧,當紅鼻到粵之時,正清黨發(fā)生之際,所以也許有人疑我之滾,和政治有關(guān),實則我之“鼻來我走”(與鼻不兩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原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顧傅為攻擊我起見,當有說我關(guān)于政治而走之宣傳,聞香港《工商報》,即曾說我因“親共”而逃避云云,兄所聞之流言,或亦此類也歟。[46]
對于顧頡剛到中大,以及其與傅斯年的“勾結(jié)”,魯迅的不滿溢于言表。傅斯年為挽留二人,先讓顧氏避開魯迅,到外地購書,魯迅也視之為鉆營[47]。
然而魯、顧二人矛盾的完全公開化,乃是五月初孫伏園將魯迅、謝玉生寫給他的信,以《魯迅先生離開廣東中大》[48]為題,發(fā)表在武漢的《中央副刊》上。文中不管是魯迅、謝玉生信中內(nèi)容,還是孫伏園的解讀,都一致將魯迅之離開廈大到中大、復離開中大的主要原因歸之于顧頡剛,且有謂顧氏“反對民黨”、“反動”等語。顧氏于六月中讀到此文,后于七月底致信魯迅,要求九月中旬在廣東對魯迅、謝玉生提起訴訟;而魯迅答以九月在滬,可就近在浙起訴[49]。對于顧氏的訴訟要求,魯迅憤懣有加,認為此乃“放刁”:“他用這樣的方法嚇我是枉然的;他不知道我當做《阿Q正傳》到阿Q被捉時,做不下去了,曾想裝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點牢監(jiān)里的經(jīng)驗。”[50]魯迅看似放達的言詞中包含著某種悲憤之感——他大概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一向被人排擠,卻反而被要求“法律解決”!雖然最后雙方并未對簿公堂,但魯迅對顧氏的怨憤也由此加深,在私人信件中仍然極盡嘲諷之能事[51]。
在魯迅看來,顧頡剛不僅是“現(xiàn)代評論派”一員,更是“研究系下的小卒”,因而,對于自己在廈大所受顧氏等人的“排擠”,也曾想“到廣州后,對于研究系加以打擊”,但他也表明自己的無奈:“研究系是應(yīng)該痛擊,但我想,我大約只能亂罵一通,因為我太不冷靜,他們的東西一看就生氣,所以看不完,結(jié)果就只好亂打一通。”[52]然而,魯迅還是多次在私人信件中,表達了對顧氏等人的學問的不屑:“你要知道鼻的小玩藝,是很容易的。只要看明末清初蘇州一帶地方人的互相標榜和攻訐的著作就好了”;而《新月》“雖然作者多是教授,但他們發(fā)表的論文,我看不過日本的中學生程度”[53]。魯迅的這一看法甚至延及北平乃至整個中國學界:“北平之所謂學者,所下的是抄撮功夫居多,而架子卻當然高大,因為他們誤解架子乃學者之必要條件也。……看不到‘學’,卻能看到‘學者’”;“而所謂‘大師’‘學者’之流,則一味自吹自捧,絕不可靠……”[54]據(jù)此來看,魯迅對所謂“整理國故”之“學者”的評價,實與顧氏“根本”“穩(wěn)重”的斷語大相徑庭。而此中也不難看出,新文化運動落潮后,魯迅對陳西瀅、顧頡剛等人產(chǎn)生惡感乃至最終交惡的主要原因,并非源于各自職業(yè)、身份及專長的客觀差異,而是源于對方攜手抱團以排擠、打壓進步人士的共同伎倆。
三 革命時代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
“五四”之后,“國民性”也曾是顧頡剛所關(guān)注的問題之一,所謂“知道了中國國民性,才可從根本上去改良中國社會”[55]。然而,由于相信“科學常識同精密確當?shù)娜松^”才是“使人起自覺心”的根本,顧氏最終認定安心學術(shù)也是一種實實在在的“革命”。故此,1919年9月,在給妻子的信中,他認為當前最要緊的事情有二:“(一)自己充足了學問,從根本上立革新計劃;(二)喚起國人好學的心神,教他自己去求學問,自己去立革新計劃。因為要實現(xiàn)以上的二條,所以一方面要自己努力求學,一方面又要做社會教育事業(yè)。”然而“現(xiàn)在的社會教育,或是只有形式,或是專輸進舊思想、死思想。不見善果,翻成惡業(yè)。所以我輩不可再蹈此弊,當以‘自己努力求學’,去做社會教育的骨子”[56]。
在“五四”一周年紀念前夕,顧頡剛一度表達了對“革命”的懷疑:
對一種惡制度,要改變他,非得革命不可。要革命成功,非得聯(lián)絡(luò)各界,號召黨徒不可。但聯(lián)絡(luò)各界號召黨徒之后,他的自身也變成了一種惡制度。前者之惡雖革,而后者之惡已興。或前者之惡尚未革,而后者之惡已興起而并與之對峙。民國以來的幾次革命,都是如此。[57]
不僅如此,彼時顧氏應(yīng)羅家倫之邀,本擬做一篇《對于群眾運動的懷疑》給《晨報·五四紀念號》[58],但后來發(fā)表時題為《我們最要緊著手的兩種運動——教育運動 學術(shù)運動》。在該文中,顧氏闡釋“學問”對于“革命”的根本意義:
學問是感情和沖動的指導者,也是感情和沖動的約束者。他可以給我們以明確的主張、正當?shù)牟襟E、永久的意志。大家有了做學問的誠信,自然使世界上的惡勢力,都失掉了原來在糊涂腦筋里的根據(jù);更使世界上的好勢力,在清明的腦筋里,確定了他的根據(jù)。那末,世界便能隨時革命,不須有特別的革命標榜了。人人都能用自己的知識去辨別是非,有修養(yǎng)去定進行趨向,人人都堂堂的做個人,便人人都是革命者,也無須有專做指揮他人屈抑他人的革命領(lǐng)袖了。[59]
本著這樣的信念,在1926年底,顧氏說明自己專注學問、不涉政治的意義所在:“我的意思,只是斬荊棘不必全走在政治的路上,研究學問只要目的在于求真,也是斬除思想上的荊棘”;“我不愿以‘革命’自己標榜,但我自己知道,我是對于二三千年來中國人的荒謬思想與學術(shù)的一個有力的革命者”[60]。
當然,此時國民革命軍北伐節(jié)節(jié)勝利的形勢,也大大刺激了顧頡剛的思想。1927年1月,因受廈門大學委派,顧頡剛到福州采購古籍和地方志,會晤了當時在北伐軍東路軍總指揮部任職的王悟梅,由此得與幾位軍官交往。后來在給胡適的信中,顧氏寫道:
我深感到國民黨是一個有主義、有組織的政黨,而國民黨的主義是切中于救中國的。又感到這一次的革命確比辛亥革命不同,辛亥革命是上級社會的革命,這一次是民眾的革命。我對于他們深表同情,如果學問的嗜好不使我卻絕他種事務(wù),我真要加入國民黨了。
此時顧氏對國民黨的好感溢于言表,以至于極力勸說胡適歸國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動為宜。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國民黨”[61]。
受這股“民眾的革命”大潮刺激,顧頡剛一度熱衷于談?wù)摗案锩薄皞鞯馈钡仍掝}。1927年7月,在給好友王伯祥、葉圣陶的信中,顧氏認為“在廈大中真實立革命目標,作革命工作,有革命計劃的”只有他自己,相反,讓他瞧不起的魯迅“他們以喊革命口號為全部的工作,反以不喊口號而埋頭工作的為反革命,真是可笑。然而革命不成,‘革命家’的頭銜卻已取得了,魯迅們也心滿意足了”[62]。在顧氏看來,是“不喊口號而埋頭革命”,還是“以喊革命口號為全部的工作”,正是自己與魯迅們的根本區(qū)別。兩天之后,在給葉圣陶的另一封信中,顧氏甚至表示:“我近來頗有傳道的沖動,我的道是‘打倒圣賢文化,表章(彰)民眾文化’,故無論作文或演說,總要說到這上去。但自己覺得豫備還沒有充分,不敢章明較著的鼓吹耳。”[63]
實際上,此時顧頡剛的興趣不止于圣賢文化與民眾文化的對立關(guān)系,而且涉及知識階級與勞動階級的身份問題。在所撰《悼王靜安先生》一文中,顧氏仍然主張學者“做文章只是做文章,研究學問只是研究學問,同政治毫沒有關(guān)系,同道德也毫沒有關(guān)系”,然而與此同時,他認為“做文章和研究學問的人,他們的地位跟土木工、雕刻工、農(nóng)夫、織女的地位是一樣的。他們都是憑了自己的能力,收得了材料,造成許多新事物。他們都是作工,都沒有什么神秘”。顧氏由此指出,士大夫自以為讀書比平民高尚的觀念“是害死靜安先生的主要之點”:
他覺得自己讀書多,聞見廣,自視甚高,就不愿和民眾們接近了。……他少年到日本早已剪發(fā),后來反而留起辮子,到現(xiàn)在寧可以身殉辮,這就是他不肯自居于民眾,故意立異,裝腔作勢,以鳴其高傲,以維持其士大夫階級的尊嚴的確據(jù)。
在這篇悼文的末尾,顧頡剛喊出了諸如“我們應(yīng)該打倒士大夫階級!我們不是士大夫!我們是民眾!”[64]等口號。這些頗具宣傳、鼓動色彩的口號,折射出顧氏在革命時代對知識分子身份的某種自我反省。“九·一八”事變后,顧氏不僅號召青年“走到鄉(xiāng)間去,做根本救國大計”[65],而且親自投入民眾教育事業(yè),恐怕與此不無關(guān)系。
或許是受時局觸動,1931年12月8日,顧頡剛在日記中寫道:
昨北平《晨報》社論云:今中國所需要者,不僅為一民族英雄,而在能洞燭世界大勢,提挈整個民族,樹立其信,而己不必居于領(lǐng)袖,以數(shù)十年之奮斗,成為普遍之潛勢,內(nèi)掃封建殘骸,外抗帝國主義,如是人物,方為上上。
顧頡剛在此段社論之后所加斷語云:“此言予甚謂然,予將努力為之。”[66]因而,作為一度強調(diào)“整理國故”為啟蒙民眾之“根本”的學者,彼時顧氏仍然堅持“我以為如不能改變舊思想,即不能改變舊生活,亦即無以建設(shè)新國家”[67]的信念。雖然他也曾“晨夢加入義勇軍殺敵人及漢奸,甚酣暢”,然而“醒而思之,我研究歷史,喚起民族精神之責任,實重于殺敵致果,其工作亦艱于赴湯蹈火。我尚以伏處為宜。斐希脫所謂‘我書不亡,德國民族亦必不亡’者,我當勉力赴之。”[68]說到底,其內(nèi)心所鐘情者,依然是作為“整理國故”的學者,而其所倚重者,依然是思想革命和學術(shù)革命。
《顧頡剛?cè)沼洝窌?/p>
與顧頡剛強調(diào)“整理國故”“改變舊思想”的“學者”身份可堪對照的是,魯迅對于自己的學術(shù)研究和學者身份,有著更為迫切的現(xiàn)實訴求。1924年5月30日,在北大上完《中國小說史》課后,魯迅邀請旁聽的學生許欽文到中央公園喝茶。當許欽文問及魯迅講《中國小說史》并不限于中國的小說史,而且重點好像還是在反封建思想和介紹寫作的方法上時,魯迅回答道:“是的呀!如果只為著《中國小說史》而講中國小說史,即使講得爛熟,大家都能夠背誦,可有什么用處呢!現(xiàn)在需要的是行,不是言。”按照許欽文的回憶,魯迅彼時所說的“行”,主要在于培養(yǎng)一大批能夠?qū)懽鞯那嗄曜骷遥源舜輾Э酌现溃蚺f社會多方面地進攻[69]。此一材料雖然出自許欽文半個世紀后的回憶,卻十分合乎魯迅彼時倡導實際“革命”和“行動”的思想旨趣。1925年初,在《京報副刊》發(fā)起的“青年必讀書目”征集活動中,與梁啟超、胡適、顧頡剛所開大量傳統(tǒng)中國的書目不同[70],魯迅不僅在“青年必讀書目”上交了白卷,而且還主張少看或不看中國書。在他看來,“少看中國書,其結(jié)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xiàn)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71]
不惟如此,在1927年4月為黃埔軍官學校學員所做演講中,魯迅否認了外界封給自己的“文學家”頭銜,同時以之前在北京的斗爭經(jīng)驗,告以聽講者血的教訓:“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并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并且認為:“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蕩,大家由呼喊而轉(zhuǎn)入行動,大家忙著革命,沒有閑空談文學了。”基于對“革命”“行動”的提倡,魯迅進一步指出:“諸君是實際的戰(zhàn)爭者,是革命的戰(zhàn)士,我以為現(xiàn)在還是不要佩服文學的好。……中國現(xiàn)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zhàn)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72]。由此,魯迅希望青年不要被先前鼓吹國學救國的學者所騙,成為躲進書齋的“糊涂的呆子”,而要成為“對于實社會實生活略有言動”,即敢于行動乃至投身革命戰(zhàn)爭的“勇敢的呆子”[73]。因為在革命年代,“知道革命與否,還在其人,不在文章的”[74]。換句話說,在魯迅看來,此時社會所需要的是關(guān)于實際革命的言動,而非空談革命的文學;要的是“戰(zhàn)士”和“勇敢的呆子”,而非“文人”與“學者”。
對于中國的文人學者,魯迅揭露其注重功利與便利的一面:“清初學者,是縱論唐宋,搜討前明遺聞的,文字獄后,乃專事研究錯字,爭論生日,變了‘鄰貓生子’的學者,革命以后,本可以開展一些了,而還是守著奴才家法,不過這于飯碗,是極有益處的”[75];“我看中國有許多智識分子,嘴里用各種學說和道理,來粉飾自己的行為,其實卻只顧自己一個的便利和舒服……”[76]魯迅甚至認為,在世界范圍內(nèi),唯獨中國“真的沒有實在的偉人,實在的學者和教授,實在的文學家”[77],并進一步指出,中國的讀書人“自己一面點電燈,坐火車,吃西餐,一面卻罵科學,講國粹”,不僅言行不一,而且“往往只講空話,以自示其不凡”[78]。或許出于對文人學者的本質(zhì)認識,魯迅在談及從事寫作的起因時,強調(diào)自己“本來也還無須賣文糊口的,拿筆的開始,是在應(yīng)朋友的要求”;“我也不想充‘文學家’,所以也從不連絡(luò)一班同伙的批評家叫好”[79]。在別一場合,他再次聲明自己留心文學,并不想以“文學家”身份“出世”,也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80]。因此,對于自己的作品,魯迅并不擔心“書賈怎么偷,文士怎么說”[81],對于作家身份、個人名望更無心經(jīng)營,以至于1934年,陶亢德、林語堂多次邀約他在《人間世》半月刊刊登所謂“作家”并“夫人及公子”照片,均被他婉言謝絕[82]。
對于文人學者所能發(fā)揮的戰(zhàn)斗功能,魯迅其實早有警覺。1925年5月,在給許廣平的信件中,魯迅寫道:“我現(xiàn)在愈加相信說話和弄筆的都是不中用的人,無論你說話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動人,都是空的。他們即使怎樣無理,事實上卻著著得勝。然而人,世界豈真不過如此而已么?我還要反抗,試他一試。”這種試著反抗的念頭,使得魯迅在選擇成為中國文學研究方面的學者,還是成為社會批評、文明批評的戰(zhàn)士時,一度傾向于后者:“但我想,或者還不如做些有益于目前的文章,至于研究,則于余暇時做……”[83]魯迅如是說,更由此認為,“現(xiàn)在需要的是斗爭的文學,如果作者是一個斗爭者,那么無論他寫什么,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斗爭的。就是寫咖啡館跳舞場罷,少爺們和革命者的作品,也決不會一樣”[84];而“讀經(jīng),作文言,磕頭,打屁股,正是現(xiàn)在必定興盛的事,當和其主人一同倒閉。但我們弄筆的人,也只得以筆伐之”[85]。
然而,作為弄筆的“戰(zhàn)士”,魯迅不僅“常常有‘獨戰(zhàn)’的悲哀”[86],也意識到“戰(zhàn)友”的易變與脆弱:“據(jù)我所見,則昔之稱為戰(zhàn)士者,今已蓄意險仄,或則氣息奄奄,甚至舉止言語,皆非常庸鄙可笑,與為伍則難堪,與戰(zhàn)斗則不得,歸根結(jié)蒂,令人如陷泥坑中。”[87]對于此中原因,魯迅指出:“我覺得文人的性質(zhì),是頗不好的,因為他智識思想,都較為復雜,而且處在可以東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堅定的人是不多的。”由此他表達了對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敬意:“這樣的才可以稱為戰(zhàn)士,真叫我似的弄筆的人慚愧。”[88]如此表述,在折射魯迅對“革命”“行動”諸多向往的同時,也再次凸顯了他對“空談革命”的文人學者的疏離與拒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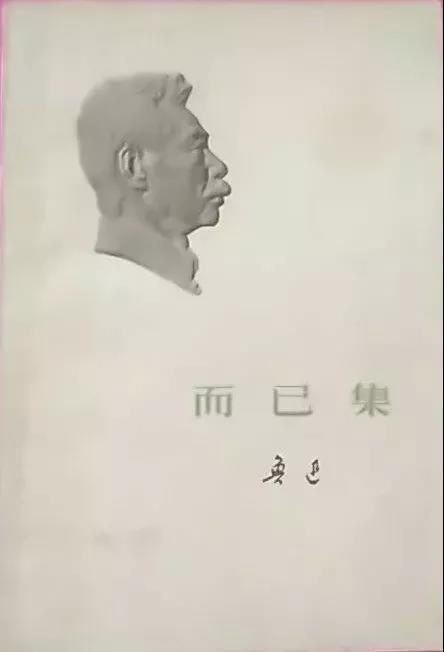
魯迅《而已集》書影
四 后五四文化場域的“勢位”之爭
自1920年9月起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編目員,以及稍后兼任胡適的助手,顧頡剛短短五、六年間就在學術(shù)界廣為人知,以至于1926年9月,傅斯年就稱贊顧頡剛在這個古史研究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頓之在力學,達爾文之在生物學”[89]。顧氏的聲名鵲起,除了古史研究方面的學術(shù)貢獻外,也與其所取“為學問而學問”的主張有關(guān)。在“戊戌”和“五四”學人[90]那里,當面臨重大歷史社會問題時,“為學問而學問”的聲音在多數(shù)場合中仍然被具體的政治革命或思想革命的命題所壓抑。因而,在“五四”前后,當顧氏強調(diào)以科學常識和新學術(shù)打破舊有道德、思想體系,以此實現(xiàn)“思想革命”“人的覺醒”等等現(xiàn)實社會命題時,也明顯未能離開這一思路。然而,在新文化運動落潮的背景下,學界又經(jīng)歷“問題與主義”之爭、“科學與人生觀”論戰(zhàn)、“非基督教大同盟”辯論等諸多浪潮后,顧氏獨獨樹立起“為學問而學問”的旗幟,并進而在知識界提倡“學術(shù)界的生活獨立問題”,顯示了與注重改良、啟蒙的前輩們的不同追求。
對于為自己博得學界稱贊的主張,顧頡剛晚年指出其來源:“我記得羅家倫在《新潮》二卷一期上發(fā)表的一篇題為《古今中外派的學說》一文,對我曾產(chǎn)生過一定的消極影響。我當時很贊成他那種只鉆研學問,不問外事的說法。”[91]由于時隔多年,且經(jīng)過特定時期的政治審查,顧氏的說法未必十分切實。然而不論如何,這種“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的姿態(tài)與對于前輩“尋求差別”[92]的策略所帶來的象征性資本,顧氏顯然心知肚明。他曾對友人說:“近來有的地方,固然是要造成自己的名譽(例如《古史辨》的自序),但所以要造成名譽是由學術(shù)上的目的的,并不是普通之所謂‘名利’。”[93]顧氏所強調(diào)的是,自己更著意于身后之“名”,亦即“圓百年以后的勝利”[94]。雖說如此,彼時顧氏對于自身社會地位、名望的提升及反響,卻是十分在意。1926年7月13日,顧氏在日記中寫道:“恒慕義先生欲以英文為余譯《古史辨》序,日來又為余譯《秦漢統(tǒng)一》一文,西洋人方面亦漸知予矣。”[95]1926年夏,廈門大學原聘顧頡剛為研究所導師與大學教授,在國文系中本須授課,然而因《古史辨》的出版,顧氏到校后,在本年8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乃改為‘研究教授’,不必上課,甚快。”[96]對于個人名望、地位的飆升及其帶來的實際好處,顧氏可謂看在眼里,喜在心頭。
此外,對于現(xiàn)實中的人際沖突乃至派系之爭,顧頡剛甚是了然于心。1927年4月底,在力勸胡適加入國民政府的信中,顧氏特意提醒胡適:“這幾年中,周氏兄弟假公濟私,加以伏園、川島們的挑撥,先生負謗亦已甚意,在這國民革命的時候,萬不可再使他們有造謠的機會,害了先生的一生。這是我和淚相勸的一件事,請先生聽我罷。”[97]1927年6月,在給好友羅家倫的信中,顧氏則對北京以馬幼漁為代表的“章太炎學派”大加撻伐:
自從他們各占主任地位之后,一意固植自己勢力,學業(yè)荒蕪已甚,教課亦松惰異常。……他們雖非共產(chǎn)黨,而頗受共產(chǎn)黨的同化,凡異己者盡力抵排,必使體無完膚而后已。以自己一班人不會做文章,故竭力捧周氏兄弟,而周氏兄弟以厚負時譽,遂自視為“口含天憲”,有“朕即真理”之氣概。[98]
這樣的譴責,正是發(fā)生在顧、魯沖突的過程中。而在兩年多后,當徐旭升擬聘顧頡剛擔任女師大史地系主任時,顧氏則忌憚“女師大為魯迅大本營,我為某籍某系之罪人,充教席且不可,何況作主任耶!”[99]因此拒絕上任。不惟如此,在給學生何定生的信中,顧氏也挑明了彼時北平學界的“勢位”之爭:
我固然是不好勢位的,想專心治學的,但在他們看來,已是一個具有替他們爭奪勢位的資格的人物了。你只要看適之先生所以不敢到北平來,就可知道。我的聲望不及適之先生,所以他們還容我在燕京。假使我不自韜晦,歡喜出主張,常常到城里來,或在城里兼幾件事,那么,我離下獄之日不遠矣。
在同一封信中,顧氏苦口婆心地提醒何定生:接近錢玄同等一批老人物,才有希望“踏進北平的學界”[100]。就此來看,顧氏對于現(xiàn)實復雜厲害關(guān)系和人際網(wǎng)絡(luò)的把握,即使未必如魯迅后來所說的“遍身謀略 ”[101],卻也稱得上深諳此道。
不管是有心抑或無意,顧頡剛在學術(shù)態(tài)度和學術(shù)思路上,確然找到了與前輩學人相區(qū)別的道路或者是具有差異性的面向,由此闖入了原本由“戊戌”和“五四”兩代前輩學人所把持的文化場域,伴隨著聲譽日隆,在古史領(lǐng)域乃至在整個后五四文化場域中,他也逐漸擁有了與老師輩抗衡的象征性資本。而隨著個人學術(shù)地位的攀升,顧氏以“學者”身份與前輩“權(quán)威”在文化場域展開新的“占位”競爭也就可以想見了——與他在思想立場、文化取向、身份認同方面都相去甚遠的魯迅,乃至與他同為“整理國故”一派的胡適,最終都成了他的主要競爭對手乃至前進路上的障礙[102]。從客觀上看,與魯迅的沖突,不僅無損于顧頡剛已經(jīng)取得的學術(shù)地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他對“學者”身份的自我確認。此一方面,顧氏將之歸因于自己擁有同時代的人所缺乏的“情感與意志”:
晨起漱口,忽思予之為人,有目的,有計劃,有恒心,有定力,故得不避艱難,不畏險阻,不慕虛榮,不見異思遷,雖有種種之缺陷,仍無礙其成功。只要不受大力者之摧殘,身體亦支持得下,積以年月,當然有成。回思才干學問比我好的人何限,顧以缺乏如此之情感與意志,故終不能勝我而惟有妒我耳。若今日之青年,則急于小成,只肯做表面的工作,惟以虛聲作哃喝,徒成為隨時淘汰之分子耳。(1932,10,08)
然而,實際是否如此,顧頡剛心里也明白:“予之所以終不灰心者,則以對于愛與學有終必成功之信念。此信念毫無事實的根據(jù),只仿佛有上帝的默示而已”[103]。這樣的反省,表明顧氏對于自我的學術(shù)事業(yè)與“學者”身份具有某種理性的天然疑慮。而此一疑慮也表明,顧氏用“學者”身份來區(qū)隔、對抗魯迅的“文人”身份,其看似理性的文化立場、思想選擇與身份認同,實則包含著強烈的主觀情感因素。
在魯迅方面,其與顧頡剛之間的沖突,只是他與陳西瀅等“現(xiàn)代評論派”之間斗爭的延續(xù),他在這一斗爭中,所增加的是自己遭受對方聯(lián)手排擠的體驗。正因為與陳西瀅、顧頡剛等人的論爭和沖突,使得魯迅后來處處表示出與“現(xiàn)代評論派”對立的姿態(tài)。在廈大時,當孫伏園未聽從魯迅的話,讓受雇于魯迅的工友也去包“陳源之徒”的飯時,魯迅極其憤怒[104]。而當在廣州意外碰到陳西瀅、張奚若時,魯迅的反應(yīng)是“叭兒狗也終于‘擇主而事’了”[105],幸災樂禍的心情溢于言表。不惟如此,當李小峰要魯迅與鐘敬文在中山大學合開北新書局的分店時,魯迅在給章廷謙的信中表示:“這里的‘北新書屋’我擬于八月中關(guān)門,因為鐘敬文(鼻子傀儡)要來和我合辦,我則關(guān)門了,不合辦。”魯迅于此想到的是讓對方“不高興”,甚至在講述自己答應(yīng)市教育局夏期學術(shù)演講的動機,言語之中也充滿負氣的意味:“幾點鐘之講話而出風頭,使鼻輩又睡不著幾夜,這是我的大獲利生意”;“革命時代,變動不居,這里的報紙又開始在將我排入‘名人’之列了,這名目是鼻所求之不得的,所以我倒也還要做幾天玩玩”[106]。魯迅對此也曾有所反省:“有人不高興,我即高興,我近來良心之壞已至如此。”[107]但實際上,由于確信這種態(tài)度源于自己被對方聯(lián)手排擠的體驗,因而,“我已經(jīng)管不得許多,只好從退讓到無可退避之地,進而和他們沖突,蔑視他們,并且蔑視他們的蔑視了”[108]。由此,除了在與友朋的信件中大力譴責外,他在所作小說《眉間尺》和雜文《擬預言——一九二九年出現(xiàn)的瑣事》中明顯表達了對顧頡剛的不滿,甚至直到1935年,也仍然在小說《理水》中加以刻意嘲諷[109]。在此種對立的姿態(tài)中,魯迅表達的顯然不僅是一種個人化的情緒,更是一種來自實際經(jīng)驗的自我立場:那就是,以一種光明磊落而又愛憎分明的諷刺回擊“學者”以“公平”“公理”等名目所掩蓋的“黨同伐異”。
魯迅后來對顧頡剛的印象一直沒有改善。1929年3月,在給章廷謙的信中,他諷刺顧頡剛:“此公急于成名,又急于得勢,所以往往難免于‘道大莫能容’。”[110]同年五月回北平省親時,魯迅又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寫道:“他此來是為覓飯碗而來的,志在燕大,但未必請他,因燕大頗想請我;聞又在鉆營清華,倘羅家倫不走,或有希望也。”[111]雖然如此,魯迅還是有把握地認為,在就聘燕大一事上,自己的優(yōu)勢大于顧氏。而在兩年前,也就是1927年6月,當?shù)弥约号c顧頡剛一同被聘入研究院時,魯迅寫道:
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學乎,胡適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惡”而已。可惡之研究,必為孑公(蔡元培——引者)所大不樂聞?wù)咭玻鋵崳液痛斯瑲馕恫煌墩咭玻裨院螅p識者,袁希濤蔣維喬輩,則十六年之頃,其所賞識者,也就可以類推了。[112]
魯迅于此對蔡元培的怨言,不乏意氣之辭。但此中不自覺的對比也表明,在國民革命時期直至三十年代的后五四文化場域中,魯迅客觀上確實面臨著來自顧頡剛占位競爭的壓力。盡管這種壓力在魯迅看來尚不足一提,但他顯然并不漠視。而這也說明,在顧、魯沖突以至交惡的過程中,魯迅所展現(xiàn)的刻意對立與諸多嘲諷,除了追求打擊對手的客觀效果之外,未嘗沒有來自占位競爭所導致的非理性因素。
綜上所論,重審顧頡剛、魯迅沖突的緣起,除了關(guān)注實際生活中的人際罅隙、勢位之爭以及黨派政治等外在因素,顧、魯二人文化立場、思想旨趣、身份認同乃至個人性情的差異,也是不可忽視的內(nèi)在因素——正是這些遍布日記、書信以及講演、文章中迥然有別的個人言說,構(gòu)成了顧、魯沖突過程中潛在的思想交鋒。換句話說,在國民革命時期,顧、魯對學術(shù)研究(“整理國故”)、文學批評(“欣賞藝術(shù)”)之功用的不同認識,尤其對學者文人在投身現(xiàn)實革命抑或?qū)W⑽幕ㄔO(shè)方面的觀念分歧,以及對自我的身份定位的差異等方面,雖然并未形成直接的論爭,卻是有跡可循、可堪對照并加以解讀的思想對話。而反過來,作為思想對話之外化的顧、魯沖突事件,也足以成為代表后五四時代知識分子陣營的分化,以及新文化場域激烈的占位競爭的一個縮影。當然,顧、魯所代表的不同陣營、代際之間思想、立場、信仰、個性等等差異的豐富內(nèi)涵,顯然不是一篇文字所能窮盡的。在此,筆者謹以顧、魯二人在評價“戊戌”學人章太炎時的不同標準和取向來作為本文的收束。
在顧頡剛的心目中,章太炎作為“古文家”和“整理國故的呼聲始倡”者,是晚清以降與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等并列的學術(shù)重鎮(zhèn),也是顧氏古史辨?zhèn)窝芯恐兴獱巹俚膶ο笾籟113]。1925年11月3日,顧氏在日記中寫道:“吳山立君告我,謂吳稚暉先生說,近為國學者惟胡適之、顧頡剛,其次則梁任公。若章太炎則甚不行者。”[114]在此國民革命風起云涌的年代,亦即古史辨派迅速崛起的時期,顧氏借他人之口來凸顯自己的學術(shù)地位,其參照標準正是作為“學者”的章太炎。而在魯迅方面,其1936年10月所寫的《關(guān)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卻肯定“太炎先生的業(yè)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shù)史上還要大”,強調(diào)自己當時前去聽他講學,“并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xiàn)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115]。
至此,魯迅對乃師章太炎“革命家”身份和革命業(yè)績(“行”)的推崇,與其十多年前國民革命時期對“革命”和“行動”的倡導其實一致,也與當年顧頡剛對“學者”身份、“整理國故”的執(zhí)著,再次構(gòu)成了潛在的對話。然而,此中耐人尋味的是,在魯迅寫下這篇悼念文章的那一年,顧頡剛已然走出書齋,發(fā)起民眾運動,加入了國民黨,正努力實踐著他的“事業(yè)心”[116]。
注釋:
[1]這方面的論述,見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00—117頁、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6-220頁、邱煥星《魯迅與顧頡剛關(guān)系重探》(《文學評論》2012年第3期)、施曉燕《顧頡剛與魯迅交惡始末》(《上海魯迅研究》2012年夏、秋二期)等。
[2]錢穆:《〈崔東壁遺書〉序》,上海:亞東圖書館,1935年。
[3]顧頡剛:《致殷履安》,1920年4月21日,《顧頡剛書信集》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17頁。以下《顧頡剛書信集》皆同此版本。
[4]顧頡剛等:《通信》,《教育雜志》第14卷第5號、第6號,1922年5月、6月。
[5]李石岑:《自序——我的生活態(tài)度之自白》,《李石岑演講集》第1輯,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24年。
[6]顧頡剛:《顧頡剛序》,收《李石岑演講集》第1輯,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24年。
[7]顧頡剛:《一九二六年始刊詞》,《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
[8]顧頡剛:《入主出奴之學風》,《顧頡剛讀書筆記》卷一,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90年,第470頁。
[9]顧頡剛:《我們對于國故應(yīng)取的態(tài)度》,《小說月報》第14卷第1號,1923年1月。
[10]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文學周報》5卷1、2合期,1927年8月。
[11]王國維在文學批評、創(chuàng)作方面的代表作《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靜安詩稿》等,皆完成于三十五歲(1912年)之前。
[12]顧頡剛:《與孟真書》,1919年8月11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二,第184頁。
[13]顧頡剛:《致羅家倫》,1920年5月5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237頁。
[14]顧頡剛:《致傅斯年》,1919年2月21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180—181頁。
[15]顧頡剛:《致葉圣陶》,1919年4月20—21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57頁。
[16]顧頡剛:《致葉圣陶》,1919年3月4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52頁。
[17]顧頡剛:《致蔡元培》,1922年1月23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144頁。
[18]顧頡剛:《致蔡元培》,1922年2月3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145頁。
[19]顧頡剛:《致葉圣陶》,1923年6月7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76頁。
[20]顧頡剛:《致殷履安》,1924年6月14日,《顧頡剛書信集》卷四,第447—448頁。
[21]顧頡剛:《致劉經(jīng)庵》,1922年6月19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二,第113—114頁。
[22]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硪唬本褐腥A書局,2011年,第710頁。以下《顧頡剛?cè)沼洝方酝税姹尽?/span>
[23]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硪唬?26頁,
[24]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矶?4頁。
[25]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矶?5頁。
[26]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矶?2頁。
[27]顧頡剛:《致葉圣陶》,1927年7月4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88頁。
[28]魯迅:《讀書雜談——魯迅在廣州知用中學演講 》,黃易安筆記,《北新》周刊第47、48期合刊,1927年9月16日。
[29]參見魯迅《這個與那個》(《國民新報副刊》,1925年12月10日、12日、22日)、《碎話》(《猛進》周刊第 44期,1926年1月8日)、《并非閑話(三)》(《語絲》周刊第56期,1925年12月7日)等文。
[30]魯迅:《通訊》,《猛進》周刊第3期、第5期,1925年3月20日、4月3日。
[31]魯迅:《<華蓋集>題記》,《莽原》半月刊第2期,1926年1月25日。
[32]魯迅:《不是信》,《語絲》周刊第65期,1926年2月8日。
[33]以上參見魯迅《無花的薔薇》,《語絲》周刊第69期,1926年3月8日。
[34]西瀅:《閑話(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現(xiàn)代評論》第3卷第71期,1926年4月。
[35]魯迅:《我的態(tài)度氣量和年紀》,《語絲》周刊第4卷第19期,1928年5月7日。
[36]關(guān)于顧頡剛與“現(xiàn)代評論派”及“研究系”之關(guān)系,參見邱煥星《魯迅與顧頡剛關(guān)系重探》,《文學評論》2012年第3期。
[37]以上參見《魯迅全集》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532頁、第538頁、第539頁、第577頁、第620頁、第624頁、第632頁、第637頁;第十六卷,第3頁。以下《魯迅全集》皆同此版本。
[38]以上參見魯迅《致許廣平》三通,1926年9月20日、25日、30日,《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50頁、第553頁、第559頁。
[39]參見魯迅《致許廣平》二通,1926年10月16日、23日,《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75-576頁、第585 頁。
[40]參見孫郁《魯迅與胡適——影響20世紀中國文化的兩位智者》,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4頁。
[41]魯迅:《致章廷謙》,1926年10月23日,《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83頁。
[42]魯迅:《致許廣平》,1926年11月4日,《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01頁。
[43]魯迅:《致李霽野》,1927年4月20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9-30頁。
[44]魯迅離開廈大的原因,除了“言語不通”“飯菜不好”“無法用功”外,“國學院無非裝面子,不要實際”的態(tài)度也是其中的一個主要方面。以上參見魯迅《致許廣平》三通(1926年11月8日、26日,1926年12月2日)、《致章廷謙》(1926年11月30日),《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33頁、第637頁、第640頁,第618頁。
[45]魯迅:《致孫伏園》,1927年4月26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1頁。
[46]魯迅:《致章廷謙》,1927年5月30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4-35頁。
[47]魯迅:《致章廷謙》,1927年6月23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9-40頁。
[48]伏園:《魯迅先生脫離廣東中大》,《中央副刊》第48號,1927年5月11日。
[49]魯迅:《辭顧頡剛教授令“候?qū)彙薄罚遏斞溉返谒木恚?0-41頁。
[50]魯迅:《致章廷謙》,1927年8月8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61頁。
[51]參見魯迅《致江紹原》(1927年8月2日)、《致章廷謙》(1927年8月17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59頁、第64頁。
[52]以上參見魯迅《致許廣平》三通,1926年11月4日、8日、1日,《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01頁、第606頁、第599頁。
[53]魯迅:《致章廷謙》二通,1927年7月28日、12月26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55頁、第99頁。第一通引文中的“鼻”字,在原文中為一個手繪的鼻子圖案。
[54]魯迅:《致姚克》二通,1934年2月11日、3月6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23頁、第39頁。
[55]顧頡剛:《致王伯祥》,1919年8月19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111頁。
[56]顧頡剛:《致殷履安》,1919年9月10日,《顧頡剛書信集》卷四,第72頁。
[57]顧頡剛:《致殷履安》,1920年4月22日,《顧頡剛書信集》卷四,第230頁。
[58]顧頡剛:《致殷履安》,1920年4月23日,《顧頡剛書信集》卷四,第219頁。
[59]顧誠吾:《我們最要緊著手的兩種運動——教育運動 學術(shù)運動》,《晨報·五四紀念增刊》,1920年5月4日。
[60]顧頡剛:《致葉圣陶》,1926年11月6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85—86頁。
[61]顧頡剛:《致胡適》,1927年2月2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440頁。
[62]顧頡剛:《致王伯祥、葉圣陶》,1927年7月4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89頁。
[63]顧頡剛:《致葉圣陶》,1927年7月6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91頁。
[64]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文學周報》第5卷第1、第2合期,1927年8月。
[65]顧頡剛:《充實雜志發(fā)刊詞》,《充實雜志》第1期,1932年12月。
[66]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矶?88頁。
[67]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矶?93-594頁。
[68]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矶?98頁。
[69]參見許欽文《魯迅日記中的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6頁。
[70]顧頡剛所開書目為:《山海經(jīng)》《梁武石室畫像》《世說新語》《洛陽伽藍記》《大唐西域記》《宋元戲曲史》《唐人說蕓》《元秘史》《馬可波羅游記》《陶庵夢憶》《徐霞客游記》《桃花扇》《西秦旅行記》《南洋旅游記》。見顧頡剛:《有志研究中國史的青年可備閑覽書十四種》,《京報副刊》第75號,1925年3月1日。
[71]魯迅:《青年必讀書——應(yīng)<京報副刊>的征求》,《京報副刊》第67號,1925年2月21日。
[72]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四月八日在黃埔軍官學校講》,原載《黃埔生活》周刊第4期,1927年6月12日,后經(jīng)作者修改收入《而已集》。此據(jù)《魯迅全集》第三卷,第436頁,第438頁,第441—442頁。
[73]魯迅:《<書齋生活與其危險>譯者附記》,《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7年6月25日。
[74]魯迅:《通信(并Y來信)》,《語絲》周刊第4卷第17期,1928年4月23日。
[75]魯迅:《致姚克》,1934年4月9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68—69頁。
[76]魯迅:《致蕭軍、蕭紅》,1935年4月23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445頁。
[77]曼雪:《一思而行》,《申報·自由談》,1934年5月17日。
[78]魯迅:《致阮善先》,1936年2月15日,《魯迅全集》第十四卷,第27頁。
[79]魯迅:《通信(并Y來信)》,《語絲》周刊第4卷第17期,1928年4月23日。
[80]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收《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驗》,上海:天馬書店,1933年。
[81]魯迅:《并非閑話(三)》,《語絲》周刊第56期,1925年12月7日。
[82]參見魯迅《致陶亢德》二通(1934年3月29日、1934年5月25日)、《致林語堂》(1934年4月15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56頁、第123頁、第78頁。
[83]以上參見魯迅《致許廣平》二通,1925年5月18日,1926年11月1日,《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91頁、第599頁。
[84]魯迅:《致蕭軍》,1934年10月9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224頁。
[85]魯迅:《致曹聚仁》,1934年6月9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145頁。
[86]魯迅:《致蕭軍、蕭紅》,1934年12月6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280頁。
[87]魯迅:《致章廷謙》,1930年3月27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27頁。
[88]魯迅:《致蕭軍、蕭紅》,1934年12月10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287頁。
[89]傅斯年:《傅斯年遺扎》第一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第62—63頁。
[90]關(guān)于“戊戌”與“五四”兩代學人的具體劃分,參見陳平原《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8頁。
[91]顧頡剛:《回憶新潮社》,見《五四時期的社團(二)》,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第125頁。
[92]參見戴維·斯沃茨《文化與權(quán)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陶東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第256—263頁。
[93]顧頡剛:《致葉圣陶、王伯祥》,1927年7月4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88頁。
[94]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矶?49頁。
[95]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硪唬?68頁。
[96]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硪唬?84頁。
[97]顧頡剛:《致胡適》,1927年4月28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442頁。
[98]顧頡剛:《致羅家倫(志希)》,1927年6月9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250頁。值得注意的是,顧頡剛說魯迅們“受共產(chǎn)黨的同化”,在當時國民黨清黨之后的氛圍中,如若被公開,就其危害之嚴重性而言,與魯迅致孫伏園信上說顧頡剛“反對民黨”相較,恐怕并不亞于后者。
[99]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矶?92頁。
[100]以上參見顧頡剛《致何定生》,1930年1月18日,《顧頡剛書信集》卷二,第327—328頁。
[101]魯迅:《致鄭振鐸》,1934年7月6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169頁。
[102]有關(guān)顧頡剛與胡適之間的“占位”競爭,參見林分份《古史辨派“科學”形象的自我塑造——以顧頡剛、胡適為中心》,《云夢學刊》2007年第1期
[103]以上參見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矶?96頁、第708頁。
[104]參見魯迅《致許廣平》二信,1926年10月23日、28日,《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86頁、第590頁。
[105]魯迅:《致章廷謙》,1927年7月7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46頁。
[106]魯迅:《致章廷謙》,1927年7月17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51-52頁。
[107]魯迅:《致江紹原》,1927年7月12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49頁。
[108]魯迅:《海上通信(致李小峰)》,《魯迅全集》第三卷,第420頁。
[109]《眉間尺》后來改題《鑄劍》收入小說集《故事新編》。實際上,要將顧頡剛寫入小說,魯迅1927年間就曾有過念頭,但當時覺得“他似乎還不配,因為非大經(jīng)藝術(shù)化,則小說中有此輩一人,即十分可厭也”。參見魯迅《致章廷謙》,1927年7月28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55頁。
[110]魯迅:《致章廷謙》,1929年3月15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151頁。
[111]魯迅:《致許廣平》,1929年5月26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175頁。
[112]魯迅:《致章廷謙》,1927年6月12日,《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7頁。
[113]參見顧頡剛《自序》,收《古史辨》第一冊,北京,景山書社,1926年。
[114]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洝肪硪唬?78頁。
[115]魯迅:《關(guān)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六卷,第565—566頁。
[116]有關(guān)三十年代顧頡剛發(fā)起民眾運動、加入國民黨與其“事業(yè)心”之關(guān)系,余英時先生有十分中肯的論述。參見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cè)沼洝悼搭欘R剛的內(nèi)心世界》(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4—23頁。
作者簡介:林分份,男,福建漳浦人,2008年7月于北京大學獲得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博士學位,現(xiàn)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等發(fā)表論文多篇,目前主要關(guān)注領(lǐng)域為五四思想文化史、周氏兄弟研究、現(xiàn)代小說詩學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