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童年:美國式的個人奮斗還能不能創(chuàng)造奇跡?
《新聞編輯室》第一季第一集中,威爾在美國大學(xué)演講,臺下有學(xué)生提問,為什么美國是世上最偉大的國家?威爾猶豫間看到觀眾席中舉起一塊答題板,上面寫著“美國不是”。
許多美國人認為在美國獲得成功的機會,在世上其他國家是找不到也不存在的。這一發(fā)展于19世紀(jì)的美國民族精神影響深遠而廣泛,它賦予了美國人獨特的優(yōu)越感,美國的環(huán)境沒有人為的阻礙,每個人在抉擇時不會因為出生階級、種族、信仰而受到限制,人們稱之為美國夢。
美國夢意味著人們在美國容易獲得經(jīng)濟自由,政府在社會中扮演很小的角色,社會階層不停流動。因此美國夢的實現(xiàn)依賴個人的努力,而非特定的社會階級和他人的援助。也就是說,美國夢激動人心的關(guān)鍵在于,人們的機會的平等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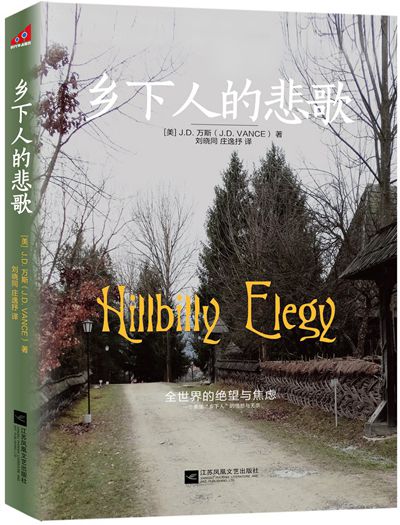
但現(xiàn)如今的美國是否是一片平等的樂土?《鄉(xiāng)下人的悲歌》這部藍領(lǐng)階級后代的自傳體小說,就是對一大批人喪失美國夢的審視。作者J.D.萬斯的祖父母為脫離貧窮,從肯塔基州遷至俄亥俄州。他的母親和其不停變更的男友不斷搬家,他的成長過程中父母缺席,母親還因為貧窮、酗酒、濫用藥物、精神創(chuàng)傷等問題,使他的童年在混亂的環(huán)境下度過。他回憶,整個童年所接觸的人中間,有機會念大學(xué)的人寥寥無幾,許多人甚至不能從高中畢業(yè)。而人們都借口家庭、環(huán)境、貧困默認了這樣的生活狀態(tài),鮮有人將失敗的原因歸結(jié)于自身。那么是否可以理解為,這個群體首先接受了自己沒有所謂通向上層階級的平等機會,“美式勤奮”在他的故鄉(xiāng),不是一種理想,而是一個奇跡。
盡管他最終實現(xiàn)了向上流動,但這對他而言也是一種奢侈和難得的幸運。為他創(chuàng)造這種幸運的,正是他的祖父母,還有與他同母異父但感情深厚的姐姐。祖母為他提供了穩(wěn)定的生活和學(xué)習(xí)環(huán)境,并使他相信,只要愿意的事,一定可以做到,尤其別為自身的慘淡找借口。他們的陪伴是他困境的出口。萬斯堅持念完了高中,參加了海軍陸戰(zhàn)隊,完成了耶魯大學(xué)法律系的學(xué)業(yè)。彼時的他才第一次認識到上層的世界,也意識到藍領(lǐng)階級和中產(chǎn)階級的差距不僅在財富,也是生活和行為方式、親子及人際關(guān)系各方面的背道而馳。他通過掙扎獲得的地位,對別人而言,只是水到渠成的結(jié)果。從而為自己生長的世界深深悲哀。
美國貧富兩極的分化真正造成的,是對下一代生活機遇的影響。《鄉(xiāng)下人的悲歌》代表了美國正在經(jīng)歷的現(xiàn)象,人們不再抱持樂觀的態(tài)度。有一批學(xué)者先后跟蹤調(diào)研了上百個不同階級的家庭和生活在美國各地的年輕人,與黃金時代相比,美國社會結(jié)構(gòu)已然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顯著的現(xiàn)象是階層固化,盡管藍領(lǐng)階級也在極力適應(yīng)中產(chǎn)階級生活的要求,依舊難以解除因為階級鴻溝日益擴大而面臨的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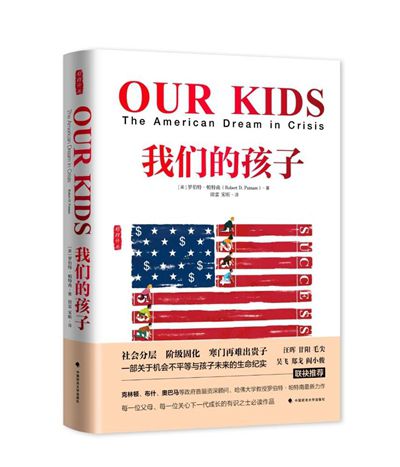
哈佛大學(xué)教授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中描繪,“20世紀(jì)50年代的克林頓港早已不知何處去,隨之一同消失的是普遍的經(jīng)濟繁榮、社區(qū)中無所不在的凝聚力、惠澤所有家庭的平等機會。”如果曾有美國夢存在,機會平等性的消失正是美國夢衰落的警鐘。“富家子可以輕而易舉地理解通向機會之路的種種制度。而且游刃有余地運用這些制度,為他們服務(wù)。相比之下窮孩子,往往就不得其門而入了。因此錯過了向上走的機會。上層階級的孩子見多識廣,更懂得如何把握人往高處走的時機。然而下層階級的孩子,卻總是滿懷疑慮,猶豫不決,機會從手邊溜走也不自知。”
《我們的孩子》花費數(shù)年,追蹤訪問了生活在美國各地的107位18-22歲的年輕人,包括工業(yè)衰退地帶的小鎮(zhèn)、中產(chǎn)階級云集的旅游勝地、發(fā)展不平衡的都會區(qū)和超級富豪的住宅區(qū)。感知他們對各自童年的理解,和對未來的規(guī)劃。書中以“剪刀差”為意象,討論了窮人孩子與富人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所經(jīng)歷的全方位不同。除了最直接地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上,窮人父母陪伴孩子的時間、給予孩子的引導(dǎo)、提供孩子的資源也都因此出現(xiàn)了短板。或者更糟,和J.D.萬斯一樣,孩子可能出生在破碎的家庭,童年無法獲得父母的關(guān)愛,還要飽嘗生活的苦難,他們寧可相信,努力都是徒勞。這些差異也正是逐漸導(dǎo)致美國階級流動停滯的原因,也難怪人們要發(fā)出“在這個生而不平等的年代,僅僅談機會均等都是不公正的”的感慨。
事實上,貧困未必是絕對的劣勢。富孩子與窮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征和品格。他們理應(yīng)得到各自發(fā)揮的機會。
不同階級的人們操持不同的行為語法,人們對此形成了共識。富人家重視協(xié)作培養(yǎng),父母平等對待孩子,鼓勵他們說出自己的感受和觀點,孩子也敢于挑戰(zhàn)權(quán)威。家庭的節(jié)奏以孩子的活動為中心,孩子以成人社會的規(guī)律組織著自己的活動。但兄弟姐妹間容易形成競爭關(guān)系,親戚之間或鄰里之間維持著點頭之交;而窮人家的孩子多為自然養(yǎng)成,父母與孩子有明顯的界限,孩子通常接受或服從父母的命令,很少發(fā)起挑戰(zhàn)或反駁。但孩子們的活動多為自發(fā)組織和形成的,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和兄弟姐妹或鄰居孩子一起度過,互相扶持。

客觀而論,兩種培養(yǎng)模式各有所長,難以簡單地評判,但最終確實是中產(chǎn)階級孩子得以從社會中獲利。美國賓夕法尼亞社會系教授安妮特·拉魯定量考察了貧困家庭、工人階級家庭、中產(chǎn)階級家庭孩子的生活后,寫下了《不平等的童年》,直擊要害。“美國也許是一片充滿機會的土地,但它也是一片不平等的土地。父母的社會地位會以一種在很大程度上是無形的但又是強有力的方式?jīng)_擊著孩子的人生經(jīng)歷。”“‘兒童教養(yǎng)’的文化邏輯”是其中之一。“工人階級和中產(chǎn)階級的母親可能多會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反映出類似‘無微不至地照顧孩子’的理念,但她們的具體行為是截然不同的。當(dāng)他們走出家門進入社會機構(gòu)的世界里,他們發(fā)現(xiàn)這些文化慣性并未被賦予同等價值”。
從學(xué)校到公司,社會核心機構(gòu)到整個美國社會推崇的價值觀與中產(chǎn)階級的價值觀相當(dāng),反之亦然,中產(chǎn)階級影響或形成了社會思維的主流,養(yǎng)成了社會有利于他們自身的評判標(biāo)準(zhǔn)。和《我們的孩子》其中的結(jié)論相似,安妮特·拉魯認為中產(chǎn)階級的孩子具有熟悉社會規(guī)則的優(yōu)勢,因此對日后所處環(huán)境如魚得水,生成優(yōu)越感;而貧窮階級的孩子的優(yōu)勢無法獲得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認同,面對完全陌生的成人環(huán)境,生活在局促感中。
優(yōu)越感與局促感同樣體現(xiàn)在家長身上,導(dǎo)致不同階級家長對孩子生活的了解和干預(yù)程度的差距。中產(chǎn)階級的家庭習(xí)慣挑戰(zhàn)(以學(xué)校為主的)社會機構(gòu),書中提到中產(chǎn)階級母親在目睹舞蹈班老師糾正女兒的每一個動作后,并不是要求女兒,而是對老師的教學(xué)方式提出質(zhì)疑(事實上不少老師都表示自己受到過中產(chǎn)階級家長的質(zhì)疑和建議)。她了解兩個女兒的弱點是答題速度慢,對應(yīng)的方式也不是要求她們加快速度,而是事先告知老師她們的做題方式,并希冀老師對此作出特殊的照應(yīng)和培養(yǎng)。而工人階級的家長則盡可能規(guī)定孩子滿足學(xué)校要求的各項條件。他們也許會對別的機構(gòu)據(jù)理力爭,但學(xué)校在他們心中保有權(quán)威性。工人階級家長們傾向教育孩子服從和適應(yīng)學(xué)校,在與學(xué)校的關(guān)系中處于被動地位。而中產(chǎn)階級家長則更多地對學(xué)校形成影響,促使學(xué)校為迎合自己的孩子做出調(diào)整。孩子也在這一過程中通過對家長行為的觀察,各自接收了不同的暗示。“由于家庭中的文化技能庫與組織機構(gòu)采用的那些標(biāo)準(zhǔn)有很高的相似度,中產(chǎn)階級孩子及其家長擁有很多優(yōu)勢,雖然他們看不到自己是如何受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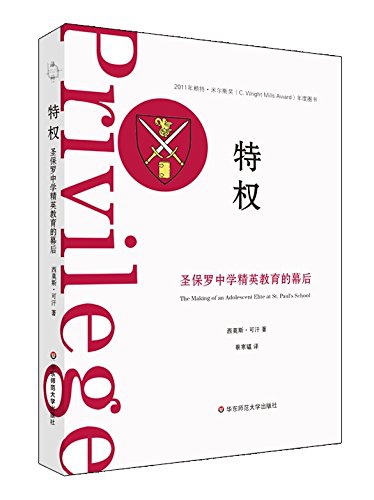
或許現(xiàn)在仍然相信“美國夢”的,恰恰是已經(jīng)擁有了特權(quán)的精英。他們也在做出一些維系夢想的嘗試。以精英教育聞名的圣保羅中學(xué)通過設(shè)立一系列制度,終止依靠繼承和封閉復(fù)刻的特權(quán),取而代之的,培養(yǎng)開放壞境下美國的“新精英”。例如,讓學(xué)生褪去家庭背景,統(tǒng)一起跑線,體驗階層流動,通過個人能力向上流動的“等級教育”。切斷學(xué)生與家長的一切聯(lián)系,將所有人的身份統(tǒng)一為“圣保羅化”,依靠個人經(jīng)驗積累自然形成他們認為屬于精英的“淡定”氣質(zhì)。知識教育上,不再局限于知識點本身,而是重視思維習(xí)慣的培養(yǎng),并以更開放的態(tài)度接納更多新事物。
但實質(zhì)上,這些企圖消解特權(quán)的儀式,只是堆砌了一種真空環(huán)境下的假象。當(dāng)學(xué)生走出學(xué)校,現(xiàn)實社會中的特權(quán)依然存在。而在學(xué)生們被“圣保羅化”之前,他們不平等的經(jīng)歷和文化地位也是既成事實。而正如作者在書中指出的,“開放并不等于平等”,當(dāng)精英正在展開高階的學(xué)習(xí)研究,公立學(xué)校的孩子還在為曾經(jīng)舊精英們瞄準(zhǔn)的知識點奮斗。“新精英”的規(guī)則,是舊精英們?yōu)樽约哄懺斓倪M步階梯,這些假象說服的,也正是享用著特權(quán)卻看不到自己正在受益的精英們,使他們錯覺,他們的地位全憑自己贏得,忽略了父母的財富保證了他們穩(wěn)定優(yōu)良的生活環(huán)境,或是當(dāng)自己實力不夠時,父母的付出代價如何替他們買了單。奮斗無疑可以創(chuàng)造奇跡,但我們也至少可以肯定,在機會平等不存在的語境下,“美式勤奮”的意義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偏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