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莫桑比克的巫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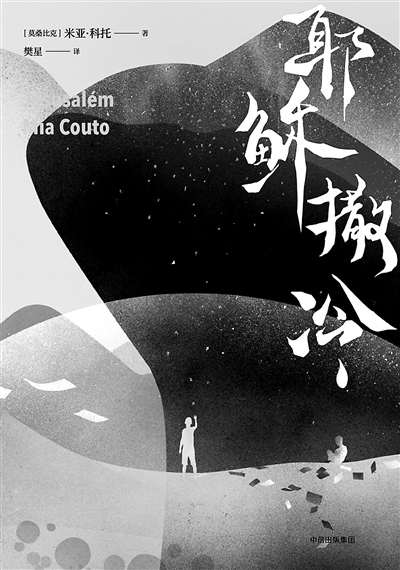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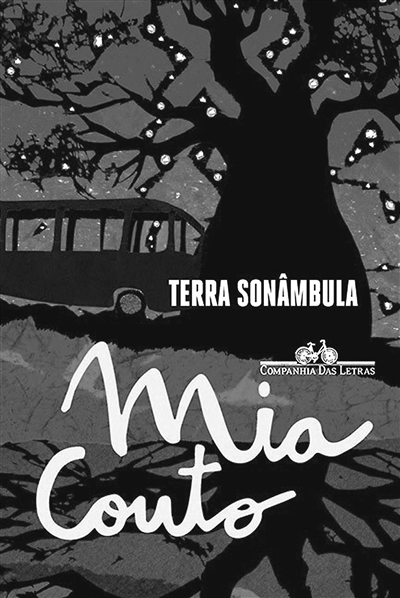
◎采訪:張中江 ◎翻譯:邱宇同
第一次來到中國的莫桑比克作家米亞·科托(Mia Couto),對這里的一切都充滿好奇。他會在第一時間問出版方,中國女性出嫁后是否會改隨夫姓?還很好奇記者的筆記本電腦,敲下鍵盤之后怎么會顯示出中文字符。同樣的,對中國讀者來說,米亞·科托還是一個相對陌生的名字,“中信大方”才剛剛翻譯引進(jìn)了三本他的書——《母獅的懺悔》《耶穌撒冷》和《夢游之地》。對于新事物,人們常常會貼上簡單易識的標(biāo)簽,比如“非洲作家”。但這其實是一個米亞·科托不愿意接受的輕率的介紹方式。
“非洲深受本質(zhì)化與田園牧歌化之苦,很多聲稱是純正非洲的東西其實不過是非洲之外的臆造。幾十年里,非洲作家要去證明純正性:人們要求其文本傳遞出大家認(rèn)為的真實種族性……確實有很多非洲作家面臨著特殊的問題,但我并不想因此便將非洲視為一個唯一、獨特、同質(zhì)的地域。”作家本人在2008年斯德哥爾摩國際作家與翻譯大會上這樣說。
身為葡萄牙后裔的他,出生在莫桑比克的第二大城市貝拉,父親是當(dāng)?shù)刂脑娙撕陀浾摺C讈啞た仆猩蠈W(xué)時參加了反殖民斗爭的莫桑比克解放陣線,后來自己選擇定居在莫桑比克。他的身份很多樣,詩人、小說家、記者、生物學(xué)家,同時也是文化思想者,對文化沖突、種族、環(huán)境、性別等諸多議題都有深入思考,這也使得他的作品呈現(xiàn)出廣博、多元的氣象。在今年上海書展“大方文學(xué)節(jié)”的演講中,他分享了這樣一個故事:十年前,他在一個動物保護區(qū)遇到一個獵人,也是通靈者。在他們相處的最后一晚,已經(jīng)失去視力的獵人說,“為什么你現(xiàn)在對待我的方式就好像我看不見一樣?我不用眼睛看,我的朋友,我借助夢來看。”在他的作品里,米亞·科托也盡力傳達(dá)莫桑比克人關(guān)于身體和意識的概念,“我們是用整個身體來思考的。我們的大腦分散在身體各處,從頭到腳。思想并沒有自己的家,它在我們拜訪他人的時候發(fā)光。”
將本土語言與葡萄牙語創(chuàng)造性結(jié)合,通過添加詞綴、舊詞合并等創(chuàng)造新詞,是米亞·科托作品的一大特點。在這點上,巴西作家羅薩對他有過很大影響。葡語文學(xué)學(xué)者樊星說,在2009年出版《耶穌撒冷》時,米亞·科托對語言創(chuàng)新的極致追求已漸漸讓位于一種流暢自然的敘事風(fēng)格,但某些字句仍然會時不時跳出來。甚至《耶穌撒冷》這個書名本身,也是作家造詞的產(chǎn)物。“巴西與非洲都曾是葡屬殖民地,葡萄牙語是殖民者曾使用的語言,在這種情況下,對語言的改造意味著對殖民歷史的反抗。”
包括《紐約時報書評》等在內(nèi)的媒體,在談到他作品風(fēng)格的時候,都會用“魔幻現(xiàn)實主義”來形容。此次中國之行,米亞·科托也多次被問到這個問題。事實上,他本人并不認(rèn)同這種歸類,而是認(rèn)為“魔幻和現(xiàn)實這兩樣?xùn)|西是一體的”。在米亞·科托筆下,人和動物、植物甚至石頭之間,存在可以轉(zhuǎn)化的玄妙。人可以變成雞,變成獅子,甚至是一棵樹、一條船。這種看起來不可思議、十分魔幻的情節(jié),在莫桑比克本土文化中,卻非常自然,毫無違和之感。
多年的戰(zhàn)爭給莫桑比克帶來了無盡的災(zāi)難,女性的命運更加多舛。在識字率還不是很高的當(dāng)?shù)兀頌樽骷业拿讈啞た仆校瑫灰暈閹в猩衩亓α康摹拔讕煛薄I踔磷咴诼飞希矔腥税阉麛r下,訴說自己的遭遇,希望能通過他傳遞聲音。米亞·科托不僅將自己的觀察寫到了作品中,還積極投身各種社會活動,為受難者發(fā)聲。最早被引入中國的小說《母獅的懺悔》,就對女性的遭遇給予了深切關(guān)注。在庫魯馬尼村,二十多個女人接連葬身獅口。隨著調(diào)查的推進(jìn),人們開始認(rèn)識到,也許母獅并非真正的獅子,而是女性用巫術(shù)召喚出來的古老神靈……
2007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得主多麗絲·萊辛這樣評價他:“不同于我以往讀過的任何非洲文學(xué)。”在上海書展期間,米亞·科托接受了北京青年報的專訪。
北青藝評:《夢游之地》中文版序言中您說,如果你去過莫桑比克,就會理解這一點:所有人都想忘記內(nèi)戰(zhàn),仿佛它根本沒有存在過。這種失憶成為共識。今天中國的年輕人,也對幾十年前的戰(zhàn)爭基本沒有什么印象。除了人類共通的原因,為什么說所有莫桑比克人“都想忘記內(nèi)戰(zhàn)”?
米亞·科托:在莫桑比克,人們并不是真正的忘記,而是被迫忘記。因為他們害怕,那(戰(zhàn)爭的影響)并不是過去,而是依然存在著。他們?nèi)鄙僮杂桑瑖L試去忘記那段歷史,但戰(zhàn)爭還在影響著現(xiàn)在的人。我認(rèn)為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人們一定要接受那段歷史。即使那段歷史很痛苦,仍然是歷史的一部分。作家的任務(wù)不是指出歷史上的真兇是誰,他們的任務(wù)只是講一個故事,因為這是歷史的一部分。
北青藝評:《夢游之地》開篇就用富有詩性的語言描寫了戰(zhàn)后景象,寫作詩歌對您的小說語言有怎樣的作用?
米亞·科托:寫小說這件事,跟用詩意的語言是沒有對抗關(guān)系的。這是沒有邊界的,(邊界)是人們構(gòu)建出來的。人用理性去思考的時候,就把隱喻的可能推到一邊,人們不喜歡這種東西,好像非常孩子氣似的。
北青藝評:《夢游之地》在敘事上采用兩條線,其中一條是日記的形式。《母獅的懺悔》也采用類似的敘事方式,這是您所偏愛的結(jié)構(gòu)形式嗎?
米亞科托:我不喜歡一個主角的敘述方式。我只是一個傾聽者,把自己聽到的不同聲音,以這樣的方式去呈現(xiàn)。
北青藝評:“造河的人”這樣一個意象,同樣也在前面說的兩本書中有所提及。這是您特意創(chuàng)造的,還是有民俗傳統(tǒng)?
米亞·科托:這是來源于一種神話和民族傳統(tǒng)。當(dāng)?shù)厝苏J(rèn)為,河流是一個像人一樣實體的東西,跟其他比如說巖石一樣是有生命的。河流還是連接死去的人和現(xiàn)在人的一個橋梁。
北青藝評:《耶穌撒冷》這本書里,在“耶穌撒冷”的人,拒絕回憶過去,也看不到未來,那怎樣定義“當(dāng)下”這個概念?
米亞·科托:在莫桑比克人的概念里,過去和未來不是線性的,不是有前后順序的,而更像一個環(huán)。這是當(dāng)?shù)厝藢r間的理解。在莫桑比克語言里,也沒有“未來”這個詞。有“明天”,但是沒有“未來”。所以一個人從來都沒有真正死去過,因為一直都是環(huán)形的,一直是關(guān)于現(xiàn)在的。
那里的女人去生孩子之前,是不能給孩子帶任何衣服的。在你看到這個小孩之前,是不可以給他/她穿上衣服的。因為你在預(yù)測一種未來。在那里,他們認(rèn)為,“未來”這個事情是不可預(yù)測的。這看起來比較奇怪。他們認(rèn)為,你這個個體不是屬于自己的,而是屬于你和你周遭的一種協(xié)調(diào)、協(xié)商,共同存在于一種協(xié)調(diào)中。他們眼中看到的山和河流,不僅僅是固體形態(tài)的山,而是會有聲音。我的作品就是把各種不同的聲音放在一起。
北青藝評:這和東方文化里的“輪回、往生”是否比較相似?
米亞·科托:這跟東方哲學(xué)不同。在莫桑比克,沒有死而復(fù)生的過程,人是沒有真正死掉的,而是無處不在的,一直在你身邊。他們并沒有不在場,只是改變了存在的形式。即使你在活著的時候也可以變成一棵樹、一條船,或者是其他生物。
北青藝評:在這部小說中,“我”與還有過去可以比較、能感到痛苦的“哥哥”相比,沒有其他體驗,這個“我”建立的是怎樣的認(rèn)知?
米亞·科托:這本書的主人公有點像我自己。我的記性特別差,記不住很多事情。對“我”來說,保持沉默是在場的一種方式。在英文版和法語版,這本書的名字叫做《沉默的調(diào)音師》,這也是中文版一章的標(biāo)題(《我,姆萬尼托,調(diào)試寂靜的人》)。這個“我”的一個身份,就是沉默的調(diào)音師。
北青藝評:女性角色瑪爾達(dá)的闖入,直接導(dǎo)致了“耶穌撒冷”這個世界的改變。您希望通過這個人物告訴讀者什么?
米亞·科托:因為這個角色是個女性,對主人公來說,其實是帶來一種新的、和男性相對的氣質(zhì)。她來自的世界,對他們來說,是他們既渴望了解,又有些害怕的地方。因為他們的爸爸告訴他們,除了這個地方之外,其他地方都不存在了。所以他們對那個地方(女性來的地方),有這樣一種情感。
北青藝評:《母獅的懺悔》里庫魯馬尼的女人,都對丈夫有尊稱“團古”。而丈夫則直呼妻子“女人”,可以看到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命運也很悲慘。現(xiàn)在莫桑比克女性地位是否有了明顯的改變?
米亞·科托:在城市和農(nóng)村的女性是完全不一樣的,窮人和富人,黑人和白人也是不一樣的。很難說女性作為一個整體是怎樣的,這是跟你的階級、宗教相關(guān)的。不過在選舉這件事上,莫桑比克在全球來說都是很平等的,議會里百分之五十是女性。當(dāng)然這是事情表面的一個情況。
北青藝評:在爭取男女平權(quán)上,您是否參與一些相關(guān)的活動,或者給相關(guān)的組織提出好的建議?
米亞·科托:首先我是個作家,會用文學(xué)來寫這些事。其次我還會參與很多爭取女性、兒童權(quán)益的組織,在這些組織中,我也是活躍者的角色,在一個公民社會的環(huán)境里。在路上的時候,人們有時會叫我停下,讓我告訴那些人某個事情。我并不知道這些人是誰,感覺自己有點像傳聲筒的角色。對這些人來說,文字的世界,是一個不同的世界,他們并不屬于這個世界。
北青藝評:就是說文字的世界影響不到他們,他們更希望有人可以直接為他們發(fā)聲呼吁?
米亞·科托:莫桑比克在43年前獨立,但那個地區(qū)識字率還是很低的,當(dāng)?shù)厝苏J(rèn)為能寫字的人還是屬于不同的階層。我因為一方面寫文章,另外在報紙上發(fā)表言論,在當(dāng)?shù)匾彩怯忻娜耍藗儠盐耶?dāng)作傳聲筒這樣一個角色。
北青藝評:小說中提到的“同化教育”(葡萄牙在殖民時期推行的教育),對莫桑比克現(xiàn)在的文化是否還有影響?
米亞·科托:當(dāng)?shù)赜?5種以上的語言,百分之四十的人既不會講也不認(rèn)識葡萄牙語,他們還在說自己的母語。如果說小朋友的話,小學(xué)基礎(chǔ)教育里有方言和葡萄牙語的學(xué)習(xí)。
北青藝評:您曾在以前的演講中提到,“三十年前幾乎沒有莫桑比克人母語是葡萄牙語,到現(xiàn)在12%的莫桑比克人將葡萄牙語作為第一語言。”這是否意味著莫桑比克本土的語言已經(jīng)很衰弱?您對莫桑比克本土語言有怎樣的研究,在作品中傾向于怎樣運用?
米亞·科托:葡萄牙語作為莫桑比克官方語言,確實很多人漸漸不太會講母語了。在學(xué)校里,很多人是把葡萄牙語作為第一語言去教學(xué),當(dāng)作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還是有差別的。
北青藝評:中國與非洲國家,都曾有過被外國入侵殖民的經(jīng)歷,被視為文化上的“他者”。在文學(xué)作品或者評論中,會有一種“奇觀化”的想象。您認(rèn)為今天這種情形是否有比較大的改觀?
米亞·科托:情況肯定更好了,現(xiàn)在莫桑比克可以從內(nèi)部發(fā)出聲音。但是所謂對“他者”的構(gòu)建,去想象對方是怎樣的,其實是一種政治和軍事上的操縱,有目的的一種操縱。
北青藝評:可以談?wù)勛铋_始閱讀作家吉馬良斯·羅薩的體驗嗎?
米亞·科托:羅薩是個詩人,寫文章也是非常詩意的。羅薩從別的語言借鑒了一種邏輯,改造了葡萄牙語。對于那些偏遠(yuǎn)的人,他們說的語言是沒有限制的,不存在語法正確與否的問題,他把這種自由帶到了葡萄牙語中。他是個醫(yī)生,經(jīng)常騎個毛驢,帶著小本子,聽人講故事。他把其中的語法和邏輯借鑒過來,改造了葡萄牙語。舉個例子,比如他碰到兩個人坐在一起,就問其中一個人你在干嗎,這個人回答說,我什么都沒做。問另外一個人你在干嗎,他說我在幫這個朋友。
北青藝評:他給了您怎樣的啟發(fā)?
米亞·科托:羅薩作品的存在,對我相當(dāng)于一種允許——你可以去這樣做了。之前我覺得寫作是一種需要理性的東西,看過羅薩的作品之后,相當(dāng)于他對我說,“你這樣做吧,你去寫吧。”
北青藝評:在各種介紹您的文字里,會提到您是非常接近諾貝爾文學(xué)獎的作家。今年這一獎項暫停頒發(fā),您會期待這個獎項有什么新的改變嗎?
米亞·科托:對于諾貝爾獎,我其實沒什么期待,但是我希望能夠改革評選標(biāo)準(zhǔn)。現(xiàn)在有很多重要作家,并沒有進(jìn)入諾獎的視野。而且諾獎的評選是非常歐洲中心化的。這也不是以我的角度出發(fā)說的,因為在諾獎內(nèi)部就有這樣一種質(zhì)疑的聲音。比如今年上海國際文學(xué)周的嘉賓皮特·恩格倫,就有這樣一種批評的言論,認(rèn)為諾獎是歐洲中心化的。我以前得過很多獎,有些沒什么名氣。但是如果有個小孩子走過來說喜歡我的書,我的書可以打動一個小孩,那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獎項。
北青藝評:莫桑比克的年輕作家們,他們最關(guān)心的問題是什么?
米亞·科托:他們關(guān)心世界,希望成為世界的作家。
北青藝評:您對中國文化有什么好奇,想知道的?
米亞·科托:我想知道一切關(guān)于中國的事情。目前我只來過上海一個城市,非常喜歡上海,我還想再來,看到更多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