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法蘭的“英國版自信”與反修正主義史學 ——讀《現(xiàn)代世界的誕生》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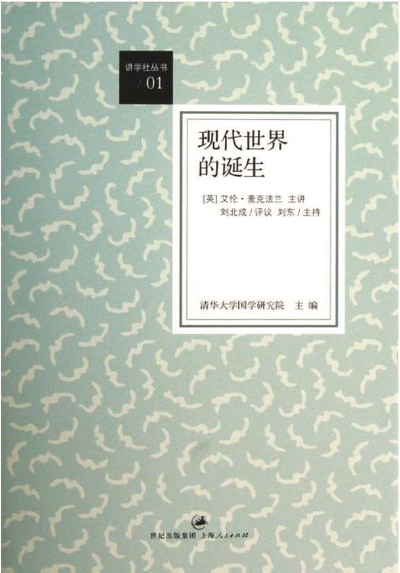
《現(xiàn)代世界的誕生》[英]艾倫·麥克法蘭主講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英國的現(xiàn)代化確實是個奇跡。要詮釋這段故事,需要一代代人的不同書寫。新近出版的《現(xiàn)代世界的誕生》就是其中之一。研究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社會學的有波蘭尼的《大轉(zhuǎn)型》和邁克爾曼的《社會權(quán)力的來源》,經(jīng)濟學的有諾斯的 《西方世界的興起》,各領(lǐng)一時風騷。相比之下,劍橋大學艾倫·麥克法蘭教授的《現(xiàn)代世界的誕生》頗為奇特。
先來看看他的研究方法。與其說它是歷史學著作,不如說是人類學的歷史延伸。不錯,它解答的是一組宏大和層次分明的歷史問題:擺脫農(nóng)業(yè)社會而邁入工業(yè)社會是如何可能的?為什么英格蘭能夠第一個跳出馬爾薩斯陷阱而其他國家或文明則不能自拔?但是,他并非完全借助英格蘭因自治而遺留的豐富檔案來說明問題,他更多地利用私人日記、旅行家日記等,帶有濃厚的民族志色彩。他所使用的概念術(shù)語也別具一格。在人類關(guān)系的表述方面,經(jīng)濟學家喜歡講尊嚴,社會學家喜歡講身份(韋伯),而他則喜歡討論友誼。他通過俱樂部、游戲、園藝等來觀察古人行為模式,探究其背后的意義。
本書之奇更在于考察視角。絕大多數(shù)有關(guān)著作都是從西方中心論角度來討論現(xiàn)代化進程的,而麥克法蘭卻試圖從中國人視角來看待現(xiàn)代化問題。2011年,清華大學國學院邀請麥克法蘭赴華系統(tǒng)闡述英國現(xiàn)代化的故事。這位向來特立獨行的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一到北京,憑借著人類學職業(yè)習慣,很快入鄉(xiāng)隨俗,和中國學者打成一片。在系列講座過程中,他與李伯重、劉北成等學者持續(xù)對話,摸清了中國學術(shù)界所關(guān)注的問題、思考世界的視角以及所熟悉的西方學者和理論。因此,他編織的英國故事打破了以往西方學者認為理所當然的假設(shè),注意到了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遭遇到的特有挑戰(zhàn),如大一統(tǒng)體制下中央地方關(guān)系以及社會凝聚等問題。為便于中國讀者理解,他特意引用廣大中國讀者熟知的學者和理論。例如,他在書中大段大段摘錄托克維爾的觀察和評論,用托氏的 “舊制度”來描畫前現(xiàn)代國家。因此,毫不奇怪,該書“給我們構(gòu)建了一個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英國形象,幾乎處處可以用來對照中國的歷史與現(xiàn)實”。
更為有趣的是,學術(shù)是雙向交流的過程。或許深受國內(nèi)學術(shù)界日益增長的自信的感染,麥克法蘭把早年強調(diào)的英格蘭獨特性升華為英國版本的三個自信。他感嘆:只有英國引領(lǐng)了其他國家踏上現(xiàn)代化之路。在他看來,歷史上,“進步倒是極不可能發(fā)生的,衰落和消亡才是正常現(xiàn)象。”數(shù)萬年前,只有東非一小群智人走向西亞,而其他族群幾乎滅絕了。走出中世紀是更小概率的事件,它要求具備人口規(guī)模、長期和平等諸多苛刻條件,還需要時間節(jié)點去耦合上述條件。而“英格蘭的現(xiàn)代性是一道橫亙1000年的‘長長的拱弧’,沒有任何間斷”。就此來看,不要說羅馬帝國、威尼斯共和國,連中央集權(quán)強大的法國都沒有能夠邁入現(xiàn)代化門檻,而是留下了托克維爾所指的“舊制度”標簽。指引英國走出中世紀迷霧的是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麥克法蘭津津樂道于此。他認為英格蘭在普通法之下早就實現(xiàn)了財產(chǎn)均為個人所有。由此,土地被視為一種商品,可以貨幣化地分割、買賣和繼承。更為重要的是,由于較早確立財產(chǎn)權(quán),貨幣化程度較深,所以英國的土地保有人或使用者都采用固定地租,從而激勵土地資本家更多投資于改良土壤。麥克法蘭引用一些地方史料斷言,14世紀英國農(nóng)業(yè)技術(shù)就已經(jīng)大有突破,直到18世紀才被超越。相比之下,亞洲和歐洲大陸普遍的分成租形式,地主壓榨佃農(nóng),成了消費性的食利階層,粒粒皆辛苦換來的是不斷內(nèi)卷化的勤業(yè)革命而非工業(yè)革命。如果說普通法分離了財產(chǎn)權(quán),那么衡平法則創(chuàng)造了信托。信托不僅存在于財產(chǎn)權(quán)的轉(zhuǎn)移和繼承方面,它無處不在。政治領(lǐng)域上,信托“滲透在君王與人民之間的微妙關(guān)系中”,議會只是民眾的受托人來表達他們的利益;在殖民統(tǒng)治領(lǐng)域,殖民地與宗主國英國構(gòu)建的是信托關(guān)系。總而言之,信托在處理群群關(guān)系方面達到了和諧和平衡,避免了歐洲大陸曠日持久和規(guī)模宏大的宗教戰(zhàn)爭。
麥克法蘭的制度和道路自信無疑來自于他的理論自信。他的有關(guān)現(xiàn)代性社會的看法類似于盧曼。他認為傳統(tǒng)社會的“舊制度將生活中互不相干的領(lǐng)域混為一鍋粥。在部落社會,親屬關(guān)系作為調(diào)節(jié)器將所有人團結(jié)在親屬關(guān)系之內(nèi)。在農(nóng)民社會,社會與經(jīng)濟不分彼此,宗教與政治不分你我,那里的基本單位是家庭和村莊共同體,上面覆蓋著薄薄一層有文化的統(tǒng)治者。”而現(xiàn)代社會則是分立社會,“對不同領(lǐng)域進行了深入劃分,致使生活中沒有任何一個領(lǐng)域,無論是親屬關(guān)系、宗教還是其他能夠提供一種基礎(chǔ)性原則的關(guān)系,每個領(lǐng)域都被另一個領(lǐng)域所制約。”簡而言之,現(xiàn)代性核心在于“分”,即將社會結(jié)構(gòu)、國家政體和意識形態(tài)等諸多領(lǐng)域進行分立。麥克法蘭指出,英國早在中古時代就開始分化,不僅僅經(jīng)濟活動不是按照血緣關(guān)系組織起來,連風險的防范和分擔也不需要親屬關(guān)系。在某種意義上,遠在工業(yè)革命之前英國就建立了福利國家。脫逸出以血緣為基礎(chǔ)的差序格局的英國人,構(gòu)成了一個以財富為基礎(chǔ)的彈性開放的社會階層,經(jīng)商有道者可以通過買賣和婚姻、自耕農(nóng)可以通過勤快的經(jīng)營,成為受人尊重的地方鄉(xiāng)紳;流入城市者則通過學徒等制度學得一技之長,加入行會而據(jù)有一席之地。社團和地方政府的強大有效地阻止了英國走向絕對主義。相比之下,這種分化在東亞很少形成強大的勢態(tài),即便中國古代經(jīng)濟繁榮。
由此觀點,麥克法蘭批評加州學派的修正主義史學。像彭慕蘭、王國斌等修正主義史學家想要破除西方中心論,認為18世紀之前中國和英國本來不相仲伯,直到1800年之后才出現(xiàn)了大分流。麥克法蘭引用羅伯特·艾倫的觀點,認為自從滿清入關(guān),中國江南地區(qū)的收入水平直線下降,到了18世紀馬嘎爾尼訪華時,與英國在勞動密度、農(nóng)田規(guī)模、人均農(nóng)業(yè)用地等方面已是差異懸殊。在能源使用上,彭慕蘭把中國工業(yè)化姍姍來遲歸咎于缺乏煤炭,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中國煤炭之豐富舉世罕見。
直白地說,無論麥克法蘭批評彭慕蘭等人是否有道理,其做法本身就值得玩味。在學術(shù)嚴謹?shù)挠粋€從事英國史的專家去跨界批評一個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多少有點不合規(guī)矩。在我看來,麥克法蘭的批評不僅是在捍衛(wèi)傳統(tǒng)觀點,可能還暗藏著他在研究方法上的輕視——一個完全靠著原始一手資料起家的大學者,對一批不大懂中文、沒接觸中國古代檔案、完全靠二手文獻編織出宏大理論的所謂的修正主義史學家,其內(nèi)心看法自然不難揣摩。當然,這不是說熟悉英國史料的麥克法蘭完全正確,他也有不少夸大之處。比如他說英國婦女自古較為自由平等,這一觀點就值得商榷。中世紀英國實行夫妻一體主義,妻子的人格都并入了丈夫之中,連獨立的財產(chǎn)權(quán)都缺乏,何來自由平等?再者,麥克法蘭說英國在中世紀晚期建立起了福利國家。但現(xiàn)代福利國家指的是中央集權(quán)化的管理和社會服務體系,而英國早期有的只是地方社區(qū)提供的千差萬別的社會服務,兩者根本無法相提并論,麥克法蘭此說極易引起誤解。不過,麥克法蘭的跨界批評給了我們很多啟示。要理解中國發(fā)展的過去和未來,我們確實需要深入探究西方,尤其是英國的制度演進。只有這種參考,才能夠更好地渡過舊制度的各種暗礁。從這一點來說,麥克法蘭的著作非常珍貴。他從中國人視角寫出了許多西方人認為理所當然而忽視的故事與制度,像普通法、信托、商業(yè)殖民帝國等都讓中國讀者耳目一新。顯然,這比那些在西方主流學界處于邊緣狀態(tài)、喜歡炮制驚人理論的所謂修正主義學者們的研究要有意義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