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的“消夏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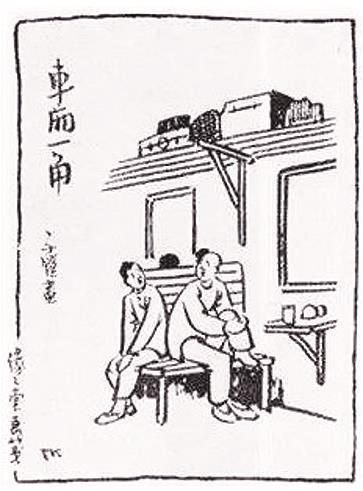
1930年代的上海充分表現(xiàn)了中國的現(xiàn)代性甚至未來性,同時也呈現(xiàn)出 “東方的巴黎”“冒險家的樂園”等駁雜性。海派文學也因此表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豐富性,并突出體現(xiàn)為“文學生產(chǎn)與流通一體化”的文學圖景。本書源于一次作家以文學廣告為中心的文學史寫作,試圖借助文學廣告這一盞聚光燈,重新照亮一些文學史空間,從文學原生形態(tài)的意義上展示1930年代的海派文學風景。正如作者所言,一種新的文學史觀照視角仿若一個探照燈,可以重新照亮歷史的某些晦暗的角隅,進而展現(xiàn)一些新的文學風景。
豐子愷的散文集《車廂社會》作為良友文學叢書之一于1935年出版,堪稱滬上出版界當年值得一書的收獲。而同年7月的《人間世》上刊載的《車廂社會》的廣告則更稱得上別致,“消夏新書”四個字,言簡意賅,卻引人矚目,既體現(xiàn)出“良友”的文學趣味,也吻合于《人間世》的辦刊風格。
消夏的方式在1930年代的上海可能花樣繁多。在這本《車廂社會》付梓的同時,豐子愷還寫了一篇《納涼閑話》,三個都市中人從一句“天氣真熱”引發(fā)的天馬行空的閑談,似乎才是最好的消夏方式。但是在炎炎盛夏,打出“消夏新書”的招牌,則可能格外會吸引那些暑熱難當?shù)淖x者。把讀書作為消夏的方式,既新穎別致,又不費什么錢,可能比起從旅游雜志上獲取關(guān)于莫干山的消夏廣告進而去旅游避暑更輕而易舉。而且絕大部分都市人是不大可能去莫干山消夏的,更可行的消夏方式是讀讀充滿豐子愷式的趣味的小品。比起魯迅的金剛怒目式的雜文讀了更加郁熱難當,顯然豐子愷的小品文更適于“消夏”。豐子愷的散文,傳承的是五四閑話風的小品文的精髓,在1930年代更是漸入佳境。在1934年作為“小品年”的文學氣候中,《車廂社會》得到出版界乃至讀者的格外青睞,是很自然的。而以聆聽豐子愷閑話的方式祛暑,也算得上是一種格外有品味的消夏方式吧?
如果帶著消夏的目的在酷暑中翻開這本書,讀者多半會首先翻看集子的最末一篇《半篇莫干山游記》。莫干山以竹、泉、云和清、綠、冰、靜著稱,素享“清涼世界”的美譽,與北戴河、廬山、雞公山并稱為四大避暑勝地。1927年,蔣介石和宋美齡在杭州西子湖畔舉行結(jié)婚儀式之后曾擬上莫干山度蜜月。現(xiàn)代諸多文人雅士也都在此山留過蹤影,郁達夫1917年即有詩詠莫干山:
田莊來作客,本意為逃名。山靜溪聲急,風斜鳥步輕。路從巖背轉(zhuǎn),人在樹梢行。坐臥幽篁里,恬然動遠情。
如果說,郁達夫是為“逃名”而作客莫干山(盡管作詩時的作者還沒有后來那么大的名氣),豐子愷則缺少類似郁達夫的這種名人的自覺,是現(xiàn)代史上最具有平民氣質(zhì)的文學家和藝術(shù)家。1930年代中期的豐子愷,早已脫離世外桃源一般的白馬湖生涯,闊大了對人間社會的觀察視野,尤其對底層社會保持著關(guān)注,這種關(guān)注,不同于“五四”時期的相當一部分啟蒙者,沒有高高在上的優(yōu)越感,而把自己也視為普通人的一員。正如在《半篇莫干山游記》中作者寫的那樣:“據(jù)我在故鄉(xiāng)所見,農(nóng)人、工人之家,除了衣食住的起碼設(shè)備以外,極少有贅余的東西。我們一鄉(xiāng)之中,這樣的人家占大多數(shù)。我們一國之中,這樣的鄉(xiāng)鎮(zhèn)又占大多數(shù)。我們是在大多數(shù)簡陋生活的人中度著嚕蘇生活的人;享用了這些嚕蘇的供給的人,對于世間有什么相當?shù)呢暙I呢?我們這國家的基礎(chǔ),還是建設(shè)在大多數(shù)簡陋生活的工農(nóng)上面的。”而《半篇莫干山游記》也與旅游消夏的動機相去甚遠,實際上恰恰相反,游記號稱“半篇”,寫的只是作者去莫干山途中所乘長途汽車因“螺旋釘落脫”而長時間拋錨于“無邊的綠野中間的一條黃沙路上”的情景。作者雖“本想寫一篇‘莫干山游記’,然而回想起來,覺得只有去時途中的一段可以記述,就在題目上加了‘半篇’兩字”。文章記錄的并非莫干山的清涼,仍是拋錨路上的所見所感。
如果說對都市里的讀者來說,欣賞豐子愷的《半篇莫干山游記》這類游記也算消夏的話,實有如酷暑中吃麻辣火鍋,在汗如雨下中覓得清涼。而如《半篇莫干山游記》這類散文的精髓實在于為酷暑中的都市人提供一種心境或關(guān)于另一種生活方式的穎悟,恰如豐子愷早期的散文《山水間的生活》中所寫:
我曾經(jīng)住過上海,覺得上海住家,鄰人都是不相往來,而且敵視的。我也曾做過上海的學校教師,覺得上海的繁華與文明,能使聰明的明白人得到暗示和覺悟,而使悟力薄弱的人收到很惡的影響。我覺得上海雖熱鬧,實在寂寞,山中雖冷靜,實在熱鬧,不覺得寂寞。就是上海是騷擾的寂寞,山中是清靜的熱鬧。
心靜自然涼,豐子愷所謂的聰明的讀者自能從《半篇莫干山游記》中獲得關(guān)于如何才能“消夏”的“暗示和覺悟”:
我和Z先生原是來玩玩的,萬事隨緣,一向不覺得惘悵。我們望見兩個時髦的都會之客走到路邊的樸陋的茅屋邊,映成強烈的對照,便也走到茅屋旁邊去參觀。Z先生的話又來了:“這也是緣!這也是緣!不然,我們哪得參觀這些茅屋的機會呢?”
《半篇莫干山游記》在呈現(xiàn)作者“萬事隨緣”的生活態(tài)度的同時,更值得讀者矚目的是豐子愷觀察社會的作為藝術(shù)家的自覺意識以及作為藝術(shù)家的觀察方式。這種藝術(shù)家的方式尤其表現(xiàn)在豐子愷的散文名篇《車廂社會》中,作者提供著自己對車廂里的人間百態(tài)的洞察,角度既獨特,看法也就因此別致,透露著一個時時留意人生世態(tài)的藝術(shù)家才具有的眼光。文章追溯了作者本人坐火車的三個階段:從“新奇而有趣”到“討厭”,繼而“心境一變”,乘車“又變成了樂事”。 “最初乘火車歡喜看景物,后來埋頭看書,最后又不看書而歡喜看景物了。”第三個階段與其說是看景物,不如說是看“車廂社會”,看眾生百態(tài),品味“車廂社會里的瑣碎的事”,車廂社會展現(xiàn)的是更加饒有意味的“風景”:“凡人間社會里所有的現(xiàn)狀,在車廂社會中都有其縮圖。故我們乘火車不必看書,但把車廂看作人間世的模型,足夠消遣了。”
這本貌似可用來“消夏”的散文集其實提供的正是足供讀者“消遣”的“人間世的模型”。消夏理念雖然是出版社的一種聰明的營銷策略,但是,豐子愷的這本包含著“人間世的模型”的散文集中所呈現(xiàn)的,卻不盡是莫干山般的清涼世界,而有相當一部分文字內(nèi)斂著火氣與燠熱,很難說適合于消夏。在林語堂主張“閑適”散文觀的時代,豐子愷的小品文,或許不盡符合論語派的理想。譬如在《肉腿》一篇中,作者展現(xiàn)出的是一幅故鄉(xiāng)農(nóng)人踏水的壯觀場景,作者稱之為“天地間的一種偉觀,這是人與自然的劇戰(zhàn)”:
從石門灣到崇德之間,十八里運河的兩岸,密接地排列著無數(shù)的水車。無數(shù)僅穿著一條短褲的農(nóng)人,正在那里踏水。我的船在其間行進,好像閱兵式里的將軍。船主人說,前天有人數(shù)過,兩岸的水車共計七百五十六架。連日大晴大熱,今天水車架數(shù)恐又增加了。我設(shè)想從天中望下來,這一段運河大約像一條蜈蚣,數(shù)百只腳都在那里動。我下船的時候心情的郁郁,到這時候忽然變成了驚奇。這是天地間的一種偉觀,這是人與自然的劇戰(zhàn)。火一般的太陽赫赫地照著,猛烈地在那里吸收地面上所有的水;淺淺的河水懶洋洋地躺著,被太陽越曬越淺。兩岸數(shù)千百個踏水的人,盡量地使用兩腿的力量,在那里同太陽爭奪這一些水。太陽升得越高,他們踏得越快,“洛洛洛洛……”響個不絕。后來終于戛然停止,人都疲乏而休息了;然而太陽似乎并不疲倦,不須休息;在靜肅的時候,炎威更加猛烈了。
作者繼而發(fā)揮道:“這次顯然是人與自然劇烈的抗爭。不抗爭而活是羞恥的,不抗爭而死是怯弱的;抗爭而活是光榮的,抗爭而死也是甘心的。”這種農(nóng)人 “與自然的劇戰(zhàn)”的場面以及內(nèi)在的抗爭精神恐怕是不十分吻合“消夏”精神的。《勞者自歌》則設(shè)身處地地站在勞動者和農(nóng)人的立場看待問題,甚至作者把自己也同樣看做一個“勞者”。這種“勞者”意識可以催生一種真正的平等主義的立場,使豐子愷的《車廂社會》中由此蘊含著都市人的自我審思的精神。這種自省精神才是在酷暑給都市人的頭腦和身體降溫的最好方式。
(《1930年代的滬上文學風景》吳曉東/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