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本忍與日本劍戟片里的“真實(sh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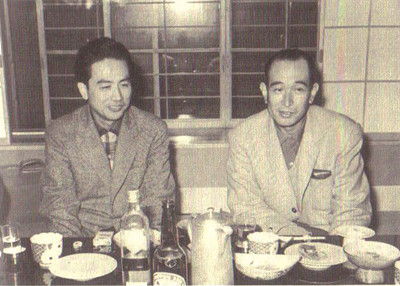
在我看來,在所有的《麥克白》影視化作品里,最傳神的竟然是黑澤明導(dǎo)演的《蜘蛛巢城》。根據(jù)11世紀(jì)蘇格蘭故事寫成的17世紀(jì)戲劇,經(jīng)由20世紀(jì)日本影人之手,在以日本戰(zhàn)國時(shí)代為背景的劍戟片中復(fù)活,強(qiáng)悍、冷酷中見悲愴,成為一出命運(yùn)與性格的真正悲劇。
前年春天,剛看了《蜘蛛巢城》,抱著很高的期待去北京國際電影節(jié)看改編自《李爾王》、同樣設(shè)定在日本戰(zhàn)國時(shí)代的《亂》。構(gòu)圖和運(yùn)鏡都臻于化境的濃烈畫面在大銀幕上極富視覺沖擊力,卻沒有帶來直指人心的撼動(dòng),有一種在規(guī)定時(shí)間里完成規(guī)定動(dòng)作的乏味,就像垂垂老矣的李爾王或者一文字秀虎(《亂》的主角)那樣疲憊而力不從心。那時(shí),我在觀影筆記里記了一句“美則美矣”。
公平地說,不只是黑澤明老了,而是日本的劍戟片即將隨著昭和時(shí)代的結(jié)束而最終謝幕。今年7月19日,《蜘蛛巢城》的編劇之一橋本忍以百歲高齡辭世,為已然遠(yuǎn)去的劍戟片在多年后畫上了一個(gè)句點(diǎn)。
“久板先生、菊島先生、植草圭、井手、小國師爺相繼離開——連黑澤先生也走了”,“對領(lǐng)頭人黑澤先生,我有一個(gè)請求,請您和大家說聲‘橋本隨后就到’,給我留一個(gè)能盤腿而坐的位置”。1998年,在給黑澤明的吊唁信里,橋本忍曾這樣寫道。
盡管在二戰(zhàn)后的日本電影黃金十年和隨后的新浪潮運(yùn)動(dòng)中,橋本忍曾與多位名導(dǎo)合作,盡管60年代以后,他已經(jīng)很少當(dāng)黑澤明的編劇了——兩人最后一次合作是1970年曾引發(fā)黑澤明第一次自殺的影片《沒有季節(jié)的小墟》,但是生前身后,橋本忍身上最顯眼的標(biāo)簽依然是“黑澤明身后的男人”。
是的,橋本忍就是那個(gè)最初把芥川龍之介的小說《竹林中》改編為劇本的人。根據(jù)黑澤明的回憶,1949年初春的一天,年輕的橋本到他家拜訪,那天會(huì)面的主題只有一個(gè),討論橋本送給他看的劇本《雌雄》。
《雌雄》的劇本長度只有40多分鐘。黑澤明對來訪的橋本說,這本子短了點(diǎn),把芥川龍之介的另一篇小說《羅生門》加進(jìn)去改寫一下如何?橋本怔了一下說“好的”,然后告辭,整個(gè)會(huì)面只有幾分鐘。這才有了電影《羅生門》。
有人說,如果沒有遇到彼此,以橋本忍的能力會(huì)在電影行業(yè)出頭的,而黑澤明也會(huì)是個(gè)好導(dǎo)演,但是他們不會(huì)是現(xiàn)在為人所知的黑澤明和橋本忍,甚至戰(zhàn)后的日本劍戟片也不會(huì)是后來的格局。
在拍攝《羅生門》前,戰(zhàn)敗后剛剛重新起步的日本電影行業(yè)中,黑澤明已經(jīng)成名。而《雌雄》是橋本忍完成的第一個(gè)劇本,可以說是黑澤明帶他入行的。而《羅生門》在威尼斯電影節(jié)和奧斯卡金像獎(jiǎng)上為日本電影爭得的關(guān)注與聲譽(yù),讓剛剛憑現(xiàn)代戲《泥醉天使》大獲成功的黑澤明,乃至更多黃金十年的日本影人將創(chuàng)作精力投向劍戟片。
正如中國電影并不是舞刀弄槍就是武俠片一樣,在日本電影里,并非刀劍相向就是劍戟片。劍戟片通常指的是以江戶時(shí)代武士、浪人為主角的電影,也就是古裝電影,日本人稱之為時(shí)代劇。之所以限定年代,在于劍術(shù)固然能傳承至今,但是武士作為一個(gè)已經(jīng)消失的階層,只屬于已經(jīng)消失的舊時(shí)代。
在《羅生門》后,這種類型片在很長一段時(shí)間里,都是一款多贏的熱銷產(chǎn)品。一方面,作為堪比美國西部片的通俗電影,劍戟片娛樂性很強(qiáng),在日本國內(nèi)的院線有廣泛的觀眾基礎(chǔ)。另一方面,劍戟片也成了西方人理解日本,日本在西方藝術(shù)殿堂里獲得認(rèn)可的一種方法,就像他們通過《黃土地》《霸王別姬》《活著》等電影來理解我們一樣。而日本影人,得以在刀光劍影的美感中,一次次喟嘆武士階層的覆滅,宛如欣賞櫻花凋謝,沉浸在肅殺、自傲又自憐的氛圍中。
接下來的主題問題是,如何講好這個(gè)多贏的故事。
橋本在吊唁信里提到的那些名字:菊島隆盡、植草圭之助、井手雅人、小國英雄,都曾是黑澤明的合作編劇。在橋本忍與黑澤明展開合作的前期,準(zhǔn)確地說是在1955年《活人的記錄》前,黑澤明采用的是“編劇先行”的劇本創(chuàng)作方式。橋本在晚年的回憶錄《復(fù)眼的影像》講述了這種創(chuàng)作方式的運(yùn)行機(jī)制。“復(fù)眼”指的是編劇們各自對同一場景進(jìn)行寫作,然后在“頭腦風(fēng)暴”中擇優(yōu)融合到一個(gè)本子里。
可能是黑澤明時(shí)代劇和現(xiàn)代戲最高成就的《七武士》和《生之欲》,都有這種眾聲合唱的復(fù)眼,因?yàn)榻y(tǒng)攝了多位作者的視角,像多聲部合唱一樣有一種復(fù)調(diào)的力與美。
在《七武士》后,黑澤明仍啟用多位編劇同時(shí)寫一場戲,不同的是不再統(tǒng)稿,而是用“競筆”的方式,誰寫的好,就用誰的這場戲作為終稿,一場一場擇優(yōu)選用,直到整個(gè)劇本完成。這種劇本成稿方式被稱為“一槍定稿”,優(yōu)點(diǎn)是效率高、成稿快,缺點(diǎn)也是顯而易見的——雖然與“編劇先行”法一樣是多人創(chuàng)作,但是實(shí)際上等于是在不斷地?fù)Q作者,那位在多人的腦力激蕩中仿佛神明附體,擁有凡人所不能有之復(fù)眼的“作者”不見了。
就是這位沒有署名的“作者”,創(chuàng)作出橋本所言的“真實(shí)感”。“放棄了自身獨(dú)特的,有真實(shí)感的電影美,轉(zhuǎn)而追求鮮明的形式美,有一種格外不和諧的感受。”橋本曾這樣批評《亂》的不足。
橋本追求的“真實(shí)感”,不只是細(xì)節(jié)真實(shí)和建筑其上的邏輯真實(shí)。
細(xì)節(jié)和邏輯當(dāng)然很重要。《竹林中》是一個(gè)有關(guān)謊言的故事,由一個(gè)兇殺案引出7個(gè)當(dāng)事人互有矛盾的供詞,細(xì)節(jié)戳破了謊言,而真相永遠(yuǎn)缺失。在電影里,這成了一個(gè)在羅生門下講述的故事,《羅生門》作為這一嵌套結(jié)構(gòu)的外層,在死亡與謊言之間構(gòu)建起新的邏輯關(guān)系——“羅生門這兒的鬼,因?yàn)楹ε氯祟惖膬礆埗幼摺保叭绻藗儾幌嗷バ湃危@個(gè)世界跟地獄有什么分別呢”。簡言之,謊言是人之惡的遮羞布,人惡起來,比死亡和鬼魂更可怕。
在拍攝《七武士》前,橋本忍和黑澤明曾經(jīng)有另一個(gè)本子《武士的一天》,終于因?yàn)闊o法在史料中確定古時(shí)武士一天吃兩頓飯還是三頓飯,而放棄了整個(gè)拍攝計(jì)劃——因?yàn)橹挥形涫棵刻斐詢深D飯,才會(huì)有主人公后來的際遇。
不過,橋本在這一項(xiàng)目夭折以及后來寫《七武士》時(shí)做的功課沒有浪費(fèi),對武士相關(guān)資料的大量涉獵,為他日后獨(dú)立創(chuàng)作出《切腹》《奪命劍》《大菩薩嶺》等劍戟片名作打下了基礎(chǔ),甚至有人認(rèn)為,橋本忍以一己之力寫出了最好的日本劍戟片。
這些作品里不只有《羅生門》里的“武士”“強(qiáng)盜”這些概念化的角色,而是見得到舊時(shí)代、舊體制的“肌理”。例如,小林正樹導(dǎo)演的《奪命劍》清晰地展示了武士作為“馬回眾”(警衛(wèi)隊(duì)),如何在一方諸侯“大名”手下盡忠任職,大名如何維持他對諸侯國的統(tǒng)治。在岡本喜八導(dǎo)演的《大菩薩嶺》里,橋本忍選取了三個(gè)標(biāo)志性的歷史時(shí)點(diǎn),用筆鋒在570萬字的原著里切開了一個(gè)剖面,用幾個(gè)命運(yùn)糾結(jié)在一起的虛構(gòu)人物,一窺幕府末年武士組織“新選組”誕生的前前后后。
而比起細(xì)節(jié)真實(shí)和邏輯真實(shí),對于藝術(shù)作品來說,更重要的是情感真實(shí)。讓西方人與溝口健二或者小津安二郎產(chǎn)生情感共鳴,應(yīng)該是太困難了。就連小林正樹,大約也只能看個(gè)大概。比起同時(shí)代或稍早時(shí)候其他出色的日本導(dǎo)演,黑澤明是最會(huì)用西方人能接受的方式講故事的一位,他常常像個(gè)美國人一樣,凝練出超越民族和文化的永恒主題:比如,人之惡比鬼還可怕;比如,強(qiáng)者隨風(fēng)而逝,反倒是弱者“贏得了勝利”。
而且,與許多喟嘆武士如櫻花凋零的同行不同的是,黑澤明和橋本忍早在《羅生門》里,就用樵夫口中最接近真實(shí)版本的講述,在電影高潮部分用一場七零八落、上不得臺(tái)面的打斗,戳穿了強(qiáng)盜和武士各自的謊言:強(qiáng)盜不是孔武有力的,武士則更是懦弱卑鄙的。一上手拍劍戟片就“解構(gòu)”武士安身立命的兩樣法寶:劍術(shù)與高尚精神,即使在70年后,也比近年來很多向武士道精神暗送秋波,給軍國主義招魂的日本電影更像是現(xiàn)代人拍的。
有趣的是,武士妻子這個(gè)角色,在樵夫的版本里,在已經(jīng)被兩個(gè)男人同時(shí)拋棄的不利境遇下用言語反擊,實(shí)質(zhì)上操縱了故事的走向,露出了比男性角色都更為強(qiáng)悍的本色,但是在她講述的版本里,偏偏要將自己描繪成倉皇無助的角色。這里,體現(xiàn)的也是《羅生門》雖歷經(jīng)時(shí)間洗刷而不褪色的現(xiàn)代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