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傳》:黑格爾和他的死亡詩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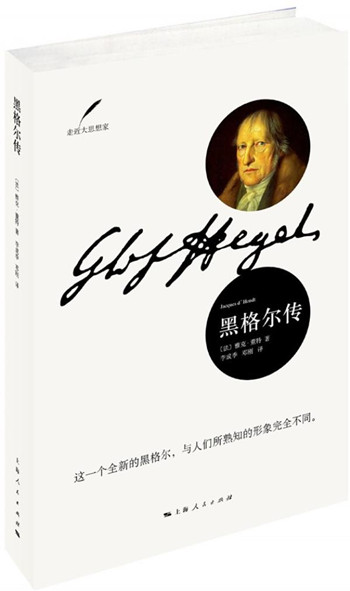
他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而自由地出賣了自己。
名人傳記算得上受眾最廣的文化讀物之一,可哲學家的傳記卻一直處于吃力不討好的境地,一方面和動輒伏尸百萬的王侯將相比,哲學家的私生活在情節(jié)上不過是小打小鬧,難以勾起一般讀者的興致;另一方面私人生活的過度曝光很容易阻斷闡釋者的自由發(fā)揮,盡管他們同樣熱衷于閱讀、汲取或批判這些傳記。哲學研究總和哲學史交織在一起,很容易把哲學史寫成大哲學家到大哲學家之間的接力跑。哲學史并不像它的詞性所表現(xiàn)的那樣,始終是哲學而非歷史,而學術(shù)類出版物中林林總總的哲學家導讀書大都屬于這個序列。
然而傳記始終是歷史而非哲學,還原時代背景與梳理線索始終是歷史學者的必要工作。鑒于闡釋之間的巨大差異,哲學家生平材料終歸比其他領(lǐng)域更難厘清,甚至更難獲取。不理解這種哲學與史料的兩面夾擊,很難評判一本思想家的傳記是否成功,也很難理解這本《黑格爾傳》所秉持的那種激昂究竟意圖何在。在這一點上,作者董特一開始就是站在歷史的立場,以哲學史上周正卻粗疏的黑格爾形象為假想敵的。這同時也意味著他與一般讀者保持了距離——并不是說本書涉及哲學討論,而是作者并不愿點透太多思想公案,除非他另有解讀。
當然,作者并不試圖貶低黑格爾哲學的分量,須知作者董特本人也是法國的黑格爾專家。只是歷史研究很難不在鉤沉中看到傳主不為人知也不愿為人知的一面,甚至是文本之下不便宣之于口的意圖與機心。難道不是每一位想成為元帥的士兵的包袱里都藏著一根搟面杖嗎?人生本就是復雜的機緣組合而成,哲學家的公共形象更是如此。在這個意義上,哲學與哲學家傳記的研究對象一開始就是不同的,并不存在對錯。黑格爾哲學當然不是黑格爾生平的必然衍生品,反之亦然。
全書以黑格爾的葬禮開篇,就是作者心中爭奪解釋權(quán)的微型戰(zhàn)場。普魯士官方對黑格爾葬禮的彈壓到底是顧忌霍亂,還是如作者與送葬者所想的那樣,全然為了抹除黑格爾哲學的影響,我們不得而知。然而,從送葬的規(guī)模和致辭的激烈程度來看,這必然不只是為一位年高德劭的老教授送行,而是為一位尖銳的旗手與先驅(qū)送行。這個倒敘非常明確點出了全書最核心的判斷——黑格爾在內(nèi)心里是,且一直是一位叛逆者。他的理智只是對世界的妥協(xié)和屈就,他留給后世的形象不過是冷寂后的余燼。董特想探求的是,這種周正平和的哲學下曾包裹著怎樣的火焰。
這不只是作者的判斷,而且是時人的風評。事實上,自康德草創(chuàng)以來,“為自然立法”的觀念論本身就是叛逆者的同義詞。無論大學生對觀念論本身的掌握到了何種層次,學習觀念論本身就帶有一種決裂的姿態(tài)。像文學上的浪漫主義一樣,觀念論對時人而言,首先是一場運動,其次才是一種風格。這場葬禮異端云集,致辭火藥味十足,主角完全可以換成李大釗或薩特,足以窺見在時人眼中,黑格爾的形象更接近瘋言瘋語的齊澤克,而非老成持重的平卡德(兩位均為當代觀念論學者)。
作者顯然對可能遇到的反駁有所準備,哲學史以馬克思為軸心,劈開所謂傳統(tǒng)哲學與當代哲學,由是觀之,黑格爾的老戰(zhàn)友都被扣上了“黑格爾右派”的帽子。作者非常直率地點出,這樣的劃分只在黑格爾學派內(nèi)部才有效,而整個黑格爾哲學在時代意識形態(tài)中都是左的(18頁)。只有理解黑格爾這種思想底色,我們才能理解黑格爾生命中反復出現(xiàn)的決絕姿態(tài)。
他的第一重決絕是他的出身。后來的研究者習慣于把落后當作抽象的反面予以鞭笞,可對十九世紀初的德國知識分子來說,落后卻是急于擺脫的切膚之痛。當康德寫《何謂啟蒙?》時,他抬頭就能望見哥尼斯堡外的山巒。以今天的標準衡量,這座普魯士的文化故都也不過是一座集鎮(zhèn)而已。這種強烈的文野之別讓他沒有理由不渴望啟蒙。生活在中產(chǎn)階級的黑格爾同理,他長期領(lǐng)著實物工資,直到法蘭克福時期才擁有獨立的房間。黑格爾的主體概念當然不限于這點內(nèi)涵,但成為主體的渴望肯定包括這一層現(xiàn)實含義在內(nèi)。
其時中產(chǎn)階級子弟并沒有太多優(yōu)越感可言,些許富足不影響其上不著天、下不落地的社會地位,唯一的優(yōu)勢只在知識上。他們能走上文化道路都與牧師有關(guān),是這個階段的德國特有的文化現(xiàn)象。圖賓根神學院的教育條件堪稱優(yōu)厚,也有畢業(yè)的公務(wù)員編制,只要付出宗教上的忠誠。這唯一的條件與德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酷刑相比不值一提,但受法國大革命耳濡目染的年輕謝林、荷爾德林與黑格爾而言,卻是不堪忍受的重負。這就是《死亡詩社》里那種生活——嚴格的儀軌、寬松的師長與詩意的遠方,無一不助長著年輕人內(nèi)心的叛逆。他們詩酒年華、尋釁斗毆,偏偏這幾位天才還有能力同時維持著陰陽兩面的優(yōu)秀,也把這種撕裂維持到自己生命的盡頭。
宗教是那代德意志知識分子永遠的夢魘。一方面,宗教是他們的源頭活水,這個時間段的德語文學和哲學幾乎都是“隱蔽的神學”,這個時代晦澀的風格也始于這種吞并神學的野望;而另一方面,學校的宗教儀式又是符騰堡公爵倒行逆施的具象化,盡管這里本來是培養(yǎng)牧師的機構(gòu)。年輕的謝林與黑格爾一無所有,都不愿出賣他們僅有的驕傲。他們對宗教又愛又恨的情結(jié)幾乎和他們的胎教呈正相關(guān),康德只需要外在地與人周旋,謝林就干脆活出了十九世紀德國文學史的大趨勢,從批判者復歸宗教經(jīng)驗之中,黑格爾介于兩者之間,可他的開場同樣決絕。董特對以往的輕描淡寫十分不滿,尖銳地指出,黑格爾逃離唾手可得的牧師職位,其決絕不下于《玩偶之家》的娜拉。
社會的捶打總是比學校來得更直接,黑格爾對自己近十年家教生涯三緘其口。他畢竟不是詩人,不同于荷爾德林的張揚,但這種沉默所體現(xiàn)出的自尊心有過之而無不及。Subject既是主體也是臣仆,沒有人比家庭教師對這種身份更為敏感。雇主提供了當時最優(yōu)厚的條件,卻換不來哲學家和詩人的尊重,因為作為打工仔的詩人和哲學家居然反過來勾引小姐、索取尊重。當黑格爾寫信求職時,他心目中的雇主該是一幫社會改良人士。事實也確實如此,但等他到法蘭克福時,又輪到哲學家嫌棄市民身上的市儈氣。他的決絕可以逃脫牧師的職務(wù)與教師的待遇,可只要他還沒有徹底皈依爛俗的世俗精神,他的逃離與退讓就必須繼續(xù)。
也許有讀者對本書俯仰皆是的共濟會線索感到不耐煩,觀念論哲學仿佛也成了共濟會陰謀的一部分。董特的表述確實很容易被誤讀,他對共濟會線索的羅列不乏對史料的炫技成分,但他意不在證實黑格爾是不是一位活躍或在籍的共濟會員——如果能的話他早就做了。黑格爾的交際圈顯然充斥著共濟會和光照派的成員,但這種范圍如此之大的共濟會沒有多少秘密可言,只是改良派社會名流的別名而已。各地共濟會主張不一,往來也取決于具體的人脈。黑格爾有意識地結(jié)交這些名流,顯然只是內(nèi)心的改革意識作祟。這是個人人思變的時代,而結(jié)社只是時代焦慮感的體現(xiàn)。共濟會的教義即使真的存在,也是毫無約束力的政治公約數(shù)而已。董特頻繁地點出黑格爾身邊共濟會和光照派成員,也是要勾勒出這種時代精神的流變。
黑格爾從孩童時代熱衷、求職信中引用,甚至在葬禮時被人們?nèi)缡腔貞浀墓畔ED隱喻,雖然意指不斷遷移,但在最廣泛的意義上,都不過是對基督教文化的反動。所謂暗語不過是些“你懂的”之類的話梗,警察未必通曉其中的具體含義,但諷刺語調(diào)難道還聽不出來嗎?可只要不付諸行動,當權(quán)者還很少追查這些文人的牢騷話。南德光照騎士團的案子恰恰證明了這一點,要偵破這種案件,難度不在于調(diào)查取證,而在于輿論能多大程度引發(fā)正統(tǒng)基督教社會的警覺。
因此,黑格爾與共濟會的關(guān)系并不是一出《達芬奇密碼》,反而中肯地點出啟蒙一直以來的問題。如阿多諾所說,啟蒙的自明性實際上是建立在對神話的反對之上,至于神話的內(nèi)涵則取決于具體社會環(huán)境。對阿多諾是納粹與美國的文化工業(yè),對十九世紀初的德國人則意味著基督教文化與邦君的雙重宰制。這些秘密結(jié)社(共濟會、光照派)、文化潮流(崇古、希臘)就其社會性質(zhì)而言,與后來學運時期的青年文化并無不同。結(jié)社是社會交際的一部分,并沒有多么神秘。康德和費希特在共濟會刊物上發(fā)文,只是因為思想上的親和力。作為法國大革命的擁躉,黑格爾豈會缺席這場盛宴?
如果讀者不急于對共濟會陰謀感到厭煩,那么本書對黑格爾《厄琉息斯》的考察其實是相當精彩的文本考據(jù),讓我們看到一個肉眼凡胎、為了求職還略有些機心的年輕黑格爾。我們也看到缺乏對歷史的掌握,即使是大哲學家的解讀也不免荒腔走板。老黑格爾形象的締造者不乏黑格爾研究名宿和狄爾泰這樣的大哲學家,如果說卡爾·黑格爾裁剪他父親的形象是別有用心,那狄爾泰們歌頌黑格爾個人情懷的強解就可以說是天真爛漫了。以同樣的原則,不難把觀念論和浪漫主義都解讀為希臘精神和基督教精神某種程度上的中和。缺乏必要的信息和線索,大而無當?shù)难芯渴冀K是了解哲學家的障礙而非臂助。難道可以因為黑格爾與荷爾德林老死不相往來而忽略荷爾德林的影響嗎?哲學研究并不能脫離史料,文本研究更不能局限于文本,特別是黑格爾這種善于沉默的作者。
耶拿是黑格爾辯證法的發(fā)跡之地,他的青教歲月包括僧多粥少的教職競爭和貧困線上的生活水平,所幸他還有謝林的庇護。這種庇護是十八世紀知識界的常態(tài),也是文人的宿命,歌德和席勒都不能例外。一場近乎兒戲的博士論文答辯像極了如今觀念論的學科形象——黑格爾自詡科學和歷史,可他的研究一直是這兩門學科的反面教材。他之后的行動也和其他理論家別無二致,主編刊物、論戰(zhàn)并撰寫自己的大部頭。一個多世紀后,哈貝馬斯幾乎找美、英、德、法的哲學家單挑了一個遍,沿著相同的軌道冉冉升起。本書沒有討論他的哲學是否真的優(yōu)于他的論敵(包括康德、費希特在內(nèi)),只能確定這一時期的黑格爾在學界表現(xiàn)得極為好斗,思想的創(chuàng)造力與成名的渴望皆有之。
他的報刊編輯和中學校長生涯嚴謹而稱職,體現(xiàn)了黑格爾德國人的一面。當然,沒有什么比私生子的另一面更抓人眼球。作者董特濃墨重彩地描寫黑格爾的私生子顯然也是懷有敵意的——不是針對黑格爾,他對私生子的教育雖然堪稱失敗,卻足夠負責,而是針對之后十九世紀的黑格爾研究者,他們一直心照不宣地掩蓋這個事件,共同完成對黑格爾的造神運動。狄爾泰、羅克都秉持著自己的寄托把黑格爾塑造成道德楷模,可近代市民社會遠不止單向度的新教倫理。真實歷史總是糾纏在七情六欲中,即使最抽象空靈的哲學也不可能沒有個人生活的影子。黑格爾遮掩丑事的小動作是人之常情,沉默的史家卻很難原諒。
以本書來看,海德堡時期也許是黑格爾生命中最愜意的時光,他家庭和睦、教職穩(wěn)定,哲學寫作也終于能有條不紊地展開,可見“中產(chǎn)階級生活”對人生有再造之功,連哲學家也不例外。他到柏林后雖然聲望和身價水漲船高,但也卷入了是非的漩渦。大革命潮起潮落,普魯士的政治光譜也隨之來回擺蕩。不意識到這種二十年一個周期的輪回,就不能理解十九世紀上半葉從歌德到馬克思那些復雜并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政治傾向,只能得出某種進步-保守的粗糙對立。
黑格爾當然不完全服膺于普魯士,但沒有理由不對它的未來懷有希望。相對于南德盤根錯節(jié)的天主教勢力,普魯士才是德意志王氣所鐘,這幾乎是新教知識分子的共識。普魯士雖然號稱專制,可從黑格爾的邀請人哈登伯格到俾斯麥,這些首相幾乎在庶務(wù)上無視王室。這并不是權(quán)宦的指摘,而是一種相對傳統(tǒng)的職能分工,特別是在一個宗教環(huán)境空前復雜的時代,君主是不便于染指經(jīng)營的。即便后來王儲對黑格爾的敲打,如今看來也在禮儀上給足了面子。“御用哲學家”高估了黑格爾在學術(shù)之外的影響力,卻沒有低估他這次任命背后的社會關(guān)系。黑格爾在普魯士最開明的時代獲得進身之階,本身就能體現(xiàn)他的哲學立場。
黑格爾的政治哲學本來就充滿爭議。只從生平來看,黑格爾確實從耶拿時代起就斷斷續(xù)續(xù)地流露出民族主義的優(yōu)先性。這個階段的德國思想始終縈繞著對法國大革命的逆向情愫,黑格爾也難免鐘情于他的民族情感和時代精神,但這個階段的德國不過是分裂與落后的別名。可如果把他和官僚制聯(lián)系在一起,就過于后見之名了。官僚制這個詞在十九世紀并不是韋伯筆下的中性詞,本來就有改革色彩在內(nèi)。他們不是冷冰冰的管理機器,而是胸懷韜略的啟蒙信徒,哈登伯格的內(nèi)閣和黑格爾的朋友圈都充斥著這個群體。黑格爾晚年的兩位助教很能體現(xiàn)這一點:甘斯和佛斯特爾——猶太知識分子和普魯士老兵,德意志的改革派和愛國者。某種意義上,黑格爾就是這兩重身份的中和。
因此,柏林的黑格爾一次次既主動又被動地卷入造反派學生的活動,他既有后臺撐腰也有教授的責任,并抱著勇氣在剃刀邊緣行進。即使如此,從本書的材料看來,黑格爾的卷入之深也是超乎想象的,須知他的每位助教都是普魯士的盯防對象,他自己也不例外。在居贊案中,黑格爾面對普魯士警察所表現(xiàn)出的勇氣和老到都令人擊節(jié),但同樣讓人懷疑,如果黑格爾再活幾年,這種貓捉老鼠的游戲能否繼續(xù)下去。黑格爾死于普魯士政局洗牌的前夜,可以說是上天對他身后名聲的一大庇護。
董特不但不想和哲學史妥協(xié),也不接受青年激進晚年保守這種零成本的轉(zhuǎn)型。時代變了,黑格爾卻不曾改變。歐洲的氣氛隨著十九世紀步步邁進,終于把昔日的先行者甩在了身后。史學家把理性和(普魯士)國家簡單劃上等號,政論家把自己在寬松環(huán)境下的放肆舉動拿來炫耀,他們都忘了黑格爾最多只能算半個現(xiàn)代人,在圖賓根的學生寢室中如此,在紐倫堡的校長室中如此,在柏林的大講堂中還是如此。
當然,董特所使用的材料并非無可指摘,比如他很喜歡搬出黑格爾年輕時“廢除國家”的激進宣言,可這個文本在各種意義上都是孤證。黑格爾柏林時期的史料最充分,也是各個版本黑傳之間差距最大的地方。撇開早期執(zhí)著于描述黑格爾的美麗心靈或稱其為專制鼻祖的那類研究,我們不妨比較董特和平卡德兩本傳記。董特似乎把黑格爾不能進入科學院當作他與王室角力的后果,只字不提他和施萊爾馬赫之間赤膊上陣一樣的互斥,須知施萊爾馬赫干脆為了阻擊黑格爾改組了整個柏林科學院的編制。
更重要的是,董特與平卡德對待黑格爾在《奧格斯堡信條》慶典上的演講,幾乎側(cè)重的是完全不同的面向。平卡德看到,黑格爾對七月革命有消極的抵觸,他最后批評英國,連課堂講義也出現(xiàn)了一些氣質(zhì)上的變化。可董特似乎抱著一種法國人特有的激情,以至于到了把慶典演講中所有歌功頌德的話當作自保和虛偽,卻把《選舉法修正案》視為對普魯士明目張膽的諷刺,置黑格爾于無間道之中。這種材料上的互補很能培養(yǎng)讀者自己的判斷,畢竟讀者沒有必要為了維護黑格爾的大寫形象而費力,只需要知道,他的偉大始于他曾在時代的激流中負重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