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里猶是少年郎——讀胡曉明《巴黎美學(xué)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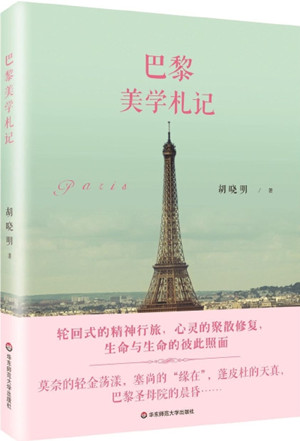
2007年,胡曉明得到了一個去巴黎做訪問學(xué)者的機(jī)會。為此他決定先學(xué)法語。當(dāng)時胡曉明的女兒在上海一所法語學(xué)校學(xué)了一年語言,胡曉明入學(xué),做了女兒的“學(xué)弟”。那幾個月里,“學(xué)弟”爸爸開著助動車,載著女兒“學(xué)姐”同去教室,捧讀教材。已經(jīng)桃李滿園的教授胡曉明,在法語面前,重新回到了少年求學(xué)的時代。
不為什么,因為前面是巴黎在等著他。巴黎讓他愿意重回課堂,重新做回少年郎。巴黎,這兩個字念出口的時候,如同念出年少時愛人的名字,是令人心馳蕩漾的召喚。它不僅是地球表面上一座城市的名字,也不僅是一個時尚熱鬧的都會。它是一個秘密的按鈕,關(guān)乎一個東方青年的情思,按下去,往日的歲月就會重現(xiàn)。
上世紀(jì)70年代,胡曉明還是東方機(jī)床廠一名十七八歲的青工,工廠遠(yuǎn)在貴州都勻市郊劍江河畔。廠里的工人中有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名牌大學(xué)學(xué)生,時代的手,將這些來自北京、上海、重慶、長沙等大城市的文理科大學(xué)生匯聚于此。每個黃昏與周末,他們會在工余聚在單身宿舍敞開的大陽臺上,一邊吃飯喝茶一邊吹風(fēng)乘涼,他們講繪畫和音樂,聊詩歌和戲劇,胡曉明在邊上聽著,猶如接受一次系統(tǒng)的文學(xué)藝術(shù)入門培訓(xùn)。巴爾扎克、莫泊桑、雨果等作家的名字和作品的情節(jié),就這樣漸漸走進(jìn)這個青工的世界。
那些夜晚與漫談,是一粒一粒小小的種子,落到胡曉明心里。雖然受環(huán)境所限,它們沒有立刻生根發(fā)芽,卻蟄伏下來。像一只經(jīng)過果林,背負(fù)了滿身果實的刺猬,胡曉明帶著這些種子讀書、成家、做老師、講學(xué),一直到2007年,他將要去巴黎了。1970年代的種子,原來從未黯淡,它們始終是胡曉明身上的一部分,引領(lǐng)他從貴州來到上海,引領(lǐng)他從門外走入藝術(shù)和美的境地。經(jīng)過想象、揣摩、回憶和感受,這些種子變得越發(fā)鮮明。30多年過去了,胡曉明從青年步入中年,而巴黎始終是巴黎。
巴黎沒有城墻,誰都可以走近,但法語像一座護(hù)城的城墻,將美麗的巴黎藏在其中,不是誰都可以進(jìn)入。法蘭西人對自己文化的這份守護(hù),讓胡曉明愿意零起點(diǎn)開始去學(xué)一門全新的語言。每學(xué)一個詞就是攀爬上一級階梯一塊磚石,每往上升一點(diǎn)高度,就能幫助他翻過一點(diǎn)城墻,好窺到巴黎的內(nèi)核。
所以,在2007年,胡曉明去巴黎不是講學(xué),不是旅游,不是探險,而是印證。印證年少時代的那些夜晚,在貴州的廠房里,在黃昏的晚風(fēng)下,聽大學(xué)生們聊過的那個巴黎,印證那個他心里向往過、描繪過,在匱乏的年代想象過,在富足的年代醞釀過的巴黎。
對這次去巴黎的機(jī)緣,胡曉明說:“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藝術(shù),后來被拋棄的藝術(shù),一下子全都復(fù)活,生命忽然有一個轉(zhuǎn)身,朝著初戀的日子與曾經(jīng)許過的愿,好像是本來一條路走到頭,單調(diào)而重復(fù),忽然有一個重新找路的機(jī)會,丘巒起伏、移步換形、柳暗花明。我忽然覺得成了自己生命可以暫時做主的主人,我也有一個機(jī)緣來將我個人的啟蒙時期沒有來得及寫下的文字,重新寫出,塞納河的歌聲、教堂的鐘聲,搖漾風(fēng)前,就像那些年傳遞鄧麗君歌聲的盒子。雙神咖啡館的香氣,溢滿字里行間。”
在巴黎的一個夏天和一個秋天,胡曉明看到了莫奈,看到了埃菲爾鐵塔,看到了巴黎圣母院,看到了拉雪茲神父公墓……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久別重逢。巴黎對胡曉明來說,是“眼前分明是外來客,心底恰似舊時友”,他貪婪地看了40多座博物館,貪婪地呼吸著雨果呼吸過的巴黎的空氣。他旁征博引寫下《巴黎美學(xué)札記》,不是交出一份游記,而是穿越時光,向少年時代的自己交出一份答卷。
在貴州的蒼穹下,撫摸著書本,青年胡曉明問:“這就是巴黎嗎?”
塞納河的晚風(fēng),欄桿拍遍,人到中年的胡曉明答:“這就是巴黎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