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年》:秋日之光

▲詹姆斯·索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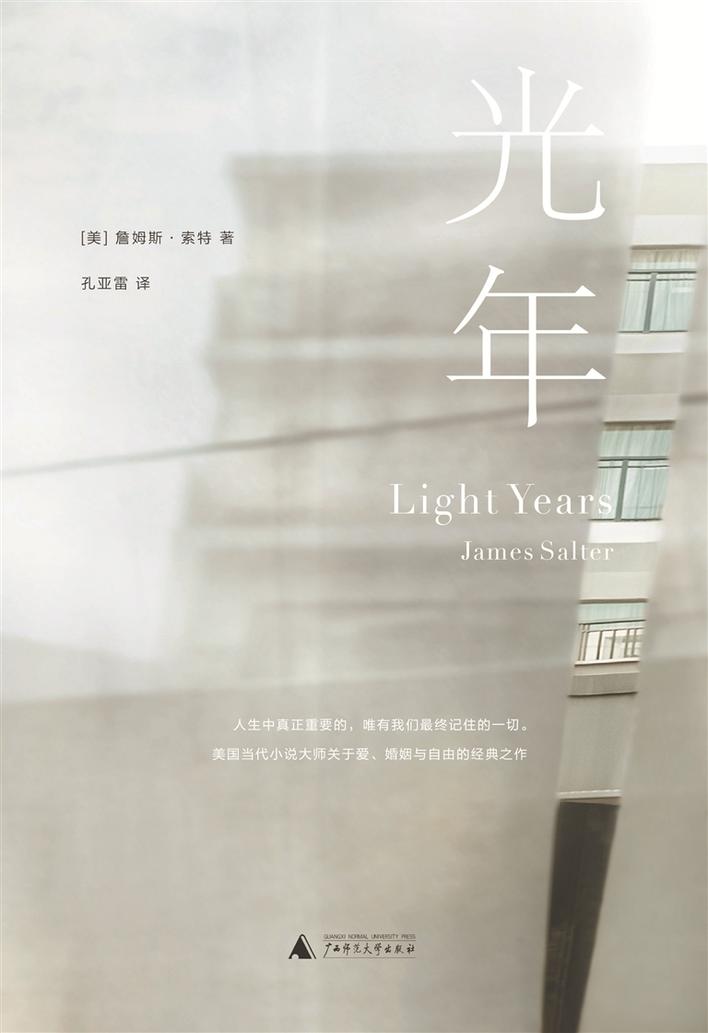
《光年》 (美) 詹姆斯·索特 著 孔亞雷 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8年6月出版
從表面上看,《光年》是一部碎片化的婚姻生活編年史。通過一系列電影化的場景切換,它為我們生動地展現(xiàn)了一對美國中產(chǎn)階級夫婦,維瑞和芮德娜,從1958到1978二十年間的生活切片。它的結構猶如巴洛克音樂,既華麗又清晰:一方面,是繁復而有質(zhì)感,令人愉悅而充實的大量細節(jié)鋪陳;另一方面,就像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這些華美的變奏都源自同一個簡潔的主題。這個主題顯然就是維瑞夫婦。哦不,等等——也許我們應該說芮德娜夫婦?或者,更確切一點,我們也許應該直接說,這個主題就是芮德娜,而且只是芮德娜。正如他們的好友彼得指出的,離婚后的維瑞之所以不快樂,是因為“任何兩個人,當他們分開時,就像劈開一根原木。兩邊不對稱。核心含在其中一邊”。“帶走那神圣核心的是你,”他接著對芮德娜說,“你可以一個人快樂地生活,他不行。”
這就是整部小說的秘密所在。芮德娜。芮德娜不僅是他們婚姻中的神圣核心,也是這部小說的神圣核心。她掌控了整部小說的精神氣質(zhì)。為什么這部以婚姻生活為主要材料的小說卻幾乎沒有任何對婚姻的深刻觀察和見解?(而且這種缺失似乎并不是由于缺乏才能,而是由于缺乏興趣。)為什么時光的流逝在書中顯得如此飄逸,如此冷漠,如此漫不經(jīng)心?因為芮德娜。因為無論是對婚姻還是時間,芮德娜都毫無興趣,也毫不畏懼。
那么,芮德娜對什么感興趣呢?生活。生活這件事本身。“她真正關心的是生活的本質(zhì):食物,床單,衣服。其他的毫無意義;總能應付過去。” 對芮德娜來說,“生活是天氣。生活是食物”。其他的——工作、交際、政治,甚至友誼和愛情——都毫無意義。對芮德娜來說,有意義的是:撫摸小狗柔軟的皮毛;開車進城(“她只在幾個固定的地方購買食物”);在書店里的藝術書籍間流連;野餐;在林間的松木教堂聽音樂會;海(“海浪絲滑”);為女兒們編寫童話;充滿生命力的性愛;松香味的希臘葡萄酒;法國布里奶酪、黃蘋果和木柄餐刀;閱讀馬勒傳記;晚睡晚起(“在床上一直賴到九點,然后醒來,舒展身體,呼吸著新空氣。久睡者通常特立獨行”)……因此,正如我們的恐懼通常與我們的所愛緊密相連,芮德娜最畏懼的,同樣是生活——也就是,不能“如你想象的那樣去生活”。跟女友伊芙逛街時,芮德娜看中了一套昂貴的葡萄酒杯,當伊芙說“你不怕它們打碎嗎”?她的回答是:“我只怕一件事,那就是‘平庸生活’這個詞。”
顯然,這里的“平庸生活”并非指日常生活本身,而是指一種生活態(tài)度。芮德娜所恐懼的(以及她所厭惡和拋棄的),是以庸常而缺乏想象力的方式去對待生活(“如你生活那樣去想象”),是怯懦或麻木地陷于那些平常而庸俗的外在規(guī)則中無法自拔——從而看不見生活本身所蘊涵的奇跡般的美……
但問題是,究竟什么才是生活的本質(zhì)?“食物,床單,衣服”這個回答顯然無法讓人真正滿意。而且我們也必須提防“品位”這個詞——它往往讓人聯(lián)想到虛榮、做作和附庸風雅。(還有什么比“品位”這個詞更沒有品位嗎?)這個詞缺乏力量、反叛和創(chuàng)意。而這些正是芮德娜的特質(zhì)。所以也許更適合她的詞是“風格”。在她極具風格化的世界里,沒有世俗規(guī)則的位置。她有自己的道德和時代,自己的標準和規(guī)則,而簡單地說,那就是竭盡全力,“如你想象的那樣去生活”,去感受生活最深處的本質(zhì),以及隨之而來的意義。于是我們又回到了那個問題:什么是生活的本質(zhì)?隨之而來的意義又是什么?事實上,這也是我們在閱讀《光年》時所面對的問題:什么是這部小說的本質(zhì)?這些連綿不絕、精妙絕倫的場景意義何在?
(本文為《光年》譯后記,有刪節(ji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