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脊背發(fā)涼的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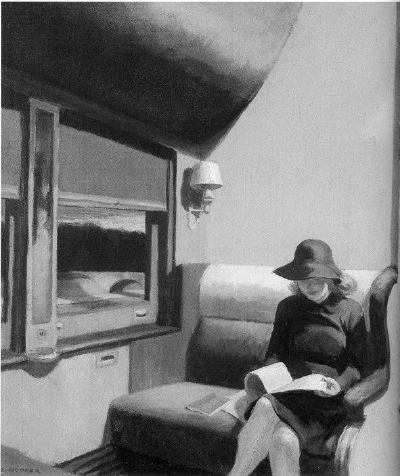
作者的族裔、性別,只是給作品帶來多樣性,而非評價的標準本身。推崇年輕作者,不如給新作者機會,而非讓年齡成為門檻。
一
2011年的4月我還在美國讀書,花了幾個月排演音樂劇。那時我們演的劇是《屋頂上的小提琴手》,一個沙皇時代下猶太家族的故事。最后一次演出結(jié)束后,觀眾散去,劇院變空,我們都舍不得走。演員穿著戲服,布景師一身黑衣,大衛(wèi)之星依然在舞臺上閃耀。沒有人能接受突然的散場,好像所有人都還沉浸在這個有關(guān)傳統(tǒng)、遷移和愛的故事中,難以就此將之丟下,回歸自己本來的身份。
4月份,美國還在下雪。我們沒有離開,在舞臺上坐成一個圈聊天。起先大家講述不舍,后來就把話題轉(zhuǎn)移到了自己的生活軌跡之上。有的人終于要離開這個小城,前往紐約,有的人選擇留下。總之,一個人在講,其他人就在聽,偶爾有人回應(yīng)。
那晚結(jié)束時已經(jīng)是凌晨五點。我們終于散場,各自踏著積雪回家。接下來的一個月里,考試,畢業(yè),懷揣著彼此的故事告別。
多年以后,在閱讀時,在寫作時,這個在雪夜聊天的場景還是會不斷浮現(xiàn)。
“我去年拿到了創(chuàng)意寫作的碩士學位,現(xiàn)在寫超短篇小說。”一次寫作練習開始前,一個女人說。她五十多歲,喜歡莉迪亞·戴維斯。
另外一個男人七十多了,還沒等到出版的機會:“我還在寫。剛?cè)チ艘粋€書展,可以花五百美元見一眼編輯。我去見了,大概有一刻鐘的溝通時間。他們應(yīng)該記不住我……他們看重網(wǎng)上的知名度,我沒有。”
短暫的交談之后,我們開始新的練習。
無論是坐在一起慢慢地說話,還是聚在同一個屋子里練習寫作,想要聆聽和被聆聽的訴求都從未改變。每一天,這個城市都有數(shù)十個寫作和閱讀的活動在等待人們加入。不斷有新的工作坊、新的課程、新的協(xié)會,即使是不知名的寫作者也不會過于孤獨。有人以筆名寫暢銷的愛情小說,再用真名出版賣不動的嚴肅文學;有人靠每天在社交媒體上發(fā)一張寫著幾行詩的圖片獲得關(guān)注;有人自己印刷,或者僅僅做成電子書,零成本地放在亞馬遜上售賣;也有人一生都沒有正式發(fā)表的機會。
二
如果只是想要被聽見,或是去聽不同的聲音,現(xiàn)在已經(jīng)比過去要容易許多。1983年,《格蘭塔》第一次公布20位英國最佳青年小說家名單,編輯比爾·布福德在采訪中說:“相信我,它能證明自己。我知道我在說什么。這些年輕作家是文學的未來。歷史將證明我的話。”他沒有說錯,伊恩·麥克尤恩、石黑一雄、朱利安·巴恩斯都在這個名單之上,而后每隔十年,都會有這樣一批年輕的、不同族裔的聲音出現(xiàn)。2017年的美國最佳青年小說家名單中,不少是少數(shù)族裔,女性作家的數(shù)量也多于男性。多樣性,這個《格蘭塔》用以打破既定標準的武器,已經(jīng)成為了標準之一。
這樣的名單越來越多,年齡、階級、性別、族裔所帶來的阻礙,似乎正在消融。平時去看國外文學界的發(fā)展,寫書評,做諾獎、龔古爾文學獎、T.S.艾略特獎的報道,又去翻海外文學期刊,看看新書的評論。在鋪天蓋地的訊息中,總能感受到,多樣性的確是海外評獎和評論的出發(fā)點之一——多樣的主題、多樣的架構(gòu)、多樣的作者。
如今作為譯者,對于海外小說的接觸又多了一點。在翻譯《紐約客》《巴黎評論》等雜志的短篇小說時,我感受到的是另一種寫作方式。這些小說大都是實驗性的、超現(xiàn)實主義的。作品中的敘事聲音、時間和空間、現(xiàn)實和虛幻,都處于轉(zhuǎn)換之中,而在陌生的結(jié)構(gòu)之下,又是陌生的內(nèi)容——來自內(nèi)布拉斯加鄉(xiāng)下的男孩,反復陷入自我身份認同的危機;從戰(zhàn)場上休假歸來的士兵,被創(chuàng)傷徹底摧毀。還有沉溺于游戲與幻想中的少年、自卑又自矜的年輕棒球手、得了臉盲癥的男孩——小說來自完全不同的文化環(huán)境,對于譯者和讀者來說都是挑戰(zhàn),翻譯的過程,也成為了一種文本細讀。
作為小說作者,我時常會因為翻譯時遇到的差異而自我質(zhì)疑:相比之下,自己的作品是不是缺少結(jié)構(gòu)和內(nèi)容上的突破?小說作者是否有責任更新讀者的閱讀體驗?想到去年參加某個小說獎的頒獎典禮,看了其他獲獎作者的作品,讓我感到有趣的恰恰是這種反差:獲獎的作者年紀不算大,但基本都選擇了傳統(tǒng)的敘事方式,以情節(jié)來支撐起整部作品;翻譯的作家已經(jīng)步入中年,在海外有所成就,卻還在挑戰(zhàn)實驗性的寫作。
我時常會想,不同的敘事手法,不同的小說結(jié)構(gòu)之間,是否有高低之分?而評論者,又是否應(yīng)該以此評判作品的好壞?
在這之外,還有其他困惑。4月中旬,我去聽了巴基斯坦裔作家莫欣·哈米德的講座。第一次看他的作品是在《格蘭塔》上,那一期的主題是旅途。他寫道:“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都是移民,正是遷移的經(jīng)歷連接起所有人類。每時每刻,人類的經(jīng)歷都在不斷變幻,我們的一生就在不同的時空中度過。”
另一個讓人迷惑之處在于,莫欣·哈米德沒有入選2013年的英國最佳青年小說家名單,他那年已經(jīng)41歲,超出了40歲的年齡限制。時任《格蘭塔》主編專門提到他,表達了遺憾。僅僅差一歲,就被“青年”的門檻所擋住了嗎?到底是鼓勵新的聲音,還是只鼓勵年輕的聲音?年輕的新人得到了贊頌,但那些年長的聲音呢,他們還值得被關(guān)注嗎?那些五十歲才開始上創(chuàng)意寫作課程的人、退休后開始參加寫作小組的人、幾乎被社交媒體時代丟下的人。
更多的問題也開始出現(xiàn):年輕的作者就寫得更好嗎?其他種族、文化的聲音更值得去傾聽嗎?
這些問題不斷出現(xiàn)。幾年來我給不同的媒體寫評論,寫略薩和劉易斯·卡羅爾,寫石黑一雄和希拉里·曼特爾,但還是沒有找到一個回答。只是有時,在寫作之前,依然能想起第一次文本細讀的經(jīng)歷:我們在美國的課上,學著分析馬克·吐溫如何在文本中運用口語和幽默,如何將南方的語言、黑人的語言等七種方言糅合在一起,再加上僅屬于男孩子的口語,呈現(xiàn)出一種混亂的生機。我們討論為什么海明威那么推崇馬克·吐溫的語言,為什么說美國現(xiàn)代文學來自《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還有馬克·吐溫對現(xiàn)實主義所產(chǎn)生的影響,書里的種種主題。這些討論最終變成一篇篇論文,幾次遷移之后,它們終歸還是丟失了。而如今,提到 《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時,已經(jīng)很難記得大段的分析,只能看見這樣的畫面:大河在樹叢間奔騰,哈克貝利順河而下,自由、孤獨,又常常因為想到死亡而感到悲涼。
三
雷蒙德·卡佛在 《關(guān)于寫作》中寫道:“在寫詩或者短篇小說中,有可能使用平常然而準確的語言來描寫平常的事物,賦予那些事物,一張椅子,一面窗簾,一把叉子,一塊石頭,一個女人的耳環(huán),以很強甚至驚人的感染力。也有可能用一段似乎平淡無奇的對話,卻讓讀者讀得脊背發(fā)涼,這是藝術(shù)享受之源,就像納博科夫能夠做到的。我最感興趣的,就是那種寫作。我最討厭拖泥帶水或者隨隨便便的那種,無論它是打著實驗的旗號,或者只是手法笨拙的現(xiàn)實主義。”因此也總是盡量提醒自己:評論讓人脊背發(fā)涼的作品,分析它們?yōu)槭裁茨艽騽尤恕?/p>
前幾年在愛丁堡國際藝術(shù)節(jié)開幕式上,看見丁尼生的詩出現(xiàn)在死火山花崗巖和愛丁堡城堡之上,也讓人脊背發(fā)涼。評判詩歌的標準一并消失,只剩下震懾和感動。
像埃茲拉·龐德說的那樣,不折不扣地準確陳述,是對寫作唯一的道德要求。這不僅適用于創(chuàng)作,對于評論者來說,準確陳述自己閱讀時的感受,比運用哪一套理論都更為重要。不是因為可以展現(xiàn)自己所知,不是因為作者跟自己在同一陣營,不是因為某種文化,某種概念。它打動你,激怒你,這就足夠了,贊美或是批判,都是因為在閱讀時真實地產(chǎn)生了感受,不是其他。
作者的族裔、性別,只是給作品帶來多樣性,而非評價的標準本身。推崇年輕作者,不如給新作者機會,而非讓年齡成為門檻。至于傳統(tǒng)或者實驗,我相信《印刻文學生活志》里的這樣一段話:“書寫小說,字里行間的技巧經(jīng)營,包括形式、人物、語言、情節(jié)、故事的塑造,皆屬表象的、邏輯的,展現(xiàn)‘非日常生活的心’。作者希望我們讀取的‘內(nèi)容’,必定是小說角色的日常生活里頭,被隱蔽被壓抑的‘心意’,另外一個與作者截然不同的‘自我’。大可以認定,挖掘出來,重見天日的‘心意’越豐富,無疑代表著小說越成功。”
而回到寫作,它本來就是一種聆聽和被聆聽的過程,一種療愈的過程。我更愿意將之理解為以前一起聊天的雪夜,每個人說著各自的故事、想法和感受,聆聽者不會去拿一套標準來衡量這些話語,只是在彼此的故事中看到另一種人生,然后去回應(yī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