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的批評(píng)及其理論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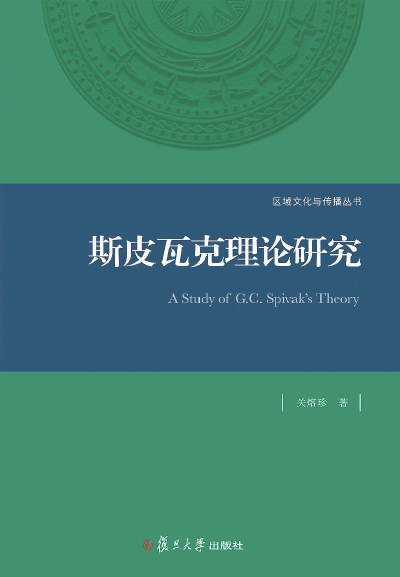
《斯皮瓦克理論研究》關(guān)熔珍 著 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
在當(dāng)今的西方后殖民主義理論思潮及女權(quán)主義運(yùn)動(dòng)中,斯皮瓦克的名字一直十分引人矚目,隨著2003年賽義德的去世,斯皮瓦克成了后殖民理論批評(píng)當(dāng)之無(wú)愧的最杰出的代表。再加之她本人既是一位多產(chǎn)的理論家和比較文學(xué)學(xué)者,同時(shí)也十分關(guān)注翻譯問(wèn)題,發(fā)表了大量的批評(píng)性文字和譯著,在整個(gè)文學(xué)理論界、比較文學(xué)界和翻譯學(xué)界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因而,對(duì)她的批評(píng)理論進(jìn)行研究,不僅在英語(yǔ)文學(xué)理論界和她的祖國(guó)印度的比較文學(xué)界是一個(gè)重要的課題,而且近20年來(lái)也開始引起了中國(guó)學(xué)者的關(guān)注。
佳亞特里·斯皮瓦克1942年2月出生在印度加爾各答的一個(gè)知識(shí)分子家庭。大學(xué)畢業(yè)后來(lái)到美國(guó),進(jìn)入了康奈爾大學(xué),1962年獲得英文碩士學(xué)位,后于1967年獲得比較文學(xué)博士學(xué)位,導(dǎo)師就是當(dāng)時(shí)大名鼎鼎的耶魯大學(xué)教授保羅·德曼,他是著名的浪漫主義文學(xué)研究權(quán)威,解構(gòu)主義批評(píng)在美國(guó)的最杰出代表和旗幟性人物。斯皮瓦克也和許多從第三世界來(lái)到第一世界留學(xué)的莘莘學(xué)子一樣,獲得博士學(xué)位后沒有回到印度,而選擇了在美國(guó)發(fā)展自己的學(xué)術(shù),而且成了少有的成功者之一。她先后在美國(guó)多所大學(xué)任教,自1991年以來(lái),一直執(zhí)教于哥倫比亞大學(xué)。2008年以來(lái),她又接替賽義德的空缺,擔(dān)任了哥倫比亞大學(xué)的校級(jí)講席教授。每每和她談到這一點(diǎn),她都感到由衷的自豪:她不僅是整個(gè)哥倫比亞大學(xué)有史以來(lái)獲此殊榮的唯一一位女性,而且也是其中的唯一一位亞裔學(xué)者。斯皮瓦克著述甚豐,不僅在英語(yǔ)世界影響很大,在中國(guó)也一直有著持續(xù)的影響。在中文的語(yǔ)境下經(jīng)常為學(xué)界討論和引證的就有這樣幾部最有代表性的著譯:《在他者的世界:文化政治論集》(1987)、《外在于教學(xué)機(jī)器之內(nèi)》(1993)、《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行將消解的當(dāng)下歷史》(1999)、《一門學(xué)科的死亡 》(2003)、德 里達(dá) 《論文字學(xué)》英譯等。
在三位最重要的后殖民理論家中(另兩位是霍米·巴巴和薩義德),斯皮瓦克是唯一的一位女性,同時(shí)也是唯一的專注形而上思考的思想家和理論家,但這也并非意味著她就不關(guān)心反抗殖民主義斗爭(zhēng)的實(shí)踐。她對(duì)印度“底層研究”小組的介入之深是任何一位印度的后殖民理論家都無(wú)法比擬的,因此她并不喜歡人們稱她為“后殖民理論家”,而寧愿被稱為“底層研究者”,因?yàn)樗_實(shí)也是這三位理論家中最為直接地投身殖民主義/后殖民主義歷史和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研究的一位學(xué)者和社會(huì)活動(dòng)家。我早就聽到學(xué)界有人作過(guò)這樣的比較,閱讀斯皮瓦克的著作,假如不知道她的性別,我們很可能將其混同于一位男性思想家,因?yàn)榫科渌伎嫉男味咸卣骱屠碚撏蒲莸某橄笮裕约帮L(fēng)格的雄辯性,她堪與德里達(dá)相比美。但德里達(dá)本人很少?gòu)氖戮唧w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實(shí)踐,他對(duì)文學(xué)的閱讀和闡釋,大都將其作為演繹自己的哲學(xué)理論的文本材料,他所處的位置是哲學(xué)和文學(xué)之間,而且是從哲學(xué)走向文學(xué)乃至整個(gè)人文學(xué)科的。而斯皮瓦克則首先是一個(gè)文學(xué)研究者,十分關(guān)注對(duì)文學(xué)文本的批評(píng)性閱讀,而且她的閱讀和批評(píng)視角也具有鮮明的第三世界特征。可以說(shuō),她的學(xué)術(shù)生涯與德里達(dá)的恰好相反,她是從文學(xué)走向歷史和哲學(xué)乃至整個(gè)人文學(xué)科的。在當(dāng)今的北美乃至整個(gè)西方文學(xué)和文化批評(píng)理論界中,斯皮瓦克的批評(píng)和學(xué)術(shù)生涯是相當(dāng)有代表性的,同時(shí)也自然而然成了來(lái)自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批評(píng)家們興趣的中心和爭(zhēng)論的話題。這種現(xiàn)象的存在實(shí)際上正好實(shí)現(xiàn)了以斯皮瓦克等人為代表的有著第三世界血統(tǒng)和民族文化身份、同時(shí)又有著第一世界的深厚文化修養(yǎng)和良好教育背景的后殖民批評(píng)家的這一嘗試:從邊緣向中心運(yùn)動(dòng),通過(guò)對(duì)中心的消解而達(dá)到消除舊的中心和重建新的中心之目的。這就是為什么當(dāng)后殖民理論一經(jīng)被推上后現(xiàn)代主義大潮衰落之后的學(xué)術(shù)理論前沿,就立即受到了來(lái)自第一世界 (前殖民地宗主國(guó))和第三世界(后殖民地)批評(píng)家的激烈批評(píng)的原因所在。一些對(duì)后殖民理論批評(píng)抱有偏見的白人學(xué)者甚至斷言,所謂后殖民主義不過(guò)是幾個(gè)印度裔學(xué)者自己“炒作”出來(lái)的,維持不了多久就會(huì)自然消退。但事情果真如此簡(jiǎn)單嗎?恐怕并不盡然。至少我們讀完關(guān)熔珍的這本專著后多少會(huì)改變這一看法。就目前的研究以及后殖民理論批評(píng)本身的現(xiàn)狀來(lái)看,對(duì)后殖民主義理論思潮的研究遠(yuǎn)未達(dá)到深入的地步,而在中文的語(yǔ)境下,對(duì)后殖民理論的研究可以說(shuō)才剛剛開始。隨著全球化時(shí)代以來(lái)更多后殖民理論著作中譯本以及中國(guó)學(xué)者的著作的出版,圍繞它的爭(zhēng)論將結(jié)合第三世界國(guó)家的一些實(shí)際問(wèn)題而進(jìn)一步展開,因而現(xiàn)在就武斷地對(duì)之進(jìn)行價(jià)值判斷顯然是不合時(shí)宜的。
關(guān)熔珍這部專著的出版不僅對(duì)國(guó)內(nèi)的斯皮瓦克及后殖民研究起到一定的推進(jìn)作用,而且她基于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立場(chǎng)提出的一些新觀點(diǎn)也可以與國(guó)際同行進(jìn)行對(duì)話和討論。本書的出版或許可以成為中國(guó)學(xué)者介入到國(guó)際性的理論爭(zhēng)鳴和討論中,從而改變中國(guó)學(xué)者在國(guó)際學(xué)界的“失語(yǔ)”狀況的一個(gè)契機(jī)。
我和斯皮瓦克在相識(shí)之前就神交已久,我們于2005年在弗吉尼亞大學(xué)舉行的 《新文學(xué)史》雜志研討會(huì)上一見如故,并由此成了長(zhǎng)期的摯友。當(dāng)斯皮瓦克得知我下半年要去她曾經(jīng)作過(guò)“底層人能發(fā)言嗎?”的著名演講的伊利諾伊大學(xué)講學(xué)半年時(shí),立即邀請(qǐng)我前往哥倫比亞大學(xué)演講,也就是在那次重訪哥大期間,我得知斯皮瓦克自本世紀(jì)初以來(lái)一直堅(jiān)持學(xué)習(xí)中文,現(xiàn)在她不僅能夠進(jìn)行簡(jiǎn)單的口頭交流,而且在閱讀方面也沒有什么問(wèn)題。2007年,我應(yīng)邀在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xué)從事研究半年,期間斯皮瓦克再度邀請(qǐng)我前往哥大演講,并邀請(qǐng)了我們共同的朋友戴維·戴姆拉什為我的演講作介紹。就在那以后,我逐步進(jìn)入世界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2006年和2015年,我也曾兩次邀請(qǐng)斯皮瓦克到北京和廣州講學(xué),她都十分爽快地應(yīng)允。有鑒于此,我期待著學(xué)界對(duì)關(guān)熔珍這部《斯皮瓦克理論研究》的反應(yīng),同時(shí)也期待著斯皮瓦克本人對(duì)這部中文學(xué)界的研究專著的反應(yī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