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dāng)中國當(dāng)代詩歌進(jìn)入拉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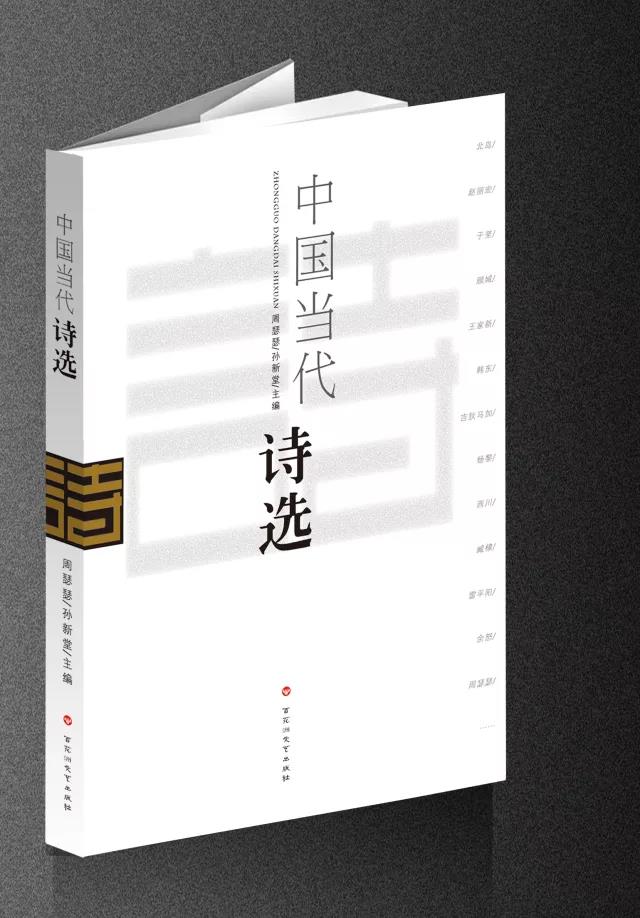
中國新詩走過了100年歷程,當(dāng)代詩歌40年來取得了較高成就,中國詩人受邀參加國際詩歌節(jié),進(jìn)行廣泛的國際詩歌交流。拉丁美洲有著深厚的詩歌傳統(tǒng),但目前對中國當(dāng)代詩歌還缺乏了解,認(rèn)知不足。近年來中國詩人在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城國際詩歌節(jié)、麥德林國際詩歌節(jié)、羅莎里奧國際詩歌節(jié)、格拉納達(dá)國際詩歌節(jié)、哥斯達(dá)黎加國際詩歌節(jié)上受到關(guān)注,哥倫比亞《普羅米修斯》、墨西哥《詩歌報》、阿根廷《當(dāng)代》等詩歌雜志連續(xù)刊登中國詩人的作品,古巴、墨西哥、哥倫比亞、智利、阿根廷等國的出版社開始對中國當(dāng)代詩歌產(chǎn)生興趣。
近日出版的《中國當(dāng)代詩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8年4月)將與拉丁美洲國家的出版社合作出版(智利普雷門特出版社、古巴南方出版社即將推出西班牙語版),對于中國當(dāng)代詩歌在拉丁美洲的閱讀、接受和傳播具有開拓性意義。該書收入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當(dāng)代詩人及近年參加拉美國際詩歌活動的多位詩人,共43位,涵蓋了從朦朧詩、第三代詩歌到1990年代以來的知識分子寫作、民間口語寫作,以及“80后”“90后”“00后”等年輕詩人的寫作,呈現(xiàn)出中國當(dāng)代詩歌的生命意識與日常經(jīng)驗(yàn),語言實(shí)驗(yàn)與先鋒精神。
對于詩歌來說先鋒是一種常態(tài),但在當(dāng)代詩歌里又確實(shí)稀有。什么是先鋒呢?是從中國當(dāng)代詩歌的整體格局里跳出,寫出帶有個人語感與節(jié)奏的詩歌,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寫作內(nèi)容與姿態(tài)上的先鋒。中國當(dāng)代詩人在中國寫作,看到的是世界各個角落,詩人四處走動,獲得更多的思考。我在2017年到了拉美,在兩個不同的文學(xué)世界里思考,一是中國的,一是拉美的,中國的本土經(jīng)驗(yàn)我已經(jīng)爛熟于心,拉美的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我早已從上世紀(jì)80年代就開始進(jìn)入,但畢竟是通過翻譯獲得的。而當(dāng)我在他們中間的那些日夜,不同語言的朗誦與豐富多彩的拉美文化,令我感到先鋒文學(xué)的傳統(tǒng)無所不在。
我邊走邊寫,留下了六七十首詩,結(jié)集為《從馬爾克斯到聶魯達(dá)》,我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的馬爾克斯文化中心感受到拉美文學(xué)大爆炸的氣息。在詩歌之城麥德林,我意識到這是詩歌的狂歡之地,麥德林國際詩歌節(jié)開幕式持續(xù)到天黑,世界60多個國家的詩人聚集在一起還不是什么奇跡,奇跡是城市中孩子、青年和老人都涌向詩歌朗誦現(xiàn)場。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的孔子學(xué)院拉美中心、聶魯達(dá)基金會,以及奇廉市圣托馬斯大學(xué)組織的朗誦會上,我感受到拉美的詩歌文化。拉美的詩歌文化并不只是聶魯達(dá)、米斯特拉爾、帕斯、巴列霍、卡彭鐵爾、富恩特斯、科塔薩、穆尼蒂斯,還有胡安·赫爾曼、馬加里托·奎亞爾等當(dāng)代詩人,以及拉美民眾對于詩歌的熱愛,這或許與他們血液里與生俱來的性格有關(guān),我想更多的是他們對于詩歌與生活、與世界的緊密關(guān)系的認(rèn)同。回國后,我陸續(xù)讀到了翻譯家孫新堂翻譯的馬加里托·奎亞爾的作品,他寫的是中國云南之行,我很高興我與他無意間形成了一個詩歌寫作的互動。
拉美另一個詩歌文化高峰則是對傳統(tǒng)先鋒的反叛,今年初離世的智利詩人帕拉的“反詩歌”寫作主張,在當(dāng)代詩歌寫作中并不陌生。帕拉創(chuàng)作手法簡潔,反對隱喻象征,語言上更趨口語化、散文化,與中國當(dāng)代詩歌的口語化寫作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中國廣受贊譽(yù)的智利小說家、詩人羅貝托·波拉尼奧更是視其為偶像。波拉尼奧曾說“我讀自己寫的詩時比較不會臉紅”。對于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發(fā)起“現(xiàn)實(shí)以下主義”詩歌運(yùn)動的波拉尼奧評價說:“很糟糕。”這是另一種不斷否定與更新的拉美先鋒詩歌文化。
在編選《中國當(dāng)代詩選》時,我腦子里不時蹦出在圣地亞哥聶魯達(dá)基金會上三位曾獲得聶魯達(dá)詩歌獎的詩人形象,胡須雪白如安第斯山脈的雪,他們特意朗誦了口語化的詩歌,通過現(xiàn)場翻譯,我對他們詩歌的節(jié)奏與短促的語氣充滿興趣。中國當(dāng)代詩歌進(jìn)入拉美時遇到的首先是他們的閱讀與評判。拉美詩人、讀者迫切想聽到中國詩歌的聲音,我們在帕拉的故鄉(xiāng)奇廉市朗誦時,92歲的智利詩人、智利語言文學(xué)院院士雷內(nèi)·伊巴卡切一直在現(xiàn)場,他說通過中國年輕詩人的語氣和朗讀感受到了中國詩歌。
我在讀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的《火的記憶》時,想到我們的現(xiàn)代性之路與拉美的道路有相似的地方,只是歷史的出發(fā)點(diǎn)與出發(fā)的時間不同,我們面對的精神危機(jī)與出路并沒有本質(zhì)的不同,也就是說我們要處理的是同樣孤獨(dú)的文學(xué)題材。我在圣地亞哥與當(dāng)?shù)匾晃辉?jīng)在亞馬遜叢林中生活、現(xiàn)在像一頭困獸一樣的作家交談,他面對中國詩人時發(fā)出感慨:“我們已經(jīng)失敗”。我隨后以一首詩寫到他復(fù)雜的情感:“我站在胡安先生家的高窗邊/看到圣地亞哥在夜色里燈火輝煌/這一夜胡安先生傷感地承認(rèn)/他們是失敗者/而我呢/我的失敗才剛剛開始”。我覺得我們不必掩蓋失敗。只有意識到失敗,才能從被異化的現(xiàn)實(shí)中獲得真實(shí)的自我,重塑歷史,重塑身份,從而進(jìn)行自我啟蒙。加萊亞諾直接告訴讀者:“寫作是我擊打和擁抱的方式”,立場之外,不發(fā)表中立或假裝中立的言論,歷史之內(nèi),為一直排在歷史隊(duì)尾的人寫作。當(dāng)我踏上拉美的土地,置身于《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的背景中時,我深感我們的反思還遠(yuǎn)遠(yuǎn)不夠。
當(dāng)103歲的帕拉逝世時,時任智利總統(tǒng)米歇爾·巴切萊特在第一時間表達(dá)哀悼:“西方文化失去了一個獨(dú)特的聲音。”我們“獨(dú)特的聲音”在哪里呢?必須在我們的詩里。

周瑟瑟,男,當(dāng)代著名詩人、小說家、書畫家和紀(jì)錄片導(dǎo)演。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現(xiàn)居北京。著有詩集《松樹下》《暴雨將至》等,長篇小說《曖昧大街》《蘋果》《中關(guān)村的烏鴉》等。作品被譯成英、法、西班牙、蒙古、韓等多種文字。曾獲得2009年中國最有影響力十大詩人、2014年國際最佳詩人、2015年中國杰出詩人、第五屆中國桂冠詩歌獎(2016)等榮譽(yù)。主編《卡丘》詩刊,編選有《新世紀(jì)中國詩選》《那些年我們讀過的詩》《讀首好詩,再和孩子說晚安》《中國詩歌排行榜》等多部詩選。應(yīng)邀參加第27屆哥倫比亞麥德林國際詩歌節(jié)、孔子學(xué)院拉丁美洲中心“中國作家講壇”。

孫新堂,男,孔子學(xué)院拉丁美洲中心(智利圣地亞哥)執(zhí)行主任,北京語言大學(xué)教師。著有西班牙語教材多種,中文譯有西班牙、智利、阿根廷作家和詩人的作品,西班牙文譯有十多位中國作家和詩人的作品。主編“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精品”西班牙語翻譯工程,兼任《人民文學(xué)》雜志西班牙文版《Farolas》(路燈)翻譯總監(jiān)。2013年在拉丁美洲創(chuàng)辦“中國作家講壇”,持續(xù)推動中國和拉美的文學(xué)交流與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