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荒僻處,隱藏著600年前的精美壁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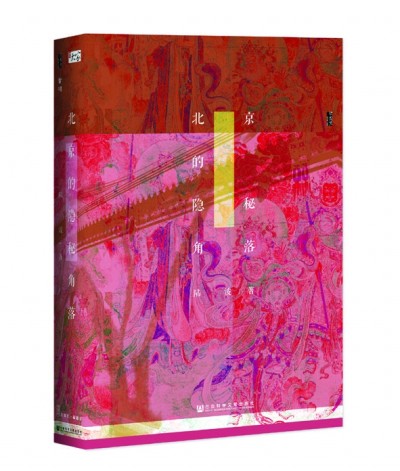
《北京的隱秘角落》陸波著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出版

北京法海寺明代壁畫是中國古代繪畫藝術(shù)史上的奇跡。
作為多個(gè)朝代的都城,北京留存下來很多古跡,但也有一些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在歷史變遷中消失了,只留下一個(gè)名字。
作為生于斯長于斯的北京人,作家陸波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尋定慧寺、宜蕓館、藍(lán)靛廠、保福寺、櫻桃溝等“北京隱秘角落”的歷史足跡,考察那里的文物遺存,講述那些在歷史上留下或深或淺印記的人們的故事,試圖將大時(shí)代與小事件勾連起來。
2016年12月,藏有明朝壁畫的法海寺經(jīng)過整修重新開放。這是一條普通的消息,但“明朝壁畫”確實(shí)是無與倫比,跨越近600年時(shí)空再次驚艷世人。我不知如何形容我們的幸運(yùn),至少,我們比乾隆皇帝幸運(yùn)。
乾隆對藝術(shù)珍品的癡迷是以實(shí)際據(jù)為己有著稱的。但在其長達(dá)89年的人生里,他并不知道一處有著絢麗明朝壁畫的地方,幽幽地遙視京城,隱身于世間。
西方女士對東方壁畫的重大發(fā)現(xiàn)
法海寺在京西石景山模式口,即使當(dāng)下京城已經(jīng)膨脹到如多層巨無霸大漢堡的程度了,這里還是顯得有些荒僻。公交車只到達(dá)離這里還有兩三公里的地方,來尋訪的人們需要邁開腿再朝翠微山走上一段距離,才能找到這間坐落半山的不算大的寺院。據(jù)說,平常日子來參觀的全天也就二三十人,周末好點(diǎn),能有五六十人。即使這般可憐數(shù)字,來訪的人們基本上也只是奔著一個(gè)目標(biāo)——瞻仰那驚世駭俗的明朝壁畫,或者說是15世紀(jì)中期的漢地寺院壁畫。
20世紀(jì)30年代,先后有兩位西方女士造訪此地。第一位是1933年來自德國的24歲年輕姑娘赫達(dá)·哈默,她有著天生的好奇心和冒險(xiǎn)精神,剛到北京熱血甫定,就打聽怎么去法海寺。她進(jìn)入寺院后發(fā)現(xiàn)大殿里有大幅明代壁畫,激動(dòng)不已。年輕的她不可能清楚這些壁畫的價(jià)值,只是覺得有趣,并記錄道:
最有意思的寺廟是法海寺,這是一座不大而頗具景致的寺廟,它以保存完好的明代壁畫而受人關(guān)注,壁畫在大殿的墻上,永遠(yuǎn)位于陰暗處,處于非常好的保存狀態(tài),要描繪它須將屋瓦挪開,才有一個(gè)好光線。
于是,魯莽的她為了制造好光線拍下大殿里的情形,竟然拆了小汽車?yán)龋美锩娴南鹌で蚯o對著點(diǎn)燃的副醛燃料吹鎂粉,試圖造出鎂光的巨大光亮,幫助她拍出清楚的壁畫。結(jié)果此舉引發(fā)了一次小型爆炸,非但沒能成功拍照,還把自己灼傷險(xiǎn)些毀容。她只是收獲了一些勉強(qiáng)可見的羅漢雕塑的照片,壁畫拍攝并不成功。
4年后,英國女士安吉拉·萊瑟姆也尋到法海寺,這次她不但成功地將壁畫、雕塑等拍攝下來,還寫了一篇游記發(fā)給當(dāng)時(shí)的《倫敦新聞》畫報(bào)。她的文字透著女性的細(xì)膩與感性:
在遼闊的華北平原上,有一座造型極其優(yōu)美的佛教寺廟……有一位剃了光頭的年輕人將我們迎入了一個(gè)寺廟庭院之中,并沿著石階往上走,來到第二個(gè)庭院,那兒有和尚在拆除為牡丹花穿上的越冬稻草衣。這就是法海寺。
“第二個(gè)庭院”即主殿之前的庭院,自然他們進(jìn)去是找壁畫的。當(dāng)然,她比赫達(dá)·哈默更具有安全意識,她很聰明地用一面大鏡子把室外燦爛的陽光折射進(jìn)大殿,拍下了一批質(zhì)量尚可的照片。她還寫道:
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無聞的壁畫堪稱世界上最偉大的繪畫作品之一!我敢說自己從未見過其他任何繪畫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風(fēng)格。
她這篇圖文并茂的報(bào)道在西方世界引發(fā)巨大轟動(dòng),這畢竟是對15世紀(jì)中葉東方壁畫藝術(shù)的一次重大發(fā)現(xiàn),在相當(dāng)長的一段時(shí)間里,法海寺以其明朝壁畫藝術(shù)在西方反而比在中國更出名。
明朝太監(jiān)造法海寺,留下藝術(shù)奇跡
今天,每日去法海寺的那三五十人就是專程去看壁畫的,他們被某種小眾而高雅的風(fēng)聞所染,探奇或者附庸各有其好,因?yàn)榉êK卤诋嬅麣獯螅凰囆g(shù)史學(xué)家歸類于中國古代三大壁畫藝術(shù)瑰寶之一,另兩個(gè)為敦煌壁畫、永樂宮壁畫。一個(gè)貌不驚人的小小寺院以藝術(shù)價(jià)值聞名,這反而奪其宗教光芒,讓人們忽略了其實(shí)這原本是一間皇帝賜額、太監(jiān)牽頭修建的佛教寺院。如果寺院最初的興建者——?dú)v經(jīng)四朝的太監(jiān)李童——知道會(huì)有今天這么個(gè)奇怪的結(jié)局,他會(huì)想辦法把自己也繪到壁畫上,哪怕躲在一個(gè)角落里。事實(shí)上,他在原大殿雕塑的十八羅漢群里加上了自己。這在赫達(dá)·哈默及安吉拉·萊瑟姆的照片里都有體現(xiàn),所謂十八羅漢實(shí)則只有16個(gè),剩下兩個(gè)一個(gè)是大黑天神,另一個(gè)就是李童自己,他倆都不是羅漢。可惜后來這18尊雕塑都被砸爛,那位多少有些留戀人世并顧影自憐的太監(jiān)李童沒有留下最后的樣子。
明英宗正統(tǒng)四年(1439),50歲的太監(jiān)李童整合了他可以整合的各種資源,傾盡其為四朝皇帝服務(wù)所得的賞賜,并多方募集,要建一座寺院。首先,他以內(nèi)廷重要太監(jiān)的身份說服年輕的英宗,英宗當(dāng)時(shí)只有12歲,已是“三楊輔政”后期,“三楊”老臣死的死老的老,他身邊的太監(jiān)王振開始得勢,這給老太監(jiān)李童行了方便。李童說他承蒙四朝皇恩,只有建一所寺院以修佛薦福才能報(bào)恩。他向英宗敘述了一個(gè)比較俗套的故事,說他有一天睡夢中來到一個(gè)“巖壑深邃,林木茂美”的深山之處,遇到某白衣仙人,仙人指示說“此精藍(lán)地也,他無以過此者”,意即這里最適合建一所寺廟了。李童驚異,拿捏不準(zhǔn),畫了張草圖便差人在京城周邊有山林的地方四處踅摸。結(jié)果差人到了玉河鄉(xiāng)水峪,發(fā)現(xiàn)四周景致與草圖一致,問當(dāng)?shù)厝擞泻喂袍E,當(dāng)?shù)厝苏f這里有一座叫龍泉寺的廢寺。李童恍然大悟,認(rèn)定這就是神仙托夢讓他修建佛寺的地方。于是李童拿出全部資財(cái),并動(dòng)員善眾、僧侶一起發(fā)力建設(shè),還找來“諸良工”(即宮廷繪畫師等)各類能工巧匠,歷時(shí)4年,終于將寺院建成一座比較標(biāo)準(zhǔn)的“伽藍(lán)七堂式”漢地寺院。直至今天,這個(gè)規(guī)模基本保持不變。
李童向年輕的英宗講述了建寺緣起,對于只有12歲的年輕的英宗皇帝而言,李童還是有些資本的,當(dāng)年他“儀度不凡,端莊祥和”,年紀(jì)小小便被成祖朱棣留在身邊侍候,時(shí)刻不離左右,甚至朱棣北征蒙古人,他也披盔戴甲跟隨出征。朱棣死于北征回師途中的榆木川(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烏珠穆沁),秘不發(fā)喪,太監(jiān)李童便是護(hù)衛(wèi)朱棣遺體回京的親隨之一。繼之仁宗、宣宗朝代,李童始終被皇帝信任并被委以重任,宣宗出征喜峰口討敵,李童同樣跟隨御駕,回來便升職并得到厚賞。有能力承建寺院,是明清兩朝一個(gè)太監(jiān)的權(quán)勢和成功的標(biāo)志。
英宗給寺院的賜額是“法海寺”,比喻佛法深廣如海。李童不光自己傾盡身家,同時(shí)動(dòng)員同好。其一,他請求當(dāng)時(shí)有著崇高宗教地位的藏傳佛教領(lǐng)袖前來助緣。其二,李童請來了當(dāng)時(shí)中國最優(yōu)秀的藝術(shù)家——宮廷畫師們,這些人來自南方寧波一帶,他們秉承了宋朝以來的“院體畫風(fēng)”,并把他們卓越的藝術(shù)天賦奉獻(xiàn)給了這座寺院的壁畫繪制。其三,他說服了當(dāng)朝德高望重的老文臣,均為進(jìn)士出身的胡濙、王直為寺院撰寫碑文,這兩位被后人稱為“清德正學(xué)”的賢臣。他們都是四朝侍明的老人,彼此熟悉且關(guān)系良好。在修建法海寺的時(shí)候,這些氣味比較相投的人湊在一起,各自發(fā)揮所長,為李童的終身事業(yè)添上錦繡花朵。
李童在寺院修好15年后因半身不遂過世,就葬在離法海寺不遠(yuǎn)的山坡上,以示不舍。他的朝中大官朋友、禮部尚書胡濙再次為他撰寫了生平碑銘,大致勾勒其生平事跡:李童出生于洪武己巳年(1389),江西廬陵人(今江西省吉安市),相繼侍奉了永樂、洪熙、宣德、正統(tǒng)、景泰五位皇帝,在宣宗時(shí),升授為御用監(jiān)太監(jiān),在代宗時(shí),得到明王朝的最高賞賜——蟒袍玉帶。碑銘形容他“周旋殿陛,儀度從容。小心慎密,竭力攄忠。護(hù)駕出入,環(huán)衛(wèi)圣躬。歷事五朝,職業(yè)愈崇”。寥寥數(shù)筆,寫出李童的性格特征。他是一個(gè)儀表從容之人,做事謹(jǐn)慎周密,且周璇于宮廷內(nèi)外,合宜有度。換言之,他可以在各類人群中受到歡迎,不僅有高官朋友,也有地位不高的工匠及宮廷畫師朋友。他請這些人來大殿創(chuàng)作壁畫,他們從構(gòu)圖設(shè)計(jì)、人物安排到運(yùn)筆繪制,竭盡所能,完美展現(xiàn)其精湛技藝。
李童只是明朝的普通太監(jiān),自己根本想象不到,他在法海寺的一番作為竟然創(chuàng)造了中國古代繪畫藝術(shù)史上的奇跡。
法海寺的壁畫有中華文化的“純潔性”
壁畫中人物眾多,但構(gòu)圖大氣嚴(yán)謹(jǐn),相間適度,有序不亂。雖說都是佛教典故的描繪,但生動(dòng)盎然,刻畫細(xì)膩,人物面貌活靈活現(xiàn),富于個(gè)性。無論是線條柔美、慈悲四溢、望之心化、衣著飾物美輪美奐到無以復(fù)加的水月觀音,還是滿滿慈愛、柔情萬種、雍容華美的訶利帝母(鬼子母),她在佛教中已從專吃小孩的惡神轉(zhuǎn)化成孩子的保護(hù)神。她撫頭的小孩更是眼神俏皮,活靈活現(xiàn)得可以從墻壁上跳下來。與敦煌壁畫及永樂壁畫相比,法海寺的壁畫畫風(fēng)手法更為細(xì)膩精美,用料奢華考究,尤其是大量金粉的使用。
有后人說法海寺壁畫可以與西方中世紀(jì)壁畫藝術(shù)媲美,是藝術(shù)史上偉麗之作,堪稱“中國西斯廷”。我反而認(rèn)為,法海寺壁畫令人矚目在其珍稀性上,就華夏漢地壁畫繪畫之藝術(shù)精品而言,它們整體的過于匱乏顯示了其卓爾不群。傳統(tǒng)上的美術(shù)繪畫似乎成為宮廷皇室的雅好和高貴的奢侈品,除了皇宮與權(quán)貴人家的建筑裝飾雕龍畫鳳花鳥蟲魚之外,降落民間的這類藝術(shù)作品還是過于稀疏。加之戰(zhàn)亂滅失的唐宋壁畫已蹤影難覓,雖然不少古代建筑也留有壁畫,但達(dá)到如此之高藝術(shù)水準(zhǔn)的組團(tuán)式的精品之作不多。敦煌壁畫準(zhǔn)確些說是中華、印度、希臘、伊斯蘭四大文化體系匯流的體現(xiàn),并非獨(dú)屬華夏文化。而法海寺壁畫有中華文化的“純潔性”。宮廷畫師的作品落戶法海寺純粹出于李童個(gè)人關(guān)系的偶然性,或許,李童也是接受了藏地僧侶關(guān)于繪制壁畫的建議。在藏地,壁畫分布在寺廟、府第、宮殿、民宅、驛站、旅店等地的墻壁上,普遍尋常。而漢地寺廟里成規(guī)模且達(dá)到藝術(shù)水準(zhǔn)的只有永樂宮及法海寺。永樂宮是道教道場,繪畫內(nèi)容以道教經(jīng)典為主,雖然規(guī)模更大些,但繪制的精美程度達(dá)不到法海寺水準(zhǔn)。所以,大中華漢地佛教寺院里,只有法海寺保存下來了一批極高水準(zhǔn)的佛教題材壁畫。
清廷入主中原之后,大肆修葺并恢復(fù)了不少明朝寺院,但法海寺始終沒有進(jìn)入清當(dāng)朝者的法眼。根據(jù)乾隆中期《日下舊聞考》記載的情況分析,法海寺沒有被清朝官方考察過,沒有被皇帝親訪過,甚至藝術(shù)愛好者乾隆皇帝也沒有聽聞如此瑰寶(這是空前的憾事),也就不可能有朝廷出面的任何復(fù)建與修繕。《日下舊聞考》只將法海寺作為一座普通的前朝寺院簡單記錄了一下遺留物品,包括三通明碑、二通石幢,對大殿內(nèi)部的佛像、羅漢雕塑只字未提,壁畫部分更是無從談起。也就是說,歷經(jīng)清朝267年,法海寺壁畫如沙里藏金,無人得識。
法海寺作為寺院的輝煌基本至明朝滅亡便戛然終止,在清朝,它只是作為普通的民間寺院存續(xù)著。到了民國時(shí)期,這里已經(jīng)非常破敗,僧人也逐漸離開。
1958年文物部門盡管經(jīng)費(fèi)有限,還是對壁畫進(jìn)行了一次時(shí)隔500年的維修,并給大殿裝了避雷裝置。1988年法海寺便已是國家重點(diǎn)文物保護(hù)單位了。如今,法海寺壁畫已經(jīng)和圓明園遺址、三星堆遺址等一起名列國家第三批國寶級文物,地位極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