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則臣:小說是個(gè)體面對(duì)整個(gè)世界言說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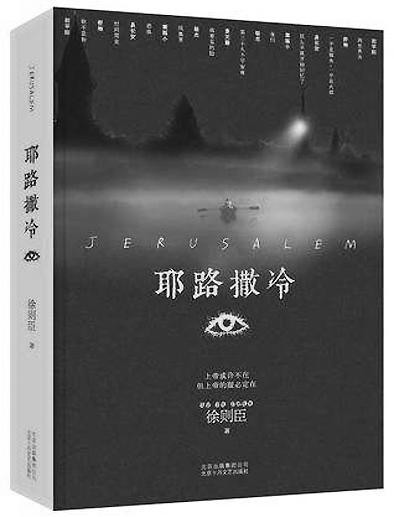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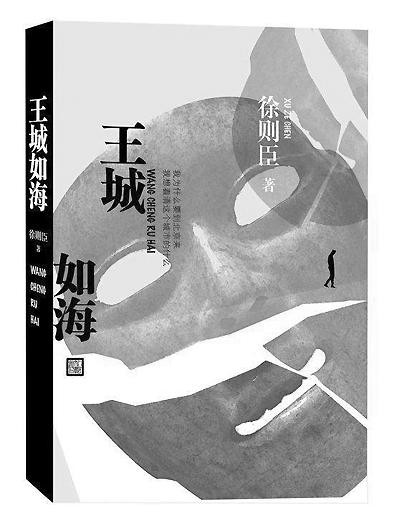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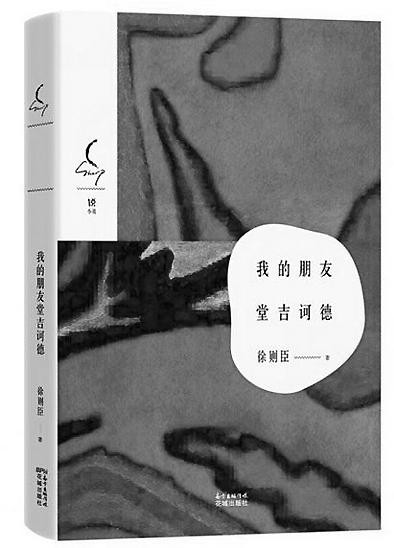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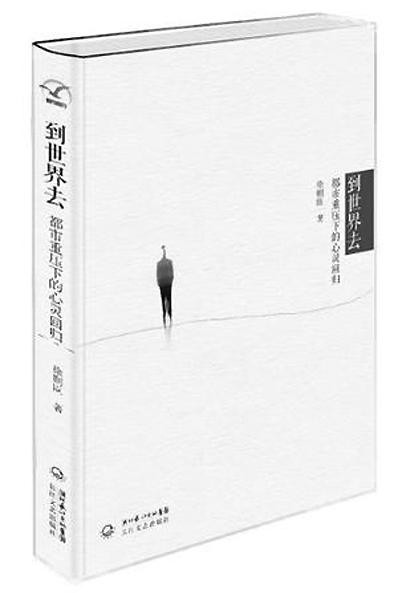
必須找到經(jīng)得起推敲的結(jié)構(gòu),既可以充分地自我表達(dá),又能區(qū)別于他人
記者:讀《耶路撒冷》,先是翻到扉頁上的一句話:這么早就開始回憶了。這其實(shí)也是其中一個(gè)專欄的題名。在我感覺里,這句話像給小說定了一個(gè)基調(diào),或者說隱含了你一個(gè)寫作的理由。如果說這部小說包含了為一代人寫心靈史的意圖,這樣的回憶似乎還早了一點(diǎn),畢竟1970一代還算年輕。所以自然會(huì)引人發(fā)問,為何這么早就開始回憶了?但它從另外一個(gè)角度給了我一個(gè)提醒。“70后”作家居多已過不惑之年,像你,還有其他一些同時(shí)代作家都寫了十多年,確乎可以對(duì)自己的寫作做個(gè)回望了。
徐則臣:出版社選了這句話放在扉頁上,有他們的考慮。準(zhǔn)備寫這個(gè)小說的時(shí)候,有朋友也說,寫“70后”太早了。我覺得不早。原因是,我們都已經(jīng)開始回憶了。早與不早,跟年齡沒關(guān)系,跟你的經(jīng)歷,跟故鄉(xiāng)的失去,還有整個(gè)世界的變化,有很大的關(guān)系。如果你身處故鄉(xiāng),局內(nèi)人,即使故鄉(xiāng)天翻地覆滄海桑田,你未見得會(huì)意識(shí)到,可能完全產(chǎn)生不了回憶,因?yàn)槟阍谀莻€(gè)變化流中,變化是你習(xí)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但當(dāng)你離開再返回,你所熟悉的都已消失或者是行將消失的時(shí)候,你會(huì)產(chǎn)生回憶,必須回憶,要不你可能連僅剩下的那點(diǎn)東西都抓不著了。是時(shí)候了,再遲你可能就來不及了。
記者:我感覺這部小說章節(jié)的編排,似乎就體現(xiàn)出了回憶的特點(diǎn)。怎么說呢,可能很多人會(huì)覺得,回憶該是線性的,從此刻起沿著某種路徑一點(diǎn)點(diǎn)往回追溯。但我覺得回憶或許更像是一個(gè)同心圓,圍繞一個(gè)或幾個(gè)中心,像漣漪般一圈圈擴(kuò)散開去。
徐則臣:這本書首尾相接,是一個(gè)圓:它從一個(gè)點(diǎn)出發(fā),又繞了回來。這可能比較合乎我們文化里循環(huán)的理念。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循環(huán)也的確是一個(gè)重要的概念。開始我沒刻意這么想,但寫著寫著,就成這樣了。可以想一下:這世界就是這樣,開始我們都想往外跑,離開故鄉(xiāng)到世界去,但后來你會(huì)發(fā)現(xiàn)故鄉(xiāng)就是世界,你繞一圈又回來了。小說也相應(yīng)呈現(xiàn)出這樣一個(gè)圓形結(jié)構(gòu)。
記者:想必你為找到這個(gè)結(jié)構(gòu)花了很多心思。
徐則臣:真花了不少時(shí)間。這小說寫了六年,前三年主要在找結(jié)構(gòu)。就像現(xiàn)在要寫一部有關(guān)運(yùn)河的小說《北上》,萬事俱備,就是結(jié)構(gòu)差那么一點(diǎn)意思,動(dòng)不了筆,所以中間又寫了《王城如海》和《青云谷童話》。必須找到一個(gè)經(jīng)得起推敲的好結(jié)構(gòu),既可以充分表達(dá)出我想要的東西,又能跟別人區(qū)別開來。
記者:說到結(jié)構(gòu),我倒想起英國作家大衛(wèi)·米切爾說過,在情節(jié)、人物、主題、形式和結(jié)構(gòu)這五個(gè)元素里面,只有結(jié)構(gòu)還有不少創(chuàng)新的空間。我也同樣想起作家張煒曾表示,結(jié)構(gòu)是最少創(chuàng)新空間的。這是個(gè)可以討論的話題,當(dāng)然我更想探討的是,僅只是結(jié)構(gòu)的創(chuàng)新,是否足以讓你的創(chuàng)作跟別人不一樣?
徐則臣:區(qū)別應(yīng)該是全方位的,所以每一個(gè)角落都不能輕易地懈怠和放棄。結(jié)構(gòu)非常重要。其一,你要結(jié)構(gòu)這世界,就得找到與這個(gè)世界同構(gòu)的一個(gè)形式。其二,寫一個(gè)中短篇,甚至一個(gè)小長篇,就好比蓋一間房子,你可以沒有特別詳細(xì)的構(gòu)思,就跟著感覺走,完全可以。唯手熟爾,夠了。寫《王城如海》我就沒下那么多功夫。但一個(gè)大長篇,不僅是一間房子,而是一座樓、一個(gè)建筑群。牽一發(fā)而動(dòng)全身。很多人看完《耶路撒冷》說,小說一直寫到結(jié)尾氣都沒斷掉,后勁源源不斷,滾滾而來。我把這當(dāng)成是贊揚(yáng)和鼓勵(lì)。這固然是寫作經(jīng)年訓(xùn)練的結(jié)果,其實(shí)跟結(jié)構(gòu)也有相當(dāng)大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立住了,關(guān)鍵處你不會(huì)捉襟見肘、顧此失彼。你可以從容地轉(zhuǎn)向局部,讓每塊磚、每塊石頭都結(jié)結(jié)實(shí)實(shí)在它們?cè)撛诘牡胤剑嗪谩_@就是結(jié)構(gòu)的意義。
記者:小說說到底是時(shí)空的藝術(shù),結(jié)構(gòu)關(guān)乎空間,結(jié)構(gòu)安排好了,相當(dāng)于給時(shí)間提供了縱橫馳騁的場(chǎng)所。
徐則臣:對(duì),結(jié)構(gòu)科學(xué),時(shí)間處理起來就方便了。所以,我愿意花一半的時(shí)間先來解決結(jié)構(gòu)問題。長篇,尤其是大長篇,必須在故事、細(xì)節(jié)、想法、結(jié)構(gòu)諸方面,盡你所能,全方位地提供新東西,結(jié)構(gòu)是非常重要的一環(huán)。《耶路撒冷》之后再寫小說,我沒再出過這樣的情況:某個(gè)題材短篇放不下,那就寫成中篇吧,中篇放不下,就寫成長篇吧。短中長都有它匹配的尺度和結(jié)構(gòu)。理想的結(jié)構(gòu)找起來的確有點(diǎn)麻煩,但功夫到了,你力所能及處,老天應(yīng)該不會(huì)辜負(fù)你。一部偉大的小說,結(jié)構(gòu)極少是平庸的。
記者:結(jié)構(gòu)與空間之間構(gòu)成什么樣的關(guān)系?像約克納帕塔法這樣一個(gè)虛擬的空間,是否也在某種意義上促成了福克納小說各個(gè)不同的結(jié)構(gòu)藝術(shù)?現(xiàn)代小說之前,無論中西方一些古典小說,尤其是流浪漢小說,人物在空間里流動(dòng),結(jié)構(gòu)是比較單一的。當(dāng)空間確定以后,小說結(jié)構(gòu)倒越來越復(fù)雜、立體了。
徐則臣:對(duì)現(xiàn)代小說來說,更重要的命題是時(shí)間。當(dāng)然空間也很重要,它是橫向的、廣闊的、鋪展開來的,天然地和“規(guī)模”、“豐富”等詞連在一起。而時(shí)間是縱向的、幽深的、尖銳的。但時(shí)間往往沒有空間討好;空間更容易立竿見影,在短時(shí)間內(nèi)出效果。如果把約克納帕塔法那樣的地域,理解為“精神故鄉(xiāng)”,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每個(gè)作家都需要這樣一個(gè)根據(jù)地,一提筆,就會(huì)不由自主地往印象最深、最理解、最熟悉也最有感覺的地方跑。區(qū)別在于,有的作家始終守著同一個(gè)地名不離不棄,有的作家則是打一槍換一個(gè)地名。忠貞不渝顯然要付出代價(jià),那就是得常常費(fèi)盡心思去全盤考慮,保證這地方相對(duì)穩(wěn)定,包括地理環(huán)境、風(fēng)土人情、山高水長,不能這個(gè)小說里說“花街”在溫帶,邊上有條運(yùn)河,到了那個(gè)小說里又說,它跑熱帶去了,周圍全是高山,長滿了棕櫚和椰子樹。
記者:你的“花街”不斷容納進(jìn)新的內(nèi)容,以至于“花街”越走越長。
徐則臣:沒錯(cuò)。在這里,人物、時(shí)間、故事也得注意連貫性,細(xì)節(jié)也要經(jīng)得起推敲。在同一個(gè)根據(jù)地上,越往后寫難度越大,它逼著你越站越高,越看越遠(yuǎn)。作家之所以愿意受這種折磨,一是跟他們?cè)敢饣蛘咧荒芑氐绞煜さ牡胤剑硪粋€(gè),跟文學(xué)的野心有關(guān),他們要經(jīng)營一個(gè)獨(dú)立的世界,福記的、馬記的、莫記的、童記的、賈記的。恐怕有點(diǎn)野心的作家都想整出這么個(gè)地盤,大的蔚然成就王國,小的也得弄出個(gè)大觀園來。我寫一條街、一個(gè)地方,所謂的野心固然有,也是不想把自己弄得太麻煩,就像出箱包多了麻煩,就一兩個(gè),大小零碎都塞進(jìn)去,上下車走路都方便。
我極少在小說里大規(guī)模地運(yùn)用偶然性和戲劇沖突,這次逮著機(jī)會(huì),狠狠地嘗試了一把
記者:你迄今最“當(dāng)下”的小說,或許該是《王城如海》了。因?yàn)樾≌f觸及這些年正在發(fā)生,也備受關(guān)注的霧霾問題。這部小說在每一個(gè)章節(jié)里,嵌進(jìn)去話劇《城市啟示錄》的一個(gè)部分,話劇的各個(gè)部分合在一起可以說是和正文構(gòu)成互文或補(bǔ)充關(guān)系的一出完整的話劇。有意思的是,整部小說也有著很強(qiáng)的戲劇性。
徐則臣:最初想寫一個(gè)關(guān)于北京的話劇劇本。嘗試過,很多東西處理不好,還是小說更順手。那我就想,如果把小說戲劇化、劇本化呢,不只是在小說里加一個(gè)片段、引進(jìn)戲劇的形式,還要把戲劇的一些要素,偶然性、戲劇沖突,都移植進(jìn)去,結(jié)果就這樣了。我極少在小說里大規(guī)模地運(yùn)用偶然性和戲劇沖突,這次逮著機(jī)會(huì),狠狠地嘗試了一把。
記者:小說里的確有很多的偶然性,偶然性會(huì)不會(huì)讓人感覺在某些地方缺乏說服力?畢竟,小說里的偶然性,要有足夠說服力的話,也因?yàn)槠渲邪吮厝恍浴?/span>
徐則臣:在一部小說里動(dòng)用那么多戲劇性因素,已經(jīng)不只是表現(xiàn)方式的問題了,還是一個(gè)關(guān)于戲劇的方法論問題。比如《雷雨》,一段時(shí)間里發(fā)生了很多事,一件事牽出另一件事,互為因果,跟多米諾骨牌似的,就一路倒下去了。有個(gè)問題可以探討:在戲劇里,大量運(yùn)用戲劇手段,是成立的,你不會(huì)覺得唐突冒犯。為什么在一個(gè)小說里就不行?我當(dāng)時(shí)就想試一試,把未竟的戲劇夢(mèng)想,放到小說里來實(shí)現(xiàn)。
記者:那是不是說,從寫作的角度看,你先得假設(shè)一些巧合都是成立的,什么事都是可能發(fā)生的。然后一步步論證這些巧合,這些事它怎么就發(fā)生了。
徐則臣:寫到每一個(gè)轉(zhuǎn)折點(diǎn)我都會(huì)反復(fù)琢磨,這地方是不是完全不可能?絕對(duì)不可能,我不會(huì)寫。如果有可能,我就可以寫。不管是小說里,還是生活里,總有很多命懸一線的時(shí)刻。薩拉馬戈在《失明癥漫記》開頭的假設(shè),所有跟醫(yī)生有關(guān)系的人,都失明了,就他老婆沒有失明。不需要問為什么,你只要承認(rèn)有這種可能就行了。再比如,心臟生在左側(cè),一刀刺下去人肯定就廢了。但有些人就沒事,他所有的器官都是反著長的。我有一個(gè)同學(xué),體檢的時(shí)候,把醫(yī)生嚇壞了,心臟找不著了。他的心臟長在右邊。金庸小說里也有這樣的人物。正常情況下我們的確不該拿特例說事,但我想在這部小說里嘗試一下。肯定不會(huì)一直這么干。
記者:問題是有人或許會(huì)問,小說的戲劇化,是不是非得由很多巧合來促成呢?尤其是小說的最后一章,就像是很多事在一天之間發(fā)生碰撞,然后瞬間爆發(fā)。
徐則臣: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這個(gè)結(jié)果往前倒推,能否成立?能成立就沒問題。
小說結(jié)尾部分,整個(gè)戲劇沖突的時(shí)間很短,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一天之內(nèi)發(fā)生的。為了這一刻的相遇和沖突,前面我草蛇灰線地鋪墊了很多細(xì)節(jié),把人物的后路一條條全給堵死了,讓他們只有這一條道可以走。
記者:你能這么放開寫,該是因?yàn)榻?jīng)過這么多年寫作的歷練,變得更加自信了。上次在紹興聊天,你說到讀波拉尼奧的《2666》給你一種“如入無人之境”的感覺,我不知道你在寫這般有一定探索性的小說時(shí),會(huì)不會(huì)也有這樣的感覺?
徐則臣:波拉尼奧寫《2666》,絕對(duì)是高度自信,什么都不管,真是信馬由韁,愛怎么寫怎么寫。小說里僅兇殺案,一口氣就羅列了幾百個(gè)。這膽子也太大了,誰敢這么玩?但他就旁若無人地干了。看上去漫不經(jīng)心,但漫不經(jīng)心本身也可能就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結(jié)構(gòu)。寫《耶路撒冷》的時(shí)候,也有不少人質(zhì)疑,你怎么寫怎么有問題。但現(xiàn)在,我要感謝這部小說,有些年輕作家跟我說,他們看了小說后很受鼓舞,膽子大了,因?yàn)樾≌f也可以這么寫。所以,文無定法,小說沒什么確定的形式。什么是真理?成了就是真理,不成就是謬誤,成王敗寇。我們的問題是,在寫之前只想著成,就沒想過其實(shí)你不這么樣寫也可能會(huì)成。大家更愿意選擇保險(xiǎn)的路子。也沒什么不對(duì),但的確限制了我們的創(chuàng)造力。
記者:有些作家在寫作之前,想寫作之外的東西太多了。
徐則臣:我們總想著寫一個(gè)四面討好、老少咸宜的東西。開始我也是,現(xiàn)在不管了,愛誰誰。《王城如海》這么短的篇幅,我用了一個(gè)復(fù)雜的結(jié)構(gòu),當(dāng)然不是為了形式而花哨,這個(gè)形式是必須的,它對(duì)內(nèi)容有意義,相輔相成,相互生發(fā)。
記者:我們談到要不斷給自己設(shè)置“寫作的難度”,甚至于有作家還說“沒有難度的寫作是可恥的”。但寫作的難度,是否只體現(xiàn)在不斷變換形式,不斷拓寬疆域。在同一個(gè)領(lǐng)域里深挖,不也同樣能體現(xiàn)難度?
徐則臣:我很看重“寫作的難度”,一直以此激勵(lì)自己,也喜歡用這個(gè)標(biāo)準(zhǔn)來評(píng)價(jià)其他作家。寫作是一個(gè)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的過程,失去了難度也就談不上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就成了偽寫作。難度不僅僅是技術(shù)上的問題有沒有解決,能否解決好,更重要的在于,是否對(duì)過去的寫作構(gòu)成挑戰(zhàn),是否有勇往直前的膽量和信心,是否不斷地將自己從眾多寫作中區(qū)別開來并最終確立出自己。在我看來,那些蜻蜓點(diǎn)水般到處攻城略地縱橫馳騁的作家,打一槍換個(gè)地方,換個(gè)地方打一槍,恰恰是在逃避寫作的難度,缺少對(duì)某一個(gè)和某幾個(gè)領(lǐng)域的深度掘進(jìn)。對(duì)擺脫不掉局限性的個(gè)體來說,存在無邊界的寫作嗎?但也必須承認(rèn),很多作家的確也在通過形式和題材本身的變化,努力拓寬自身和我們共同的文學(xué)。凡事都不能絕對(duì)。
記者:沒錯(cuò)。再是“如入無人之境”的寫作,實(shí)際上也是“戴著鐐銬的舞蹈”。寫作有自信的同時(shí),也得有自知。因?yàn)樽灾艜?huì)更有自信。
徐則臣:我以前總會(huì)擔(dān)心,一個(gè)東西寫出來,會(huì)有這樣那樣的毛病,弄不好就會(huì)失敗。問題是有哪部小說沒毛病?沒毛病就成功了嗎?當(dāng)真說起來,沒毛病本身也是一個(gè)毛病,完美就是個(gè)陷阱。
不要以單一的聲音去呈現(xiàn)這個(gè)世界,就算自我表達(dá),也要盡力復(fù)調(diào),盡量眾聲喧嘩
記者:《耶路撒冷》和《王城如海》看似寫的全然不同的兩個(gè)題材,但從主題的層面看,又是特別相關(guān)的。說白了,前者說的是“到世界去”的問題,后者說的是“從世界回來”的問題。因?yàn)檫@兩部小說,差不多也在同一個(gè)時(shí)期,所以有必要問問,你是不是在構(gòu)思的時(shí)候,就有這樣的設(shè)計(jì)?
徐則臣:真沒有任何的設(shè)計(jì),因?yàn)槭裁矗谖铱磥恚绞澜缛ジ毓枢l(xiāng)是一體兩面的事,在我潛意識(shí)里,這兩個(gè)東西是連在一塊兒的。《耶路撒冷》之后,我就一直想寫《北上》,沿運(yùn)河從南到北。寫不了,我就繼續(xù)想《王城如海》的事。以我的習(xí)慣,一部長篇寫到一半,就不必管它了,它的“大勢(shì)”已成,可以自己走,你可以開始考慮另一部小說了。這大概是兩者在問題意識(shí)上有所勾連的原因之一。
記者:“世界”可算得你的關(guān)鍵詞。你不只是在小說里提,在散文隨筆里也不斷提到。《小說、世界和女作家林白》《 一個(gè)人面對(duì)世界的方式》兩篇隨筆,主要就是探討人、小說與世界之間的某種關(guān)系。
徐則臣:小說不是個(gè)多高深的東西,它就是作為個(gè)體的作家切入他所面對(duì)的世界的一種方式,也是個(gè)體面對(duì)整個(gè)世界言說的方式。小說解決的就是個(gè)人與世界之間的問題。世界不是簡單的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或者某某單一的東西,而是與個(gè)體有關(guān)的整個(gè)存在。存在主義、后現(xiàn)代等等,只是對(duì)世界的眾多描述中的其中一種,它們有意義,在一定時(shí)間內(nèi)也有效,但不是唯一的,世界在變,存在主義和后現(xiàn)代之前已經(jīng)有很多種理論上的描述,其后也一定還會(huì)有很多種描述。就目前而言,它對(duì)我的意義,主要是借助這樣的理論部分地實(shí)現(xiàn)對(duì)世界的某些本質(zhì)的認(rèn)識(shí),引發(fā)一些思考和發(fā)現(xiàn),可能會(huì)作用于我的寫作,也可能僅僅停留在思考的層面上。當(dāng)然,理論本身也有可能是自足的,只在它自己的邏輯里才成立,就是一種智力游戲,這種時(shí)候,它玩的就是空轉(zhuǎn),對(duì)實(shí)踐可能沒什么意義。
記者:你似乎對(duì)理論有濃厚的興趣,而且你對(duì)寫作有自己獨(dú)到的心得體會(huì),說你有一套相對(duì)自足的理論構(gòu)架也不為過。以我的感覺,你是作家里面自我闡釋能力特別強(qiáng)的,也是擅于闡釋的評(píng)論家里面寫作能力特別強(qiáng)的。
徐則臣:我當(dāng)然談不上什么理論構(gòu)架,我寫的就是自己的一些雜七雜八的想法。它們看起來有點(diǎn)一脈相承,是因?yàn)槲矣幸粋€(gè)比較堅(jiān)定的對(duì)理想中的好小說的想象。所有的想法只是從不同的角度對(duì)那個(gè)好小說的描述和逼近。可能會(huì)有一些矛盾處,但整體上這些想法是漸進(jìn)的、相互修正和完善的。一個(gè)作家不可能完成了所有的寫作才開始整理自己的寫作理論,他會(huì)邊寫邊想邊實(shí)踐,要實(shí)踐出真知,要理論聯(lián)系實(shí)踐,互動(dòng)著往前跑。
記者:我有時(shí)也想,作家在寫作上是不是不妨糊涂一點(diǎn),開個(gè)玩笑,作家自己都充分闡釋了,就沒評(píng)論家什么事了。其實(shí),作家有很強(qiáng)的理論構(gòu)建能力挺好,前提是能促進(jìn)寫作,而不是用理論把自己給框死了。更何況,寫作和理論在一個(gè)作家身上并不總是并行不悖的,有時(shí)候反而會(huì)是相互背離的。
徐則臣:我覺得你的擔(dān)憂,不是因?yàn)槲以谶厡戇吙偨Y(jié)自己的想法,而是擔(dān)心我會(huì)畫地為牢,把自己活生生地憋死在預(yù)設(shè)的寫作理念里。這的確是我需要警惕的。在我的想象里,好小說是開放的,關(guān)于好小說的理論也是開放的,我希望我的思考也是開放的,這就意味著,當(dāng)我的努力事與愿違時(shí),我能夠及時(shí)地反省和調(diào)整。不是最終非此即彼地服從哪一個(gè),而是盡力找到最合理的那一條路。所以并行而悖并不可怕,恰恰是一帆風(fēng)順可能更糟糕,它會(huì)讓你忘記反思這回事。
記者:沒錯(cuò),不管怎么說,作家有一定的理論基礎(chǔ)總是好的。也因?yàn)橐庾R(shí)到這一點(diǎn),這些年來一直有人提作家學(xué)者化的問題,我覺得這應(yīng)該不是說要作家同時(shí)做一個(gè)評(píng)論家,或是要作家有大學(xué)問。如果作家學(xué)者化有必要的話,你覺得必要性在哪里?也不妨說說,有闡釋能力,有理論基礎(chǔ)對(duì)你自己的寫作有何幫助?
徐則臣:在我看來,作家學(xué)者化的最重要一條是:你要有問題意識(shí)。你知道你寫這個(gè)故事的意義和必要性在哪里。由此,你才會(huì)以文學(xué)的方式去研究問題、表達(dá)問題、解決問題。由此才會(huì)產(chǎn)生及物的文學(xué),文學(xué)也正是這樣一步步發(fā)展至今的。作家的任務(wù)不僅僅是講個(gè)好看的故事,故事漫山遍野,不需要一群人當(dāng)個(gè)事兒專門去干。自我闡釋說到底不重要,真要寫得好,會(huì)有無數(shù)人幫你闡釋,甚至你永遠(yuǎn)也想不出的東西都能掘地三尺給你找出來。學(xué)者化肯定不是為了做學(xué)問,而是讓你有問題意識(shí),能夠就某些重要的問題深入有效地思考下去,讓你成為一個(gè)有腦子的作家。
你的世界觀與別人真正區(qū)別開了,你的寫作也必然成為獨(dú)特的存在,但做到這樣很難
記者:說“世界”都說到理論上去了,因?yàn)槟阍诓簧匐S筆文字里談到對(duì)“世界”的理解。你還寫了一篇《零距離想象世界》,挺有意思。感覺應(yīng)該能代表你現(xiàn)在理解和把握世界的一個(gè)角度,或某種方式。
徐則臣:這是寫作面臨的現(xiàn)實(shí)。現(xiàn)在的科學(xué)技術(shù)、網(wǎng)絡(luò)這些東西,讓世界上任意兩點(diǎn)間的距離越來越短。我們處在一個(gè)地方,卻要去想象它。敘述本身就是想象的一部分。你無論怎么描述,其實(shí)都包含了你對(duì)一個(gè)事物的想象。比如,我在北京寫北京,就是一種零距離的寫作,所以零距離是我們根本的處境。那么,我在零距離的情況下怎么寫北京,就是我在小說里要解決的問題。
記者:由“世界”延伸開去,不妨談?wù)勈澜缬^的問題。想到這個(gè)是因?yàn)橄氲剑粋€(gè)作家的寫作該怎樣在本質(zhì)上與別人區(qū)別開來?對(duì)于初學(xué)寫作者來說,模仿是不可避免的。反過來說,不同的作家寫作很不相同,那不同又在哪呢?這關(guān)系到作家該有怎樣的世界觀,該怎樣確立自己的風(fēng)格的問題。
徐則臣:沒錯(cuò),模仿和超越,在我看來,關(guān)鍵在于是否形成了自己面對(duì)世界的獨(dú)特方式。有自己的獨(dú)特看法,必然要求與之契合的表達(dá)方式,別人誰也幫不了,模仿在這里是失效的。李敬澤先生有一句話說得特別好,怎么寫其實(shí)是個(gè)世界觀的問題。你的世界觀與別人真正區(qū)別開了,你的寫作必然也會(huì)成為獨(dú)特的存在。但做到這樣很難,所以才會(huì)有“影響的焦慮”。總的來說,模仿在寫作中是必要的,因?yàn)槟愕弥烙螒虻幕就娣ǎ愕脤W(xué)習(xí)和借鑒,需要?jiǎng)e人的光照亮你幽暗的角落,激發(fā)你的創(chuàng)造;其后,超越是自己的事。
記者:其實(shí)你已經(jīng)“在世界上”了。這不只是說你有多種小說被翻譯到國外,也不只是說你走了多少個(gè)國家,而是說從《耶路撒冷》,還有你的其他一些小說里,能感覺到你有了一種“世界意識(shí)”。當(dāng)然我這么說,說實(shí)在我也不是很清楚“世界意識(shí)”到底指的什么。游歷這么多國家后,對(duì)你有怎樣的影響?
徐則臣:不知道別人在周游列國之后感受如何,這些年斷斷續(xù)續(xù)地在外面跑,慢慢地覺得好像開了第三只眼。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開闊視野毋庸置疑。地域、種族和文化的差異帶來看世界角度的不同,別一種和數(shù)種眼光可以補(bǔ)濟(jì)我們相對(duì)單一和有限的思維。橫看成嶺側(cè)成峰,世界有多復(fù)雜,取決于你有多少看取世界的角度。偏聽則暗,兼聽則明,我相信多一個(gè)角度總比少一個(gè)角度要好。諸多差異性的眼光可以補(bǔ)濟(jì),可以修正,可以提醒,最不濟(jì),也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gè)比照和參考:有比較才有鑒別,有鑒別才能有所本、有所執(zhí)。世界觀的變化必然帶來文學(xué)觀的變化。這些年我對(duì)文學(xué)的想法一直在調(diào)整,是否更加科學(xué)不敢說,但的確一直在變,說明持續(xù)有新東西在刺激,同時(shí)也在持續(xù)地反思、敞開、接納、比較和確立新的自我。我以為這是好事。古巴對(duì)一個(gè)中國人來說似乎很熟悉,但事實(shí)上可能比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更陌生。到了美國,你會(huì)說,嗯,這就是美國;到古巴,你的感嘆可能會(huì)是,啊,原來這才是古巴!
記者:視野日漸開闊以后,我想你對(duì)“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這句老生常談,也會(huì)有不一樣的理解。
徐則臣:這句話,要放在什么條件上談。首先,一個(gè)東西和另一個(gè)如果沒有差異性,它存在的意義在哪里?我們想看一個(gè)東西的前提就是,我能從中獲得不一樣的東西,如果看來看去都差不離,你看一個(gè)就行,你自言自語就可以。但這個(gè)東西也得是世界的,得是大家能夠接受的,這是理解的前提,也是大家能夠相互交流的前提。所以,沒有差異,就沒有交流的需要。沒有通約,就不存在理解的基礎(chǔ)。兩者很重要。我們不妨把文學(xué)比作一個(gè)分?jǐn)?shù),有分子、分母,我們通常認(rèn)為文學(xué)的公約數(shù)更重要。但五分之二與七分之二的區(qū)別不在于分子,而在于分母。分子是分母之所以存在的前提,分子就代表的差異性。而在分子一樣的情況下,能夠區(qū)別自己的,確立自己的,則是分母的差異性。
記者:我們講民族與世界的關(guān)系,隱含了寫出一種既民族又世界的作品的渴望。不管怎樣,我都覺得“70后”作家理當(dāng)有這樣的抱負(fù)。記得有一次張莉說到,“70后”作家生正逢時(shí),他們?cè)诔砷L期看到改革開放前一些大事件的背影,又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浪潮,他們是兩邊的資源都占了,理當(dāng)肩負(fù)起更為重要的反映時(shí)代的責(zé)任。我可能記不準(zhǔn)確,只是記得她說的大意。當(dāng)然,換個(gè)角度看,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70后”作家生不逢時(shí),他們好比被架在一個(gè)山崗上,雖然能看到兩邊的風(fēng)景,卻都沒能深入到谷底,也就體會(huì)不到站在風(fēng)暴中心的那種深入骨髓的體驗(yàn)。待到寫作時(shí),難免會(huì)有心有余力不足之感。事實(shí)上,要是碰到能力不相匹配的時(shí)候,寫作上的雄心倒反而會(huì)有損于實(shí)際的創(chuàng)作。
徐則臣:我贊同張莉的結(jié)論,我也認(rèn)為從理論上說,這一代作家應(yīng)該不會(huì)讓人失望。但在蓋棺論定之前,不管多么強(qiáng)悍的邏輯都只能是推測(cè)。事實(shí)上,所有的正反面教材歷史早給我們提供好了:看似生不逢時(shí)的一代人,沒準(zhǔn)最后冒出了幾個(gè)大師;而那些在蒼茫浩瀚的大時(shí)代里摸爬滾打過的,也可能最終煙消云散。也就是說,文學(xué)上其實(shí)是不講概率的,大作家、大作品出來就出來了,出不來講多少大道理都是白搭。身處其中,時(shí)代咱們沒法再選了,剩下的就是各各努力,好自為之,看修為和運(yùn)氣了。
徐則臣,1978年生于江蘇東海,畢業(yè)于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供職于人民文學(xué)雜志社。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過中關(guān)村》《青云谷童話》等。曾獲莊重文文學(xué)獎(jiǎng)、華語文學(xué)傳媒大獎(jiǎng)·年度小說家獎(jiǎng)、馮牧文學(xué)獎(jiǎng),被《南方人物周刊》評(píng)為“2015年度中國青年領(lǐng)袖”。《如果大雪封門》獲第六屆魯迅文學(xué)獎(jiǎng)短篇小說獎(jiǎng),同名短篇小說集獲CCTV“2016中國好書”獎(jiǎng)。長篇小說《耶路撒冷》被評(píng)為“《亞洲周刊》2014年度十大小說”第一名,獲第五屆老舍文學(xué)獎(jiǎng)、第六屆香港“紅樓夢(mèng)獎(jiǎng)”決審團(tuán)獎(jiǎng)、首屆騰訊書院文學(xué)獎(jiǎng)。部分作品被翻譯成德、英、日、韓、意、蒙、荷、俄、阿、西等十余種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