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的博物館”:雕版上的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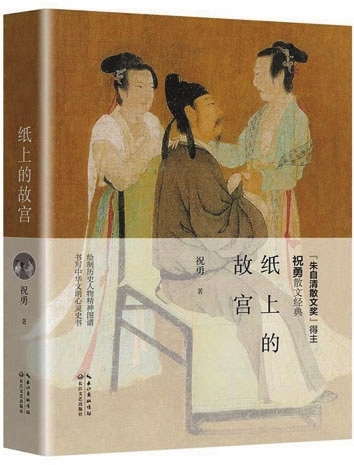
每當清晨,印經院的殿堂就如同一個布景華麗的巨大舞臺,被晨曦的追光照亮。許多匠人會在不同的作坊中分組排開,他們長長的影子拖在老舊的木質地板上,在時光中不聲不響地移動。當影子像日晷一樣旋轉到相反的位置時,就會有許多經文在瀟灑的造型中脫穎而出。
一
我至今仍對在印經院度過的那個夜晚記憶猶新。起初,我從遠山向它走近的時候,就看見暮色一點一點地披掛到它的身上,它像一個龐大的神話,漸漸消失在黑夜的內部,變成講述的一部分。所以后來,我在印經院回環(huán)往復的廊道中游走的時候,我感覺自己是走在夜的腹部,一個不可思議的離奇場所。我看不見建筑的整體——當我目睹它的一部分的時候,它的另一部分正在消失。當我走過一段樓板的時候,剛剛踩踏過的樓板就在身后不見了,新的樓板則在腳下應運而生。這種感覺頗為離奇,仿佛我走在一座虛構的宮殿內,它建筑在虛空中,卻給我提供層出不窮的道路,使我不會墜入深淵:無邊的黑暗甚至使我產生某種錯覺,即腳下的道路,會如江水一般源源不斷。沒完沒了的樓梯、藕斷絲連的暗道、意想不到的出口,使我無法預言自己的道路。我只有把自己交給它——這座龐大的宮殿,一心聽從它的調遣。
更多的人把自己的一生交給了這座龐大的寺院,或者說,印經院給僧侶、匠人們提供了一生的道路,它的內部空間,比高山大河更加遼闊。從西藏江達來的澤仁羅布,十九歲進入寺院,刻制印經版,到現(xiàn)在已經十四個年頭了。他還會在這里待更多的年頭。許多匠人在這里度過了一生的時光。一生的時光,對于個體來說是漫長的,但投放在這里,倏忽間就不見了。他們的生命,都變成了經卷、刻版,層層疊疊地,羅列在架子上。看見它們,就等于看見匠人們消逝的面孔。所以,印經院是成千上萬的僧侶匠人共同的存在之所,他們來自不同的朝代,卻濟濟一堂。印經院的遼闊不僅僅是空間賦予的——它只是一座并不高峻的三層建筑(底層除外)——而主要是時間賦予的。它無疑具有永恒性,正是這種永恒性,使它具有了超凡脫俗的容量。
因而,德格印經院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地方。它容納了道路,把無數條穿越雪山河谷的艱辛之路,最終收束于自己的懷中;它吸納了時間,并且為我們提供了進入各種時間的入口——可能一個無意的轉身,就會使我們跌落到幾百年前的某一個時刻里去;更不用說它成為雕版和經卷的聚集之所,據這里的喇嘛介紹,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藏文化典籍,都收藏在德格印經院中,它有三十多萬塊雕版、六千多塊畫版,其中不乏珍本、孤本和絕本的雕版。印經院以一種巧妙的方法占有了世界,即:它保存了時間深處的種種智慧,與這種種智慧相比,任何珍寶,無論怎樣價值連城,都是外在的,而智慧,卻內在于我們的身體,與我們的精氣血脈相連,這種無形的智慧,在超越物質的阻撓之后抵達我們的內心。它們像血液一樣注入我們的身體,使我們的精神日益強大。
那些穿越了千難萬險之后一步步向印經院投靠的道路,以及印經院內部迷宮似的回廊,其實都與我們身體內部的經絡血脈相連通的。有一種隱形的通道存在于它們之間。它們有自己的交通法則。有多少虔誠的生命在其中生生死死、輪回往復。像此刻的我,一旦進入它的內部,就找不到出口——或者說,不愿再去尋找出口,而是在那些幽深的殿堂間,沒完沒了地游走下去。
二
從甘孜過去,就是德格了,但是,從甘孜通往德格的道路并不平坦。它從峽谷中穿越,像江河一樣劇烈地顛簸,要翻越幾座雪山。我們坐在車上,經歷了由天國到人間的幾道輪回。其中最大的挑戰(zhàn),來自海拔6168米的雀兒山:6000米的高度,對生命的存在進行了嚴格的篩選,仿佛對進入圣地的一次資格考試,只有內心堅定的人,才能獲得通行證。我的高山反應不像其他人那樣強烈,只有寂寞最為難耐。除了皚皚白雪,我什么也看不見。它幾乎使我確信,天國是如此寂寞,并非如我們想象的那樣繁花似錦、富麗妖嬈,神靈的業(yè)余生活,也一定單調乏味。一萬年以前下過的雪,還停留在原處,沒有人動過。在起伏連綿的雪山之巔,一切都是靜止的,包括時間。氣喘吁吁的汽車在冰滑的路面上掙扎頑抗,但它的努力成效有限,幾個小時之后,我們仍然在雪山上盤桓。此時的運動,約等于靜止。
在搖晃的車上,我只想一件事——從前的喇嘛,是如何跨越雪山,前往他們心中的圣地?那時還沒有三一七國道,但那條通往德格的路肯定是存在的。那條道路上危機四伏,而德格,看上去更像一種永不存在的虛假誘惑。在德格到來之前,沒有任何征兆表明它的存在。那輝煌的印經院,與冰冷似鐵的巖石格格不入。它藏在風里,以一種隱秘的方式,宣布它的存在。
整個康巴地區(qū),如同善于思考的大腦,遍布著溝回和隆起,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些落差巨大的山脈,把藏民們各自分割在狹窄的區(qū)域內,難以探聽彼此的消息。山武斷地隔斷了人們的交往,在山面前,人是那么無助:藏民們如何能夠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樣子?這時,宗教的力量就顯現(xiàn)出來了——它把一些支離破碎的個體聯(lián)系起來,在無數個零星的群落之間建立一個巨大的網絡,所有人會在不同的地方念著相同的經文,這是一種多么美妙的和聲,只有最高的神才能聽見。人不再是孤島,每個人的身體里都藏著別人的信息。精神的一致性,改變了他們生存的局面。他們因此而那么容易動情,有了神的存在,山地就不再荒蕪。他們在神的啟示下開始長途之路,把身體交給冰冷的山路。陌生的人,都是在各自的朝圣路上相遇的。他們在朝圣路上遇到了更多的自己。而德格,正藏在道路的盡頭,不動聲色地,等待他們到來。
三
盡管德格把自己隱藏在深山的皺褶中,但是,幾乎所有的藏人都對德格的存在了如指掌,他們把前往德格朝拜視為自己一生的使命。無論道路如何坎坷,它都出現(xiàn)在每個人生命的必經之路上,成為每個虔誠藏民生命中無法回避的巨大存在。無論道路的起點在哪里,它都將成為那些道路必然的終點。人們不禁會問:“為什么在色曲河谷這樣一個狹小地方所誕生的文化形態(tài),會對整個青藏高原的文化形態(tài)產生如此巨大乃至舉足輕重的影響呢?”
現(xiàn)實的問題需要在歷史中得以解答。這是我們今天無法對歷史漠然置之的原因之一。所有消失的事物,會在某一個不經意的時刻,突然顯示出它的重要性,令人猝不及防。仔細打量唐朝的地圖,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當時整個藏文化區(qū)域,分為上阿里三國、中衛(wèi)藏四如、下多康六崗三大部分,而現(xiàn)在的德格地區(qū),剛好位于下多康六崗中最重要的色莫崗地區(qū),不偏不倚地出現(xiàn)在多康與衛(wèi)藏相連接的最重要部位上。那份古老地圖,仿佛一張具有游戲性質的圖紙,而德格,剛好成為圖紙上最關鍵的一顆棋子。不知是誰最先發(fā)現(xiàn)了這一點,但無論怎樣,我們都將對那只妙不可言的手贊嘆不已。這看似偶然的選擇,包含著藏民族對歷史的或是個體命運的必然性認識。通過德格這一跳板,衛(wèi)藏的政治與宗教文化,與多康地區(qū)剽悍英武的族群發(fā)生了歷史性的聯(lián)系,幾種質地不同的文化被德格這個金巤牢牢地焊接起來。它劃開了兩種文化,可兩片土地卻因德格的存在而結合得更加緊密。它們漸漸融化在對方的內部,像兩個人,長久地靠近,生命粘連,血液交融,無法拒絕地長在一起,相互成為對方的一部分,蛻變?yōu)榻裉斓目蛋臀幕?/p>
德格,藏語意為“善地”,原是一個土司家族的名稱。從公元617年到1951年德格縣人民政府成立,1334年間,在藏區(qū)歷史上,占據了最為顯赫的地位。元憲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途經甘孜州,召見薩迦派領袖八思巴和噶瑪噶舉派領袖噶瑪拔希。八思巴在前往覲見忽必烈的途中,受到德格家族第三十代索郎仁青的朝拜,于是,八思巴將他選任為“膳食堪布”,并賜以“四德十格之大夫”稱號。
德格家族的榮耀是大地賦予的。人們甚至以“天德格”“地德格”的稱號比喻他們如天地一般無邊無際的權勢,使藏區(qū)其他的土司家族黯淡無光。
家庭勢力像一個體格健壯的康巴漢子,日夜不停地在高山峽谷間奔走。我查閱《德格縣志》,發(fā)現(xiàn)明末清初,是德格家族的權威迅速擴張的時期,家族意義上的德格,也轉變?yōu)榈乩硪饬x上的德格,成為一個地名。此時的德格,包括了今天四川甘孜的石渠、德格、白玉,西藏的江達和已撤銷的鄧柯縣五縣區(qū)域,并逐步滲入今西藏昌都和青海西南地區(qū)。清代史籍中記載的“得爾格”“得爾格特”“德格特”等,指的都是德格。
據說德格第十二代土司、六世法王曲杰·登巴澤仁在一個日暮時分走出官寨,就在這里,他聽到孩童般誦經聲,在風中隱約傳來,童稚中帶著一種古老的音韻,既急促又緩慢,既燦爛又蒼涼。四下里并沒有人,但他被那若有若無的誦經聲弄得十分癡迷,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他的身體里油然而生。
公元1729年(清雍正七年)2月28日。一個建造印經院的龐大計劃開始展開。實際上,它既是藏書樓,又是出版機構,因為它同時肩負了收藏古老經卷并印刷、傳播它們的雙向使命,但無論怎樣,它在日后都將注定成為藏民族精神信仰的制高點。從那一天開始,它就不再是德格登巴澤仁的夢想,而變成一個日益長高的現(xiàn)實。印經院選定在土司官寨西南三十米一個被稱作尼干普絨的小山包上,與藏族傳統(tǒng)風水文化中典型的“八瑞相”相吻合。一雙智慧的眼睛能夠看出,它周圍的山水格局,自然地排列成了一系列被認為是吉祥寶地的符號:妙蓮、吉祥結、寶傘、右旋海螺、金輪、勝利幢、寶瓶、金魚,而金沙江的兩條支流——色曲河與歐曲河,也剛好在這里匯聚。大地如一套精密儀器,如此縝密地吻合。如果這一切是真的,那么,印經院出現(xiàn)在這里,則恰到好處地體現(xiàn)了神的意志。人們對神的意志心領神會,并用謙卑的手,對神的意志予以落實。
四
即使在黑暗中,我還是被架子上的雕版排山倒海般的氣勢鎮(zhèn)住了。它們一排一排,親密無間地擠靠在一起,所有的文字都隱在夜幕里,蠢蠢欲動。至少有幾億個字聚集在一起,即使沒有聲息,它們的力量也是駭人的。我知道了什么是卷帙浩繁。我聽見澤仁康珠在說:“不知為什么我會如此的悲傷。或許,它強大的力量令我感到莫名的傷感。我無法平靜地與它對視,我穿越無數的輪回就是為了能夠覲見它慈悲的容顏!”它們是那么強大,即使在黑夜中,仍然不停地晃動和奔走。不需要任何宣言,它的正義性,已經存在于它強大的存在中。在如此強大的存在面前,所有的辯駁都是不值一提,甚至是愚蠢的。我們早就不再具有與之對話的可能,就像我們無法挑戰(zhàn)陽光的權威,我們只能接受它的教誨,并把這種接受當作一種榮耀。
除了酥油燈,殿堂拒絕明火。黑暗封閉了我們的視線,但我們可以用手觸摸。高顯銀帶著手電,我跟在這位年輕的縣委宣傳部長的后面,看見手電照亮佛經的只言片語,沒等我看清,就消失了。它們在黑暗中一望無際,深不可測,我不知道哪里才是它們的盡頭。我索性站住,觸摸到雕版的把手。我把它抽出來,動作很輕,生怕對其他的雕版有所驚擾。我的手指暗自滑向雕版上凸起的字跡。這時我突然感到一陣暈眩。我發(fā)現(xiàn),手是可以看的,在眼睛力不從心的時刻,手是那么的機敏,可以清晰地看清文字的形狀。我似乎明白,盲人的世界并不完全是黑暗的,光亮會順著他的手指進入他的內心。他們與世界的聯(lián)系,不會因目光的夭折而受任何阻撓。
據說,最古老的雕版,應該是《般若八千頌》,刻制于1229年,但是聽喇嘛講,還有雕版誕生于更古老的朝代,只是我沒有記住朝代的名字。《般若八千頌》在德格第十代土司、第四世法王松杰登巴時代,以梵文、烏爾都文和藏文三種語言刻制完成。而最著名的《甘珠爾》和《丹珠爾》兩部經書,則是在十八世紀刻制完成的。我悄悄抽出一塊雕版,雙手捧著它,發(fā)現(xiàn)它居然很沉,我甚至懷疑它的材料是否來自人間。那上面有遙遠時代的語言,在經歷了漫長的時間之后,它的語氣絲毫未有更改。我有些感動——即使我們對印經的文字一竅不通,我們仍然感動。我決定去讀經。經文具有一種穿透人心的力量。每個人在細密的經文面前都不可能無動于衷。回到北京以后,一定把漢語經書找來,讓那些安詳的文字,像米粒一樣,在我的身體里靜靜融化。
我的朋友、生于德格的藏族作家茨仁唯色說:“假如我能夠,我愿意化身為這印版上的一個字,愿意湮沒在這千千萬萬的印版之中,不為別的,只為了變成誰的密碼,讓誰把我放在這里,一直留在這里,留在我的德格老家。
“——這些印版,似乎讓我看見了一個美妙的前景。我對來世的承諾,再好不過如此。”
五
可惜我沒有目睹匠人們雕刻印版的場面。據說,那種場面驚心動魄。每當清晨,印經院的殿堂就如同一個布景華麗的巨大舞臺,被晨曦的追光照亮。許多匠人會在不同的作坊中分組排開,他們長長的影子拖在老舊的木質地板上,在時光中不聲不響地移動:當影子像日晷一樣旋轉到相反的位置時,就會有許多經文在瀟灑的造型中脫穎而出。經版從書寫到刻制,大約需要十五道工序。縣志上說:
“印版材料多選擇紅葉樺木。每年初,印經院造計劃交土司以派差的方式向差民下達當年應繳納印版材料數額。秋后,德格、白玉、江達境內的差民便上山伐木,將剛落葉的紅樺砍倒,截去節(jié)疤,選較順直無疤的樹干截成數十至一百多厘米的若干段,再將木塊劈為厚四至五厘米的板塊,然后將板塊就地上架,點微火熏烤。待木板干后,差民們用人背牛馱的方式將木板運到下山,放進糞池中漚制一個冬天,到次年四月,將木板取出水煮,再烘干,推光刨平。至此,印版的初胚加工告成,差民們將版胚馱運至更慶,經印經院管理人員嚴格驗收后,這些經久耐放、堅韌皆具的木板才能供刻版之用。”
而一部經書,常常要刻幾萬塊經版。那部《長壽經》,就是江達工匠花了三年時間才刻出來的。印經院從刻版、造紙、印刷到裝幀,完整地保持著傳統(tǒng)的印刷工藝與程序,所以從印刷史的角度上,被稱為“活著的博物館”。比如制作模板,通常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由書法家將文字直接用筆反寫在胚板上,交付工人雕刻;另一種則是將透明度較好的紙模反貼在胚板上,雕刻工人再依據紙模上的筆跡進行刻制。無論怎樣,整個過程無疑是一次漫長而艱險的旅行,容不得絲毫差錯。這使我想起“文革”中一個故事(我有意把它寫入我的小說中):一個造反派為了懲治一位“臭老九”,給他強加了一種懲罰,讓他把報紙上的字,一個一個剪下來。這當然是一種頗具創(chuàng)造力、同時也最為殘酷的懲罰。但對于受罰者而言,它是必須完成的任務,是“組織決定”。為此,他以認真細致的態(tài)度,用了大半天的時間,把報紙上的字,一個一個均勻地剪下。當他勝利完成任務之時,又接到一項新的任務——將剪下的字,按照原來的順序,一個一個粘回去。
這是一項足以讓人發(fā)瘋的酷刑。我想到它,是借助于刻版的提示。后者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并非僅僅是一項機械的工作,同時是匠僧們的信仰寄托,在手指與經文之間,存在著那么醇厚的關系——它們彼此信任,而不是像那位受刑者,與他的“任務”,相互敵視。或者,刻經本身,也成為一種修行方式。它不是刑罰,每個匠人都在刻刀的回環(huán)曲折中完成內心的祈禱。
八十歲的向巴是印經院最老的工人,過去負責經文的印刷,年紀大后,他無法割舍這份干了近四十年的工作,被調到相對輕松的顏料加工組。昏暗的房間里,兩根木杵、一對石臼陪伴著兩位老人,他們一邊口誦經文,一邊手握木棍慢慢地磨制朱砂。他們動作緩慢,但他們磨制的朱砂,顆粒微小,配制出的顏料也格外精細。由于價格昂貴,制作費時,朱砂這種高級顏料,只有在印制珍貴經文時才會使用。向巴老人原本是可以回家養(yǎng)老的,兒女們也愿意他回家享福,可是他認為這是在積公德。他的工作態(tài)度得到了神的贊許——在印經院干了幾十年活,他從未生過病。
工匠與經印院,互相創(chuàng)造著對方。向巴從不囂張,但沒有人比他更幸福。宗教使他內心安然、歲月無驚,而故鄉(xiāng)德格,則是他手中的一塊雕版,因他虔誠的手指而華美、親切和永恒。
六
即使今天,我在北京的春天里回憶德格,我依然無法忘記它的氣息。我曾經說過,記憶,常常是以味覺的形式存在的,它甚至比其他任何感覺都更加頑固和準確。那是一種由酥油、梵香、紙張、木板、顏料、油墨、防腐劑等諸多物質混合而成的氣味,奇異無比。這種氣味,有一種攝人魂魄的力量。我想,兩情相悅有一個不被言及的隱秘動機,就是彼此之間身體氣息的誘惑,以及因此帶來的某種化學反應。妖嬈的誘惑不僅來自視覺,同時也來自嗅覺。以此比喻印經院顯然失敬,我只想借此強調氣味的秘密價值——我們可能在視覺面前保持理性,而在氣味面前卻心馳神往欲罷不能。德格印經院的氣息不是刻意營造的,而是在漫長的時間中釀造出來的,是這座古老寺院綜合氣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我們對于宗教的迷戀,想必也包含了許多不易察覺的心理因素。它不是一種直白的芳香,而是如同建筑、木器的包漿一樣,隱晦、幽暗、若有若無地釋放它的光澤。經卷的紙頁,是以德格阿須草原上一種名叫“阿交如交”的植物制成的,它的學名頗有文學色彩,叫“瑞香狼毒”,是一種藥材。這種藥材在經過清洗、切剝、蒸煮、捶打、出漿、抄紙、晾曬等一系列程序之后,變成色澤微黃的“藏紙”。在陽光下,它植物的紋路隱約可見。手指捻動這種紙印制的經卷,輕輕念誦紙頁上的神秘符號,每個誦經喇嘛的姿態(tài)都那么風神古雅,像壁畫上的人物。而“瑞香狼毒”本身具有的藥用價值,不僅使古老經卷避免了蟲蛀鼠咬,而且保佑喇嘛們目明心清,不受眼疾之苦。而這一切,都包含在它隱約的芳香中,一種來自大地深處的香氣,在屢經輾轉之后,變作紙頁,與佛經上的優(yōu)美文字相呼應,在人們的心頭駐足。
在這種氣味面前,攝影已經束手無策——它可以記錄有關德格的一切影像,只有在氣味面前,它無能為力。于是我們發(fā)現(xiàn),當攝影企圖把世界的一部分提取下來的時候,那部分已經與世界脫離了關系,它無法“回去”,而是一個新的入口,有它自己的命運與生涯。如同一個孩子的出生,不是為了復制出母親的經歷。蘇珊·桑塔格所說:“攝影既是一種確證經歷的方式,同時也是一種否定經歷的方式。”當我們企圖把記憶托付給某種載體的時候,我們發(fā)現(xiàn)那種載體并不可靠。由此我想到另一個問題:雕版上浩繁的文字,如今不是可以記錄在一張薄薄的光盤上嗎?這樣,我們不就可以把古老的印經院隨身攜帶了嗎?晶瑩剔透的光盤,是否可以取消印經院的存在價值呢?我想,它或許可能取代印經院工具性的一面,但無法取代它情感性的一面,無法將有關印經院的所有歷史信息囊括其中。網絡的普及,不能斬斷人們的朝拜之路。如同對待攝影一樣,我們不能輕信一張光盤的許諾,在印經院這個繁復神秘的實體面前,它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在這個技術肆虐的時代,我們必須對技術保持警惕。它不是萬能的上帝,也無法取代原有的神。在技術時代里,我們能夠依賴的事物只有記憶自身——只有它,能夠保全事物原有的格局。遺忘并不可怕,遺忘是因為你已不需要它而將它暫時擱置,那些被遺忘的細節(jié),都會在你最需要它的瞬間意外地提取出來,像從前一樣完整、清晰和生動。所以,在幾千公里以外的北京,我覺得德格并沒有遠去,它那種繚繞的氣息仍然包圍著我,把我?guī)Щ啬莻€芳香彌溢的夜晚。
我跟在高顯銀的后面,走到這座回字形建筑的天井中。夜色已呈深藍,玲瓏透徹,在夜光中,印經院看上去更像一團幽暗的火,兀自燃燒。我站立在印經院的中心,寺廟像一件溫暖的僧袍,裹在我的身上,讓我覺得無比安詳、靜穆。那是一種幻覺。寺廟是培養(yǎng)幻覺的地方,但在寺廟的經驗里,那一切都是真實的,而我們所謂的現(xiàn)實,只是一場拙劣乏味的虛構。
(本文摘自《紙上的故宮》,祝勇著,長江出版集團長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定價:36.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嬋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