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長篇小說的現(xiàn)實主義書寫:文學就是介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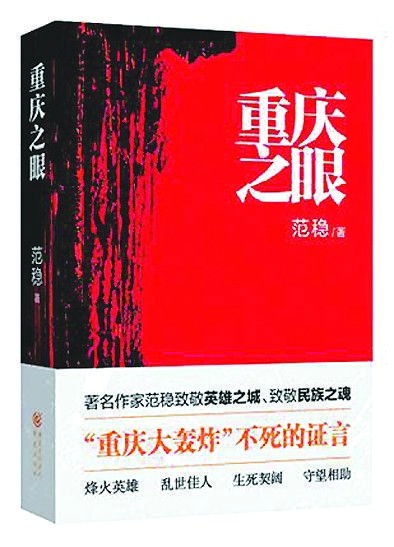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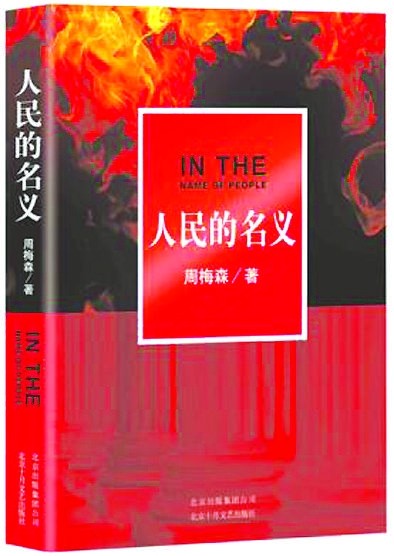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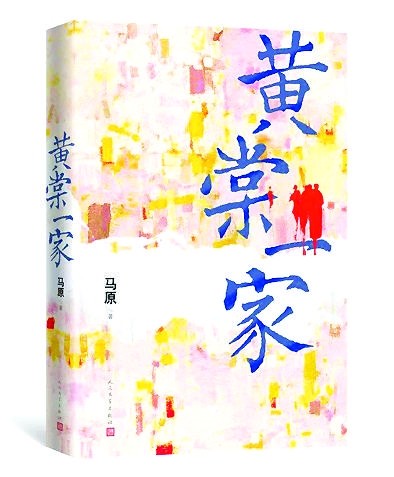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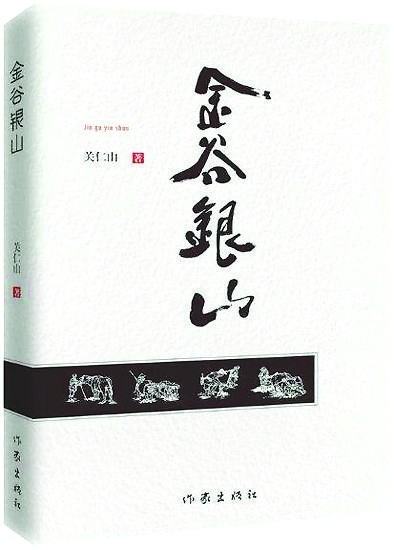

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曾一度在新潮小說的沖擊下式微,這不可避免地導致文學與現(xiàn)實生活的疏遠。這種弊病引起不少作家的警覺,近年來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深度介入生活與現(xiàn)實主義復興的態(tài)勢,拉近了文學與生活的距離。當下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總體特征是以現(xiàn)實書寫為主,作家深入生活,深度介入現(xiàn)實,對人類面臨的現(xiàn)實處境有著細微深刻的描摹,這種書寫態(tài)度顯現(xiàn)出現(xiàn)實主義的磅礴力量,這也正是作家對普遍被詬病的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脫離現(xiàn)實的有力回應。具體表現(xiàn)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戰(zhàn)爭書寫有了新的動向,出現(xiàn)了很多新的篇章,戰(zhàn)爭歷史題材書寫既緬懷歷史,更回應當下;二是批判現(xiàn)實主義依舊流行,作家們不光介入現(xiàn)實,還對現(xiàn)實進行批判,具有新的力度;三是對城鄉(xiāng)空間進行深入挖掘,城鄉(xiāng)書寫有了新的思路;四是除了對現(xiàn)實物質(zhì)世界的關注,作家們對心靈世界的探幽進行了新的嘗試,出現(xiàn)了很多探討靈魂世界的作品,通過對心靈世界的觀察,寫出人性的多樣和復雜;五是主旋律書寫有了新面貌,對重大現(xiàn)實事件都有文學的表達;六是一些反現(xiàn)實的現(xiàn)實書寫也通過作家創(chuàng)造的現(xiàn)實對時代予以表達。總之,2017年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題材紛呈,但都深深扎根土地,處處介入生活,全面圍繞現(xiàn)實展開,反映了時代發(fā)展的新問題、新出路、新面貌。在現(xiàn)實描摹中體現(xiàn)了人性書寫的豐富性與多樣性。
一,戰(zhàn)爭歷史書寫有新的切入點和視角。2017年戰(zhàn)爭書寫集中爆發(fā),以戰(zhàn)爭為主題和以戰(zhàn)爭為背景的作品集中呈現(xiàn)。戰(zhàn)爭書寫一直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大宗,2017年的戰(zhàn)爭小說在延續(xù)之前的書寫模式基礎上有所突破,很多作品寫出了戰(zhàn)爭小說的新篇章和新高度,與一般作品單純的仇恨情感抒發(fā)和平鋪直敘的描寫有了很大差異。戰(zhàn)爭書寫融進愛情、人性、歷史、文化等多重元素,內(nèi)容更多,敘述線更密,韻味也更豐富。趙本夫的《天漏邑》中的主要線索是民間的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個體愛恨情仇;張翎的《勞燕》以戰(zhàn)爭為切口書寫女性命運,探尋人性的復雜性;范穩(wěn)的《重慶之眼》則在直接書寫“重慶大轟炸”的大背景中展現(xiàn)普通人的愛恨情仇以及當下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王雨的《碑》、李明忠的《安居古城》與之相仿。嚴歌苓的《芳華》從側(cè)面寫到了戰(zhàn)爭,戰(zhàn)爭書寫與人性反思結(jié)合在一起。戰(zhàn)爭書寫還出現(xiàn)了新的切入點和新的視角。葉兆言的《刻骨銘心》、陳正榮的《紫金草》、陶純的《浪漫滄桑》都是如此。除了戰(zhàn)爭書寫,很多歷史題材的寫作也有新的突破,這些作品大都是透過歷史回應當下。張新科的《蒼茫大地》、劉慶的《唇典》、宗璞的《北歸記》、修白的《金川河》、肖克凡的《舊租界》等都將歷史經(jīng)驗予以重寫,對當代生活有警示作用。總體來看,這些戰(zhàn)爭歷史題材的書寫較之以前的書寫達到新的高度,尤其是宏大敘事中的小情致等細節(jié)描寫十分精致。
二,現(xiàn)實批判體現(xiàn)作家對社會的關切。深度介入現(xiàn)實仍然少不了批判,現(xiàn)實批判書寫是2017年度長篇小說的特征之一。介入現(xiàn)實并不僅僅是呈現(xiàn),很多作者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對現(xiàn)實進行了批判。2017年的長篇小說對官場腐敗、高校怪相、社會亂象都進行了深度書寫,對現(xiàn)實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周梅森的《人民的名義》將反腐小說提高到新的階段,隨著同名電視劇的播出,關于反腐題材的作品也火起來了,從高官到底層官員腐敗落馬都有所展現(xiàn),進行人性的深度開掘;李佩甫的《平原客》、楊少衡的《風口浪尖》、錢佐揚的《曇花》涉及高官腐敗;馬笑泉的《迷城》、李駿虎的《浮云》、紅日的《駐村筆記》則涉及基層腐敗;紅柯的《太陽深處的火焰》將筆觸伸向高校,揭示高校的腐敗現(xiàn)象。馬原的《黃棠一家》、劉震云的《吃瓜時代的兒女們》都用文學的方式對時代進行了嚴肅的批評。這些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長篇小說的寫作無論是采用現(xiàn)實的直接描摹,還是用荒誕、反現(xiàn)實、非自然等藝術筆法,抑或是使用黑色幽默、非虛構等技法,骨子里都是立足于現(xiàn)實,深度介入現(xiàn)世生活的。小說不可能是絕對的零度風格,而是具有敘事倫理,無法擺脫道德說教的一面。對現(xiàn)實問題的關切實際上也顯示出作家們的一種敘事倫理,批判也好、啟蒙也罷,都是對生活美好一面的期許和向往。
三,城鄉(xiāng)書寫探尋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發(fā)展之道。一直以來,中國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都是作家筆下關注的對象,城鄉(xiāng)空間變奏成為21世紀以來文學表達的重要母體之一。這種對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的書寫既有矛盾展現(xiàn),更有和解之道。近期的城鄉(xiāng)書寫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那就是并非呈現(xiàn)二元對立,而是描繪各自的優(yōu)劣,探尋城鄉(xiāng)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發(fā)展之道。城鄉(xiāng)空間書寫既有鄉(xiāng)村風俗的生動畫卷,也有大都市的紙醉金迷帶給鄉(xiāng)村的沖擊,既有日常生活的描摹,也有人性深處的反思。2017年的長篇小說中有多部作品涉及這一書寫。《平原客》既是反腐小說,也是一部探尋城鄉(xiāng)關系的作品。梁鴻的《梁光正的光》塑造了梁光正這一中國普通農(nóng)民形象,通過他的尋親之路,回顧中國農(nóng)村的變遷史,也書寫了農(nóng)村面臨的現(xiàn)狀,特別是對中國式父子(女)關系的書寫極具典型性。陳倉的《后土寺》延續(xù)其農(nóng)民進城的書寫。趙獻濤的《村官》反映農(nóng)村歷史變遷。曉航的《游戲是不能忘記的》以烏托邦的形式書寫了一個虛擬城市的種種故事。城鄉(xiāng)生態(tài)環(huán)境是城鄉(xiāng)空間的基本立足點,城市化進程中對鄉(xiāng)村生態(tài)的破壞是顯而易見的,小說對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帶給人類的傷害也有所體現(xiàn),鐘正林的《水要說話》、關仁山的《金谷銀山》對此有所表現(xiàn)。
底層寫作是城鄉(xiāng)書寫的另一選題。底層是城鄉(xiāng)一個重要的空間場域,關于底層的書寫也是關于城鄉(xiāng)空間的探討。賀享雍的《盛世小民》、李亞的《花好月圓》、任曉雯的《好人宋沒用》、李師江的《中文系2:非比尋常》、陳彥的《主角》、姚鄂梅的《貼地飛行》、麥子楊的《可口與可樂》、賀享雍的《大城小城》等作品,既是關于底層的書寫,也是關于城鄉(xiāng)空間的書寫。許多新作品聚焦到這一點上,通過書寫婚姻關系來透析整個社會經(jīng)濟文化以及精神層面的變遷。王旭東的《復調(diào)婚姻》、張五毛的《春困》、魯敏的《奔月》、陳慶予的《我是你的誰》、馬拉的《思南》、喬葉的《藏珠記》等都是這樣的文本。此外,還有很多文本不是以此為主題,但也涉及婚姻關系的思索。城鄉(xiāng)空間書寫細致描摹了一幅幅眾生生存百態(tài)圖,既有生存空間、生存環(huán)境、生存狀態(tài)描寫,也有情感、倫理、精神的書寫。蕓蕓眾生的生存空間、奮斗打拼、情愛婚戀、精神面貌在這些作品中得到了有力的表現(xiàn),這也正是文學拉近與現(xiàn)實的距離、深度介入生活的最好例證。
四,心靈探幽探詢個體心靈密碼。除了對物質(zhì)層面的現(xiàn)實關注,很多作品關注人的精神層面,探詢靈魂深處的秘密,很多作家對心靈世界的探尋關注進行了新的嘗試。不少作品從形而下走向形而上,探詢個體心靈密碼。上文提到的城市小說《游戲是不能忘記的》里很多內(nèi)容涉及心靈救贖與懺悔。石一楓的《心靈外史》在這一領域的書寫較為典型。陸天明的《幸存者》講述了一代人在時代浮沉下的追求與探索,更是一部關乎心靈世界的小說,李陀的《無名指》探詢?nèi)说男撵`問題。徐兆壽的《鳩摩羅什》則將筆觸伸向佛法。默音的《甲馬》是一部關于歷史的小說,更是一部心靈史。在交叉敘述的三段時空中,謝曄一路找尋,既是找尋逝去的時間,也是尋求當下的心靈慰藉。很多心靈探幽的作品走向人性探尋的縱深處。幾乎所有題材的小說最終都將筆觸伸向人性深處,還有很多小說直接立意于此。安昌河的《羞恥帖》最重要的主題是對人性的憂患和呼喚。龐余亮的《有的人》有多條故事線,最終復歸到人性這里。作者用多種手法多種人稱以及多種身份的交叉敘述還原了一個活生生的父親,充滿人性的悲涼,也豐盈了人生的光華。須一瓜的《雙眼臺風》用精致的細節(jié)構筑起精彩絕妙的故事,同時也不斷伸向人性的深處,將人性探詢縱深化。
五,主旋律書寫呈現(xiàn)新態(tài)勢。宏大題材的主旋律書寫在2017年也出現(xiàn)了較多作品。對“一帶一路”、“香港回歸”、“精準扶貧”等重大現(xiàn)實事件都有文學表達,主旋律書寫呈現(xiàn)出了新的態(tài)勢。巴隴鋒的《絲路情緣》是中國絲路題材長篇小說的先聲之作。朱秀海的《喬家大院》(第二部)描繪了一個風云際會的大時代,深刻發(fā)掘中國商道誠信經(jīng)營、以商救國、以商富民的文化精神。張強、李康的《我的1997》反映香港回歸后20年的歲月變遷。精準扶貧書寫是2017年主旋律書寫的一大亮點。紅日的《駐村筆記》將筆觸伸向具體的精準扶貧場面。小說以日記的形式講述毛志平一行人駐村扶貧的日程,反映了如火如荼的扶貧面貌。小說有矛盾、有沖突,有思索,更有千方百計解決問題的決心與努力。周榮池的《李光榮下鄉(xiāng)記》講述青年干部李光榮下鄉(xiāng)進行文化扶貧的故事。關仁山的《金谷銀山》既是生態(tài)主題的小說,也是一部扶貧題材作品,描寫了白羊峪人民通過辛勤勞動脫貧致富的生動畫面。后現(xiàn)代社會削平深度,文學仍在堅守,具有時代感的宏大書寫是最具深度的表現(xiàn),弘揚主旋律,謳歌正能量的作品不斷涌現(xiàn)。
六,反現(xiàn)實書寫體現(xiàn)作家的藝術探索。現(xiàn)實主義的源流是對現(xiàn)實生活的一種關注和焦慮。秉持現(xiàn)實主義精神也會有“反現(xiàn)實”的書寫,這是因為作家、藝術家可以創(chuàng)造出藝術層面的現(xiàn)實。2017年的很多作品是現(xiàn)實主義題材書寫,但也都呈現(xiàn)出了反現(xiàn)實的一面。《勞燕》的敘述者是亡靈;《藏珠記》的女主人公從唐朝活到現(xiàn)在;王旭東的《復調(diào)婚姻》出現(xiàn)了劉光華現(xiàn)世的一家三代婚姻愛情故事和他死去后在陰間的“一生”這兩條線索;《太陽深處的火焰》仍有紅河一貫的神性書寫。
反現(xiàn)實的書寫往往以寓言的形式呈現(xiàn)。趙本夫的《天漏邑》情節(jié)奇譎、人物生動。整個故事懸疑叢生,充滿了非自然敘事與反現(xiàn)實書寫,創(chuàng)建了一個關于自然與文明的寓言式作品。盧一萍的《白山》是一部關于歷史的寓言式書寫。非自然敘述雖然有反現(xiàn)實的一面,但仍是立足于現(xiàn)實的書寫,是藝術創(chuàng)造的另一現(xiàn)實。
韋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指出,真正的小說一定是現(xiàn)實主義的。無論是戰(zhàn)爭歷史、城鄉(xiāng)空間、現(xiàn)實批判,還是心靈探幽、反現(xiàn)實的現(xiàn)實主義題材書寫,都指向現(xiàn)實、指向人性,是人性探詢的多樣化、縱深化書寫。這些書寫都是深度介入的姿態(tài),將文學從虛無縹緲的空中樓閣漸漸拉回現(xiàn)實。對現(xiàn)實的描摹自然是作家們最主要的功課,這是希望文學履行它的介入功能。當然,并不是說只要深度介入現(xiàn)實的就是成功的作品,文學不是社會學文本,很多作品成為了社會學文本,失去了美學性和藝術性。部分作品踏上主題先行的老路,人物類型化臉譜化,社會性蓋過了文學本身的屬性。現(xiàn)實書寫并非對生活的原樣復制,而是提煉出生活性。所有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者,同時都是偉大的形式主義者。這種生活性,讓作家超越生活,成為生活自由的仆人。當一大批作家進行文體實驗、技法創(chuàng)新、模仿西方之后,開始了自我更新與完善。后現(xiàn)代小說遠離生活,陷入自娛自樂、虛無縹緲的怪圈,現(xiàn)實主義正是對此有力的反駁。2017年的小說全面介入生活,現(xiàn)實主義并非只是一個文學術語、一個理論概念或者一種文化思潮,而是對現(xiàn)實、對生活、對社會,包括對精神層面的深度介入與直接打量。無論如何,這些作家們已經(jīng)意識到這些問題,開始切入生活,進行具有本土意識的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一種接地氣的寫作態(tài)勢。現(xiàn)實書寫漸趨常態(tài)化,對現(xiàn)實的深度介入與關切讓現(xiàn)實主義文學漸漸走上正途,發(fā)揮出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