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紙墨是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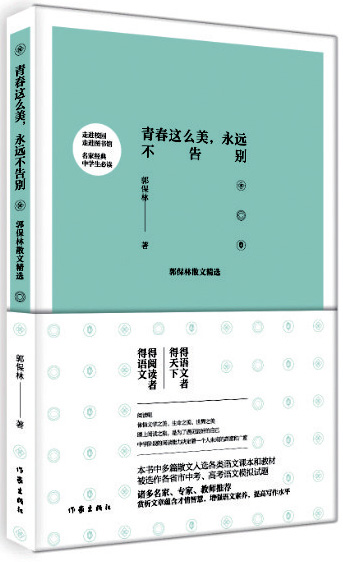
一
茫茫神州,物華天寶。每一個地域都以自己鮮明而富有特色的文化瑰寶,熱情地、踴躍地奉獻于華夏文明的發(fā)展,為此作出積極的貢獻。皖地表現得更為突出。
這就是筆墨紙硯,這也是皖地的名牌,享譽海內外。
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幾經以夷變夏的風狂雨驟,卻沒有改變華山夏水的基因——古老的象形文字。大江南北,盡管方言口音相異,但倉頡創(chuàng)造的古老的文字把中華各民族緊緊地凝聚在一起。歐洲蠻夷南侵,古羅馬文明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便是拉丁語文被肢解了。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們,高舉上帝之鞭,裹雷挾電,縱橫馳騁,歐亞四十國袞袞王公,王冠落地,身首異處。成吉思汗建立了橫跨歐亞大蒙古帝國,版圖之遼闊前空千古。后來,當他的孫子忽必烈定鼎中原,狼煙俱凈,烽火熄滅,以勝利者的姿態(tài)威風凜凜地站在大都城頭上,欣欣然、陶陶然之時,他的目光觸及華山夏水,驀然間倒抽了口冷氣:乖乖,茫茫中原大地,到處浸滿了儒家文化的汁液,甩不掉,洗不凈。他心怵了,膽怯了,南宋可滅,古老的方塊字不可滅!這橫平豎直、一撇一捺,簡直像魔方似的弄得你神魂顛倒。無可奈何,他只好乖乖地洗去手上的血垢,恭恭敬敬請來漢族太傅太師,教子孫從小學生啟蒙開始,老老實實地坐在案前,規(guī)規(guī)矩矩地一筆一畫地描起紅來。
大清帝國的金戈鐵馬,踏破長城雄關,推翻了龐大的大明王朝,最后把南明的小皇帝趕進大海,溺水而死,但卻趕不走一個方塊字,文房四寶,他動不得一寶。同樣遇到麻煩,愛新覺羅氏的子孫們那雙握長劍、拉強弩的手,十分笨拙地握起一管小小竹筆,面對潔白如雪的宣紙,兩眼茫然,不知所措,不得不在漢族大臣指點下,歪歪扭扭地批示奏章。于是放下架子,年年月月磨煉。筆磨人,人磨筆。筆墨紙硯終于征服了這喝馬奶子酒、吃手抓肉的北方強悍民族,使他們在橫平豎直中規(guī)矩起來。由浮躁變得沉靜,由蠻野變得文雅。他們尊崇儒學,師承漢典,苦讀線裝書,護蔭翰林院,詩才書藝,風騷朝野。他們的野性被象形文字束縛起來,他們的悍氣被筆墨紙硯收斂起來。一個漂泊的民族秉性發(fā)生變異,白山黑水間女真人后裔的生命和靈魂得到了洗禮和升華。
筆墨紙硯代替戰(zhàn)刀和長劍。一個疆域遼闊的大清帝國成了漢字縱橫、筆墨馳騁的天下,詩書經史成了這個風雪里出生在馬背上長大的民族的啟蒙課本。
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洶涌澎湃的二十五史,中華文化發(fā)展史,燦若群星的文人騷客,哪個不是用筆墨紙硯創(chuàng)造的輝煌?他們筆飛墨舞,滿紙煙云,寫下震撼千古的華章,完成了光照千秋的人格造型。
甲骨文不說,自竹簡絹帛(這是紙的前身)以來,五千年的漢語文字就用一管竹筆一硯墨汁,寫出千秋華章。莽莽大野,荒荒大漠,皇皇戈壁,到處都眠著用筆墨紙硯書寫的古老故事。
筆墨紙硯寫下了風雨蒼茫的千古春秋。老子、莊子、孔子一代圣賢圣哲,君子好逑的《詩經》,魂兮歸來的《楚辭》,半部《論語》治天下,渺渺的漢宮秋月,高山流水的琴韻,魏武的老驥伏櫪之志,無韻離騷的《史記》,書圣王羲之的《蘭亭序》,草圣張旭的狂草,李太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蘇東坡“大江東去”的豪情,岳武穆面對瀟瀟江雨的仰天長嘯,文天祥的丹心汗青,名垂青史的《永樂大典》,前空百代的《四庫全書》,還有十年寒窗苦、一把辛酸淚的紅樓夢痕……哪一部不是筆墨紙硯的歌飛色舞,淋漓盡致的瘋笑癲哭!
再看那一幅幅書畫,開拓了精神世界的廣闊空間:滴露研朱點《周易》的冷哲莊嚴;風雨痛飲《離騷》的激烈浪漫;三百篇《關雎》之唱孕育化衍出詩的狂想,詩的天真,詩的激情;文人雅士“度白雪以方潔,干青云而直上”的飄逸和悠遠,將詩心托付于翰墨,寄興肝腸于紈素。筆鋒在撇捺之中、橫平豎直之間縱橫馳騁,孕育出炎漢盛唐文化的璀璨,隆宋治明的華彩樂章,為古今開萬世之繁華,為泱泱中華賡續(xù)五千年綿綿之煙篆。
浩浩翰墨鑄就了一個民族的心靈史、文化史。
唐代女詩人薛濤曾吟詠筆墨紙硯:“磨捫虱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默默,入文廟以休休。”
濃墨塑鑄的風景,矗立地球東海岸的古大陸上,托起華夏精神的太陽。與其說筆墨紙硯是書寫文化的工具,不如說筆墨紙硯是一種精神,是它的涵養(yǎng)培育了一個民族儒雅、大氣、剛毅、莊嚴而蓬勃向上的精神,中華民族正是憑著這精神,開掘了敻敻華夏文明之巨流,洶涌澎湃,濤飛浪卷。東方古大陸不沉,方塊文字不老,筆墨紙硯將伴隨一個民族走向永遠。
二
我走進宣城,走進筆墨紙硯的故鄉(xiāng)。
宣城造紙業(yè)歷史悠久。早在唐代就用檀樹皮和稻草搗制紙漿,制成宣紙。所謂青檀,是一種落葉喬木,系榆科,只在皖南的涇縣(古屬宣州)、宣城等地區(qū)生長。
在進入五代后,宣紙紙質比起蜀紙尚有差距。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父子,酷愛詩詞書畫,自然酷愛筆墨紙硯,刻意書畫工具的精良,便派紙工去蜀學習,或請蜀地紙工來皖南傳經送寶。這種“走出去,請進來”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宣紙的質量。“既得蜀工,使行境內,而六合之水與蜀同,遂于揚州置物。”經過改良的宣紙,紙質有了很大的變化,光潔柔軟,極富有彈性、韌性、吸水性,頓時聲名鵲起,成了市場的名牌、搶手貨。李后主倍加喜愛,每當宣紙進貢,他都用手細細撫摸,仔細辨識,愛不釋手,贊不絕口。
李后主《書評》云:“善書法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蘊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于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氣而失于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驚急無蘊藉態(tài)度。”李后主書法的藝術鑒賞力由此可見。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他仍然陶醉在藝術如夢如幻、美麗的氛圍中。
古史記載倉頡造字,而“天雨粟,夜鬼哭”,可謂驚天地而泣鬼神。
中國的象形文字,有許多文字從結構上看來匠心獨具,本身就是一種超絕的藝術品,這是千年古國的國粹。譬如“靜”就是極美的字,一旁是“青”,一旁是“爭”。“青”者蘊含著激情洋溢的生命力,“爭”又體現出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的奮斗精神。“靜虛”“靜能致遠”,闡述了天地間一個大哲理,似乎自然和人生充滿了催人奮進、騰天躍地又不事張揚的神秘力量:奮斗和超越,希冀和信念所凝結成的感悟,一種莊嚴肅穆的精神,崇高的詩意。
宣紙上燃燒著詩人的靈感。
宣紙上奔騰著藝術家的激情。
宣紙上有著皇帝老兒威嚴的圣旨。
宣紙上有封疆大吏六百里的“加急”。
……
畫之神韻,詩之靈性,民族之文采,古國之風貌,皆現于尺素。
千秋紙墨,是中華民族有聲有色的歷史,從漢魏兩晉時代“博哉四庚,茂矣六郗,三謝之盛,八王之奇”的壯觀場面開始,無論浪漫的風流雅士,狂放的文章俊彥,落魄的士子,還有失意的皇帝,漂泊的隱者,得道的高僧……都借助紙墨,釋放他們的才情,馳騁他們的靈感,放牧他們的思想。思接千載,神游八極,昭示他們內心世界的高遠和幽深。這是中華民族文化發(fā)展史上永恒的風景。大漢的樸拙粗獷,兩晉時代的典雅秀逸,盛唐的放浪任性,宋朝的瀟灑風流……他們的得意和失落,怪誕和卓犖,悲歌和歡欣,或生與死,苦與難,沉與浮,意志和信念,曲曲折折,蹀蹀蹣蹣,一路走來,形成一個民族的精神財富和生命符號。
紙墨鑄就了一個民族靈魂的偉岸和莊嚴。
李后主將宣紙命名為“澄心堂紙”,這怕是中國商業(yè)史上比較早的商品注冊。
而宣筆又是宣城一大瑰寶,是宣城人超越時空的驕傲。
這是上帝的恩賜還是天地之造化?正是一管兔毫筆,柔軟如泥,又堅硬如鐵,是它驅石鼓、鐘鼎、甲骨、秦權、詔服,刀幣文字,或剛毅奔放,或嫵媚婀娜,或樸拙雄健,那一個個漢字因它們而精神了,瀟灑了,靈性了,有了生命和靈魂!
宣筆產于涇縣境內,迄今已有兩千多年歷史,被歷代譽為“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而馳名中外。中國的歷史是毛筆書寫的歷史。毛筆原比歐洲的鵝翎筆不知先進多少倍。當歐幾里得在羊皮上演算幾何習題時,當塞萬提斯用鵝翎筆描繪堂吉訶德?lián)]動著驕傲的長矛,為夢中情人,同風車大戰(zhàn)的故事時,當莎翁用鵝翎筆寫出羅密歐與朱麗葉經典的愛情悲劇時,中國已用精制的狼毫筆、兔毫筆書寫山河了。宣筆與宣紙一樣成為宣城值得驕傲的名牌。宣筆的制作迄今已有兩千五百多年歷史了。據韓愈《毛穎傳》記載,公元前230年,秦大將蒙恬南下時,途經中山(今涇縣一帶山區(qū)),發(fā)現這里兔肥毛長,便以竹為管,在原始的竹筆上改良毛筆。到了大唐帝國,涇縣成了全國制筆中心,自然皇上用的御筆也產自這里。涇縣就是被李白稱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的皖南小縣,屬宣城郡,也就取名宣筆。
毛筆在中國古代稱謂不一,說法各異。據史記載:戰(zhàn)國時期,楚國稱筆為“聿”,吳國稱筆為“律”,燕國稱筆為“弗”,直至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才統(tǒng)稱為筆。史稱“恬筆倫紙”,即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筆字拆開,上頭為竹,下頭為毛,秦定為筆,這是中國造筆史上一大革命,它奠定了中國毛筆生產的根基。毛筆文化從此揭開了輝煌的篇章。
中國宣筆傳至漢代,制作技藝得到進一步發(fā)展,筆身裝飾十分講究,據清代唐秉均《文房肆考圖說》:“漢制筆,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極為華麗矣。”魏晉時期,中國宣筆制作工藝又有所改進,此時對名家制筆取毫、制管、鑲飾均有嚴格要求。主要是采秋毫之穎,削文竹為管,從而達到“寫文象于紈素,動應手而從心”之奇特效果。
宣筆,那么一綹平平庸庸、纖細柔弱的兔毫,當它們化為不足盈寸的筆鋒時,便能落筆起風雷,墨潑潤天機;便能書寫千秋文章,一管小小的竹筆能卷起萬重巨瀾,能攪起九天狂飆,能點燃狼煙滾滾,戰(zhàn)火紛飛,能使萬家墨面沒蒿萊,能使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一管弱筆能勝十萬戈矛,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筆伴絲竹舞,意隨翰墨香。它以搖曳的千姿百態(tài)、濃墨重彩地繪出東方古大陸的歷史大風景,這是人類文明的奇跡!
墨的發(fā)明大約要晚于筆。史前的彩陶紋飾、商周的甲骨文、竹木簡牘、綿帛書畫等到處留下原始用墨的遺跡。文獻記載:古代的墨刑(黥面)、墨繩、墨龜(占卜)也均曾用墨。經過漫長的歲月,終于出現了人工墨品。這種墨大多是松煙和水膠的混合物。據史料記載,早在漢代就有人用松煤制墨,到了唐代制墨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色澤黑亮有光澤,以紙墨為載體的中國獨具特色的古老書畫,從漢代就覆蓋了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化發(fā)展史。文人書畫把東方哲理、人文、詩學精神涵蓋其中,在中國漫長的農業(yè)社會條件下,這種文化精神涵養(yǎng)并滋潤了一個民族的靈魂,這是一種古老的文明,一種嚴謹優(yōu)雅的人生。書畫家利用筆墨紙硯揮灑自己的激情,他們的筆墨造型、情趣、筆線的力感和韻味,墨色的層次和變化,在灑脫與豪放中,在婉約與細膩中,在點、擦、皴、染中,盡顯自己的真性情。
(《青春這么美,永遠不告別——郭保林散文精選》,郭保林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