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瑤琴:世界華文小說的家國情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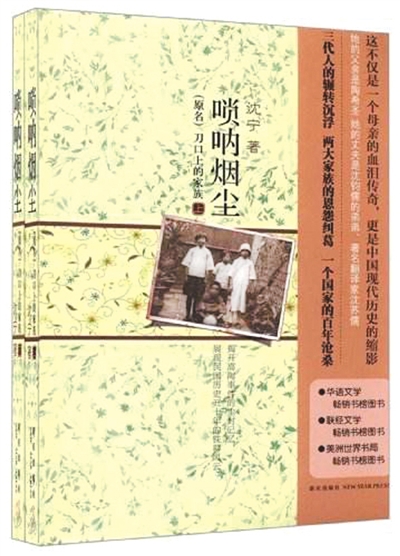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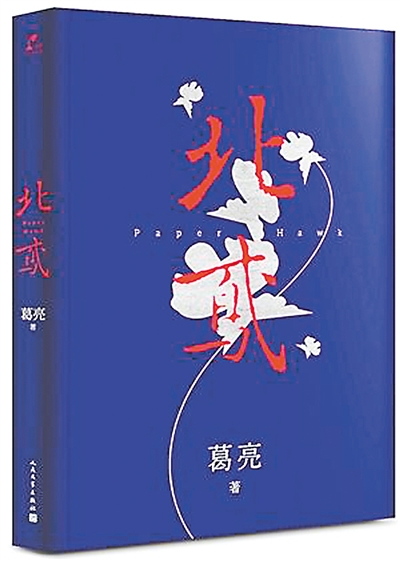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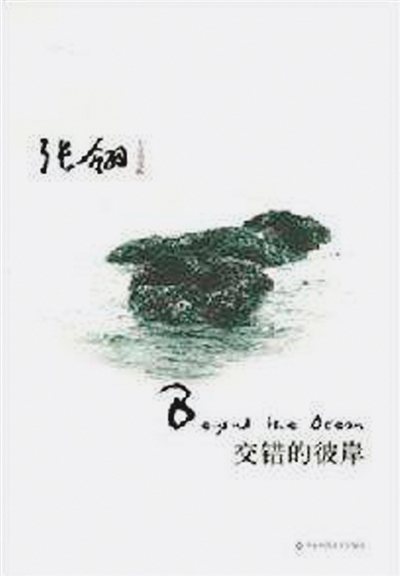

家國情懷是世界華文文學(xué)的母題,輻射懷鄉(xiāng)戀土、血緣追索、生存焦慮、民族復(fù)興等創(chuàng)作維度。從20世紀(jì)60年代的留學(xué)生文學(xué)至今,創(chuàng)作者雖適應(yīng)了“把自己連根拔起栽種到異國”的文化陣痛,但原本已無比堅(jiān)定的“落地生根”,卻發(fā)生了再次“落葉歸根”的微妙轉(zhuǎn)向,隨之衍生的是文化鄉(xiāng)愁由感性逐漸讓渡于理性。家國情懷可以有三重解讀,即對(duì)家國的定義、對(duì)家國的感情、對(duì)家國的期待。隨著題材廣度與技巧精度的雙向提升,家國記憶、家國情感、家國使命的傳承和發(fā)展體現(xiàn)華文文學(xué)的新意與新變。
從“落地生根”到“二次移民”
20世紀(jì)60年代留學(xué)生文學(xué)中“邊緣人”的困頓消極與渴望民族振興的家國夢(mèng)共生。海外游子的自豪感和責(zé)任感,從對(duì)親人的依戀、對(duì)鄉(xiāng)土的回憶、對(duì)故國的熱愛中播撒開來。小說醞釀起失根的困惑,流轉(zhuǎn)著“日暮鄉(xiāng)關(guān)何處是”的傷感,對(duì)母國的眷戀,更深層次目的是獲得文化的認(rèn)同與精神的歸屬。同時(shí),留學(xué)生文學(xué)特別關(guān)注留學(xué)生群體的切身問題,以此凸顯中西文化間差別的明晰性和碰撞的必然性,但陳若曦借《突圍》《二胡》等作品提議“告別畸形的、分裂的家國之恨,擁有健康的、平和的中國形象及中國情懷”。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是揭示留學(xué)生失根痛苦的經(jīng)典文本。叢甦是在《野宴》中較早提出了“夾縫”概念,“生活在別人的屋檐底下,屋檐雖好,終究是別人的。”她同時(shí)回答了留學(xué)生該“怎么辦”:“我們,我們的下一代,我們下一代的下一代,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書寫我們的向往和夢(mèng)……”
上世紀(jì)80年代的新移民文學(xué)延續(xù)了於梨華、白先勇、叢甦、陳若曦等人對(duì)隔膜論的闡發(fā),而此時(shí)的家國夢(mèng)已與個(gè)體的自我實(shí)現(xiàn)交織在一起。比照同時(shí)期華裔作家的英文小說,同樣有對(duì)文化失根的思考,它顯現(xiàn)為父輩(中國經(jīng)驗(yàn))與子輩(西方經(jīng)驗(yàn))之間的文化理念沖撞,進(jìn)而激化現(xiàn)實(shí)與理想的既定矛盾。譚恩美《喜福會(huì)》中龔琳達(dá)的一段獨(dú)白可與其互證:“長期以來,我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適應(yīng)美國的環(huán)境但保留中國的氣質(zhì),可我哪能料到,這兩樣?xùn)|西根本是水火不相容,不可混和的。”我認(rèn)為,留學(xué)生文學(xué)重點(diǎn)在失“魂”,而新移民文學(xué)則為失“根”。前者一直堅(jiān)定于對(duì)中國文化的堅(jiān)守和對(duì)西方文化的防御,家國之愛是格外濃烈而痛徹的;后者立足于個(gè)體的心靈體驗(yàn),以文化夾縫中的兩難心態(tài)為中心,傳達(dá)新移民的即時(shí)狀態(tài):渴望融入西方但無法被完全認(rèn)同,于是重回中國又不能再被全然接納,最終還是選擇回歸西方。而90年代新移民文學(xué)代表作家張翎從中國故事起步,信奉寫作這一行為本就是一種對(duì)故鄉(xiāng)的回歸,依據(jù)自己的青少年經(jīng)歷實(shí)施對(duì)江南記憶的重構(gòu),又將成年經(jīng)驗(yàn)?zāi)塾诒狈綌⑹轮性僭臁?/p>
21世紀(jì)以來的世界華文小說持續(xù)對(duì)家國的關(guān)注,但思考點(diǎn)已實(shí)現(xiàn)新的著陸:從海外處境/想象中國的思維范式,轉(zhuǎn)為現(xiàn)時(shí)問題/現(xiàn)實(shí)中國的思路結(jié)構(gòu)。從某種意義上看,視角的變化與創(chuàng)作者的頻繁“海歸”密切相關(guān),他們得以直接融入中國現(xiàn)實(shí)生活,親歷中國新變,故而對(duì)家國的體驗(yàn)不再是來自記憶或經(jīng)驗(yàn),而是源自真實(shí)當(dāng)下。薛憶溈在《希拉里·密和·我》中提供一個(gè)論點(diǎn):“移民最大的神秘之處就是它讓移民的人永遠(yuǎn)都只能過著移民的生活,永遠(yuǎn)都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家。‘回家’對(duì)移民的人意味著第二次移民。”那么,對(duì)于海歸作家而言,故鄉(xiāng)與異鄉(xiāng)是辯證的,中國具備故鄉(xiāng)與異鄉(xiāng)的雙重特性。他們是在場的旁觀者,具有更自由的審視距離和更從容的觀察視角,于是他們對(duì)家國的表達(dá),可以從原先的情感攀援直擊入現(xiàn)時(shí)的問題解決。《空巢》(薛憶溈),解析城市空巢老人為何成為電信詐騙主要受害群體的原因;《垂老別》(張惠雯),揭露農(nóng)村城市化進(jìn)程中傳統(tǒng)人倫的崩壞,揭示失去土地的農(nóng)村老人因其無用性與無利性反遭子輩遺棄的悲劇;《佐敦》(周潔茹),刻畫內(nèi)地女性移民在香港面對(duì)的生活窘境、身份歧視、家庭畸形。“香港的天,就比鄉(xiāng)下的藍(lán)嗎?阿珍看不出來。”現(xiàn)居香港的阿珍、阿芳卻與60-80年代歐美世界“邊緣人”處境不期而遇。
從家族溯源到家庭記憶
家族譜系構(gòu)建是“家”的重要呈現(xiàn)方式。家族的代際傳承是最基本敘事線索,與門風(fēng)、鄉(xiāng)土、歷史、文化等因素形成組合體,目的是反觀社會(huì)問題與人性問題。考察華文文學(xué)的家族小說,如《交錯(cuò)的彼岸》《嗩吶煙塵》《海神家族》《金山》《北鳶》,家族被視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展示的平臺(tái),深耕于文本的家國情懷,以家族血緣為點(diǎn),以種族血脈為面。
張翎采用地標(biāo)式的家族建構(gòu),即聚合家族流變史、個(gè)人成長史、文化發(fā)展史,將溫州夢(mèng)與他國夢(mèng)譜系化和具象化,例如在《望月》《交錯(cuò)的彼岸》《郵購新娘》里,形成西方望族與江南世家的中西呼應(yīng)。而《金山》是她的家族敘事的階段完結(jié)篇,最顯著的文學(xué)價(jià)值是用現(xiàn)代漢語為“長眠在洛基山下的孤獨(dú)靈魂,完成一趟回鄉(xiāng)的旅途”。小說以洛基山與開平碉樓共同裝載方氏家族的家國夢(mèng),方錦山、方錦河、方錦繡,托起“山河錦繡”的家族祈愿,包裹海外華人懷鄉(xiāng)的濃釅和還鄉(xiāng)的企盼。沈?qū)幍摹栋偈篱T風(fēng)》探討的論題是,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該如何保留和傳承中華文明的血脈。它側(cè)重家族文化內(nèi)涵的開發(fā),以沈鈞儒和陶希圣的家族譜牒為本,細(xì)數(shù)沈、陶兩家歷代傳承的三大精神遺產(chǎn):感恩、書生的傲骨和獨(dú)立、明確的是非觀念。2016年葛亮的《北鳶》,也是延續(xù)類似的節(jié)奏,設(shè)計(jì)盧文笙與馮仁楨兩條家族敘事線,以家族文脈昭示民國風(fēng)骨。
近年來,世界華文小說對(duì)“家”的塑造主動(dòng)規(guī)避集體經(jīng)驗(yàn)的疊加,格外專注個(gè)體家庭的事件與心理,以中國故事為敘事背景,收縮宏大的家族敘事,轉(zhuǎn)而書寫變動(dòng)不居的普通家庭沉浮。《陸犯焉識(shí)》是嚴(yán)歌苓以祖父嚴(yán)恩春故事為小說藍(lán)本,檢視陸焉識(shí)、馮婉瑜與命運(yùn)較量幾十年中歷歷在目的跌宕唏噓。張翎在《流年物語》里將全家放置于不同年代,由不同的機(jī)遇與處境撞擊出劉年對(duì)自由的各種形式探索。李鳳群的《大風(fēng)》詳述張家每一代人的尋根行動(dòng),重新定位個(gè)人與鄉(xiāng)土的關(guān)系:“倦鳥總會(huì)歸巢,而我們卻將一去不返。”戴小華以《忽如歸》為家人立傳,誠懇記錄戴家故事,視滄州“鎮(zhèn)海吼”為精神旨?xì)w,闡明“歷史激流中的一個(gè)臺(tái)灣家庭”秉持并堅(jiān)守“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價(jià)值觀。
當(dāng)前世界華文文學(xué)對(duì)中國故事與中國經(jīng)驗(yàn)越加重視,家國情懷追隨著“落葉歸根”/“落地生根”中空間與身份的動(dòng)態(tài)轉(zhuǎn)徙,產(chǎn)生理念與理解的變化推演。家國情懷的持續(xù)性與新質(zhì)性,彰顯了海外華人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不停歇的文學(xué)想象力與不中斷的社會(huì)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