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guó)《文學(xué)雜志》訪2016年龔古爾獎(jiǎng)得主蕾拉·斯利瑪尼:“我要講述圍繞母性建立的神話和謊言”

蕾拉·斯利瑪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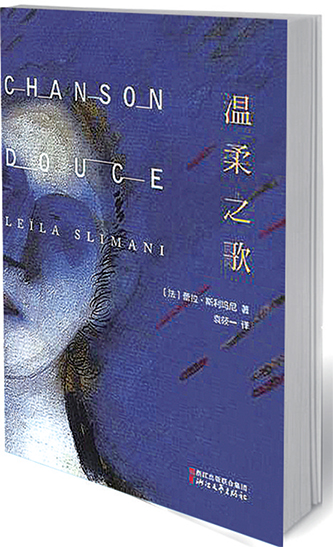
阿萊克西·布洛卡(以下簡(jiǎn)稱“布洛卡”):和您的上一部小說《食人魔花園》一樣,《溫柔之歌》這部作品有一半也是留給讀者去想象和填補(bǔ)的:對(duì)行為的描繪占了大部分篇幅,同時(shí)您給出了許多具有象征意義的細(xì)節(jié)——如保姆給保羅夫妻留下的干干凈凈的雞骨頭,這些細(xì)節(jié)給讀者留下豐富的闡釋空間,這是有意為之的嗎?
蕾拉·斯利瑪尼(以下簡(jiǎn)稱“斯利瑪尼”):我很欣賞讀者應(yīng)當(dāng)介入閱讀的觀點(diǎn)。我不喜歡人們把文學(xué)當(dāng)作純粹的消遣,那樣讀者處于完全被動(dòng)的地位。當(dāng)然,這類書是有必要的,但我在寫作時(shí)會(huì)嘗試寫出其他東西,能夠打動(dòng)讀者、讓讀者走出舒適區(qū)的東西,強(qiáng)迫他們看到那些不太愿意看的內(nèi)容。在這樣一個(gè)隨處販賣舒適感的世界里,我主張的是一種文學(xué)上的不適感。
布洛卡:您的作品里經(jīng)常有童話世界的影子。比如《食人魔花園》這個(gè)書名就是一個(gè)黑色童話,在《溫柔之歌》中,小米拉會(huì)說“我的保姆是仙女”。童話呈現(xiàn)的是一個(gè)理想化的、神奇的世界,但里面隱藏著許多能夠用精神分析法研究的內(nèi)容……
斯利瑪尼:童話是一種隱喻。在童話世界里,每人都有一個(gè)既定角色——父親、母親、孩子們、仙女和女巫,最終,人物的面貌會(huì)隨著故事發(fā)展而改變。我也欣賞童話能夠帶著某種距離感甚至漫不經(jīng)心去挖掘最原始的恐怖。我的作品是扎根于社會(huì)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故事,但同時(shí)也建立在更普遍、更古老的基礎(chǔ)之上。阿黛爾(注:蕾拉·斯利瑪尼第一部小說《食人魔花園》的主角,一名女性癮者),這位21世紀(jì)的女性,也是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和小紅帽的女兒——在童話里,人物無法逃脫命運(yùn)的掌控,無法逃離等待在前方的那只狼。
社會(huì)階層
布洛卡:您的小說清楚地展現(xiàn)了這個(gè)家里雇主和雇員關(guān)系的轉(zhuǎn)變。19世紀(jì)時(shí),傭人不是“家庭的一員”,而更多是“家具的一部分”。保羅和米莉亞姆給予了路易絲很多善意的關(guān)注,他們?cè)诓恢挥X間促成了路易絲的瘋狂舉動(dòng)。
斯利瑪尼:保羅和米莉亞姆不屬于大資產(chǎn)階級(jí)。大資產(chǎn)階級(jí)雇傭傭人是正常現(xiàn)象,而他們是布波族(注:即“布爾喬亞-波西米亞族”,該詞因美國(guó)作家大衛(wèi)·布魯克斯《天堂里的布波族》而廣為人知,指的是在信息時(shí)代進(jìn)入社會(huì)中上層階級(jí)的新知識(shí)分子,他們追求資產(chǎn)階級(jí)式的生活享受,又兼具波西米亞人的自由不羈,崇尚獨(dú)立精神和創(chuàng)新意識(shí))。雇保姆對(duì)他們來說是經(jīng)濟(jì)上的犧牲,是一種奢侈的選擇。然而,很快,他們意識(shí)到此舉使他們進(jìn)入了新的社會(huì)階層,一個(gè)他們不希望進(jìn)入的階層。由于他們不想與路易絲產(chǎn)生等級(jí)關(guān)系,因此他們嘗試用親切和友善來消弭等級(jí),而他們的行為往往會(huì)傷害路易絲。他們想把事情做好……但怎樣才算做得好?
布洛卡:您幾乎是用一種科學(xué)的手法來使用這些具有社會(huì)學(xué)意義的細(xì)節(jié)。通過人物所屬的社會(huì)符號(hào)來將其分類,這是您寫作時(shí)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嗎?
斯利瑪尼:人們以這種方法給他人分類,他人也希望以此被分類——有些人想顯得比實(shí)際的自己更富有,或者更無辜,或者更低調(diào)。我對(duì)此很有感觸。我確實(shí)對(duì)細(xì)節(jié)十分敏感。我認(rèn)為一個(gè)人的吃穿、談吐或走路的形象往往比長(zhǎng)段的語(yǔ)言或者心理描寫更有說服力。在這個(gè)問題上,我屬于契訶夫一派,他說:“如果文中寫到了槍,就要讓槍派上用場(chǎng)。”要給予你呈現(xiàn)的普通細(xì)節(jié)以生命。這對(duì)小說而言是一個(gè)美好的挑戰(zhàn)。
布洛卡:從前,人們的名字、出生決定了他的社會(huì)地位。如今一切都混亂了。所以這些符號(hào)是否顯得更為重要了?
斯利瑪尼:確實(shí),現(xiàn)在的一切都比從前更混亂,或許可以說沖突更劇烈,總之社會(huì)的融合度在下降。要說工人階層的敵意和資產(chǎn)階級(jí)故步自封于其規(guī)則和思維方式的程度,我感覺法國(guó)比摩洛哥更為嚴(yán)重。我認(rèn)為這是我們面臨文明困境的原因之一。不同階層的人生活在一起困難重重,或者說,他們根本不愿意共同生活。在巴黎第十八區(qū),政府打算把兩所高中合并在一起,其中一所是布波族孩子的學(xué)校,另一所都是家庭條件較差的學(xué)生。這些布波族不愿自己的孩子與黑人或阿拉伯小孩成為同學(xué),然而他們其實(shí)很友善,不是種族主義者,他們會(huì)送舊套頭衫給難民穿。我也試著描述這個(gè)階層的人內(nèi)心的矛盾狀態(tài),他們沒有人們想的那樣夸張和諷刺。
母親身份與個(gè)人發(fā)展
布洛卡:您在《食人魔花園》中探討的另一個(gè)主題是母親的身份。她承受著一種矛盾的折磨:如果她去工作,人們就指責(zé)她忽視了對(duì)孩子的照顧;如果她照顧孩子,人們就諷刺她的家庭主婦身份……
斯利瑪尼:母性的問題在文學(xué)中得到的挖掘并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多,由女性來挖掘的則少之又少。許多女作家不想成為母親,認(rèn)為這與她們的寫作前途背道而馳。這并非一個(gè)無關(guān)痛癢的問題。如果你需要照顧小孩,這就與你坐在辦公室里和寫作的意愿相矛盾。如果你有孩子,而你花在寫作上的時(shí)間比照顧小孩的時(shí)間多,人們就認(rèn)為你是個(gè)不稱職的母親。這不同于你為了養(yǎng)活他們而出去工作。此外,做母親的幸福感也是一個(gè)問題:這往往都出自男性之口!女作家如何看待“成為母親的幸福”?我想要講述圍繞母性與“母親的本能”建立起來的神話和謊言,我一直在做這件事。在現(xiàn)在的社會(huì),人們告訴母親,工作、母親的職責(zé)和生活?yuàn)蕵啡呖梢约骖櫋5c此同時(shí),人們又一點(diǎn)一點(diǎn)向母親灌輸罪惡感,這種罪惡感日漸沉重。在《溫柔之歌》中,米莉亞姆看著她的孩子,心想:“人們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時(shí)候才是幸福的。在我們自由的時(shí)候。”這種由照看孩子產(chǎn)生的暈頭轉(zhuǎn)向的感覺,以及意識(shí)到他們是多么需要你的感覺,是不容易擺脫或者成功適應(yīng)的。在文學(xué)層面上,這種眩暈感有引人入勝的效果。
布洛卡:確實(shí)是這樣。當(dāng)我們思考文學(xué)中的母性時(shí),我們會(huì)想到阿爾貝·科恩《我母親的書》、羅曼·加里《黎明的承諾》等。
斯利瑪尼:是的,這是一個(gè)小男孩對(duì)母親的認(rèn)知。“我最愛的人,我完美的媽媽,如果沒有她,我永遠(yuǎn)不可能成為作家,是她對(duì)我寄予了厚望。”他寫到過他母親那些絕望的、或許對(duì)他感到厭煩、想把他扔到窗戶外的時(shí)刻嗎?沒有!他想象不出這些。我想講述的就是與這種美好的粉飾相反的東西。
布洛卡:人們認(rèn)為母性代表著一種絕對(duì)的人生完整性,您是否被要求相信它,重新戴上一個(gè)“完整”女性的面具呢?
斯利瑪尼:當(dāng)你推著童車?yán)飫倽M月的可愛小嬰兒走在路上,別人對(duì)你說:“你一定開心極了吧”,你肯定不會(huì)說:“其實(shí)我并不幸福,如果可以話,我倒想把搖籃給你。”這是禁忌。很長(zhǎng)時(shí)間以來,人們也把這種代表了人生完整性的母性形象當(dāng)作是對(duì)孩子的保護(hù)。需要告訴母親她們是幸福的,否則她們會(huì)拋棄自己的孩子。正是出于這一考慮,那些有名的心理學(xué)家或社會(huì)學(xué)家都維護(hù)著這個(gè)謊言。《溫柔之歌》從根本上說是一部黑色小說。它以一樁殺害兒童的事件開始,回溯過去,人們看到了一個(gè)女人如何一步步變成殺人兇手,人們找到了證據(jù)。
關(guān)于寫作
布洛卡:您的語(yǔ)言十分簡(jiǎn)潔,從來不為敘事制造障礙,不追求文體學(xué)上的雕飾以顯示自我的與眾不同。這是一種有意識(shí)的寫作手段嗎?
斯利瑪尼:我給讀者設(shè)置了其他障礙,因此在修辭風(fēng)格上要讓讀者感覺簡(jiǎn)潔明了。由于人物和話語(yǔ)往往曖昧不明,在寫作風(fēng)格上,我就盡力做到明白曉暢。另外,我感覺簡(jiǎn)潔的法語(yǔ)是優(yōu)美的法語(yǔ)。當(dāng)我們囿于復(fù)雜風(fēng)格時(shí),就無法表達(dá)簡(jiǎn)單的東西,最終會(huì)給人留下偏離主題的印象。
布洛卡:您也曾為報(bào)紙撰寫文章,積極介入社會(huì),對(duì)社會(huì)事件發(fā)表看法。您的小說中也展現(xiàn)了一種政治維度,但并沒有同樣的憤怒情緒。在您看來,應(yīng)當(dāng)區(qū)分二者的界限嗎?
斯利瑪尼:坐在桌前寫小說的那個(gè)我,是擺脫了憤怒、生理性別、社會(huì)性別和社群歸屬的我。我關(guān)心的問題是:作為一個(gè)人,而非一個(gè)生于80年代的馬格里布女性,我可以講述怎樣的故事?我也喜歡寫介入社會(huì)的文章,把我的觀點(diǎn)展示在世人面前。但這是兩個(gè)截然不同的世界,也許它們?cè)谖磥頃?huì)有交集。寫作會(huì)受到所處時(shí)期、靈感和外界支持的限制。我正在構(gòu)思的下一部小說將觸及更為政治化、更有爭(zhēng)議的主題。 (編譯 劉舒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