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北美》:游走在真實(shí)與虛構(gòu)之間

波麗娜·蓋納(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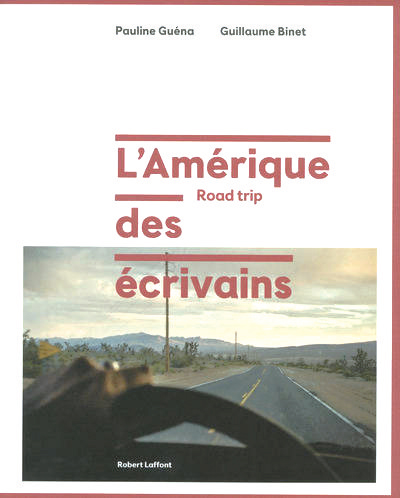
《作家的北美》法文版
法國(guó)作家波麗娜·蓋納遭遇了一場(chǎng)寫(xiě)作危機(jī),遂同丈夫一起,帶上孩子,奔向北美,意圖求得疏朗開(kāi)闊之道。他們見(jiàn)了北美的26位作家,從莽莽森林奔向遼闊海洋,從黑奴莊園聊到卡特琳娜颶風(fēng),從兒童凌虐提及槍支管械,于是便有了《作家的北美》。
由作家采訪作家,面對(duì)思想上的同行者和共鳴者,作家們往往會(huì)給出更加真摯細(xì)膩的答案。北美文學(xué)除了美國(guó)以外,也包括加拿大文學(xué),所以這場(chǎng)文學(xué)盛宴顯得更為誘人。盡管福克納的余暉仍照耀著北美,但仍有許多作家脫穎而出:威廉·斯泰倫、尤多拉·韋爾蒂、弗蘭納麗·奧康納、凱瑟琳·安·波特、瑪格麗特·勞倫斯、愛(ài)麗絲·門羅等等。而《作家的北美》中受邀接受訪談的26位作家,既有為人熟知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理查德·福特,也有年紀(jì)輕輕就已嶄露頭角的迪奈·門格斯圖、克雷格·戴維森等等。
蓋納的問(wèn)題很多,有瑣碎的重復(fù),也有出其不意的發(fā)問(wèn);有精心準(zhǔn)備的訪談,也有可遇不可求的會(huì)面。作為讀者,最關(guān)心的大概就是作家們是如何成為了作家的。有趣的是,我們看到作家們的職業(yè)生涯選擇往往有天意注定的意味。即如約瑟夫·波登所說(shuō):“我從來(lái)沒(méi)有真正地決定過(guò),是寫(xiě)作選擇了我。”約翰·畢蓋奈還是個(gè)孩子時(shí)就渴望成為畫(huà)家,為了參加閱讀報(bào)告比賽所以畫(huà)了39幅畫(huà),寫(xiě)了一個(gè)小段落,卻因?yàn)樽詈蟮倪@個(gè)小段落拿了冠軍,氣得“眼淚都要哭干了”;上了中學(xué)后,因?yàn)樯险n無(wú)聊所以寫(xiě)詩(shī),被老師抓到行政處,領(lǐng)導(dǎo)卻對(duì)這些詩(shī)大加贊賞,寄去參加詩(shī)歌比賽又拿了獎(jiǎng),畢蓋奈趕緊花錢收買學(xué)校報(bào)紙主編,千萬(wàn)不要透露“籃球隊(duì)隊(duì)長(zhǎng)居然贏了一場(chǎng)詩(shī)歌比賽”!所以約翰·畢蓋奈不無(wú)挪揄地自諷:“在某種程度上來(lái)說(shuō),生活一直在驅(qū)使著我寫(xiě)作,一直到我停止反抗為止。”而也正由于生活這無(wú)情的驅(qū)使,才有了他在《模子》《上漲的水》中對(duì)卡羅琳娜颶風(fēng)后新奧爾良城中百態(tài)入木三分的刻畫(huà)和對(duì)不作為政府的鞭撻。
提到政府,蓋納在這本訪談錄中無(wú)數(shù)次地問(wèn)到各位作家:“您是一位介入作家嗎?”這也許是一個(gè)典型的法式問(wèn)題,因?yàn)楫?dāng)提到介入作家時(shí),首先跳入我們腦海的名字必然是如雷貫耳的薩特和加繆。和作家們不約而同地認(rèn)為寫(xiě)作是宿命的選擇不同,對(duì)于這個(gè)問(wèn)題,作家們的回答莫衷一是。波義耳告訴蓋納:“我不認(rèn)為文學(xué)有什么政治功能。我覺(jué)得文學(xué)可以給你帶來(lái)歡樂(lè)和感動(dòng),它可以改變你的思想和觀點(diǎn)。但文學(xué)并不是萬(wàn)靈藥。藝術(shù)和政治是不能相融的。”詹姆斯·李·伯克說(shuō):“政治是我們寫(xiě)作的一部分,這是不可避免的,因?yàn)檫@是我們生活的擴(kuò)展。”迪奈·門格斯圖則堅(jiān)定地認(rèn)為:“我的寫(xiě)作決不能離開(kāi)政治。”不可否認(rèn),無(wú)論是否介入,這些作家都坦承對(duì)于當(dāng)今社會(huì)的擔(dān)憂:“一邊是赤貧,一邊是極富!”多倫多的克雷格·戴維森提到加拿大和美國(guó)邊境線人民生活時(shí)憂心忡忡。當(dāng)然,這些作家中最激進(jìn)的大約是大衛(wèi)·范恩,他對(duì)美國(guó)感情深刻,卻一生也不愿再回去生活和工作。為了揭露生活的某些真相,作家往往需要鼓起勇氣揭開(kāi)社會(huì)的某些鮮血淋漓而層層疊疊的傷疤。槍擊案、恐怖分子都是美國(guó)的傷疤之一,范恩稱之為“巨大的謊言”。頻繁發(fā)生的槍擊案刺痛了美國(guó)人的神經(jīng),但他們?nèi)砸粠樵傅叵嘈胖拔覀兪莻€(gè)善良的民族”。大衛(wèi)·范恩冒了天下之大不韙,憤怒抨擊美國(guó)政府和軍隊(duì)“政府想要將人民變成他們的奴隸”,“軍隊(duì)惟一給我們帶來(lái)的,就是潰敗”。自然,作家在如此強(qiáng)力地介入政治后,被戳到痛處的民眾們往往會(huì)猛虎暴起而攻之,所以范恩遷居到了新西蘭,把這里當(dāng)做自己的國(guó)家。真相往往殘酷,這也讓人想到了大聲疾呼社會(huì)吃人的魯迅,這樣強(qiáng)烈的斥責(zé)總不會(huì)受到當(dāng)時(shí)民眾的歡迎,但當(dāng)我們跳出當(dāng)時(shí)的歷史環(huán)境來(lái)看,魯迅的《狂人日記》也正真實(shí)而鮮明地反映了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而同時(shí)也正如托馬斯·麥葛尼所說(shuō),家里可以有紛爭(zhēng),外人卻不能指責(zé)。但若是這紛爭(zhēng)已影響到外人呢?或者說(shuō),在世界這個(gè)大家庭里,沒(méi)有外人,我們都被全球化操弄于股掌之中?所以無(wú)論是美國(guó)槍支,還是恐怖分子和難民潮,我們永遠(yuǎn)也無(wú)法置身之外,漠然視之。
在訪談錄中,有個(gè)出現(xiàn)頻率很高的詞是“暴力”,這讓人多少有些驚詫,并顯得突兀。但正如耶穌所說(shuō):“我來(lái)不是叫這世界和平,乃是叫這世上動(dòng)刀兵。”所以暴力的反復(fù)出現(xiàn)又顯得平常而自然。當(dāng)然這暴力除了子彈出膛的巨響以外,還有民眾的麻木和冷漠。正如范恩所提到的:“對(duì)于真正的恐怖來(lái)說(shuō),暴力和心理是完全分離的。”當(dāng)你能對(duì)他人的苦痛漠然視之時(shí),你便已經(jīng)參與了暴力。而勞拉·卡塞斯克對(duì)暴力則有另外一種解讀,她認(rèn)為:“暴力主要還是心理層面上的,是平凡人物內(nèi)心斗爭(zhēng)的產(chǎn)物,而且會(huì)通過(guò)人物的外在行為表現(xiàn)出來(lái)。”因而有了《魂歸故里》中殘忍的姐妹會(huì),《欲望懸流》中麻木的揮霍與嫖妓,《眼前的生活》中高中校園的槍擊事件,又或是《冬天的心》中無(wú)法建立的母女關(guān)系。正如“百分百平凡的日常在我們眼前裂出縫隙,暴力以最慘烈的姿態(tài)噴涌而出”。
從《作家的北美》書(shū)名便可知作家對(duì)于地理意識(shí)的重視,所以書(shū)中在每一篇訪談前,都或濃或淡的筆墨勾勒當(dāng)?shù)仫L(fēng)情,因而讀者會(huì)看到阿第倫達(dá)克山脈在班克斯書(shū)中投下的倒影;詹姆斯·李·伯克書(shū)中受到毒害的路易斯安那州,阿斯維特書(shū)中的紐約和大城市……眾所周知,地緣環(huán)境與個(gè)人身份及文化身份總是緊密相連,須臾不離的地理意識(shí)的背后蘊(yùn)含的必然是對(duì)于身份的認(rèn)知。來(lái)自埃塞俄比亞、生活在紐約的非裔美國(guó)作家迪奈·門格斯圖坦言是對(duì)于身份的焦慮促使自己走上文學(xué)道路:“只有在文學(xué)中,才不用擔(dān)心我有沒(méi)有朋友,我夠不夠好,是德國(guó)天主教白人還是黑人……”“我一直認(rèn)為我只能把自己定義為美國(guó)作家,因?yàn)槲矣X(jué)得沒(méi)有其他的文化能夠給予人如此復(fù)雜的身份了……”身份和地理是無(wú)法分離的褡褳,對(duì)于有色人種來(lái)說(shuō)尤其是這樣。當(dāng)然也有對(duì)此十分坦然的非裔美國(guó)作家約翰·埃德加·維德曼:“我的全部人生,以及滋養(yǎng)我長(zhǎng)大的文化,在大眾眼中都是邊緣化的,不是美國(guó)偉大傳統(tǒng)的一部分。這不重要。如果您對(duì)此有所了解,當(dāng)然更好,如果不了解,那也無(wú)所謂。“事實(shí)上,我們也看到有色與否并不能遮掩或放大作家們的光輝,身份與地理因素同樣,都只不過(guò)是寫(xiě)作的機(jī)緣或是寫(xiě)作的一部分而已,寫(xiě)作的真正意義在于寫(xiě)作本身。
當(dāng)談及純粹的寫(xiě)作時(shí),作家們?cè)谠L談中始終堅(jiān)持的一點(diǎn)是:寫(xiě)作之路是一場(chǎng)冷暖自知的苦役,需要堅(jiān)持,不可氣餒。因?yàn)閷?xiě)作也許無(wú)法給作家?guī)?lái)直接回報(bào),甚至是沒(méi)有回報(bào)……成就事業(yè)必然要忍受時(shí)間的凌辱,這一點(diǎn)大概是所有學(xué)科都共通的。詹姆斯·李·伯克說(shuō)道:“為了活下去,臟活苦活我全都干過(guò)……”“我被出版社拒絕了111次”。丹尼斯·勒翰為了生存專門給人停車,一個(gè)月瘦了13斤……如今輕描淡寫(xiě)的,當(dāng)初大抵也都是在焦慮彷徨中灼灼不安。當(dāng)然能堅(jiān)持到接受訪談的,必是從這些苦役中提煉出甘泉暢飲再繼續(xù)踟躕前行的。寫(xiě)作的確是件單調(diào)乏味的事,而同生活一樣,正因?yàn)檫@單調(diào)乏味的一日又一日,寫(xiě)作才有了偉大的意義。然而一直話題不斷的作家詹姆斯·弗雷在抗拒單調(diào)時(shí)又一次“倒行逆施”:在所有人都對(duì)“商品文學(xué)的大規(guī)模出版”這個(gè)概念憤慨反感之時(shí),他卻開(kāi)始了自己的工作室,和其他五人一起,開(kāi)始大規(guī)模出版商業(yè)文學(xué),這些書(shū)的激進(jìn)之處不在于其內(nèi)容,而在于它們的創(chuàng)作方式,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是,有五部作品都登上過(guò)暢銷書(shū)排行榜榜首……“文學(xué)是否可以被大規(guī)模出版”并不是一個(gè)新鮮的問(wèn)題,但答案卻久久未曾統(tǒng)一,在這個(gè)人工智能時(shí)代,一切都可以被大規(guī)模制造,文學(xué)應(yīng)當(dāng)進(jìn)入車間的流水線嗎?這倒是一個(gè)很有意思的問(wèn)題了,文學(xué)若是能大規(guī)模制造,是否還可以被稱之為文學(xué)呢?畢竟我們深知,暢銷書(shū)或可從思路手法相互效仿,但所有經(jīng)典文學(xué)之珍貴之處都在于它們的不可復(fù)制性。也許終有一天文學(xué)要走上商品線,也許不會(huì)。無(wú)論如何,我們終將滿懷熱忱地期待著作家們的思想點(diǎn)燃文學(xué)未來(lái)的道路。
正如佩索阿在《惶然錄》中所言,寫(xiě)下就是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