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的“已過時”與“正當時”
經(jīng)過瓊瑤、張愛玲,通過《我的前半生》被再次提起的亦舒,同樣標志著時代精神的又一次轉變。《我的前半生》的改編所引發(fā)的爭議,正是在重讀亦舒之際,對亦舒“已過時”與“正當時”的重審。《我的前半生》的故事,疊加了五四之后魯迅《傷逝》以及“娜拉走后怎樣”的拷問、當代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與社會轉型中女性對重新表述自我身份的呼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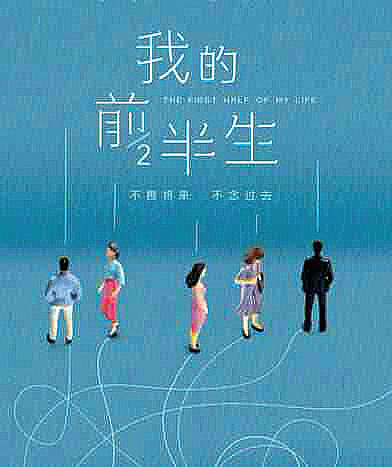
無論是嚴肅文學還是通俗文學,只要經(jīng)過影視化改編,從作品到作者,就都會引發(fā)一次大規(guī)模的重評。這種重評是兩方面的,一方面,受眾群體從文學讀者變?yōu)楦訌V泛的普羅大眾,相比文學技法的賞析,他們更喜歡用自己樸素的價值觀來衡量作品對社會問題的把握;另一方面,改編所經(jīng)歷的漫長過程,也讓作品不得不經(jīng)歷一次時間的考驗,看看在業(yè)已變遷的時代精神與世道人心中,作品能否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能夠被賦予新的意義和解讀。
電視劇《我的前半生》的熱播,就讓亦舒經(jīng)歷了這樣一次重讀。故事背景從20世紀80年代的摩登香港搬到了今時今日的繁華上海,全劇除了男女主角的名字仍舊保留,情節(jié)結構與情感線索幾乎面目全非,頂著一個“亦舒原著”的名頭,平白無故成了當下最時髦的“大IP”,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行徑,自然引發(fā)了一票亦舒擁躉的強烈不滿。但是收視率的持續(xù)走高,以及幾次劇情陡轉引發(fā)的熱烈討論,又讓人不得不承認,這是一部非常具有當下性和現(xiàn)實感的大眾文化作品。
若是放在30年前,亦舒的作品還只能被稱為通俗文學、流行小說,哪里就能被如此神話成不得改動的經(jīng)典。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亦舒在筆法上的簡單逐漸被忽略,情節(jié)走向上囿于時代之處也被寬容,倒是故事里的一個個生動鮮活的人物,愈發(fā)顯現(xiàn)出超越時代的先進特質,凝練成一系列“亦舒女郎”的形象。亦舒的作品不好改編,就表面而言,她走的是舒朗而非綿密的風格,又沒有波瀾起伏、大開大闔,驚心動魄之處總是在一兩句旁白時冷語,因而改成電影已經(jīng)非常勉強,要拍成電視劇簡直是天方夜譚。更關鍵的是,就深層而言,同樣是寫言情,“抓馬”如瓊瑤、蒼涼如張愛玲、凄艷如李碧華,多多少少,都相信“愛情”是存在的,至少是存在過的。但是亦舒則不同,她看似在寫言情,實際上始終擱置著“愛情”二字,不說相信,也不說不信,她打心眼兒里輕視這個,但又心知肚明大家看重這個,于是亦舒制勝的法寶,就是要在這一輕一重之間,將“愛情”作價賣掉,而且要姿態(tài)好看,這樣一來,就如同變賣一件傳家的古畫,銀子落袋古卷賣出,但那傳奇上面,始終會鐫刻著你這一位藏家的名章。但是,“愛情”這個概念,再是后天建構,在人們心中,也始終有些普世與恒定的價值,因此信愛之作改編起來不難。但是“愛情”作價的匯率,卻是要隨著市場日日變化的,這便成為了亦舒小說每每被重讀所引發(fā)的爭議。
亦舒寫作的20世紀80年代,正是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經(jīng)濟迅速騰飛的時期。螺獅殼中做道場,發(fā)展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經(jīng)濟,以勞動密集型產(chǎn)業(yè)優(yōu)勢,拿下歐美等先發(fā)國家在經(jīng)濟轉型時移交海外的蛋糕,就要充分調動本港資源。女性作為重要勞動力,進入社會參與生產(chǎn),則成為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重要戰(zhàn)略。因而香港雖然精神上備受潮汕傳統(tǒng)重男輕女思想影響,但行動上總還是誠實的,香港女性的社會化、職業(yè)化程度一直在亞洲名列前茅。正是在這種保守思想和先進行動的矛盾之中,才醞釀出了別具特色的港式愛情小說。在亦舒的筆下,愛情固然可貴,但重要的還是女性要擁有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對于有才的女子來說,出門工作自掙薪水,對于有貌的女子來說,把這份色相好好兌換成資本。愛情是馬斯洛金字塔的上層,面包和牛奶才是每天都要面對的下層。因而愛情這件奢侈品,只有自己衣食無憂,才有追求純粹感情的底氣,否則布衣懷璧,饑寒交迫之時還是要賣掉的。
因而,亦舒的小說,總是開篇精彩,各個女主不但都是驚艷亮相的美女,而且難得頭腦清楚,曉得進退分寸,知道得失取舍,但是到了故事后半,就不免失去一些趣味,《印度墨》也好,《喜寶的故事》也罷,最終美人服膺豪門,看客不得不承認這是最冷靜的選擇,但終究替她們意難平。原封不動搬上銀幕的改編電影,怎么看都像是只畫出了亦舒的骨肉皮,她真正的精氣神,反而是在TVB港劇里那些英姿颯爽的職業(yè)女性。她們更大地脫離了傳統(tǒng)觀念的束縛,沒有絕色美人的光環(huán),但卻有獨立理性的精神,認真地將工作視為事業(yè)而不只是飯碗。在事業(yè)與愛情間作取舍,比在面包與愛情間作取舍,姿態(tài)當然更加好看。正是經(jīng)過了這層洗練,所謂港式“亦舒女郎”才成為獨立女性的標志。
而在同時期的大陸,卻正經(jīng)歷著另一番婚姻與愛情的大討論。20世紀80年代,正是人們從禁閉走向開放的社會轉型期,“愛情”作為“新時期”文學的重要主題,成為人性自由、追求解放的表征,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所引發(fā)的社會討論,在為女作家與老干部疑似精神出軌的愛情正名的背后,是在為人們告別集體主義、重提個體自由進行合法性論證。瓊瑤在此時進入大陸,成為風靡一時的大眾文化現(xiàn)象,并以1998年《還珠格格》的成功達到頂峰。在瓊瑤的愛情觀中,為了愛情,可以不顧家庭、階級,甚至道德倫理,這種對絕對純粹之感情/個人表達的追求,正是這種時代精神的表征。
然而進入新世紀之后,張愛玲被重新發(fā)掘,并通過影視化進入大眾視野。在張愛玲的小說中,與愛情息息相關的,是時代與個人的命運。對愛情追求也好,放棄也罷,最終都無法抵抗命運的安排,愛情并未讓人們得到超越日常生活的機會,反而是因求之不得而屢屢露出卑瑣的一面。這種個人面對時代和命運的無力感,鑄就了張愛玲冷淡蒼涼的風格。
經(jīng)過瓊瑤、張愛玲,通過《我的前半生》被再次提起的亦舒,同樣標志著時代精神的又一次轉變。如同最能代表亦舒風格的不是亦舒電影,而是TVB港劇,這次亦舒精魂的泛起,不是《我的前半生》熱播,而是此前一系列以女性的個人奮斗為主要題材的小說、影視劇陸續(xù)出現(xiàn)。點燃這一燎原之火的,當屬李可的《杜拉拉升職記》,“這本書的出現(xiàn),讓中國的出版人突然恍然大悟,原來中國的職場女性是一個如此巨大的圖書消費群體,她們對成功的渴望,并不亞于這個國家里的男人”(水木丁)。如果說“杜拉拉”揭開的是表象,那么《甄嬛傳》直擊的則是背后的根源:當生存受到威脅,愛情就是一個偽命題。在這一表一里的基礎上,編劇張巍創(chuàng)作的“女性三部曲”:《女相·陸貞傳奇》《女醫(yī)·明妃傳》《女傅·班淑傳奇》,從古代歷史中挖掘女性獨立的資源,而《翻譯官》《談判官》則在都市題材中尋找職業(yè)女性的成長道路。直至《我的前半生》出現(xiàn),再次引發(fā)關于女性自立與“亦舒女郎”的討論。
和20世紀90年代的女性文學熱潮不同,彼時安妮寶貝、棉棉、衛(wèi)慧帶著“美女作家”的頭銜登場,將女性主義訴諸身體解放,最終不免成為商品經(jīng)濟下圖書出版的一枚棋子。這一次的女性主義覺醒,反而是通過商品經(jīng)濟起步,最終落實到參與社會公共事件之中。
《我的前半生》的改編所引發(fā)的爭議,正是在重讀亦舒之際,對亦舒“已過時”與“正當時”的重審。《我的前半生》的故事,疊加了五四之后魯迅《傷逝》以及“娜拉走后怎樣”的拷問、當代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與社會轉型中女性對重新表述自我身份的呼喚。從家庭主婦到職場精英,子君的漂亮轉身是作為“亦舒女郎”的從未過時之處,但是無論是電視劇中,子君與閨蜜前男友相愛,還是亦舒原著里,子君從在前一個丈夫那里做全職太太、跳到下一個丈夫那里做全職太太,都未免將“愛情”作價太低。亦舒未曾預料的是,在30年后的今天,女性的獨立自強與職業(yè)奮斗,決不是為了能找到新的長期飯票,亦不僅僅為了顧得上自己的面包和牛奶,而是為了有能力染指愛情。她們不再是為了將自己或愛情價格合理地賣出去,而是為了把更多的東西買回來——這或許才是這個時代重讀與重寫亦舒的關鍵。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