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酒之名的碰撞與相遇 陸帕與鈴木忠志:兩位戲劇大師的同題問(wèn)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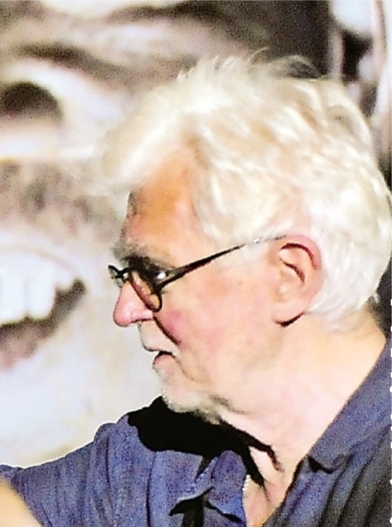
陸帕攝影/趙天陽(yáng)

《酗酒者莫非》劇照攝影/王曉明 趙天陽(yá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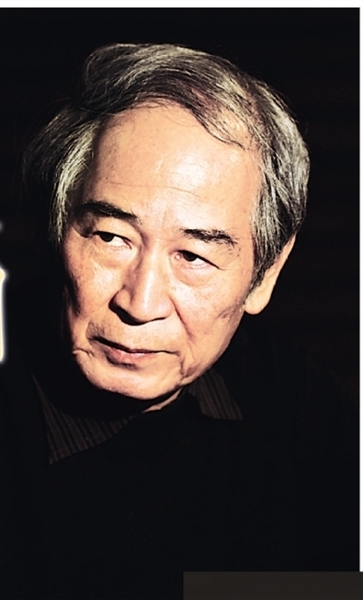
鈴木忠志供圖/SCOT

《酒神狄俄尼索斯》劇照攝影/王小京

波蘭的克里斯蒂安·陸帕和日本的鈴木忠志,可能是近三年在中國(guó)舉辦的戲劇節(jié)上出鏡率最高的兩位外國(guó)導(dǎo)演。細(xì)想之下,他們還有不少共同點(diǎn):二人年紀(jì)相仿、地位相當(dāng),陸帕73歲,鈴木78歲,同屬當(dāng)代劇壇舉足輕重的戲劇大師。他們的作品都是自2014年開始被中國(guó)的戲劇觀眾廣泛認(rèn)識(shí),對(duì)國(guó)內(nèi)業(yè)界產(chǎn)生影響。上月末,陸帕和鈴木的舞臺(tái)作品同期在中國(guó)上演。陸帕取材史鐵生著作導(dǎo)演《酗酒者莫非》,鈴木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加入了中國(guó)演員,兩位外國(guó)名導(dǎo)都染上了中國(guó)色彩。巧的是,兩部戲都和“酒”有關(guān)。
在近年頻繁密集地邀請(qǐng)外國(guó)戲劇來(lái)華演出之后,外國(guó)藝術(shù)家用創(chuàng)作這個(gè)最為根本的方式,與中國(guó)戲劇發(fā)生更深入的聯(lián)系。以此為契機(jī),北青藝評(píng)以相同的問(wèn)題,分別采訪了二位導(dǎo)演。藉著他們的回答,也許能幫我們繼續(xù)思考學(xué)習(xí)了解外國(guó)戲劇的意義以及對(duì)中國(guó)戲劇自身發(fā)展的價(jià)值所在。
北青藝評(píng):您曾多次來(lái)到中國(guó),這一次是和中國(guó)演員、中國(guó)團(tuán)隊(duì)合作作品。在中國(guó)做戲的經(jīng)歷中,有沒有令你難忘的細(xì)節(jié)?
陸帕:我們選擇演員的過(guò)程比較漫長(zhǎng),經(jīng)常有人離開,有人加入,主角也換了好幾個(gè),王學(xué)兵是最后出現(xiàn)的。能跟一個(gè)想象力這么棒的演員合作,我非常開心。創(chuàng)作的最初幾周是最困難的,演員和我的看法有很多不同,他們表達(dá)的方式、工具跟我的不一樣。但是,讓我害怕的東西忽然間變出了奇妙的結(jié)果,我們互相對(duì)對(duì)方不同的看法著了迷,發(fā)現(xiàn)可以用不同的語(yǔ)言表達(dá)自己。我相信雙方的收獲都很大,我學(xué)會(huì)了很多東西,因?yàn)槊看魏腿嗽谝环N愉快的環(huán)境中見面,都可以學(xué)習(xí)到新的東西。相聚的快樂是十分重要的。
開始排練的時(shí)候,我們還在尋找出演母親和妹妹的演員,本來(lái)想找年齡大一點(diǎn)的,突然有幾個(gè)年輕女孩出現(xiàn),其中有三個(gè)讓我非常驚嘆。我想,雖然我的劇本里沒有這樣的角色,但我可能該給她們特意設(shè)計(jì)一下,這就是卡里忒斯的來(lái)源。后來(lái)我開始慢慢設(shè)計(jì)三個(gè)卡里忒斯的場(chǎng)景,她們是一個(gè)奇怪組織的成員,她們的頭兒不知道是男的還是女的,非常想當(dāng)導(dǎo)師、領(lǐng)袖,希望自己的組織變成宗教機(jī)構(gòu),總部是一個(gè)祭壇。但另一方面,這個(gè)隱秘的老板還做婚紗生意。時(shí)間久了,婚紗生意非常成功,祭壇變成了婚紗倉(cāng)庫(kù)。
第一次見這三個(gè)女孩,我讓她們講講上次演的是什么角色,因?yàn)槊總€(gè)角色演完,演員心里都會(huì)有遺憾。我跟她們說(shuō),讓她們嘗試一下,彌補(bǔ)上次角色表演不理想的地方。當(dāng)時(shí)三個(gè)女孩都哭了。那是個(gè)非常神奇的時(shí)刻,我感覺到演員對(duì)表演的滿足感的強(qiáng)烈需要。我一直在思考她們哭的原因,是不是那種滿足感有那么殘酷、強(qiáng)烈?總之,當(dāng)時(shí)我特別感動(dòng),我告訴她們,來(lái)加入吧。
鈴木忠志:跟日本人相比,中國(guó)的男演員都長(zhǎng)得特別高大,像田沖就很高。女演員總是……馬上就退出了,合作的時(shí)間特別短,一下就不做了。在美國(guó)和日本,女演員和在中國(guó)的女演員不一樣。她們不會(huì)太想要結(jié)婚、生孩子,就是考慮我要做演員。那些女演員也不是對(duì)男人沒有興趣,只是不放在第一位。她們更想成為明星,不是為了一個(gè)男人,是讓非常多的男人喜歡自己。這還是挺不一樣的,女性只有希望更多男人來(lái)愛你,才可以把演員作為自己的職業(yè)。只想著喜歡一個(gè)男人,和他結(jié)婚,這樣的人做不了女演員。相比之下,中國(guó)的男演員更堅(jiān)強(qiáng)一點(diǎn)。
北青藝評(píng):在異國(guó)與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員、團(tuán)隊(duì)合作,您個(gè)人的期待是什么?
陸帕:我在波蘭有一個(gè)合作多年的劇團(tuán),我們認(rèn)識(shí)了很多年,工作的時(shí)候不用從頭開始,每部作品都是向前的一步。按說(shuō),和熟悉的人合作要更容易,和第一次面對(duì)的演員、劇團(tuán)不可能走得那么遠(yuǎn)。但在中國(guó)的創(chuàng)作完全不一樣,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是發(fā)展自己的珍貴的機(jī)會(huì)。現(xiàn)在看來(lái),如果《酗酒者莫非》的成員全都是我合作過(guò)的波蘭人,面對(duì)一個(gè)中國(guó)的劇本,我們沒法走得那么遠(yuǎn)。這個(gè)團(tuán)隊(duì)非常神奇,好像他們?yōu)榱俗兂蛇@個(gè)戲里的角色而生。
鈴木忠志:我是做戲劇的,不會(huì)去想國(guó)家(的分別),只要是能去實(shí)現(xiàn)自己的目標(biāo),和能夠認(rèn)同我的人一起工作,他們的國(guó)籍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無(wú)所謂。不要把美國(guó)人、中國(guó)人、日本人分開。一般人可以這樣想象,但作為藝術(shù)家,我就是跟優(yōu)秀的演員合作。何況有時(shí)候,連日本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都覺得是“別的國(guó)家”。
北青藝評(píng):這次和這些中國(guó)演員的合作,讓您有什么新發(fā)現(xiàn)嗎?關(guān)于“如何成為一個(gè)優(yōu)秀的演員”這個(gè)老生常談的話題,有何建議?
陸帕:一開始有人告訴我,中國(guó)的劇場(chǎng)里沒有太明確的即興的習(xí)慣。但在我的創(chuàng)作方式中,即興是根本的工具,是起點(diǎn)。有人告訴我,中國(guó)演員不會(huì)做即興創(chuàng)作,不愿意、害怕做即興表演。
后來(lái)我慢慢把這種方式介紹給演員,開始他們跟我說(shuō),他們都很害怕,這個(gè)方式對(duì)他們來(lái)說(shuō)很陌生,很別扭。過(guò)了一段時(shí)間之后,大家有了很大的進(jìn)步和收獲,他們的即興表演非常有價(jià)值。特別是王學(xué)兵,他有一種即興的想象力,每一場(chǎng)排練的演出都是一種即興,其實(shí)他每次排練、表演,演的是不一樣的角色。
鈴木忠志:不要只是講中國(guó)演員。無(wú)論到哪里,都只有男人和女人之分,而不是國(guó)籍之分。你也不是走到哪兒,都背著自己的國(guó)籍的。現(xiàn)在都是國(guó)際化、全球化了,韓國(guó)人、日本人、中國(guó)人是看不出來(lái)的。
好的演員跟運(yùn)動(dòng)員一樣,必須有一個(gè)目標(biāo),要朝著目標(biāo)去挑戰(zhàn)自己。也有點(diǎn)像做商業(yè),哪怕是一個(gè)很小的企業(yè)也要有自己的目標(biāo)。在美國(guó)的演員就很明確,我想做百老匯明星,那就朝著目標(biāo)去克服很多困難,不要只是為了找一個(gè)男人結(jié)婚。但是確實(shí)有這樣的人。
北青藝評(píng):您所在的國(guó)家,在世界戲劇的版圖上可能都不屬于“主流”。如何看待主流戲劇的影響?你在其中的位置是怎樣的?
陸帕:我不太愿意告訴你們我在歐洲戲劇版圖上的位置。我當(dāng)然有一些特別喜歡的歐洲的、主流的導(dǎo)演和大師,但是這幾年我的工作方式比較獨(dú)立,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直覺創(chuàng)作。除了排戲,我在克拉科夫國(guó)家戲劇學(xué)院導(dǎo)演專業(yè)當(dāng)教授,在教育的過(guò)程中,能夠吸引很多學(xué)生到我的實(shí)踐中。這就是我的本性,喜歡把自己喜歡的東西“傳染”給別人。波蘭和法國(guó)那里有很多被我“傳染”的年輕藝術(shù)家。歐洲傳統(tǒng)主流的戲劇,我認(rèn)為之前最強(qiáng)的是德國(guó)前衛(wèi)的創(chuàng)作者,但他們變得越來(lái)越弱,越來(lái)越形式化。現(xiàn)在中東歐有很多新的劇場(chǎng),他們一直在尋找新的創(chuàng)作方向。到目前為止,波蘭在歐洲戲劇版圖上,是一個(gè)比較重要的地方,出現(xiàn)了康托、格洛托夫斯基這樣的人物,后來(lái)又出現(xiàn)了很多年輕的波蘭導(dǎo)演,大部分都是我的學(xué)生。
鈴木忠志:我覺得亞洲和歐洲沒有什么區(qū)別。在當(dāng)代戲劇上如果去區(qū)分日本、歐洲就不太合適,區(qū)別只能是放在過(guò)去的傳統(tǒng)戲劇上,像能劇、歌舞伎這種會(huì)有些差別。歐洲的東西我年輕時(shí)也學(xué)習(xí)過(guò),也有人說(shuō),在某些方面,我比歐洲人還更了解歐洲。比如這個(gè)酒店、你的穿著,都是歐洲的東西。上海是中國(guó)的土地,但看上去感覺也是歐洲。中國(guó)還有很多怪怪的“歐洲感”,怪怪的“美國(guó)感”。而日本是比美國(guó)還要更美國(guó)化,中國(guó)也有一些人比美國(guó)人還美國(guó)化的。所以一定要摒棄這種歐洲、亞洲的想法。雖然我現(xiàn)在在中國(guó),但并沒有特別的感覺,北京、紐約、東京,在我看來(lái)都是一樣的。要說(shuō)我的位置,這應(yīng)該問(wèn)你(笑)。我是一個(gè)生活在山里的人。
北青藝評(píng):當(dāng)您以戲劇為媒介,游走在東西方之間,有什么切身的感受?
陸帕:比如這次,要做這樣一個(gè)跨文化項(xiàng)目,不瞞你說(shuō),我一開始很害怕,但我愿意冒險(xiǎn)。劇場(chǎng)工作需要關(guān)鍵時(shí)刻,雙方互相了解的時(shí)間點(diǎn)。沒有這樣的時(shí)間點(diǎn),我們就像海上的一艘船,不知方向,不知要去哪兒。在這個(g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我們永遠(yuǎn)也不知道這個(gè)關(guān)鍵時(shí)刻什么時(shí)候會(huì)發(fā)生,但沒有它,就完不成創(chuàng)作。我們找不到方向的時(shí)候,會(huì)開始互相討厭對(duì)方,懷疑對(duì)方。所以我認(rèn)為,互相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才能突然找到那個(gè)創(chuàng)作能力的爆發(fā)點(diǎn)。
在這樣跨文化的項(xiàng)目里,還有一個(gè)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翻譯。如果我們沒法超越基本的交流,我們的人物也完成不了。一開始工作的時(shí)候,翻譯工作非常混亂,基本上每天換一個(gè)新人。一開始我認(rèn)為這不是我的作品,而是那個(gè)翻譯的作品。但到了最關(guān)鍵的時(shí)刻,正確的人出現(xiàn)了。
鈴木忠志:你知道,日本是一個(gè)單一民族,都是日本人,也不太接受移民。所以在日本這個(gè)國(guó)家里,你去看戲,坐電車,碰到的都是日本人。去了巴黎、紐約就完全不一樣了,劇場(chǎng)里有各個(gè)國(guó)家、民族的人。四十年前,我第一次去巴黎的時(shí)候,還是挺吃驚的。我看到觀眾有不同職業(yè)、不同階層的,有政治家,有商人,年齡差異也很大。劇場(chǎng)是國(guó)家的領(lǐng)導(dǎo)者,經(jīng)濟(jì)決策人物都會(huì)出現(xiàn)的地方,從中可以看出,戲劇在那里的社會(huì)地位是很高的。看完戲以后大家一邊喝酒,一邊討論。我很是羨慕這點(diǎn)。
北青藝評(píng):劇場(chǎng)和世界的關(guān)系是什么?
陸帕:生活不是為了尋找快樂,而是為了了解未知。我不逃避生活中有一些讓人難過(guò)的經(jīng)歷,我喜歡把這些痛苦變成學(xué)習(xí)的過(guò)程,我是我生活體驗(yàn)的載體。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劇場(chǎng)的目的不僅是告訴觀眾一個(gè)什么故事,而是一種宗教儀式,由演員和觀眾一起參與。在這樣的儀式中,我們自身的生活只是一種素材,同時(shí)還有很多其他的素材。
鈴木忠志:劇場(chǎng)是一個(gè)可以談?wù)撋鐣?huì)話題的地方,能提供給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問(wèn)題。
北青藝評(píng):藝術(shù)是什么?你做藝術(shù)是為了什么?
陸帕:如果我們有飯吃,有酒喝,看起來(lái)已經(jīng)完美了,如果還有錢,那就太棒了。但是人一直有種需要,不滿足,所以我們才需要藝術(shù)這種奇怪的東西。我們可以選擇一種比較偏激的角度,把藝術(shù)變成生活方式。作為創(chuàng)作者,作為觀眾,我們應(yīng)該盡可能去了解藝術(shù),這樣的話收獲會(huì)非常大。
史鐵生有一句話我特別喜歡:寫作是為了不自殺。他創(chuàng)作的方式非常極端。排戲其實(shí)也一樣,都有一種潛在的危險(xiǎn),像酗酒。這個(gè)道理和上癮是一樣的。比如,今年這個(gè)作品我們比較滿意,明年就會(huì)想往前再走一步。藝術(shù)家要不斷發(fā)展,不然他會(huì)“死掉”。向前走得越遠(yuǎn),接下來(lái)再發(fā)展也就越難。
鈴木忠志:我是考慮人,考慮人性的。像《特洛伊女人》和《酒神狄俄尼索斯》都是在講人類這么長(zhǎng)時(shí)間沒有變化,這種社會(huì)發(fā)展是不是可行,而關(guān)于戰(zhàn)爭(zhēng)和殺人,過(guò)去和現(xiàn)在都沒有改變。現(xiàn)在社會(huì)上依然有很多暴力,很多人死去。
北青藝評(píng):支持您在劇場(chǎng)工作至今最重要的動(dòng)機(jī)是什么?是興趣、熱情、成就感,或是別的?
陸帕:每個(gè)藝術(shù)家在某一時(shí)候,都可能認(rèn)為自己的創(chuàng)作能力消失了。我有時(shí)候接受采訪會(huì)逗記者說(shuō),在我們心里,藝術(shù)家的壽命可能跟一只貓或一匹馬一樣,反正比人的壽命要短。如果你心里的“貓”死了,你得再買一只。我有時(shí)會(huì)告訴記者,我心里的“貓”已經(jīng)死了,有時(shí)又會(huì)說(shuō),這是我的第三只“貓”。
這是一個(gè)沒法控制的過(guò)程,我要接受環(huán)境給我的刺激和影響。我們面對(duì)巨大困難的時(shí)候,也會(huì)有很大的收獲,這種收獲能讓我們持續(xù)創(chuàng)作。很多人都逃避困難、困惑,但這樣你沒法創(chuàng)作,或者創(chuàng)作得很有限。我經(jīng)常會(huì)跟演員講這樣一個(gè)道理,不要怕失去你已經(jīng)得到的東西。比如說(shuō),演員如果害怕失去已經(jīng)設(shè)計(jì)好的、非常滿意的角色,只要一旦害怕,其實(shí)馬上就會(huì)失去。你如果只是想保持現(xiàn)在的狀態(tài),你會(huì)變成一具尸體。
我們波蘭很多藝術(shù)家面對(duì)的困難,不僅是政治原因,還是一種難以描述的社會(huì)上、精神上的變化。有時(shí)社會(huì)會(huì)走到非常奇怪、沒有靈魂、沒有自由思想的階段。但我認(rèn)為,這種社會(huì)上、精神上的困惑,對(duì)于很多波蘭藝術(shù)家來(lái)說(shuō),是一種機(jī)會(huì),是你可以重新買一只“貓”的機(jī)會(huì)。
鈴木忠志:我希望很多人可以帶著愉快的心情來(lái)劇場(chǎng)里考慮問(wèn)題。如果能做到這點(diǎn),我就很開心了。劇場(chǎng)里總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和這些人相遇,我感到很愉快。比如一個(gè)人50歲了,老公、孩子放一邊,想要做一個(gè)女演員,我就覺得很有意思。人很有意思的。
北青藝評(píng):這次的戲和“酒”有關(guān),您本人喝酒嗎?怎么看待“酒”這種事物?
陸帕:其實(shí)我自己從來(lái)沒有達(dá)到那么嚴(yán)重的酗酒程度。當(dāng)然我喝過(guò)酒,年輕的時(shí)候,如果沒有酒我沒法創(chuàng)作,必須喝酒,有想象力才能產(chǎn)生有價(jià)值的東西,和幾個(gè)創(chuàng)作者在一起,把自己的感受寫下來(lái)。甚至以前,我在看演出之前都要先干一杯,這樣感受會(huì)更強(qiáng)烈。在戲劇界,酒是一種生活習(xí)慣,演員、導(dǎo)演都一樣。演員喝酒是為了剖開自己,把普通人的靈魂放在一旁,找到比較特別的、難得的精神狀態(tài)。在波蘭戲劇界,為達(dá)到這個(gè)目的而酗酒是很常見的事。
鈴木忠志:我喝酒的,但不太會(huì)喝,因?yàn)楹攘司蜁?huì)想睡覺,所以想睡覺的時(shí)候喝一杯很好。但是我不喜歡人喝醉了。文/陳然 來(lái)來(lá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