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說二十年:有精神的寫作,而不是避世的夢境

也 斯

陶 然

董啟章

潘國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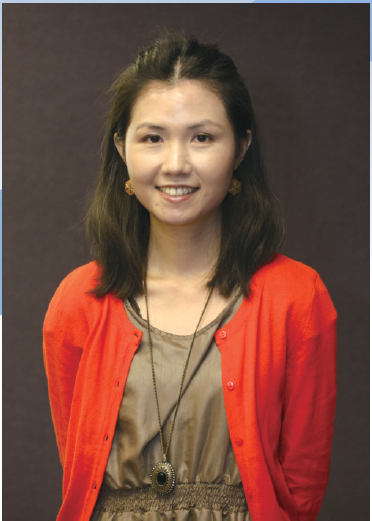
韓麗珠

謝曉虹

唐 睿

香港一向以商業(yè)化大都巿的形象示人,時尚文化成為潮流,卻并沒有因此而失卻文學(xué)的空間。回歸20年,香港文學(xué)始終自有光芒,值得細(xì)加品味。
20年來,香港社會環(huán)境發(fā)生很大變化,港人的生活形態(tài)、生存狀況、社會意識以及標(biāo)志性事件都在文學(xué)作品中有所反映。概括地說,香港小說在現(xiàn)代商業(yè)文化的叢林下自成蹊。香港小說在內(nèi)容題材方面譜系繁多、意象駁雜,有社會世相的揭示,也有個體生命狀態(tài)的呈現(xiàn);有地方記憶的回溯,也有都巿漫游者倉皇無地處境的表現(xiàn);有情色的書寫,也有疾病的隱喻。敘述美學(xué)也是形式多樣,有傳統(tǒng)寫實(shí)筆調(diào),也有魔幻筆法,更不乏后設(shè)實(shí)驗(yàn)。總的來說,回歸20年來,香港小說多姿多彩的創(chuàng)作風(fēng)貌為“我城”書寫增添了新的維度,也有一些創(chuàng)作現(xiàn)象值得探討。
食物的隱喻:香港味道
說到20年來的香港小說,也斯的《后殖民食物與愛情》無論從時間或是從象征意義,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起點(diǎn)。作品發(fā)表于1998年4月,即香港回歸后幾個月,是香港歷史新篇章中的一個重要小說文本,響應(yīng)了某種歷史經(jīng)驗(yàn),且以“食色性也”的方式來想象與言說。對于這部作品,人們很自然地聯(lián)想到殖民與后殖民,甚至試圖從中品讀出微言大義。《后殖民食物與愛情》圍繞著“我”與一班朋友“搵食”的經(jīng)歷,真實(shí)細(xì)致地展現(xiàn)出港人的生活方式——食的庶民文化,同時也扣連著“九七”回歸及后殖民年代的社會世相。作者以“食物”作為切入點(diǎn),進(jìn)入香港尋常百姓家,出入茶餐廳乃至高級食府,游走于橫街窄巷,展示香港人真實(shí)的生存狀態(tài),品味地道的香港味道,但又讓人聯(lián)想到社會的嬗變。也斯晚年執(zhí)著地追尋“香港味道”,這不是從理念出發(fā)去圖解香港,他在《后殖民食物與愛情》的后記中一言道破了“食物”的符號作用:“食物總連起人情,連著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想象。”也斯另辟蹊徑,為我們認(rèn)識后殖民時期的香港社會提供了別具意趣的視角。也斯說:“小說首先是書寫的藝術(shù),不失閱讀的樂趣,可以整理出想法來,卻并不是依據(jù)一套觀念寫出來的。”這確實(shí)是創(chuàng)作的真義,體現(xiàn)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本質(zhì)。
也斯的小說創(chuàng)作經(jīng)歷了一種“回歸”,即由現(xiàn)代主義的探索、實(shí)驗(yàn),向傳統(tǒng)寫實(shí)技藝的回轉(zhuǎn),以貼地的方法講述故事,著實(shí)是其創(chuàng)作理路的一大飛躍。對此,也斯有一番夫子自道:“每當(dāng)我寫作,為什么總得面對理論的干預(yù),為什么理論變成壓抑性的概括,理論帶著它的偏見,否定我們的探討,把我們復(fù)雜的文字放進(jìn)它們?nèi)菀紫驳男】蚩蚶铮チ嗽瓉碡S富的意義?” “對我來說,當(dāng)然是由于我在這地方長大,很想理解這地方的問題,是什么形成了大部分人主流的意見呢?是什么歷史令那么多人帶著偏見的看法呢?我在面對種種偏見中長大,想去理清問題,觀察不同的人生,去想他們經(jīng)歷了怎樣的歷史而形成自己的想法而已。”
也斯的“港味”作品及創(chuàng)作理念,似乎為我們考察20年來的香港小說,提供了一個坐標(biāo)。
“咬著自己的尾巴書寫”
深受歐美文學(xué)濡染的香港文學(xué),都以生命的勘探、靈魂的拷問為能事。欲望、肉體、生命,就成了糾纏不清的話題,成就了無窮的書寫空間。
董啟章的《衣魚簡史》寫“我”到藏書庫查找史料,對圖書管理員“維”產(chǎn)生性幻想。兩個書癡因書結(jié)緣,女子的祼體讓“我”聯(lián)想到“衣魚”,“衣魚”即書中的蛀蟲——應(yīng)和了廣東話“書蟲”(書癡)之意。作品中的女孩復(fù)述父親的一句話,泄漏了這個迷離故事的意旨:“衣魚在傳統(tǒng)里是讀書人的敵人,因?yàn)樗茐牧藭乾F(xiàn)在像他一樣的讀書人卻都變成了衣魚,靠著把書殘余的能量吃回去來生存,直至有一天把書都吃完,世界再沒有書,衣魚也沒書可吃,人們就可以安然地把書和衣魚忘記了。”作品體現(xiàn)了董啟章以具象、寫實(shí)的筆觸詮釋概念和書本經(jīng)驗(yàn)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從某種意義上說,作者本身也是“衣魚”,寄書本而生。
這不是一個孤立的現(xiàn)象,在香港當(dāng)代作家中,有不少作家,如昆南、潘國靈等,都有“以學(xué)問為詩”的特點(diǎn):從理念出發(fā),開掘本身的內(nèi)在資源,嚙啃典籍和身心,這類創(chuàng)作或可用一句話來形容:“咬著自己的尾巴書寫”。
昆南上世紀(jì)50年代進(jìn)入文壇,60年代初出版長篇實(shí)驗(yàn)小說《地的門》,至今已逾半個世紀(jì)。昆南的創(chuàng)作一向以現(xiàn)代主義的先鋒藝術(shù)形式呈現(xiàn),追問存在的意義,執(zhí)迷于情色生死的探究與反思,顛覆世俗的道德觀和凡夫俗子的眼光。如《旺角記憶條》,憑著“云”的思緒流轉(zhuǎn),展示一段纏繞不清的多角男女關(guān)系,借記憶的回溯,揭示藝術(shù)人的私密空間,呈現(xiàn)旺角的種種面相。
潘國靈是“給寫作附魔的人”,對文學(xué)有宗教般的虔誠,寫作也成了其生命存在的一種形式。他的小說有一種“病氣”,是一種典型的疾病書寫。《給寫作附魔的人》中的“游幽”與其說是小說人物,不如說是潘氏自己的化身。這個寫作者“吸吮書葉以療饑”,“以文字書寫作生命的放血治療”和“自我贖救”。他的《分裂的人》,表現(xiàn)人的二分狀態(tài),“我”與“你”是生命的共同體,“我”是外在的存在,而“你”則是蟄伏在靈魂中的另一個自己,會時不時地慫恿“我”做出不合禮數(shù)或社會規(guī)范的行為。作品叩問的是靈魂,探討的是生命、存在、性別的內(nèi)在困惑,是思辨化的、意念化的,我稱其為思辨小說。
通過這種追問內(nèi)在的寫作,香港小說加深了對“人”的認(rèn)識,但我也有一個疑惑,不少寫作者似乎都在“我”身上做文章,那么“人在何方”?目光只盯著自己,只在私我處挖掘的寫作,又與“人”何干?
魔幻的空間:都巿幽靈
魔幻是香港小說的另一個面向,自西西、也斯于上世紀(jì)70年代開風(fēng)氣之先,奇幻敘述已成香港小說的一大傳統(tǒng)。
在香港當(dāng)代創(chuàng)作人中,韓麗珠、謝曉虹都是港式魔幻派的傳人。她們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相近,還合寫過一部《雙城辭典》,在書寫上不乏交集,過從甚密,有不少可以相提并論的地方。
韓麗珠、謝曉虹不是在寫實(shí)之路上亦步亦趨的作者,而是長著翅膀的都巿漫游人,作品都帶一點(diǎn)鬼氣森森的病相,呈現(xiàn)的都是一些靈異的世相。這當(dāng)然與她們的美學(xué)觀有關(guān)。她們的創(chuàng)作驅(qū)動力來自意念和想象,寫作路數(shù)也十分接近,只是在格調(diào)上一灰一黑。
韓麗珠運(yùn)筆表現(xiàn)都巿人生的疏離、隔膜,筆下的人物大都像魅影。從創(chuàng)作基調(diào)來看,她的作品大都是“灰色敘述”,《寧靜的獸》就是一個典型的文本。這個作品中的“我”是個報(bào)紙編輯,但作者刻意模糊人物形象,以陌生化的筆法來呈現(xiàn)她與周邊的關(guān)系。“我在樓梯間碰到認(rèn)識的人,雖然不認(rèn)得他的臉,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但那確實(shí)是跟我同在那個工作間共事的人”。冷漠的心理、疏離的關(guān)系、孤獨(dú)的狀態(tài),這就是“我”的生存空間,這是一個自我隔絕的世界,“我”只生活在我的意識里,形象也極為模糊,沒有社會角色、沒有肉身,只有一個虛幻的人形。這種灰色的書寫,只滿足于一種夢囈般的自言自語和自我意識的投射,無意于人物形象的立體刻畫,也無意于外在社會、歷史環(huán)境的呈現(xiàn)與反思。
謝曉虹的創(chuàng)作可以“黑色敘述”命名。她的小說大都充斥著怪誕而暴虐的內(nèi)容,筆法魔幻,書寫時如處于夢游狀態(tài),完全打破了時空的界限,現(xiàn)實(shí)與記憶交相迭現(xiàn),過去與現(xiàn)在隨意穿插,運(yùn)筆行止自如。照理,這樣的敘事總不免有幾許歇斯底里的錯亂,但在她的筆底,卻徐緩而冷峻。
謝曉虹的“黑色敘事”除了內(nèi)容的暴虐、風(fēng)格的冷酷,一大特點(diǎn)是表現(xiàn)生命的倉皇無著與空虛,今昔莫辨,真假難分,如她的早期作品《旅行之家》《理發(fā)》,已體現(xiàn)了這種趨向,表現(xiàn)現(xiàn)代人尤其是都巿人生的荒蕪;更能體現(xiàn)“黑色敘事”風(fēng)格的,當(dāng)數(shù)《頭》與《幸福身體》。前者講述一個換頭的故事,兒子阿樹的頭不見了,父親阿木把頭給了他。“阿樹(阿木?)微微發(fā)紅的頭顱看來欣欣向榮”,意味著父親的意志主宰著兒子的身體。父親發(fā)現(xiàn)兒子“漸漸遠(yuǎn)離了他”,接受了“與他人相似的思維方式,而且走進(jìn)了他們的世界”,“漸漸不再相信他的話”,這是何等失落?但最終父親還是重新占據(jù)了兒子的身心。為什么父親會這樣做?在小說的結(jié)尾揭開了謎底,阿木在兒子未出生時把耳朵貼在妻子肚皮上,以手指輕輕觸碰,發(fā)現(xiàn)“第一次以聲音與觸覺感受到真實(shí),那甚至要比從鏡里看見自己更為真實(shí)”。
香港的作家不太以文學(xué)形式介入社會、對公共議題做出積極響應(yīng),有時失之于“貧血”,缺少了文學(xué)應(yīng)有的血性。在這樣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里,李維怡可算香港文學(xué)界的一個異數(shù)。她是一位社會意識頗強(qiáng)的作家,以《那些夏天里我們的蛹》獲得聯(lián)合文學(xué)小說新人獎,于2009 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行路難》。她的作品大都取材于社會事件,目光投向巿井小人物,見證社會體制對個體的輾壓,揭示“我城”種種社會歷史事件的投影,以及個體生命的傷口與創(chuàng)痛。
人間的情懷:生命氣息
如果文學(xué)只剩下技術(shù),沒有了情感,沒有了精神,于世何益?在近年的香港小說中,黃碧云的《烈佬傳》、唐睿的《Footnotes》等作品,讓人看到了文學(xué)對人世間的關(guān)懷。
唐睿的《Footnotes》是當(dāng)代香港文學(xué)中一部不可忽視的佳作。小說如同一部文字記錄片,回放出上世紀(jì)80年代香港底層社會一隅——安置區(qū)的生活畫面。作品滿載兒時記憶,重現(xiàn)了80年代的平民生活、小區(qū)風(fēng)情,無疑是香港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作者的敘述筆調(diào)平實(shí)自然,坦誠生動,不做作、不煽情,最可貴的是具有真誠的文學(xué)品性,沉著內(nèi)斂。
《Footnotes》有兩大可貴特質(zhì),一是“真”,一是“有心”。“真”即真實(shí)的生活記錄與真摯的感情。安置區(qū)只是香港不起眼的一角,但其中映現(xiàn)出的人生百態(tài)是香港底層社會的縮影。作品寫出了民間社會的人情世故,充滿人情味,筆調(diào)又富于情趣,是不可多得的巿井浮世繪。“林立在安置區(qū)周遭的屋邨大廈就像一個個崖岸,每當(dāng)一幢新的大廈在安置區(qū)附近落成,安置區(qū)就往下沉一寸。” 作品不僅如實(shí)呈現(xiàn)出平民的生存狀況,更道出外人無法想象的況味。“真”的另一個含意是筆底有情。《Footnotes》中,忠平叔家的細(xì)姐姐當(dāng)輔警,在一次巡邏時遇到劫案中流彈身亡。“頭七過后,每夜巷子靜下來時,忠平叔的家就會隱約傳來忠平嬸的哭聲。這哭聲,一直持續(xù)了幾個月,就變成了咳嗽聲,然后,在幾個月過后,這咳嗽聲又變成了嘔吐聲,然而這嘔吐聲只持續(xù)了幾個星期,直到一個深夜,一輛救護(hù)車開進(jìn)了區(qū)里。盡管救護(hù)車的鳴響響徹了整條巷子,訊號燈反復(fù)地擦著每一戶人家的窗戶,可巷子里沒有一個人跑出來。那夜,那些悄悄立在窗后感到遺憾的人,心里仿佛都懷著同一股默契,那就是對于那些不能用言語或行動來撫慰的人,我們只默默地讓靜默的時間降臨到他們身上,盡管,它從來也不。”這段文字飽蘊(yùn)情思,筆力直透紙背。
作品的另一大特質(zhì)是“有心”。從香港文學(xué)的書寫譜系來說,唐睿多少繼承了舒巷城的路向——平民的視角。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從一開始就有相當(dāng)?shù)淖杂X,為生民立言。正如他在后記中所言:“我希望他們都能借著《Footnotes》,在文字的世界里,覓得一處永恒的休憩或踱步的空間”,讓后來的人“找到”他們。相對于野心勃勃的歷史敘述,唐睿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更為實(shí)在。他志在為邊緣一族留住見證,為“曾經(jīng)這樣細(xì)膩而且豐盛”的時代留下記憶。他說得好:“如果香港是一本書,這部載著我們豐厚記憶的大書,應(yīng)該在記錄一項(xiàng)項(xiàng)‘大多數(shù)’人的故事之余,配上一些生活在‘大多數(shù)’邊緣,甚至以外的人物與事物交織而成的《Footnotes》……”
黃勁輝的《酒吧旮旯的故事》、巴桐的《假發(fā)》、車正軒《和女朋友在旺角賣私煙的日子》、劉綺華《鯊魚》等作品中也充滿了人間氣息和生命色彩。黃勁輝的《酒吧旮旯的故事》,寫出了打工仔的悲辛,表現(xiàn)形式則富于幽默感、趣味性。當(dāng)然,僅靠語言的詼諧生猛,還不足以入讀者法眼,該作品更有價(jià)值的“賣點(diǎn)”,是真實(shí)道出打工仔的悲酸,將不足以為外人言的處境寫了一個透。
有精神的寫作
香港文學(xué)的一大可貴之處是,有精神追求,直視社會與人生,不回避、不閃縮、不附和,而且形式多樣,手法層出不窮。
黎翠華的《記憶裁片》是一個關(guān)于城巿記憶的故事。故事采用拼貼的手法,將不同的記憶拼接在一起,似在轉(zhuǎn)動記憶的萬花筒,展現(xiàn)轉(zhuǎn)瞬即逝的城巿人生與事物。故事中的“我”是一個迷失者,又是一個追尋者。作品將思緒與現(xiàn)實(shí)對照,虛實(shí)結(jié)合。在“我”的意識中,“虛幻的世界像車窗外的風(fēng)景,一片又一片地過去。舊家或新家,老街或新街,老城或新城,甚至歷史或新聞,都像樹葉那樣翻飛著,去而復(fù)回或一去不返”。這是一個迷失的都巿人,頻繁的搬家以及城巿的拆建,讓居于斯的人失去了根,以至于“我”只能憑照片去搜尋曾經(jīng)擁有的舊物,來使自己的回憶具體化。這不是簡單的懷舊病,而是“失城”的惶惑、迷茫與焦灼。
陶然的小說創(chuàng)作一向關(guān)注物化社會的價(jià)值扭曲、人性變異,后期的作品依然對社會世態(tài)保持觀察與省思,如《出頭》講述一對夫妻在東南亞海嘯中大難不死的故事,并借此揭示和譏刺香港世俗社會的巿井意識和庸俗價(jià)值觀。
周蜜蜜的小說關(guān)注世態(tài)人情,擅長揭示都巿眾生相。《蛇纏》透過一次討論改編《白蛇傳》的編劇會議,從電視女編劇何靜被“蛇纏”“蛇咬”的經(jīng)歷,道出了一個道理:“他們的欲望,他們的愛戀,他們的妒恨,他們的情感起伏變化……全都和時下活著的人們無異。或許你和我都認(rèn)識、都熟悉,相互之間糾纏不清、變幻無常,就有故事。”
黎海華在《異化的城巿拼圖》一文中說:“香港作家對尋常事物或偶發(fā)事件陌生化的本領(lǐng)駕輕就熟,別有意圖,形成另類看事物的角度。”這是十分準(zhǔn)確的評斷。香港作家在敘述方式上大都擅長陌生化技法,或以時空轉(zhuǎn)換為能事。但當(dāng)代香港小說的一大特點(diǎn)是人物符號化,形象模糊。縱觀20年來的香港小說,像“酒徒”那樣可以立在讀者面前的人物不多見,這不能不說是當(dāng)代香港小說的遺憾。
文學(xué)具有秉持真理、追求正義的屬性,但更應(yīng)做深入的人性探究,曲盡幽微;文學(xué)固然需要天馬行空的想象,卻也應(yīng)直面生活的沖擊、時代的洗禮。我希望,香港文學(xué)是有精神的寫作,而不是避世的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