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加科夫:被埋沒的俄羅斯文學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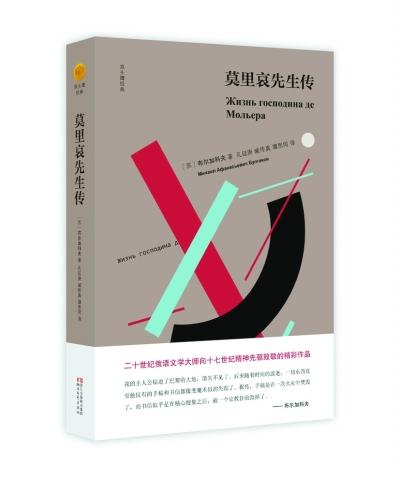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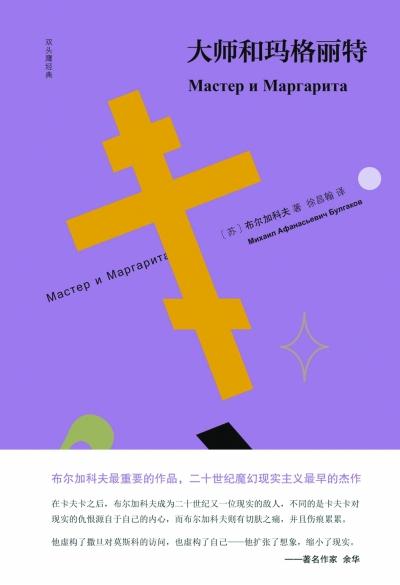
“假如像布爾加科夫和普拉東諾夫這些作家的作品,寫完后就能和讀者見面的話,我們所有人的思想就會比現(xiàn)在不知要豐富多少倍了。”
著名文學創(chuàng)作論集《金薔薇》的作者、俄羅斯作家帕烏斯托夫斯基在臨終之前曾如此說道,言語之中不乏惋惜。帕烏斯托夫斯基提到的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1891—1940),這位早逝的“白銀時代”文學大師,曾長時間被埋沒于一度無比絢爛又一度無比沉寂的俄羅斯文學史。在他生前,作品因種種原因?qū)覍业貌坏桨l(fā)表,而其花費十年之功寫成的文學名作《大師與瑪格麗特》,更是在去世整整二十六年后(1966年),才和他所摯愛的俄羅斯人民見面。
中國讀者對俄羅斯文學的印象,大多仍然會停留于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一批“黃金時代”的大師之上,但對布爾加科夫這個名字,或許也并不算太陌生——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內(nèi)在陸陸續(xù)續(xù)譯介了他的《圖爾賓一家的日子》、《狗心》等劇本和中短篇小說后,終于在1987年,最重要的代表作《大師和瑪格麗特》也有了中文版(該年先后推出了由徐昌翰、錢誠翻譯的兩個譯本,徐版譯本初名《莫斯科鬼影》)。這個魔王撒旦拜訪莫斯科的故事如此奇幻綺麗、想象奇特,那些幽默而不失從容的語詞之下,處處潛隱著象征、隱喻、荒誕,盛開著超現(xiàn)實的旖旎花朵,又處處指涉了現(xiàn)實,精妙絕倫,令人拍案。它也被當時正在努力向外尋求現(xiàn)代性表達的國內(nèi)文學潮流所捕獲,余華曾于1996年寫過一篇《布爾加科夫與〈大師和瑪格麗特〉》,評價道:“在卡夫卡之后,布爾加科夫成為二十世紀又一位現(xiàn)實的敵人,不同的是卡夫卡對現(xiàn)實的仇恨來源于自己的內(nèi)心,而布爾加科夫則有切膚之痛,并且傷痕累累。”
在作家去世26年后方才讀到其杰作的人們,如獲至寶,開始重新整理排列文學史的時間線,并發(fā)現(xiàn)它的創(chuàng)作時間比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等一眾拉美魔幻現(xiàn)實主義作品更早。于是,作家本人被后世戴上了一頂“魔幻現(xiàn)實主義鼻祖”的桂冠,以至于馬爾克斯不得不以祖母的名義發(fā)誓說,自己之前并沒有讀過《大師和瑪格麗特》。但這些遲來的榮譽,其意義更多地只能是對我們這些熱衷于標記“節(jié)點”的當代人而言的,已經(jīng)和這位郁郁而終、生前沒有機會去展露才華的作家沒有什么關系了。
而布爾加科夫最初的夢想,其實并不是當一個小說家,是當一個戲劇家。在《大師和瑪格麗特》之前,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創(chuàng)作能夠反映俄羅斯當代現(xiàn)實的劇本,帕烏斯托夫斯基曾將他的劇作和契訶夫比肩。但這條路出乎意料地艱辛而坎坷——他的十余部戲劇作品,絕大多數(shù)都不能上演。直到去世后,他的許多劇作才再次被翻出來,往往甫一上演便獲得轟動效應,成為不少劇院多年來的保留劇目,他本人也被視為俄羅斯最重要的劇作家之一。夢想成為一名戲劇家卻在現(xiàn)實中不得志,最后以一部堪稱天鵝之歌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長篇小說獲得了最高的聲望,這自然歸于布爾加科夫的天才所在,但細細品味,似乎又不能不暗示了一種略感悲涼的反諷人生,令人嘆息。
在中國,人們更熟悉的也是《大師和瑪格麗特》的盛名,對布爾加科夫的戲劇無疑是比較陌生的,僅僅在本世紀初由廈門大學出版社出過一個選譯本,內(nèi)含三種劇作。時隔多年后,今年春天,浙江文藝出版社的“雙頭鷹經(jīng)典”書系出版了《逃亡:布爾加科夫劇作集》,共收入七部劇作(其中四部為新譯),并再版其兩部長篇小說代表作《大師和瑪格麗特》和《莫里哀先生傳》,讓人們得以再次與這位被埋沒的大師相遇。此外,該書系還推出了勃留索夫、索洛古勃、安德列·別雷、布寧、安德烈耶夫、普拉東諾夫等20世紀俄羅斯作家的代表作品。
這些年,在與歐美文學閱讀的對比觀照下,往往有人驚覺,曾經(jīng)影響了幾代人的俄語文學正在變得遙遠而陌生。但正如這個民族的性格,屬于它的文學也內(nèi)蘊著一種無法替代的憂郁和沉思氣質(zhì)。布爾加科夫,和他前代的、同代的那些作家們,始終接續(xù)著關心人類和大地的精神傳統(tǒng),將永遠如同恒星一般,在北國凜冽而莊嚴的天空里,巋然不動。
一生
舊俄歷1891年5月3日,布爾加科夫出生于烏克蘭基輔的一個家庭,全名米哈伊爾·阿法納西耶維奇·布爾加科夫。他的父親是基輔神學院的一位教授,宗教背景對他日后的創(chuàng)作有一定影響。
布爾加科夫18歲時,考入了基輔大學醫(yī)學院,于畢業(yè)后成為一名醫(yī)生,并和第一任妻子塔吉亞娜結婚。此時,正逢俄國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他應征入伍,進入前線醫(yī)院工作。一戰(zhàn)結束后,他和妻子回到基輔,當了一段時間的性病醫(yī)生,并開始在業(yè)余時間寫一些小說。
和大多俄羅斯作家一樣,日后由醫(yī)生成為作家的布爾加科夫,其一生的經(jīng)歷和寫作也和大時代緊緊捆綁在一起,在時運的浮沉中變換著自己的位置——盡管多數(shù)時候,只是被裹挾著流轉(zhuǎn),或是進行微不足道的抗爭。十月革命爆發(fā)后,烏克蘭的旗幟處于不斷更迭之中,德國人在烏成立的傀儡政權蓋特曼、打著烏克蘭民族主義旗幟的彼得留拉匪幫、鄧尼金率領的白衛(wèi)軍(以支持沙皇的保皇派為基礎,和蘇聯(lián)紅軍對立的軍隊),輪番到來又輪番潰逃。命運弄人,彼時的布爾加科夫,竟被這三個政權都抓去當過軍醫(yī)。這一段起伏多舛的早期行醫(yī)經(jīng)歷,成為他的短篇集《鄉(xiāng)村醫(yī)生手記》的直接來源,但更重要的是,讓他得以更加深刻地去認識和思考他所身處和見證的時代政治,動蕩時期的何去何從、心靈拷問,成為后來他許多作品探討的主題。
1919年秋,為了尋找參加白軍、失去聯(lián)絡的弟弟,他前往被白軍占領的高加索地區(qū)。在這里,他漸漸棄醫(yī)從文,參加了《高加索》報的編輯工作。不久,白軍逃離,布爾什維克到來,蘇維埃政權接管了報紙,布爾加科夫被任命為文學版編輯,開始從事戲劇創(chuàng)作。
1921年,他來到莫斯科,希望能在首都實現(xiàn)文學夢想,但和所有懷著夢想的年輕漂泊者一樣,在這個最為挑剔的城市里,經(jīng)歷了一段慘淡艱辛的時光。為了生存,他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寫過各種各樣的東西。好在,努力最終得到了回報,他的作品開始不斷地在阿·托爾斯泰主編的《前夜報》文學副刊上刊出,漸漸引起了莫斯科文學界的注意。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加入了人才濟濟的《汽笛報》編輯部,工作和生活漸趨穩(wěn)定,文學事業(yè)也蒸蒸日上,《白衛(wèi)軍》、《不祥的蛋》等重要小說接連發(fā)表,并著手將這些小說改編為戲劇。著名導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非常看好他的戲。
這個醫(yī)生出身的年輕作者很快顯露出了他在戲劇方面的驚人才華,《土爾賓一家》(由小說《白衛(wèi)軍》改編)、《卓伊卡的住宅》、《逃亡》等的上演均大獲成功,場場爆滿。尤其是《土爾賓一家》,斯大林本人也非常喜愛,親自去看過很多場。隨著舞臺大幕在觀眾期待的目光中一次又一次拉開、演員在掌聲中一次又一次謝幕,布爾加科夫這個名字變得家喻戶曉。
然而,正當這顆新星冉冉升起時,接踵而至的卻是命運的再一次捉弄。《白衛(wèi)軍》、《逃亡》等革命英雄題材劇在社會上獲得好評的同時,因為其中白軍形象的塑造問題,也招致了一些爭議和批評。另外,他的另一篇充滿想象力的重要作品《狗心》也未能通過,被拒絕發(fā)表。當時正逢蘇聯(lián)文壇“崗位派”極左風潮泛濫,媒體上開始對布爾加科夫充滿了批評的聲音,他的劇被一個接一個撤下舞臺,有的已經(jīng)排好了也被叫停,作品也不再有刊物和出版社發(fā)表。對于一個才剛剛嶄露頭角、興奮尋求文學位置的年輕作者來說,這種變故和打擊無疑是毀滅性的。
布爾加科夫嘗試給斯大林寫信,斯大林還是比較珍惜他的才華,親自給他打電話,并安排他去莫斯科藝術劇院,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領導下工作。他轉(zhuǎn)向了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出了《莫里哀》、《死魂靈》、《普希金》等劇本,但經(jīng)歷了種種波折后,他的戲劇生命已注定不能長久。斯大林誕辰時,布爾加科夫以斯大林青年時期革命活動為題材寫了一個劇本《巴統(tǒng)》,作為藝術劇院的獻禮。為了既能符合時代的要求,又能保持藝術的真誠,他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去做,但不幸的是,斯大林本人卻不喜歡這個劇本,排演工作也沒有進行下去。
《巴統(tǒng)》是他一生的最后一個劇本。出了問題后,布爾加科夫一病不起,終于在1940年3月10日于莫斯科逝世,年僅49歲。他被葬于契訶夫墓近旁,或許,這兩位同樣早逝的、同樣兼擅小說與戲劇的、分別屬于俄羅斯文學兩座高峰——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的大師,能夠越過俄羅斯民族最跌宕的一百年歷史,在地下相互致意。
真誠
布爾加科夫去世五天后,蘇聯(lián)著名作家、《青年近衛(wèi)軍》作者法捷耶夫在致他的第三任夫人葉蓮娜的信中寫道: “我立刻就意識到我面對的是一個驚人的天才,一個心地誠摯、稟性耿直的人,一個聰明出眾的人。即使在他陷入沉疴的日子里,跟他談話也依然趣味不減。這種情況在其他人身上是少見的。無論政治家還是文學家,都了解他是一個從不在創(chuàng)作和生活中用政治謊言玷污心靈的人。他走的是一條真誠的路,是始終如一的。”
這段評論,為后世描摹出一個立體的形象來:清癯,聰慧,機敏,幽默,而最重要的——真誠。
“他走的是一條真誠的路。”法捷耶夫如是說。多年后,劇作集《逃亡》的中文譯者周湘魯補充道:“怎樣在面對 時代的要求 時保持真誠,布爾加科夫思考了很多。”
《土爾賓一家》、《逃亡》這兩個反映革命的英雄劇,是布爾加科夫生前為數(shù)寥寥的有幸獲得舞臺表演的戲劇作品。它們均從白軍的視角切入,披拂著一層戰(zhàn)爭浪漫主義,也顯出了布爾加科夫自身對待時代和藝術的真誠所在。《土爾賓一家》改編自他自己的長篇小說《白衛(wèi)軍》,劇中的主要人物是一群沙皇軍隊的軍官,與其說他們是面目可憎的對抗者,更不如說是一群被舊時代遺留下來,卻不知道跟從誰、去哪里的彷徨者。曾經(jīng)的統(tǒng)治者們逃走了,他們卻無路可逃,死在了自己深愛的祖國土地上,或是無所適從地迎接未知的新生活。而在同時期其他作品中,白軍的形象往往是標簽化的,但布爾加科夫是特殊的、獨異的,他賦予了他們正直、誠實、愛國的優(yōu)秀品質(zhì),并探入了這一為時代洪流所裹挾的特殊群體的復雜心靈史。這應當也和他早年在外省的親身經(jīng)歷和見聞有關。
《逃亡》則以八場現(xiàn)實和幻覺相交織的夢,進一步展現(xiàn)了這群“舊時代的人”的流亡史。“我們打輸了戰(zhàn)爭,被趕出來了”,但邁出俄國的國境,等待他們的不是自由,而是生計的艱難和尊嚴的盡失。有的人踏上了回到故國的長途,有的人在異國他鄉(xiāng)飲下一顆子彈,和《土爾賓一家》一樣,透過一個個在宏大歷史中無法決定自身命運的微小個體,以及他們那帶有北國特色的悲劇性結局,布爾加科夫表達了某種超越出特定時代和特定社會的、更為廣闊和深切的對于人類的同情。
于是也因此,即便布爾加科夫是在20世紀20年代執(zhí)筆寫作的,即便他冀圖反映的是俄蘇那一段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史與心靈史,但當時隔將近一個世紀后,再次進入他的敘述時,也并不會因一道名為“環(huán)境”、“時代”或“意識形態(tài)”的屏障而被阻隔其外。真實的人性,真誠的思考,在任何時代都貫穿如一。
而這或許,又能夠稍許安慰到布爾加科夫:畢竟,他在生前一直一直寫,卻沒來得及和那些與他同時代的、身處他所反映的那個時代之中的人進行最直接的對話。
大師
譯者周湘魯在后記中提到一則軼事。他在彼得堡大學訪學時,那里有一位文學教師曾半開玩笑地說過:“布爾加科夫是俄羅斯文學老師最愛的作家。考試的時候抽到了答不出來的難題,聰明的學生會將考題撇在一邊,跟老師聊聊《大師和瑪格麗特》,一般情況下,老師都會給及格的。”
想來實在有趣,在世界文學版圖上標志出俄語文學之不可撼動巍然存在的,大概更多會是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這樣的經(jīng)典大師,或者蒲寧、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這樣的諾獎獲得者等,生活在蘇聯(lián)時期的布爾加科夫如何能夠突出“重圍”,成為“最愛”?當然,所謂“最愛”自然不是絕對的說法,但若當讀過《大師和瑪格麗特》后,的確很難不被其中驚人的想象力和有條不紊的敘事所折服,仿佛變成了被沾染了魔法、跟在瑪格麗特身后飛行的女仆,一路向下俯視奇幻的國度,發(fā)出驚呼。
《大師和瑪格麗特》的閱讀感覺,實在太不像典型的俄羅斯文學。典型的俄羅斯文學,往往是凜冽的、厚重的、嚴肅的、帶有形而上的思索性質(zhì)的,這或許和北方的環(huán)境與性格有關。但《大師和瑪格麗特》,卻是溫情的、輕盈的、諧謔的、帶有濃郁喜劇風格的。這個魔王撒旦拜訪莫斯科的奇幻故事,上至判處耶穌死刑的耶路撒冷總督本丟·彼拉多,下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莫斯科文學圈,在現(xiàn)實和虛構的世界里自由滑行,其間時不時冒出的種種妙想,令人嘖嘖稱奇亦捧腹不已。比如在魔王及其助手的惡作劇下,業(yè)余合唱團走火入魔,所有人說著說著話就開始唱歌,完全控制不住;又比如讓一個人的身體消失,只留他的西裝保持原來的姿勢辦公等等。這些旁枝末節(jié)的情節(jié)如此生動,仿佛寫下這些段落的布爾加科夫,臉上正浮露出一絲狡黠的表情。
但熱鬧而圓滿的故事背后,現(xiàn)實卻是,《大師和瑪格麗特》斷斷續(xù)續(xù)寫了十多年(1928年開始寫時初名《鬼怪的故事》),后來作家重病在身,不得不進行口授,而妻子葉蓮娜就坐在床邊,忠實記錄下他的每一句話。直到去世,布爾加科夫也沒能完成一份清稿。又是26年后,才得以出版問世。
彼時處于貧病交加中的作家,在他人生最后的年歲里,竟然寫了這樣一個從形式到內(nèi)容都擺脫桎梏的狂歡故事,這本身就有些不可思議。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或許這種狂歡式的酒神精神,正成為了一種救贖,一種照亮。布爾加科夫在其形式和結構的游離之下,是對俄羅斯文學精神傳統(tǒng)的繼承。剝離出那些輕輕浮于文本之上的細枝末節(jié),他最終想表達的,如最后撕去小丑假面的騎士們的夜空飛行一般,是一些優(yōu)雅而貴重的東西。魔王毀掉虛偽的城市和卑鄙的權貴們,惟一拯救的是大師和瑪格麗特這兩個平凡的人,和他們之間絕對偉大的愛情。而大師在文學圈的不幸遭遇中,不難見到作者自身的影子。
自面世以來,《大師和瑪格麗特》的主題一直被眾說紛紜。但無疑,它已經(jīng)成為了俄羅斯和世界文學史最寶貴的財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