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忠明:理性與信仰之間的裂隙,正是希望進入之處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生于立陶宛,二戰(zhàn)時參加了華沙的抵抗納粹的運動,戰(zhàn)后作為波蘭文化專員在紐約、華盛頓和巴黎工作。1951年出走巴黎,1960年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198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米沃什的詩歌和隨筆注重內容和感受,廣闊而深邃地映射了二十世紀東歐、西歐和美國的動蕩歷史和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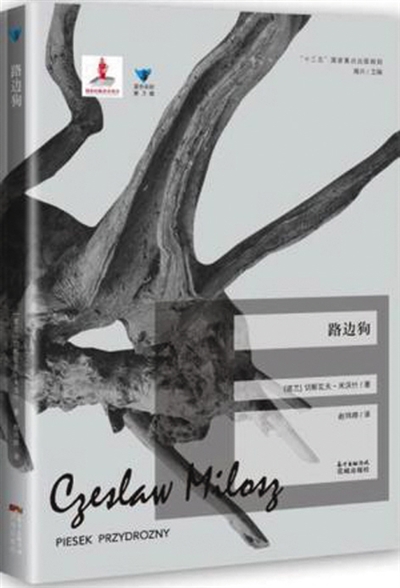
《路邊狗》 作者:切斯瓦夫·米沃什 譯者:趙瑋婷 版本:花城出版社 2017年1月
“我擔心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這本書。”波蘭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1998年接受媒體采訪時如是說,那時他剛憑借《路邊狗》獲得波蘭最有聲望的文學獎項“尼刻獎”。這位見證了二十世紀的瘋狂和荒謬的詩人,用詩歌在深淵呼喊。對詩人來說,寫詩成為一種無名的需要,為秩序、為節(jié)奏、為形式,借以對抗混亂與虛無。
《禮物》
如此幸福的一天。
霧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園里干活。
蜂鳥停在忍冬花上。
這世上沒有一樣東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羨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記。
想到故我今我同為一人并不使我難為情。
在我身上沒有痛苦。
直起腰來,我望見藍色的大海和帆影。
伯克利,1971年
(西川譯)
《創(chuàng)造日》
其實根本沒那么難。
上帝創(chuàng)造世界。誰說是在很久以前?
不久。就在今晨。也許是一小時前。
因為那快要枯萎的花,重新綻開了笑顏。
或一節(jié)仿俳句詩:
我的頓悟建成的大教堂,秋日的風,
我在感恩中慢慢老去。
即使在牙醫(yī)診所的窗外也看見:
美輪美奐的。一棟房子。高的。被白氣環(huán)繞。佇立在天上。
詩人的“復調”獨白
來自世紀老人的呼喊
凡知波蘭詩人米沃什的人,大概莫不知曉《禮物》這首小詩。寫作此詩時詩人已至耳順之年,從故國波蘭出走流亡異國二十載,終能忘卻曾經(jīng)的痛苦與邪惡,抵達澄明達觀之境界。
打開《路邊狗》這本書,我們發(fā)現(xiàn)詩人的晚年遠非超脫通透那樣簡單。這本書出版于1997年,此時米沃什已八十六歲高齡,正如書中一節(jié)“楷模”所說,他在耄耋之年對精神事務的追尋依舊熱情不減,于是寫下這些自由隨性的片段式隨筆,類似帕斯卡爾的《思想錄》,主題多樣,文短旨遠,有詩歌、有隨筆、有筆記,或反思自身、或回憶故人往事、或品評人生世相、或談論詩歌與宗教。
書名《路邊狗》,源自本書第一章篇名。作者回想自己年少時,那正是二十世紀初,乘坐運牛糧的馬車在家鄉(xiāng)土地上游蕩,行至村莊或庭院,總會有一條盡忠職守的狗沖著他吠叫。如今已是世紀末,百年轉瞬即逝,而那些狗始終陪伴著奔波勞碌的人們。“路邊狗”,作者以這個可笑而溫情的名字作為書名,或許是米沃什這位世紀老人以“路邊狗”自況,以自己的文字向人呼喊,以喚醒人們的記憶,縱然馬車與故鄉(xiāng)已消失無蹤。
雖是詩人的獨白,我們卻能從中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有些甚至互相矛盾。米沃什把自己比作一件“發(fā)出各種聲音的樂器”,其話語擁有不同聲音,而每種聲音又都是獨立平等的。我們知道,米沃什流亡美國后,在大學講授陀思妥耶夫斯基,關于陀氏的“復調”理論必定深刻影響了他。“復調”必然帶來矛盾與懷疑,詩人即在這種懷疑與矛盾中,帶著微弱的希望,步履蹣跚地尋求。
這本書的引言,詩人引用了俄國思想家舍斯托夫改寫笛卡爾的話:“我思故我在:這是確實的,因為這是不可能的。”舍斯托夫以反對必然性的哲學著稱,以信仰反對理性,抵制純粹理性對人的主體性的侵蝕,然而其批判方式卻是非常理性的,米沃什對其非常推崇。在此書談論宗教與信仰的章節(jié)中,常可見到舍斯托夫的影響。
從小接受天主教式教育,米沃什對于宗教信仰有種本能的認同,感恩“自己很久以前在橡樹林中的木頭小教堂里接受了天主教洗禮。”他贊頌創(chuàng)造之美,甘愿一次又一次陷入對美的驚嘆與欲望之中。
被懷疑包圍的信仰
萬物的“暫時與虛假”
然而,他又時常被懷疑所包圍,到了沿著“肉身之路”離開的暮年,他更感到萬物之“暫時與虛假”,世人只是戲臺上的提線木偶,表演驕傲、懺悔和愚蠢。
而對于宗教信仰,他由衷地驚嘆,認為“人類所有的榮耀和尊嚴都凝聚在了宗教信仰中,人類這一可悲并終有一死的生物,竟能創(chuàng)造出善與惡、高與低、天堂與地獄”。但他對儀式性的宗教敬拜遲疑不決,如“丈夫與妻子”一節(jié):妻子從不去教堂,認為“如果上帝存在的話,那他不應需要那些頌歌、咒語和咕咕噥噥的禱告”;而丈夫卻加入禱告人群,對他來說,人如果完全把自己交給純粹理性,就太悲慘了。
在“海倫卡的信仰”一節(jié)中,海倫卡雖然內心有著可怕的懷疑主義,卻認為“這世上有太多的丑惡,所以在某個地方一定有真和善,這就意味著上帝一定存在于某處。”在他晚年的一篇長詩中,他也坦承“我是一個懷疑主義者,但我跟他們一起唱,于是克服了存在于我的私人宗教與儀式宗教之間的矛盾。”理性上排斥,情感上愿意相信,這樣一種心腦矛盾使得詩人保持一定距離,始終審慎地站在信仰的門檻上,有時信有時不信,總是向前走一步,然后向后退一步,但他仍滿懷期待,“希望自己能成為主的葡萄園里的工人”,得到神恩的光照。
對信仰的這種猶疑態(tài)度,也源于基督信仰在近代受到巨大沖擊。自尼采以降的虛無主義者宣稱“上帝已死,真正的世界并不存在”,進化論等實證科學的出現(xiàn)使不可否認的真理不再無人質疑,而由天意推動的歷史被當作一些盲目的力量之間角逐的戰(zhàn)場,神學家們兩千年來搭建的理論大廈轟然倒塌。
米沃什批判虛無主義是“真正麻醉人民的鴉片。”在“達爾文太太”一節(jié)中批判達爾文主義抹殺了人的尊嚴,將世界變成物種之間的殘酷角斗場,而二十世紀的血腥歷史,似乎更能證明這個世界受某種無情的物理定律統(tǒng)治,如果上帝創(chuàng)造了這樣一個世界,并把它交給了無情的必然性法則,那上帝一定是兇惡的怪物,不值得信仰。
詩歌“作為一種禱告”
給“希望”留一席之地
面對塵世的無情法則,詩人感到仿佛被黑暗追趕著,只能在懷疑與不安中尋求,或選擇如舍斯托夫一樣反對“二二得四”的必然性法則,帶著“以頭撞墻”的勇氣,因其荒謬而信仰,這種反抗彰顯個體的自由與尊嚴;或如詩人極推崇的思想家西蒙娜·薇依一樣,相信世間受機械法則統(tǒng)治,上帝“退場”了,人只能拋卻一切虛假的安慰,在塵世的重負中專注地期待神恩的降臨。
傳統(tǒng)的信仰已然式微,神學語言再不能表達出二十世紀人們的經(jīng)驗,而詩歌“作為一種禱告”,仿佛其中存在著一種非世俗的東西,作為思考終極問題的人們表達自我意識的工具。或許人們可以從薇依的話中找到寫詩的理由:“絕對純粹的專注即是禱告。”
然而作者對于寫詩并非沒有懷疑,他時而感到“詩是一種令人羞恥的東西,寫詩就如同被扒光衣服在公眾面前展示身體缺陷”。他說詩人不正常,不陽剛,因為有黑暗的糾結與恐懼,才有了創(chuàng)作的沖動,用作品來抵償自己的軟弱。
“我們行走在地獄屋頂,凝視著繁花。”這是米沃什最喜歡的日本詩人小林一茶的詩句。“相信自己很出色,然后漸漸發(fā)現(xiàn),你并不出色。為一個人的人生努力就夠了。”縱使懷疑甚至虛無主義不時縈繞,內心的焦灼不安難以克服,米沃什依然堅守著人的價值,始終給超然存在留有一席之地。或許理性與信仰之間的裂隙,正是希望進入之處。而詩歌作為一種可能的希望,使他擺脫虛無之時,也給他創(chuàng)造了一方與他人聯(lián)結的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