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傅雷出發(fā)來到陳丹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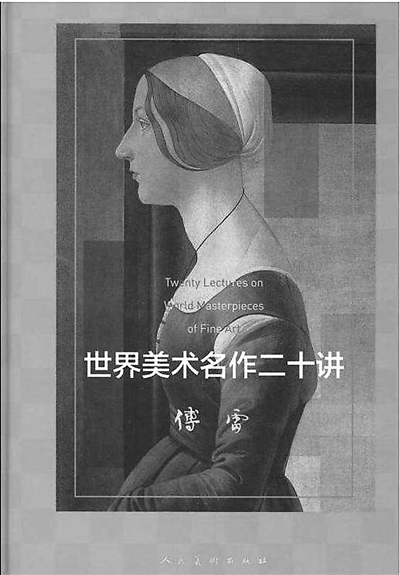

傅雷先生的美術(shù)講稿談的都是鼎鼎大名,生怕與西方美術(shù)史的權(quán)威錯位,而陳丹青的美術(shù)史生怕與任何美術(shù)史對位。遠(yuǎn)看像是美術(shù)名著欣賞教育課,近看卻是美術(shù)史的邊角料翻身課。被美術(shù)史近乎開除了的名單掉了個個兒,成了錄取通知書。
晚清的傾頹落后,使西學(xué)東漸遠(yuǎn)邁前古,民國以來,翻譯與介紹外來文藝不絕如縷,譯介興旺、學(xué)術(shù)昌盛。這段歷史的因果對現(xiàn)在的你我有如太平洋對岸的蝴蝶翅膀亭亭扇動,單就繪畫而言,我特選了時間相隔近百年的中國美術(shù)界的兩枚貝殼,來看看美術(shù)如何發(fā)生在中國。
第一枚來自傅雷。緣起是年初,得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出版的傅雷《世界美術(shù)名作二十講》一書,讀罷甚喜,推薦給眾友。
回看傅雷,知學(xué)海無涯而常惴惴默默、孜孜矻矻,一個意氣風(fēng)發(fā)的民國少年出去,一座貫通中西的文明大橋回來。他帶回來的歐洲文明一度使他留學(xué)的巴黎成了中國人心目中藝術(shù)與浪漫的代名詞,國人想認(rèn)識歐洲,就可以先去訪訪傅雷的文字。這二十課講稿中提到的藝術(shù)家不多,以點帶面,綱舉目張:喬托、多納泰羅、波提切利、達(dá)·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貝爾尼尼、倫勃朗、普桑及幾位英法畫家等,挑講了美術(shù)史上的重鎮(zhèn)關(guān)卡。以一種力求扼要“啟蒙”的邏輯,以及興中華之現(xiàn)代美術(shù)的愿景,所述皆名家杰構(gòu),從學(xué)問、人品、操守修養(yǎng)、所涉時代環(huán)境,談史論理,以示聽眾藝術(shù)之因果,種下一片興旺的愿種。美術(shù),作為人類審美之延伸,并非剛需,可人不是走獸,一群美盲創(chuàng)造的世界會何等自掣自肘呢?傅雷先生留給我們的這二十課,不僅僅是指出了歐洲那一堆作品與知識,更是把人類關(guān)于美最高的境界從此延伸到中華民眾的唾手可得之處,為你興魂動魄,幫助諸位成為更完整的人。
時隔近九十年,第二枚貝殼來自畫家陳丹青。
讀完傅雷的書之后,我的第一個聯(lián)想念及陳丹青“局部”系列視頻的出版:《陌生的經(jīng)驗——陳丹青藝術(shù)講稿》,成書時陳丹青年62歲(傅雷的藝術(shù)講稿成于26歲),前后共十六課,每課千字,與傅雷“經(jīng)典美術(shù)史”的立足完全不同的是,陳丹青“身在曹營心在漢”,統(tǒng)統(tǒng)借題發(fā)揮,弦外有音,入于過去談出現(xiàn)在,常常使人得魚忘筌。古、今、中、西,信手拈來,仿佛歷史被抽走了時間與空間的序列,成了隨時待命奉調(diào)的兵將。
書名起“陌生的經(jīng)驗”,是一樁一石多鳥的“陌生”,逼人銘記的“陌生”:
就陳丹青先生自己而言,作為寫作的《陌生的經(jīng)驗》是獨特的,因為是作《局部》系列視頻所備的講稿,我們聽一集二十分鐘的課,先生大概要花費半個月甚至更多時間準(zhǔn)備,在歷史的縫隙中抽絲插針,直到定稿交付了,再錄制數(shù)個鐘頭。拍攝罷,先生最大心得竟然是對演員職業(yè)心生崇高的敬意,從畫家到“演員”,此為陌生的經(jīng)驗之一。但就內(nèi)容,雖然先生熟識中西古今的美術(shù),但老來仍有“艷遇”,他把布法馬可的《死亡的勝利》介紹給我們的時候曾說:“去年我闖進(jìn)墓園,意外看見一幅從未見過的巨大壁畫,當(dāng)場魂靈出竅。文藝復(fù)興的大部分名作,我自以為知道,怎么這等偉大的畫,從來不知道呢?這就是無知的好處……你完全不知道一位畫家,忽然撞見了,更是大快樂。那種驚訝、歡喜,等于變回小孩子……藝術(shù)頂頂要緊的,不是知識,不是熟練,而是直覺,是本能,是騷動,是嶄新的感受力,直白地說,其實,是可貴的無知。”從先生對“無知”的有知,對“陌生”的熟悉里,仿佛倒立著一座金字塔,塔尖立在《死亡的勝利》上,而所有的上層卻一絲不茍地建筑與歌頌“陌生與無知”,照顧美術(shù)史勢利眼下的炮灰。即便是那些美術(shù)史上鼎鼎有名的作品,先生卻就其引我們朝向陌生的角度,他借他自己的陌生,談了他的熟悉,借了我們的熟悉,談出我們的陌生。此為陌生的經(jīng)驗之二。
就讀者而言,尤其是文藝青年而言,是一種巨大的陌生,更像是一種稀缺的驚喜。雖然我們頂著一個嘈雜的市場,但是從立意構(gòu)思到表達(dá)技巧,作為畫家與作家的陳丹青談藝術(shù),遠(yuǎn)遠(yuǎn)超越BBC在內(nèi)的許多文藝節(jié)目,當(dāng)然他會說這是導(dǎo)演謝夢茜的功勞。誠然,許多讀者“不知盤中餐”,又何妨這樣陌生的經(jīng)驗出現(xiàn)在歷史的街口,且它必將成為中華美術(shù)歷史中繞不過去的山頭。史航在序中記到:“生于今世,麻木最易,敏感最難。海量信息沖刷一切,世界前所未有的透明,守著搜索引擎。給我十秒鐘,什么都查得到。然而查到也就是查到了,哪有什么驚喜可言,銘記更是奢談。下次再用再查,永遠(yuǎn)可依探囊取物,也永遠(yuǎn)兩手空空……再度藝術(shù)史,再看到這些藝術(shù)家被標(biāo)簽化,我們?nèi)灾荒苄涫峙杂^嗎?”換做古人一日三省必加問:今天,我“陌生”了嗎?以上作陌生的經(jīng)驗第三。
就美術(shù)史本身而言,不論是談法或是取材,恐怕更是陌生得肝兒顫。傅雷先生的美術(shù)講稿談的都是鼎鼎大名,生怕與西方美術(shù)史的權(quán)威錯位,而陳丹青的美術(shù)史生怕與任何美術(shù)史對位。遠(yuǎn)看像是美術(shù)名著欣賞教育課,近看卻是美術(shù)史的邊角料翻身課。被美術(shù)史近乎開除了的名單掉了個個兒,成了錄取通知書。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布法馬可的《死亡的勝利》、蔣兆和的《流民圖》、巴齊耶、瓦拉東母子、民國女畫家關(guān)紫蘭、丘堤,徐揚、卡帕奇奧、蘇里科夫、安吉利科……好一副耶穌的心腸:天堂里住著的非但不是在世顯赫的財主,卻是受苦的乞丐拉撒路;世人看來,好人才能上天堂,然而天堂最后的居民卻是一幫祈求憐恤和寬恕的罪人。美術(shù)史的圖景儼然成了反轉(zhuǎn)片,甚至鼎鼎大名的梵高先生,從千百幅大名鼎鼎的作品里,陳先生精心為其挑選了一張名不見經(jīng)傳的油畫草稿,封了個“憨王”,談了令小心維護(hù)美術(shù)史威權(quán)的觀眾們“不敢聽”的“未完成”,直至編織了美術(shù)與商賈的社會關(guān)系流變之網(wǎng)。這樣貌似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論點,直到今天還會有很多人表示看不懂,不了解。善哉,這就是陳丹青羨慕的狀態(tài),想要的效果。這是第四個陌生。
當(dāng)然,還不止這些陌生。所有的宗旨都沒有變,一切的陌生都是為了恢復(fù)觀眾讀者的應(yīng)該的熟悉——對藝術(shù)的“直覺”。如果你是職業(yè)畫家,他告訴你,不要害怕權(quán)威:一切對新意的屠殺,不正是“正確”和“現(xiàn)成”的功勞嗎?如果你是路人看客,他提醒你,不要迷信權(quán)威,雖然你不能指鹿為馬,但至少你可以在誠實中積累進(jìn)步。對權(quán)威的愛與怕,是需要保持平衡的,面對大師,你不能只是磕頭,但也不意味著飛揚跋扈。當(dāng)然,大多時候我們需要導(dǎo)游,尤其是美術(shù)這樣的深水迷宮,許多人會轉(zhuǎn)得一頭霧水,所有問號匯成一句話:怎么辦?面對不確定的信息,需要有確定的信息來安慰不安。陳先生在《陌生的經(jīng)驗》后記的結(jié)尾引用蒙田的話:
“人類的所有不安,就是回到家里也靜不下來。”
又說,他所提到的那些藝術(shù)家們,真正賦予了他講稿的價值,“他們的偉大,他們的好,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他的講述。”
前半句看起來點了觀眾,其實說出了藝術(shù)家;后半句提了藝術(shù)家,其實給觀眾塞了錦囊。
將傅雷的《世界美術(shù)名作二十講》和陳丹青《陌生的經(jīng)驗》兩枚藝術(shù)海岸上的貝殼放在一起,不是為圖藝海拾貝湊出兩位來增加什么效應(yīng),為當(dāng)下的蕭條的美術(shù)博些眷顧或同情;也不僅因為他們都出于上海,這個中國通向西方的門戶,從地緣的角度看百年來文藝傳播深入的程度;不僅要比較、突出傅雷的恪守學(xué)術(shù)與陳丹青的超越學(xué)術(shù),也不僅是提醒愛好美術(shù)的人去深挖這兩座寶庫;也不是逼著大家成為傅雷或者陳丹青,去歸正美術(shù)史的綱紀(jì)或是成為尋找千里馬的伯樂。我相信有心的人,總會鐵杵成針、水到渠成。
總之,借引剛才的兩句話,還是要給大家吃一顆定心丸的:
“偉大的藝術(shù)家可以安靜下來,優(yōu)秀的觀眾可以常常驚覺藝術(shù)家的偉大。”這就是美術(shù)存活在歷史中的綱領(lǐng)。


